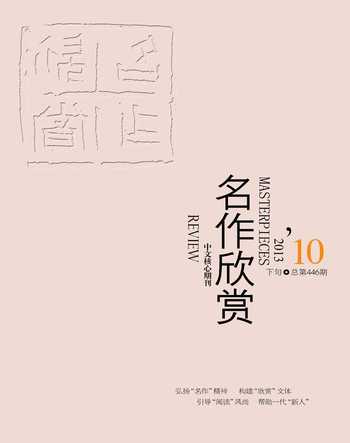加缪生存哲学视域下的《最蓝的眼睛》
摘 要: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通过讲述一个普通黑人小女孩的悲剧故事,真实地展现了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加缪的生存哲学为视角,从荒诞和反抗两方面对《最蓝的眼睛》进行解读,旨在揭示面对荒诞,唯有肯定生命,合理反抗才能获得幸福。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生存 荒诞 反抗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其作品深切关注着美国社会中黑人的生存状况。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以一个渴望得到一双蓝眼睛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惨故事为中心线索,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在白人主流文化浸染下的生存境遇。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的作品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以文学的形式阐释哲学上的思考。加缪的创作可分为两大主题:荒诞和反抗,它们有机地组合成了加缪自成一体的荒诞生存哲学。
本文以加缪的生存哲学为视角对小说《最蓝的眼睛》进行解读,分析了美国黑人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合理的反抗是远离困扰、获取幸福的唯一途径。
一、荒诞的世界
加缪在其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对荒诞做了理论上的阐释:“荒诞产生于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这里,荒诞的概念强调了一种“断裂”: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断裂,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求与自然社会生存有限性之间的断裂。小说《最蓝的眼睛》就展示了一个充满了断裂的荒诞的世界。首先,黑人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群体之中,从而获得幸福,这是他们的理性愿望。然而,在美国社会黑白两元权力结构关系中,黑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遭遇种种歧视,生活困苦,这是非理性的现实。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加缪哲学中的荒诞的世界。具体而言,这种荒诞体现在两个方面:物质世界的冥顽与格格不入;人类社会的无人性与不合理。
小说以194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为背景,描述了一个贫穷困苦的黑人社区。故事的叙述者,九岁的黑人小女孩克劳迪娅每天都要跟大人们一起到铁路沿线拣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她家的房子又旧又冷,“到了晚上只有大屋里点了盏煤油灯,其他屋子则充满了黑暗,蟑螂和老鼠”。故事的主人公,十一岁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家更是一贫如洗,一家人住在废弃的库房里,简陋,阴暗,破败不堪,家徒四壁。她们所属的整个黑人社区肮脏凌乱,死气沉沉,充满了酒精和暴力。与此相反,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做工的白人居住区既整洁又漂亮,有蔚蓝的湖水,漂亮的公园,被鲜花包围的白房子。然而“黑人是不许进公园的,因此更让我们梦寐以求”。这种对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与物质极端匮乏的现实之间的断裂体现了黑人生存世界的荒诞。
此外,小说还描绘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类社会,在那里,人与他人、自我也是分裂的。书中着力刻画了黑人女孩佩科拉由于相貌丑陋而受到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精神压迫。她首先遭遇了以杂货店老板为代表的白人的无视。当佩科拉去杂货店买糖果时,五十多岁的白人老板的目光中却是一片带有厌恶之感的空白,没有一丝对人类的认同,“他并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同时,佩科拉还遭受了以杰萝丹为代表的有色人的蔑视。有着浅棕色皮肤的美丽妇女杰萝丹格外注重自己的外表与衣着,高度警惕地跟黑人划清界限,当她看到被儿子裘尼尔领回家的佩科拉时,感觉像是一只苍蝇落到了她家,并不由分说地把这个“讨厌的小黑丫头”轰走了。不仅如此,佩科拉还遭受到了自己的同胞——黑人男孩子们的仇视。在学校里,一群男孩围着佩科拉,骂她是“小黑鬼”,尽管他们自己也是黑皮肤。黑人男孩对佩科拉的刻薄辱骂实际上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我背叛和自我憎恨。通过佩科拉的遭遇,小说展现了一个在白人价值观冲击下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相互伤害的荒诞的世界。
二、反抗的人
如果说荒诞的发现是加缪哲学思考的起点,那么他重点探讨的是:面对荒诞,人该何为?在否定了肉体的自杀,又拒绝了哲学上的自杀之后,加缪认为唯一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反抗荒诞”。不过,反抗的方式各有不同。总括起来,加缪在其作品中阐明了三种反抗方式,即小说《局外人》中默尔索的消极反抗;戏剧《卡利古拉》中其同名主人公的暴力反抗;以及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西西弗式的有节制的合理反抗。这三种反抗方式分别在莫里森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三位人物身上得以体现。
小说主人公佩科拉,面对生存世界的荒诞,始终以忍让和退缩的姿态消极反抗。面对白人小店老板的“无视”,她感到片刻的恼怒,“愤恨之中有生存的感觉,真实与存在的感觉,有价值的感觉”,然而,这种“美好的感受”未能持续,一会儿又被熟悉的羞耻感所代替。面对混血女孩儿莫丽恩的嘲弄,“佩科拉缩起脖子——既滑稽,又可怜,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面对父母之间的争吵和打骂,她不会像哥哥山姆一样或是离家出走或是加入战斗,而只能躲在被子里,默默祈祷着让自己消失。在荒诞世界的压迫面前,佩科拉像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一样漠然置之,无动于衷。她唯一的“抗争”便是渴望得到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因为那样的话,她看到的世界也许就会不同了。她日夜乞求,最终在对蓝眼睛的疯狂沉迷中脱离社会,成了一个“局外人”。
佩科拉的父亲乔利,是一个卡利古拉式的暴力反抗者。加缪笔下的古罗马暴君卡利古拉,由于深爱之人的去世,意识到了世界本身的荒诞。为了强迫民众从荒诞世界中清醒过来,他对周围的人实施暴虐,任意杀戮。莫里森笔下的乔利,在非理性的社会现实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他遭遇过的被遗弃、性屈辱和种族歧视使他清楚地看到了现实世界社会机制的异常荒诞,同时也给予了他一种危险的负面形式的自由。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辞去工作,睡在马路上,毫无顾忌地酗酒、斗殴、杀人,甚至毫无顾忌地去死,因为“如何死与何时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在目睹了女儿佩科拉孤独无望的生存之后,乔利对其实施了强暴,从反面迫使她面对不可逃脱的荒诞命运。
无论是退缩被动的消极反抗,还是以恶抗恶的暴力反抗,在加缪看来都不是对荒诞正当的反抗方式,因为它们超出了“适度”的原则,都没有保持平衡。加缪提倡的反抗方式是微妙的,他认为“反抗是既绝望又必须行动的行为”。为此,加缪设计了一个反抗的英雄,即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西西弗被诸神惩罚推滚一块巨石上山,但巨石到达山顶又会滚落下来,于是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个活计。然而,加缪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因此可以说,西西弗式的反抗就是“在充分认识到荒诞之后的为生活而生
活”。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叙述者克劳迪娅就是一个西西弗式的反抗者。克劳迪娅是个相对叛逆并善于思考的孩子,与黑人社区的其他人不一样,她并没有被动地接受白人的审美标准,而是积极主动地抵制白人审美观,反抗种族歧视,从内心深处肯定黑皮肤的价值。“我们对自己的肤色并不感到丢人,享受着感官所给予的信息。”同时,克劳迪娅对佩科拉的遭遇怀着深切的怜悯和同情。当佩科拉被一群黑人男孩围攻时,她挺身而出将他们赶跑;当她获悉佩科拉怀孕的消息时,她和姐姐计划着要保护这个未出世的宝宝免遭黑人社区的抛弃。虽然最后孩子早产死去,佩科拉也步入疯癫世界,克劳迪娅却以无比坚韧的生命力和无比宽广的精神维度在荒谬的现实世界里成长起来,为人们讲述了这个悲伤的故事。
小说《最蓝的眼睛》通过描述一个普通黑人小女孩的悲剧,真实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在西方文化霸权和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的生存困境——荒诞世界。在那里,物质生活是窘迫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疏离的,人是孤独的,亲情是淡漠的,人伦是异化的。面对荒诞的世界,无论是逃避妥协的消极反抗,还是暴力畸形的过度反抗,都不能帮助人们摆脱悲剧命运。只有像克劳迪娅那样,虽然身处社会边缘,却义无反顾地通过拒绝压迫和肯定生命来确定自己的尊严,才能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克劳迪娅既讲述了痛苦,又传递了希望——希望诗一般的故事能够弥合四分五裂的黑人社区,希望许愿和歌唱真的具有一种抚平创伤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宋兆霖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2]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4] 李钧.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5] [美]理查德·坎伯.加缪[M].马振涛,杨淑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为:“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荒诞研究”,项目编号:2012-QN-044
作 者:朱文佳,硕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