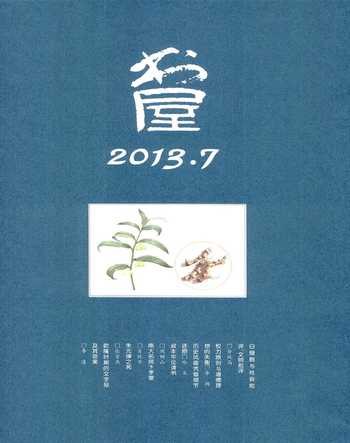南大名师卞孝萱
我是从《家学与师从——著名学者治学门径》一书认识卞孝萱先生的,随后托南京战友打听到先生通信地址和住宅电话,修书一封求先生三件事,得到先生热情回应。
其一,敬请为郑孝胥伪满国歌手迹题跋。先生跋之曰:“五代时,石敬瑭依靠契丹得帝位,称辽主为父皇帝,是历史上之可耻人物。伪满溥仪,石敬瑭之流也,汉奸郑孝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伪满洲国歌,一纸墨迹既是罪证,可供批判之用。戊子夏日,八五老人卞孝萱题。”
其二,求赐书房对联。先生从众多候选联语中挑三,挥毫“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友如作画须求澹,文似看山不喜平”,“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
其三,求赐先生自书诗。先生交白卷后解释说:年轻时候写过一些,但难登大雅之堂,中年后就此搁笔。
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肄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秘书、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乃响当当的南京大学知名教授。
先生自学文史,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涉猎广泛,书画成家,于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著名学者研究颇有偏得,2006年10月出版了洋洋洒洒三十一万字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他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详加论述,从大量材料中彰显大师们的精神风貌和学术价值。
“此稿是我二十年来研究国学之结晶,一字一句,皆反复推敲,无空话、大话,每篇皆力求特色,谈别人所未谈,表达自己的见解,非人云亦云,与目前之浮躁学风是鲜明对比。青年有志于学者,当对此书爱不释手”。先生颇为自信,并为赠我之书小跋:“余之著作,最先出版者为《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次为《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最近为《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肖跃华同志喜余之著作,寄上《学记》一册请教。2008年4月,八五老人卞孝萱题记。”
先生而立之年后,在学术上协助了三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其一,协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
先生在上海求学过程中,得知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是研究中国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遍读了钱仪吉的《碑传集》、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当时尚未出版),感到盛行于宋代的碑传编纂,至清代已登峰造极,名人碑传已辑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这件事情似乎缺少关注,私家采用“树碑立传”传统方式的也日渐稀少,于是发此宏愿,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尽一己之力抢救这批难得的史学资料。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许多名门之后将家藏碑传或赠送或借抄,许多文人、书家也将他们所撰书的碑传稿本、拓片或赠送或借抄。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业余时间逛琉璃厂掏旧书,即使出差也不忘访购这方面的书籍,惨淡经营,殊非易事,日积月累,达两大箱之多。他边整理相关资料,边撰写这方面的学术文章,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的关注,金先生主动将其推荐到所里工作。
先生报到后不再搞近代史研究,受命协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整理唐代经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他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诲,横下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二冷”治学决心,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突破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新领域。1964年春,范老病卧在床,《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就叫先生起草唐朝史学、科学、艺术方面的章节,并在一篇文章中特意指出:“第二章中第四、第五两节,所用史料是卞孝萱同志提供的。”先生还“曾提供吴越、前蜀、闽以及后周都以秘色瓷器为最上品,南唐宫女以露水染碧制衣,也是秘色”。范老用这些经济史的零散资料来说明南北统一这个大问题:“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
范老有长者之风、仁者之风,从不与人勾心斗角、争夺名利。他编著了那么多书却不拿一分钱稿费,全部缴了党费。先生受恩师影响,数十年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只做教授,不参加学术以外的其他任何活动。他对范老一直执弟子礼,念念不忘栽培之恩,公开发表了《范老的治学精神》、《范老对两个九三社员的培养》、《范文澜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难忘的恩师》、《范文澜先生的治学与为人》、《忆范文澜先生》等怀念文章,其中两篇被《新华文摘》转载。
先生主业得范老认可,副业也渐成气候。
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前夕,先生与唐文权先生合作,抉剔爬梳,筛汰精选,将所收藏清以后碑传整理出版。先生原拟书名叫《广碑传集》,由陈垣先生题签。可出版部门认为书名太高雅,不通俗,与先生协商改为《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两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章开沅先生自美国普林斯顿寄来序言,称赞“这两部书的出版,是钱、缪、闵、汪之后的一大继作,亦未尝不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汤志钧先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
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凤凰出版社修订再版了这两部书,而编者早已作古。先生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这些珍贵碑传资料,已于八九年代捐赠给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算是找到了一个好婆家。
其二,协助章士钊先生校订《柳文指要》。
我藏有章士钊先生多件墨宝,想请先生题跋,电话打过去,先生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我是卞孝萱,是章先生的弟子,你赶快过来,我用毛笔写。我们这些老人说走就走,你得抓紧时间。”
章氏与先生非亲非故,年龄相差四十三岁,为何茫茫人海中独垂青于先生?这得从1949年岁末说起。先生经常到北京各图书馆看书,当时章氏正撰《柳文指要》,其秘书王益知先生也常到各图书馆查找资料,二人遂相识。每当王秘书遇有难题求助先生,他都认真思考,详细解答。王秘书将此情况报告章氏,章氏邀约先生面谈,多有奖掖之辞,并委托先生代为寻觅永贞史料。《柳文指要》多处引用先生考证和研究成果。
《通要之部》卷二《永贞一瞥·册府元龟之永贞史料》云:“卞孝萱勤探史迹,时具只眼,顷从《册府元龟》中检得永贞史料二事见示,颇足珍异。”《柳文指要》第一三六二至一三六三页全录其文。章氏特书此事,认为先生“于攻治柳文有甚深理解”。此其一也。
《通要之部》卷二《永贞一瞥·二恨濳通史迹》云:“吾读子厚寄许孟容书:‘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一语,明与上文‘狠忤贵近相接,就中权珰强镇,此二恨如何交通构扇之迹,恨无显文露书可资左验,曾偶与卞孝萱谈及而嗟叹之,越日,孝萱果提供所谓‘永贞史料钩沈二则,持读辄为一快。”《柳文指要》第一三五八至一三五九全录其文。章氏曰:“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此其二也。
陈寅恪先生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论文,认李复言是“江湖举子”,《辛公平上仙》是“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先生考证李谅(字复言)、李复言为二人,李谅是王叔文革新集团成员,其所作《辛公平上仙》,被宋人羼入李复言《续玄怪录》中。《柳文指要·体要之部·晋文公问守原议》第一五九至一六零页全录先生其文。章氏说:“孝萱考证详明,年号遵改,并录存其说如右。”他引用先生的考证成果,否定了陈寅恪先生“江湖举子”之说。此其三也。
新闻学家王芸生先生对韩、柳关系甚感兴趣,专门撰写《韩愈与柳宗元》刊发于《新建设》1963年第2期,认为卞先生关于被杀皇帝不是宪宗可能是顺宗“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二王政权和永贞内禅一幕政变的重要意义。这对中唐和中唐以后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柳文指要》初由中华书局以大字排印。章氏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将卞先生从河南干校召回协助校勘。先生回到北京,朝夕在章氏身边工作。章氏特别交代:“书的内容由我负责,你只进行文字校勘。”先生深知章氏“吾文一落笔,即不欲任性涂抹也”的性格,虽看出书中内容有疏误之处,“但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无能为力,实为憾事”。
此书出版后,章氏赠先生一部,并用毛笔题跋:“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之后,章氏又函陈周总理,夸奖先生才华,建议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先生未再回河南干校。
章氏追悼会,新华社通稿最后一句是:“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章士钊先生的生前友好程思远、傅学文、洪希厚、郭翼青、卞孝萱、陈其英、杨伯峻、黎明晖、王益知,医护人员郭普远、张惠芬、丁万菊。”先生翻出章氏赠书及这张发黄了的《人民日报》给我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先生临终前还惦记着我收藏的章氏早年文稿,说让中华书局影印一事正在联系中。这之前,他先是当面后是来信主动提及此事,其爱屋及乌之情老而愈烈。
其三,协助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范文澜、章士钊先生逝世后,先生在北京感到孤单。母亲、子女都在家乡,他有了叶落归根之思,申请回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后来发现做学问还得大地方好,信息及时,资料丰富,人才很多,交流便利,想往省会挪挪窝。南京大学闻讯表态同意接收,可扬州师院不放人。他只好又回到北京,继续在民建中央委员会工作。但由于他的兴趣在文史方面,几年后仍想回院校工作,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学问。
江苏省教育学院欢迎先生,孙望、郁贤皓先生推荐他去南京师范学院,程千帆、周勋初先生推荐他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先生最终选择了南京大学,与程先生、周先生等组成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他开设的中国文化史、年代学研究、唐代小说与政治等课程,常常座无虚席,深受学生欢迎。
当时,著名教育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发起编辑两百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并亲自担任主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从明末黄宗羲所撰的《明儒学案》算起,至今已走过三百多年的历程。然而,当我们对这段思想史的研究认真回顾后不难发现,无论是通史类的思想史著作,如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等,还是断代的思想史著作,如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金春峰先生的《汉代思想史》等,就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大多近乎一种哲学史的研究。而这套丛书试图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梳理和正确评价,深刻揭示中国古代哲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总体认识,并对他们在各自领域学科中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形成的思想观念及其与前者的联系,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评价。
先生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具体负责《刘禹锡评传》和《韩愈评传》的撰写,工作中得与匡老接触,并得其学术真传。匡老任人唯贤,不问门第出身,十分欣赏先生,聘其担任副主编,加强审读力量,加快出版进度。丛书一百零二册出版时,先生组织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总目摘要》作附册随同发行,其编纂说明曰:“本书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志集体编写,童强、申屠炉明编成初稿,巩本栋、陈效鸿、蒋广学等同志先后参与编写和修改。最后由卞孝萱先生总纂,统一全书体例,核对材料,并在文字上加以润色。”
这套丛书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贡献和意义不容低估,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持久影响力不容低估。后来他主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中华文化百科》等,都秉承“学术自由民主、惠及千秋万代”这一出版理念,不出任何滥竽充数的书籍。
先生乐此不疲当三老助手,自己也受益匪浅、著作等身、多所建树。他常以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东先生、孤儿苦学而成当代文史大家的启功先生自勉。学术研究之初搞近代史,后来转向唐代史。他觉得研究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王维的人太多,应该将目光投向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韩愈诸人。他先研究中唐诗,后来就研究唐代的传奇小说,主张学术研究贴近本地生活。所以,他回到扬州就重点研究“扬州八怪”,来到南京就创办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他把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方法用到“以小说书画证史”上去,会长一干就是十年,出了一批六朝的书,培养了一批研究六朝史的人才。他诲人不倦的师德、提携后进的懿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尊重。
钱基博先生早知先生大名,编写《中国文学史》时曾托他到琉璃厂买书,书款有时自己从武汉寄去,有时让儿子钱钟书先生送上门,于是先生认识了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开始书信往来、互赠著作。郭绍虞、萧涤非、余冠英、程千帆、缪钺、王元化、饶宗颐、冯其庸等著名学者,应先生之请为其大作题签,亦足见先生学术造诣之高、学界交游之广。
先生曾自刻两方闲章,颇多雅趣韵味。
一方曰“小人有母”,取自《左传》“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典故。先生出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不到两个月大就丧父,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母亲靠变卖古董、亲友援助、替邻居做针线活维持家计。先生五岁时想念书,目不识丁的母亲每天向邻里学会然后回家教子。这种精神激励鞭策着先生走上自学之路后,即使在扬州沦陷、上海谋生、十年浩劫等动乱岁月,也始终没有放弃学术上的追求。
先生以母亲教子故事征诗,数十位前辈学人纷纷响应。
柳亚子先生:“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
陈寅恪先生:“卞君娱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书至。我诗虽陋不敢辞,嘉君养亲养其志。”
夏敬观先生:“学诵辛勤资转授,比之画荻更艰难。字音忆昔含声泪,恩意无涯蕴肺肝。倦眼屡窥仍夜绣,饥肠相忍弗朝餐。即兹余行皆庸行,敢谓雷同不足观。”
胡小石先生诗的末句云:“书成长泫然,小人已无母。”他看到先生信件署名下钤印的这方闲章,不由自主地想念起了已经逝去多年的母亲。
先生慈母仙去,就不再使用这方闲章。
一方曰“于树似冬青”,取刘禹锡诗句,以寒冬不凋之常青树自比节操。先生对中唐著名诗人、思想家、政治革新家刘禹锡的研究最为用功,也最为钦佩其人,先后出版了有关他的专著四部,并校订了《刘禹锡集》。
《寒碜的冬青书屋》云:“室不雅,但常高朋满座,有白发苍苍的耆旧,也有西装翩翩的青年,谈论文史、品评字画。我没有珍贵的法书、名画供人欣赏,然而藏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八千卷楼丁氏、铁琴铜剑楼瞿氏、嘉业堂刘氏、藏园傅氏的墨迹;金石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马衡、容庚、商承祚等先生的墨迹;哲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熊十力、宗白华、方东美等先生的墨迹;史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南柳(诒徵)北陈(垣)的墨迹;文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柳亚子(南社社长)、金松岑(《孽海花》创意者)等名人的墨迹……一杯清茶,其乐融融。这就是我的冬青书屋。”
这样的冬青书屋表面上看虽然寒碜,其实室内却是一座富矿,一座不可复制更不可多得的当代著名文人诗书画的富矿!
我曾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夏日登门造访先生,冬青书屋的客厅、过道翰墨飘香。书斋案头摆着半成品书法条幅,先生解释说:“你远道而来本想送幅字给你留念,但刚才写的时候笔墨不听使唤,实在羞于见人,半途作废也罢。”他认真看了我带去的章士钊先生遗墨真迹和翻拍照片,心情甚是高兴。我抱拳告退时,先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盒新茶,执意要我带回北京。
2009年9月5日12时18分,先生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八十有六。此前一个月,我还和先生通过电话,他声音一如往昔洪亮,听不出任何征兆,真的应了他“说走就走”那句话。
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在“2009年逝去的背景”中这么追忆先生:“卞先生绩学多能,博闻强记,贯通文史,兼识书画,著述丰繁,名扬中外。对唐代小说之新探,独具慧眼,别出匠心,于学者启迪尤多。”2010年9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近四百万字的《卞孝萱文集》,系统展示了先生的学术成果,从中可以领略一代文史大家独特的人格魅力所绽放出的精神花朵,似醇酒愈久弥香,如松柏万古长青!
——陈其泰先生《文史通义选读》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