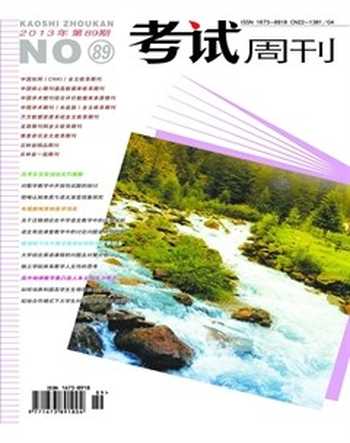遥隔千年的回响
时光
摘 要: 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为后世所称道。其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词采篇章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深邃的人生哲思之中。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其主要哲学观虽与陶渊明的思想有千差万别,但通过具体分析,还是能够发现他们在生死观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通性。
关键词: 陶渊明 海德格尔 生死观
一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隐逸文人,一位是“恒兀兀以穷年”①的学院哲人,二人相隔千余年,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有相对一致的理解。他们就是陶渊明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生死乃是人生的第一大问题,古往今来有许多思想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立论阐释。陈寅恪先生指出:“(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②陶渊明诗中有大量深邃的生命哲思,这些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形成了遥遥对应,下面我们就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经,以陶渊明的具体诗篇为纬,详细论证这两位先哲在生死观上丝丝缕缕的内在一致性。
一、诗意栖居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认为这句诗道出了生命的深邃与优雅。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提出这样的号召?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现代化社会已经使得人从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中抽身出来,成了物欲的奴仆,人在改造万物的同时,也被物的世界驱使着,在现代社会我们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但身心疲惫,感到累,感到烦,感到空虚,这种生活其实是脱离了人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生活是不幸福的,他明确指出人们追求的应是“诗意的人生”,重新定位自我,返安静归能使心灵回到“故乡”。“诗意栖居”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潜在呼唤。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当然与海德格尔所言的现代社会有本质区别,现代社会的焦虑是群体性的,而古典时代的焦虑属于敏感而真诚的个体,陶渊明即是其中一例。
陶渊明对“生”的思考一方面来自魏晋乱世对文人理想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陶渊明自身固有的性情。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无时不在语言中开启。我们通过陶渊明的具体作品,能够探求到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可见其生性冲淡自然,爱静淡泊。在他的诸多诗中,也时有他的心灵独白:“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冲淡自然、静穆淡泊根深蒂固地融入了血液之中。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的本性称之为真实状态的“本我”。
陶渊明一生坎坷曲折的履历,正是一条对“本我”进行追索并最终返归“本我”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晰地从陶诗中看到他对生命诗意栖居的诉求及思考。首先,陶渊明追求并乐于“道”。此“道”既是儒家之道德伦理之“道”,又是道家自然无为之“道”。“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的诗句就是对“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另一番阐释。反观陶公一生,之所以能忍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清贫生活,很大一部分精神资源来自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思想。陶渊明从道家之“道”中吸取人生安顿的资源,陶渊明性恬淡自然,清静不染,视仕途为“形役”,以田园青山为归宿,这与道家精神是暗暗契合的。其次,二则乐于“真”。求取自然之真,是为道家思想之精髓。陶公之诗文让人感到真气贯注,真气袭人,尤为可贵的是,陶渊明求“性”之真,从不对自己的七情六欲讳莫如深,例如他言到彭泽为官的动机时,只是“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所以求家叔举荐之,简直就是一份“酒徒的坦言”。
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时说:“诗人荷尔德林步入其诗人生涯以后,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陶公在一千余年前的一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何尝不是一种远离“家乡”所触发的不可抑制的“乡愁”。作为诗人,他和荷尔德林一样,都是用语言完成迈向“诗意栖居”生活的自我救赎。所不同的是,陶公融合了中国传统的真与善,并在此基础上乐于“生”,委于“命”,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人生的审美形态。
二、向死而在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将死亡放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死亡在其理论中是确定生存意义的支点。海德格尔把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存在、亲在、在。世间万物都是存在,而唯有人有独立意志、主动精神,万物都处于“无”的混浊状态,人处于“有”的澄明状态。万物依仗人澄明凸显,并凭借亲在(即人)得到发展的可能性。亲在(即人)内部存在又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在”(或“自我”),人们善于遗忘(或受种种阻力),这种最内在的东西常被遮掩。“亲在”往往对外寻求自身的意义,把意义附着于物质之上,使真正的自我(或者“在”)处在一种深闭状态,海氏将之称为“沉沦”。一旦“沉沦”被打破,“亲在”开始直接面对“在”,死亡的真相和人生的无意义将残酷地展示在面前。我们当然会感到“畏”、“惧”,海德格尔称其为“无家可归”。
纵览渊明的创作,对于死亡的思考极其丰富,体现在其创作的各个时期。《形影神》诗三首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独特的审美风格为后代诗评家所重视,它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死亡观。我们主要通过这组诗分析其与存在主义的内在联系。
“无家可归”状态中的“畏”、“惧”在陶渊明的诗中有大量反映。“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抚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一生复几何,倏如流电惊”(《饮酒》之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十二首》之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另外,他更写了《拟挽歌》及两篇祭文。这些诗句无一不流露出浓重的生命意识:既然天地生人而又死之,则生存的意义何在?死后所有的一切还有无意义?这些问题弄得陶身心憔悴,叹息肠热。
海德格尔针对这种“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状态,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向死而在。既然死亡是人类最终的归宿,那么就应该正视它,遗忘或者遮掩这个最大的真实等于遗忘了自身。海德格尔指出通过“先行到死”,以死作为生存的支点,从而获得自由的生命。坚守人性的本真状态,在虚无中求得实在,于死求生。陶渊明对死亡的观点更接近于道家。在《形影神》中,陶渊明在《形影神并序》的第一首《形赠影》中写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这是“形”对“影”的告诫,提出“有酒当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在第二首诗中,“影”对“形”的回答是:“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邀然兹道绝……酒云能消忧,方此讴不劣!”在此,陶渊明借“影”之口说明道教之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之说是荒谬的,所以,不如生前“立善”,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来“遗爱”后世,达到万古流芳。第三首《神释》是陶渊明借“神”对“影”“形”观点的回答,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此,陶渊明认为,自古即今,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死亡的降临。以酒醉忘怀死亡,可能会妨碍生命;立善而求名,在是非不辨的世道里,又有谁来赞誉你呢?不如人生天地间,顺随自然大道的变化,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生”也由之自然,“死”也由之自然,不必考虑得太多了。可以说《形影神》三首诗表达了陶渊明完整的死亡观。
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陶渊明和海德格尔一样,那样真诚和坦率。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以解决人生的大困惑,却没有更具体的选择。陶渊明在经过漫漫人生之路后,选择了道家的生死观作为自己践行的准则:师法自然,任性而为,保有生命的一份本真。这样的选择带有更加亲切的生命气息,是对千余年后海德格尔理论的遥远呼应。
“诗意栖居”和“向死而在”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完整生死观;陶渊明在乱世之中的守望与高蹈,无不渗透着浓浓的生命大智慧。哲学和诗歌从来都是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为人的生存寻找更为合适的尺度。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陶渊明,都以自己的实际创作,作出了鲜明而独特的回答。二者思想间殊途同归的共通性,这遥隔千年的回响,或许正指向了寻找人类生存尺度的光明之路。
注释:
①[唐]韩愈著.卫绍生,杨波注译.唐宋名家文集·韩愈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06.
②陈寅恪著.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5.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2]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刘银昌.退避,作为对存在的守护——谈陶渊明的归隐与人生领悟[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