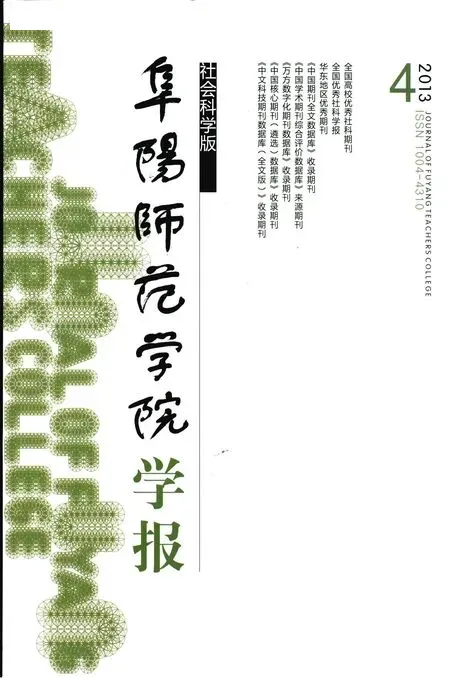反讽性典故和特·斯·艾略特的“传统观”
江 群,张 敬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汉语“典故”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用典是知识渊博、博古通今的艾略特诗歌的一大特点,这也为部分人所避讳,认为是造成其诗歌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据《辞海》解释,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了意义的改变,即言非所指”。哈琴认为反讽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语义特征:第一,反讽具有关联性,是一种所言与未言意义的交流过程。第二,反讽具有包容性,两种意义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第三种意义。第三,明言与未言之意两者之间只是差别,但并不冲突,反讽意义同时存在于两种或多种意义的交流过程之中[1]66。反讽性典故是通过将典故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情节进行关联、并置、对照,产生否定和嘲讽的效果。反讽性典故产生的“否定和嘲讽”正是哈琴提出的“文本”和“典故”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第三种意义”。
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特·斯·艾略特提出了不仅应该尊重传统而且应该将过去和现在有机结合的“传统观”。当有人说:“已故的作家离我们很遥远,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他们知道的多得多”,艾略特提出“说得对,他们本身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2]55并且,“……不仅他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们,也就是他的先辈们,最有力地表现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2]2但艾略特又提出“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的步伐,盲目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2]2所以,我们不仅应该遵循传统,而且应该将过去和现在有机结合起来,关于两者的结合方法,艾略特在《菲力普·马生格》里提出“末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剽窃;手低的诗人遮盖他所抄袭的,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或至少不同的东西。”[3]因此,艾略特一方面“剽窃”悠远的古代神话传说和文学典故中的英雄人物事迹,另一方面他将它改造成了更好的东西,即通过将典故中的英雄人物和他的早期诗歌中的反英雄人物并置,采取反讽性典故的形式,以典故中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和宏伟事迹烘托出诗歌中现代社会反英雄人物的的渺小、琐碎和堕落。
在其早期诗歌中,为了创造斯威尼和普鲁弗洛克这两个著名的反英雄人物,艾略特大量使用反讽性典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两个反英雄人物的卑微和堕落。
斯威尼故事一
《笔直的斯威尼》一诗的引言引自英国剧作家弗兰西斯·鲍芒和约翰·弗莱切的剧作《少女的悲剧》,女主人公阿斯帕蒂在被爱人阿门特抛弃后哭泣道:“至于那些我周围的树木,让它们去枯干凋零吧;让那些岩石在汹涌的波涛中呻吟吧;在我背后一切是荒凉。看啊,看啊,女娃娃们。”①阿斯帕蒂的父亲卡尼尔莱克斯是一位伯爵,阿门特同样是一位贵族绅士,阿斯帕蒂和阿门特相爱并订婚了,但最终阿门特遵守国王之命抛弃了阿斯帕蒂,和伊娃德妮结婚了,新婚之夜伊娃德妮拒绝和阿门特共寝,阿门特才发现原来伊娃德妮是国王的情妇,国王以牺牲他和阿斯帕蒂为代价,借这场婚礼来掩盖并继续他和伊娃德妮的不正当关系。虽然阿门特发现了婚礼背后的秘密但他无法报复给他带来耻辱和不幸的人,因为此人正是国王,阿门特“君权神授”的信仰和他对国王的忠诚都使他无法拿起复仇的利剑[4]。
《笔直的斯威尼》的前两节引用了阿莉德尼和忒修斯的典故,描述了克里特公主阿莉德尼被雅典王子忒修斯抛弃在爱琴海岛群中最大的纳克松斯岛中的凄凉景象。
给我画一个散布在汹涌的爱琴海
小岛周围的多洞穴的荒滩,
给我画一些面对着狰狞而狂吼的
海洋的、庄严而迂回曲折的岩石。
给我展现天上的风神
再现那些吹乱了
阿莉德尼秀发的狂风
急匆匆地吹鼓了那些难以琢磨的帆篷。
忒修斯是雅典国王埃勾斯和特隆泽公主埃特拉的私生子。克里特国王弥诺斯曾率兵进攻雅典并打败了雅典人,众神命令雅典人满足克里特所提的条件,也就是每年须向克里特王国进贡七对童男童女来喂养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那段时间,雅典城一直为自己曾许诺向克里特国王弥诺斯进贡一事而困扰不安。当忒修斯十六岁那年,也是雅典向克里特国进贡的第三年,为了杀死怪物,使同胞们免遭更大的悲痛,忒修斯决定作为选送贡品的一员前往克里特。临行前,他向父亲保证,一旦成功,他将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忒修斯到了克里特,克里特公主阿莉德尼爱上了他,她给了忒修斯一团导航线帮助他走出怪兽居住的迷宫。那天晚上,阿莉德尼护送忒修斯到了迷宫,并且忒修斯许诺如果他顺利杀死怪兽走出迷宫,他将带阿莉德尼一同离开。最终,忒修斯杀死了半人半牛的怪物并在公主给他的导航线的帮助下走出了迷宫,忒修斯带着公主一同返回。船队在纳克松斯过夜时,他得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托梦,酒神声称阿莉德尼跟他早就订了婚,他威胁忒修斯,如果不把阿莉德尼留下来,就降下灾难。忒修斯从小跟外祖父一起长大,外祖父告诫他要敬畏神灵,因此他怕神灵迁怒于他的王国,只得将悲哀的公主留在荒凉的孤岛上,自己乘船回去。忒修斯悲伤万分,当他的船驶近雅典时,他忘记换上约定好的白帆。他焦虑的父亲站在山顶上看到远处的黑帆时,就绝望地跳海自尽了,从此这片海就叫做爱琴海(埃勾斯的海)。忒修斯懊悔万分,再也没能从自责中缓过来。这就是忒修斯和阿莉德尼以及“难以琢磨的帆篷”的故事[5]217-220。
在这两个神话故事以后,《笔直的斯威尼》继续描述斯威尼和妓女寻欢的场景,十分露骨。
膝盖以上的折刀
从脚跟到腰际都是笔直的
推搡着床架
在枕边张开
寻欢过后,“斯威尼专心站直着光脸/ 腰背宽厚,颈部微带红色,/懂得女人的性格/ 揩去了脸部的皂沫。”这时,这位妓女突然癫痫病发作,痛苦地弯下身子,手抓着两边的床,尖叫起来,而斯威尼对她不管不问,他在大腿上试试刀锋,准备刮脸后离开。就连过道里的老鸨和其他妓女都不耻于他的这种行为,诅咒那些低级趣味的人。
整个诗歌的引言、前两节和其余的部分分别描述了阿门特和阿斯帕蒂、忒修斯和阿莉德尼以及斯威尼和妓女的故事,虽然这三个故事的主题都是关于爱情和抛弃,但它们本质不同。阿门特是位贵族绅士,他深爱着阿斯帕蒂,国王密令他和伊娃德妮结婚,因为他对国王的忠诚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他不得不抛弃阿斯帕蒂。忒修斯身为雅典国子,是位胆识超群的英雄人物,曾经斩杀了无数强盗和野兽,他解开了弥诺斯的迷宫,并战胜了怪兽弥诺陶诺斯,拯救了他的国家和人民,他深爱着阿莉德尼,但同样因为对“神权”的迷信,害怕酒神降祸于他的人民,不得不抛弃了阿莉德尼。斯威尼对这位妓女则毫无感情可言,在她痛苦地尖叫时,他无动于衷,完全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斯威尼是个整日出入酒馆、妓院的堕落者,与阿门特和忒修斯相比更显得卑微、龌龊;阿斯帕蒂是公爵的女儿,阿莉德尼是公主,她俩均地位高贵,热情纯真,与她俩相比和斯威尼厮混的妓女更显得身份低贱。通过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英雄人物与反英雄人物斯威尼并置对比,艾略特紧缩用词同时又扩大了诗歌的时间空间,深化了诗歌的主题,即古代的爱情故事和英雄事迹在现代社会已经演化成肉欲的沉沦和责任感的淡漠。
斯威尼故事二
在《夜莺歌声中的斯威尼》一诗中,艾略特将古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和菲罗墨拉两个典故和斯威尼的谋杀案并置对比,同样产生了反讽的效果。“艾略特曾经说,“他在诗的开头有意创造了一种凶兆感。”[6]42这种“凶兆感”通过诗歌的引言得以体现,阿伽门农被妻子和她的奸夫所刺临终前喊道:“哦,我受到致命的一击!”
阿伽门农是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阿特柔斯之子,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哥哥,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合远征军统帅,他武艺高强,擅使长矛和标枪,足智多谋。在希腊军队出征的路上,阿伽门农射死了一只怀孕的兔子,得罪了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阿尔特弥斯为了报复,便引来了巨风,使希腊军队在奥利斯港受阻。阿伽门农为了尽快进军特洛伊,听从了先知卡尔卡斯的建议,把女儿伊菲革涅亚从阿尔戈斯接来,作为祭品祭献给了狩猎女神。战争胜利后,他顺利回到家乡。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长期以来一直与她堂弟埃吉斯托斯通奸,她怕奸情败露,同时怀恨阿伽门农以长女伊菲革涅亚献祭,又出于对王位的觊觎,便与奸夫埃吉斯托斯一起把阿伽门农谋杀在浴室里[5]459-461。
诗歌第一节,斯威尼被描述成一个有着“猿颈脖”“下巴斑马似的条纹胀得好像长颈鹿的斑点”的“半人半兽”的丑陋人物,他垂下双臂笑声连连,正和“身披西班牙斗篷的女子”调情,“身披西班牙斗篷的女子/ 想坐在斯威尼的膝盖盘上,/滑下身来,拖着台布,/ 掀落一只咖啡杯,/她坐在地板上整了整身子,/打着呵欠,把长袜拉上大腿;”,“而此时死神和乌鸦在上方漂移,斯威尼在角门守定”,“据说通过角状的地狱大门,梦得以成真。”[6]42由此可见,作为滥情的嫖客,斯威尼肯定做了对不起雷切尔和“身披西班牙斗篷的女子”的事情,导致她们的梦想无法实现。因此,她们共同报复并杀害了斯威尼,“雷切尔用凶手撕扯葡萄,吃个痛快;她和披斗篷的女士被怀疑是勾结在一起的一伙人。”
据古希腊神话,菲罗墨拉是雅典国王潘狄翁的小女儿,她还有一个姐姐叫普洛克涅。普洛克涅嫁给了色雷斯国王忒瑞俄斯,并生了个儿子。几年后,普洛克涅十分想恋她的妹妹,就说服丈夫过海去接菲罗墨拉。在回国途中,忒瑞俄斯贪恋上了菲罗墨拉的美貌,他把她领进树林,强奸了她,并割去她的舌头。菲罗墨拉遭囚禁后,设法把她的可怕经历编进了花毯上的图画,并通过一个仆人把它送给了普洛克涅。普洛克涅决心替妹妹报仇,她杀了自己的儿子,把他做成菜当作美味端给丈夫。当忒瑞俄斯问起儿子时,普洛克涅拿出砍下的头,扔到忒瑞俄斯身上。两姐妹逃向森林,忒瑞俄斯在后面追赶,就在忒瑞俄斯快追上她们时,神把他变成了一只戴胜鸟,这种脏鸟会自己把自己的窝搞脏。普洛克涅变成了一只燕子,而菲罗墨拉变成了一只夜莺[5]66-69。
诗歌中引用的两个古希腊神话故事都和爱的背叛和血淋淋的复仇相关,这一点与《夜莺歌声中的斯威尼》中的两个妓女谋杀斯威尼的主题相似,但本质上大为不同。作为特洛伊战争的统帅,阿伽门农是一个有尊严的王道权威代表,为了国家的荣誉他英勇无畏,披荆斩棘英勇奋战数十载,开创了许多英雄事迹,为了自己的国家,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女儿,但他最终被他背信弃义的妻子杀害。斯威尼则是一名无情无感、无足轻重的堕落嫖客,他“名为人”“实为兽”,所以,当他被谋杀后,“阿伽门农大声高呼,让他们撒下点点血滴/ 玷污这僵硬的不光彩的尸布。”菲罗墨拉是一位纯洁高贵的雅典公主,但被他姐夫忒瑞俄斯强奸并残忍地割掉舌头,她的姐姐普洛克涅以杀死自己的儿子为代价为妹妹复仇,这俩姐妹均是淫荡的暴君忒瑞俄斯的受害者。神同情她们,并最终拯救了她们,从此她们变成了自由的夜莺和燕子。艾略特使用《夜莺歌声中的斯威尼》作为诗歌的题目,把整日和斯威尼厮混并残忍地谋杀了他的妓女和菲罗墨拉并置,产生了反讽的效果。并且,在诗歌的结尾处,艾略特写到“在圣心女修道院附近/ 夜莺们正在歌唱,”,更使读者们对于她们的结局有了许多美好圣洁的想象。
普鲁弗洛克的故事
艾略特早期诗歌中的名诗《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同样引用了许多典故,其中艾略特将哈姆雷特王子、《圣经》中的先知施洗约翰同普鲁弗洛克并置,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塑造了一位爱情无能者的反英雄人物——普鲁弗洛克,他是一位“瘦弱”“秃顶”神经敏感的中年单身知识分子,诗歌描述了他去拜访“谈论着米开朗基罗”的“高雅”女性之前的心理斗争。当他几乎决定“走吧,我们去拜访”,他劝导自己还有时间再考虑一下,“还要时间为接待你将要照面的脸孔准备好一副脸,/……,/还有时间犹疑一百遍,/看见并修改一百种想象中的景象;”当他春心萌动,心想着“我就该大胆行动了吗?”,他又不知所措,“我又该怎样开始呢?”,并且他开始怀疑行动的价值,“到底这是不是值得,/在这些杯子,橘子酱,茶水之后,/在动用这些瓷器,在议论关于你我的同时,/这是不是就值得,/用微笑来接受下这桩事情。”最终,在精疲力竭的内心挣扎以后,普鲁弗洛克坦白自我“不!我不是王子哈姆雷特,天生就不够格;”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笔下高贵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承受着父亲的被谋杀和母亲匆忙改嫁带来的巨大痛苦,他的继父既是他的叔叔,同时也是那位篡位者和幕后的谋杀犯。哈姆雷特对于复仇的犹豫是由于围绕着血腥的谋杀和复仇的复杂道德、宗教和伦理问题,但是哈姆雷特最终克服了内心的矛盾,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他的复仇大业。虽然普鲁弗洛克也以他的犹豫而闻名,但他的犹豫是关于他个人无关宏旨的风月之恋,相对于哈姆雷特的英雄行为和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结局,普鲁弗洛克这个“爱情无能者“的风月故事实在是微不足惜。并且,普鲁弗洛克最终也未能走出他的内心囚牢,勇敢地追求他所爱的人,诗歌题目中的“情歌”二字充满了讽刺的色彩。
当普鲁弗洛克犹豫着“我该不该在饮过茶点吃过蛋糕和冰点以后,鼓足勇气把当前硬逼到紧要关头”,他看见“我的头颅(稍有点秃顶)被放在盘里端了进来”,“盘子里的头颅”是关于施洗约翰的圣经典故。
据《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施洗约翰对希律王说他娶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是不合理的,希罗底因此怀恨在心。在希律王的寿宴上,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的舞姿博得了她继父希律王的喜爱,他许诺满足莎乐美的任何要求,希罗底为了报复施洗约翰,暗示莎乐美要求将施洗约翰的首级装在盘子里交给她,为了遵守自己的诺言,希律王只有派人杀死了施洗约翰,并将他的首级放在盘子里交给了莎乐美。但最终,耶稣基督复活了约翰[7]18。
施洗约翰是一位虔诚的先知,他因为自己的诚实而被谋杀,并最终被耶稣基督复活。当普鲁弗洛克犹豫着是否应该鼓足勇气去追求那些“高雅女性”时,他泄气了,但这时普鲁弗洛克又发挥了他的“阿Q 精神胜利法”,他将自己爱情的失败和施洗约翰的悲惨遭遇相比较,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别人的谋害,以使自己想象中的爱情经历更具神圣感和悲剧色彩。“但是我虽曾又哭泣又禁食,又哭泣又祈祷,虽然我见过我的头颅(稍有点秃顶)被放在盘里端了进来,”不久他就意识到他在自欺欺人,“我不是先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曾见我成为伟大的那一时刻一闪而灭”。由此,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普鲁弗洛克的自欺欺人、犹豫不决和“幻想狂妄症”,施洗约翰被耶稣复活了,而普鲁弗洛克将永远活在他自我的“坟墓”里。
结语
艾略特的“传统观”的两个方面,即尊重传统和过去和现在的有机结合决定了在其早期诗歌中他一方面大量用典,另一方面采取反讽性典故的形式,将神话传说和文学典故中的人物和其诗歌中著名的反英雄人物斯威尼和普鲁弗洛克相关联、并置、对比,找出了其中的关联性,但更突出了其中的差异性,古代神话传说和文学典故中的英雄人物淋漓尽致地反衬出现代社会中这两个反英雄人物的渺小、琐碎和堕落。以古讽今使读者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时代的堕落感,这也是艾略特诗歌的主题之一。以古讽今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互文性”的典型体现,它将“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8]211
注释:
①本文所有艾略特诗歌的汉语译文均出自赵萝蕤、张子清等译《荒原T.S.艾略特诗选》,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
[1]Hutcheon,Linda.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M].Oxon: Routledge,1994: 66.
[2]特·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3]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N].北平晨报·文艺,1937,(13).
[4]Francis Beaumont,John Fletcher.The Maid‘s Tragedy[M]ed.T.W.Craik.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
[5]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古典神话[M].曹乃云,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
[6]特·斯·艾略特.荒原T.S.艾略特诗选[M].赵萝蕤,张子清,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7]佚名.圣经[M].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2002.18.
[8]陈永国.互文性[A]//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11.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