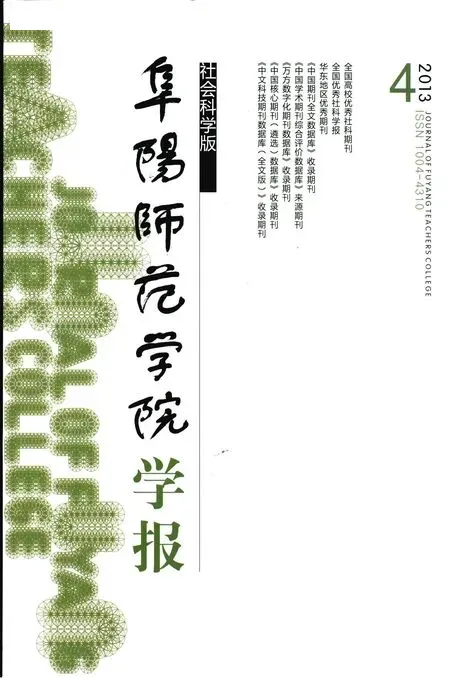边界功能视角下中印关系的演变
洪共福
(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又是山水相依的邻邦。两国建交后,既有50年代“中印是兄弟”的友好时期,又有60年代的边界冲突。80年代末,两国逐渐恢复正常关系。2005年,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演变,学者们大多从地缘政治视角或历史学视角进行研究。①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一定程度上受边界问题的影响。本文拟从边界功能视角梳理中印关系的发展演变,并探究边界问题在不同时期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一、中印边界的功能
1.构建国家身份
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应具备以下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1]65-66。领土是构建国家身份必不可少的条件。边界则划分国家领土范围的界限,划定国土和国民,具体表明一国法治到达的范围,是他国对本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标志。
对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印度来说,边界构建国家身份的功能表现为印度将边界作为民族国家构成的要素,表现为印度从民族主义立场对边界的阐释。印度历史上长期只有种姓、宗教观念,鲜有民族、国家意识。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者逐渐形成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他们强烈相信由文化、共同经历、习俗与地理所界定的印度国家久已存在。”[2]25既然印度国家“久已存在”,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领导人推论:印度传统和习惯边界早就存在并已自然演化,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活动和文化,是基于如山脊和分水岭等地理特征[2]25。“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3]
对于新中国来说,边界构建国家身份的功能,表现为中国迫切要求消除帝国主义侵略色彩。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与欺凌,疆土屡遭割让,边界数次变迁。在中国西南,由于英国侵略西藏而遗留下中印、中缅未定边界。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由于沙俄侵略而遗留下中苏未定边界。新生的人民政权明确宣布,不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自然不可能承认由不平等条约确定的边界。对于未定边界,中国政府希望维持现状,然后和有关国家友好协商,重新签订协定,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此举对构建国家身份极为重要,因为旧条约是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与有关国家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
2.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
边界是有主权的国家行使其主权的界线,是保证一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最基本的条件,边界具有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功能。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为保卫印度北部边界安全,试图将中国西藏作为印度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区”。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印殖民当局的安全战略观与边疆政策。1948年10月9日,中国政府分别向英国、印度、巴基斯坦三国政府照会,要求废止1908年中英续定藏印通商章程。巴基斯坦政府在复照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印度政府在复照中则宣称:一、印度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认为以前所有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所订条约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皆由该政府所继承;二、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应以1914年西姆拉条约及其通商附则为准[4]601。这表明印度政府不仅要全盘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特权,甚至企图将连英国政府都承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西姆拉条约强加于中国。1950—1953年,印度趁中国全力投入朝鲜战争,将英国殖民者设计的“麦克马洪线”变成地面的现实。不仅如此,印度仍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干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并且支持极端分子的分裂活动。
对于中国来说,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关系到领土归属,更关系国家安全与民族地区稳定。在安全战略层面,西藏是保证中国西部安全的重要地区。横亘绵延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是西藏的天然屏障,对南亚呈居高临下之势。青藏高原属高原高寒地带,地形复杂,环境恶劣,军事行动受到制约。西南边疆这种地缘上的安全价值,正是英属印度殖民当局与印度政府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侵略、蚕食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国家与印度在西藏长期处心积虑从事分裂活动、支持分裂势力的重要考量。在西段,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是新疆通往西藏的唯一战略要道,1956年修建的连接新疆与西藏的新藏公路即通过此地。新藏公路是新疆通往西藏的生命线,对于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具有重要意义。
3.沟通国家间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
边界地带处于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连接之处,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在资源要素与经济发展水平上,边境区间往往存在梯度差异,使得两个区域间具有经济上的互补性,边界通常是资源、劳动力、产品、资金技术相互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5]。因此,边界承担着沟通国家间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的功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国际间跨界交流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边界作为一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前沿阵地,日益突出地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而边界的军事安全功能、抵御外部安全威胁的防御屏障职能则显得相对弱化。
中印两国山水相依,两国人民很早就冲破雪山与高原的阻隔进行交往。中印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密切,文化交流、经贸往来频繁。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协定序言,它正式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协定的签订,意味着印度放弃了英国侵略西藏时取得的种种特权,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为中印友好关系清除了障碍。
中印协定生效后,中印边贸通商往来有很大发展。例如,亚东市场过去极少有印度商人,只有十多家尼泊尔商人从事印藏贸易。协定生效后到1959年初,下司马(亚东市场所在地)的印度坐商(开店有货栈的)增加到267 人,尼商增加到515人,过去印商从未去过的帕里,也有十余户印商约32 人开店做生意[6]227。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前,中央政府进藏人员和西藏大量需要的日用品、衣着布匹、杂货等多数从印度运入。和平解放前,西藏主要出口羊毛等土特产换取印度的日用杂货工业品,每年平均进出口额约300 万银元。解放后,藏印贸易大增,仅亚东下司马市场,自印度进口从1952年的800 万银元增至1957年7187 万银元[6]227。除了边界贸易,每年还有大批印度香客通过开放口岸,前来西藏阿里神山岗仁布钦、圣湖玛旁雍错朝圣。
中印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一度因边界冲突而中断。80年代末,中印关系逐渐恢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印度90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中印边界的经贸交流功能逐渐突出,关闭多年的边境贸易口岸重新开启。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两国签署《关于恢复边境贸易议定书》,这标志着一度中断的中印边贸开始解冻。1991年12月13日,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决定将强拉(利普勒克)作为双方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出入境的通道。1992年,两国签署《关于海关规则、银行协议等边境贸易事宜议定书》,同年7月1日,又签署《关于边境贸易出入境手续议定书》。至此,中断了30年的中印边贸终于得以恢复。2003年6月23日,两国签署一项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双方同意通过乃堆拉山口开展边境贸易,中方指定中国西藏的仁青冈为边境贸易市场,印方指定印度锡金邦的昌古为边境贸易市场。2006年,根据中印两国协议,乃堆拉山口恢复边贸通道。7月6日,中印双方在乃堆拉山口举行边贸通道重开仪式,随后两国分别开放仁青岗边贸市场和昌古边贸市场,恢复了这条中断44年的边贸通道。
二、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的演变
1.中印友好时期的边界问题
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人民共同唱响“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旋律,中印关系一时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楷模。印度一方面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但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出发,印度趁中国百废待兴、忙于朝鲜战争之机,悄悄向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不断推进,蚕食中国领土,从而使边界问题成为后来冲突的种子。
尼赫鲁十分注重西藏的战略地位,他说:“谁统治了西藏,谁就取得了对于敌人的确定无疑的优势。”[7]40在尼赫鲁看来,喜马拉雅山构成了保卫印度安全的有效屏障。但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印度认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印之间产生了长达1700 公里未正式划定的边界线,而且中国历届政府均未承认。这一点,尼赫鲁极为担心,因此他将中国问题置于对外政策中心地位,他说:“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第一次面对面隔着一条长长的边界,而且是一条存在争论的边界,即使我们是朋友,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争论的、威胁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8]66西藏解放后,尼赫鲁担心中国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两国边界地区逐步渗透,进而占领有争议的领土。尼赫鲁命令印军加强在边境地区的活动,力图赶在中国之前,控制更多的边界地区。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采取“无争端、不谈判”的立场。在中印关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前,印度外交部于1953年11月召开一次内部会议,会议做出决定,即“在即将与中国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不提印藏边界问题”,“不让中国利用这个机会翻这个问题的旧账”[9]155-156。1953年12月,议员兰卡·森达拉姆(Lanka Sundaram)在议会中再次提出边界问题,并提出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关于印度东北边境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是不愿意接受“麦克马洪线”的,兰卡·森达拉姆还提出边界存在争议。尼赫鲁高声强调:“边界在那里,麦克马洪线就在那里。对此,我们没有什么要与任何人,与中国政府,与任何其他政府讨论。”[10]33谈判时,印度代表团团长赖嘉文指出,在中印之间只有一些小的问题悬而未决。周恩来指出,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11]63。
中国方面认为1954年中印谈判解决的是“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在中国外交部1956年的一份文件中有明确说明,该文件对1954年《中印协定》进行总结时写道: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所解决的还只限于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除这些问题外,还有不少边境问题,如拉达克地位问题,锡金地位问题,所谓麦克马洪线问题等都还有待解决[12]。而印度则单方面故意认为谈判和所达成的协定是全盘解决所有悬而未决问题。这实际上隐藏着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外交谋略。
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思维使得尼赫鲁对中国有不信任感,希望将中国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区”。1950年西藏解放后,印度以现实的态度接受了“西藏缓冲区”的消失,并从大国战略、印巴冲突、经济建设等因素考虑,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印度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为谋求印度安全战略,在边界问题上频频采取单边主义行动。1954年,印度出版的官方地图第一次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为中印边界东段“已定界”,抹掉了1936年麦线公开后一直注明的“边界未经定界”字样。1954年7月,即《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尼赫鲁口授了一份给内阁各部的备忘录,尼赫鲁在备忘录中写道:“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北部)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同任何人讨论的。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13]81到1954年,印度几乎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并公然在这块领土上设置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印度政府对待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和单边主义行动,使中印关系在亲密友好中埋下未来冲突的隐患。
2.边界冲突与中印关系的恶化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50年代后期,印度采取“无争端、不谈判”的立场,不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实质是压服中国接受印度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
1954年中印协定虽然消除了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留下的种种特权,但印度将西藏变成“缓冲区”的幻想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印度主要从地缘政治考虑,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妄图使西藏取得独立半独立地位。1959年西藏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于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印度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干涉,使中印关系受到严重伤害。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一些政党和政客对中国大肆攻击,如3月16日印度人民院辩论外交部工作时,人民社会党议员梅达就西藏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叫嚣说印度对此不能“置之不理”。3月20日的《印度斯坦旗报》公然声称“印度非常重视西藏的‘缓冲’价值”。3月29日孟买举行所谓“西藏日”集会,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梅达主持集会时,居然称“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3月30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发表长篇讲话,一方面他说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他着重讲到印度同西藏之间“悠久的联系”,并声称“对西藏人表示很大的同情”。实际上,所谓印度对西藏“宗教和文化联系”的“感情”,不过是对中国内政干涉的借口。
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内再次掀起反华浪潮。印度媒体进行大肆渲染,唤起公众的反华情绪。反对党也趁机向尼赫鲁发难,批评其对华政策和边界政策。受政党政治影响,迫于党派斗争的压力,尼赫鲁在边界政策上更趋强硬。尼赫鲁在朗久事件后接连发表谈话,指责中国“侵略”,并宣布印度政府已采取必要措施,把原用于维持东北边境治安的准军事部队阿萨姆步枪队归于陆军指挥。朗久事件和中国穿越阿克赛钦修筑公路的消息在印度披露后,尼赫鲁在议会遭到质问,抨击他隐瞒中印边界争端的有关情况。为抵挡反对派的攻击,为表明印度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尼赫鲁决定将中印之间的外交文件公之于众,此举进一步煽动了印度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华舆论。
国内受到反对派和舆论的牵制,国际上得到苏美的支持,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更加自行其是,渐行渐远。尼赫鲁两次拒绝中国关于就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会谈的建议。对于1960年4月19日的两国总理会谈,尼赫鲁只将其看作一种姿态,一种改变不利地位的策略。事实上,印度早就关闭了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大门。
1960年初,印度内部制定前进政策,企图破坏中国对争议地区的控制,办法是:“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13]1891960年,拉达克的印军巡逻队在情报局的帮助下向前移动,并建立哨所,到1962年中建立了43 个新哨所,印军已侵入新疆境内的奇普河谷、加勒万河谷及班公湖。在东段,从1961年底到1962年上半年,印度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24 个哨所[14]164-165。与此同时,印军加紧备战。1962年9月9日,国防部长梅农主持召开国防部会议,会议制定代号为“里窝那”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必要时使用武力对中国边防部队武力驱逐。10月12日,尼赫鲁出访前在机场宣布已下令将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
印度前进政策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了边境安宁,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与主权完整,且这种行为得到美苏的纵容与支持,这使中国政府感到严重威胁,加上和谈的大门一次次被印度关闭,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予以反击。1962年10月,双方在边界东西段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3.边界谈判与中印关系的缓和
边界战争为中印关系留下了深深的创伤,直到1976年中印互派大使,双方关系逐渐解冻。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力排众议,访问中国。邓小平与之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中印关系要“向前看”的共识,同意以“互谅互让、相互调整”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拉·甘地访华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开端”,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1991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度。会谈中,双方希望不要使边界问题成为发展关系的障碍,同意恢复中断多年的边界贸易。1993年,拉奥总理访问中国,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文件。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双方达成了构建“面向21 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次访问开创了中印关系的新阶段。
为解决边界问题,中印双方进行了长期的谈判。1981年12月开始,两国进行了长达六年、历经八轮的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2003年10月,中印启动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并继续进行其他层次的定期会晤。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双方确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等重要文件。2009年10月,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就边界问题达成以下共识:遵循双方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发挥有关机制的作用,继续通过坦诚对话,逐步缩小分歧,争取不断取得进展,最终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要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稳定,这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有利于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和双边总体关系的发展。两国各界都要为此营造积极、友好的气氛,共同做出不懈努力[15]。
20 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结束后,中印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大国力量出现分化组合。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要想崛起,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国越来越注重综合国力的提高,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第三,中印经济改革不断深入,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印两国尽管存在边界争端,但如何淡化边界的政治安全功能,充分发挥边界沟通两国交流与经济联系的功能,成为两国共同思考的问题。
自1988年拉·甘地访华以来,两国在高层访问和会谈中,都提出要“扩大双边经贸合作”,从而对双边经贸交往与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印度决策者认为,要想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必须以综合实力为后盾。要提高综合国力,搞好周边关系是前提,没有和平良好的周边环境,发展经济便无从谈起。中国为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明确提出并积极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近年来,双方在多边合作机制中的接触、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在WTO 和《曼谷协定》的框架下,在中孟印缅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印双方相互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双边合作,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贸易额从2000年的29 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617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20 倍[16]。随着双方交流与合作的增多,双方的了解和互信也在不断增强,边界沟通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功能日渐突出。
三、小结
中印关系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又是崛起的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从建交初期的密切友好往来,到爆发武装冲突,再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出现波折,主要因边界问题而造成。而两国对待边界问题的态度,即如何认定边界的功能价值,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关系。
印度独立之初,在边界问题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并且从民族主义立场对边界进行阐释。因此,中印建交后,印度一方面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另一方面,在边界问题上,从构建民族国家身份和国家安全战略考虑,印度不承认存在边界争议,并且认为中国应知恩图报,在边界问题上应满足印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消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对未定边界进行平等协商与谈判。但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以毫无法律依据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损害了中国民族尊严,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严重威胁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由此导致中印边界冲突。
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战争的形式与战争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边界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功能削弱,打击跨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功能日益凸显,这使邻国之间迫切需要加强相互合作。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两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搁置边界争议、发展经贸合作越来越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中印边界传统意义上军事安全功能削弱,政治安全功能淡化,经贸交流功能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印关系的缓和与发展。
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背景下,中印关系的发展如何突破边界问题的障碍,成为两国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首先,两国需要大力增进相互信任,互不以对方为威胁。这不仅是领导人和外交家的共识,而且应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其次,加强各层次交流,全面了解对方信息。近年来,中印领导层互访逐渐加强,两国应探索交流互访的定期化和机制化,以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双方还应拓宽接触面,加强民间等各层次的交流,努力消解错误印象,增信释疑。第三,理性看待经济竞争,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精心挖掘合作潜力。第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总之,突出边界沟通经贸交流功能,淡化军事安全功能,最终通过谈判政治解决边界问题,中印关系的未来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国内代表性成果有: 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 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赵蔚文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时事出版社2000年)、张敏秋的《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叶正佳的《五十年来的中印关系: 经验和教训》(《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4 期)等。从边界功能视角进行研究的仅见邱美荣的《边界功能视角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 期),该文从边界功能视角对中印边界争端产生根源及其发展变化进行研究。
[1]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2]Steven A.Hoffman.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3]内维尔·马克斯维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J].郑经言译.南亚研究,2000,(1).
[4]吴俊才.印度史[M].台北:三民书局,1981.
[5]方维慰.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国家的边界功能[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2).
[6]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7]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8]Yaacov Y.I.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 Indian Conflict,1959-1962[M].Westview Press,1984.
[9]B.N.Mullick.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M].Bombay: Allied Publishers,1971.
[10]Nancy Jetly.India- China Relations,1947-1977[M].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1979.
[11]周恩来外交文选[Z].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开放档案[Z].档案号:102-00055-01
[13]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M].陆仁,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14]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15]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就边界问题达成共识[EB/OL]
中国新闻网http: //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0-24/1928748.shtml
[16]戴秉国:中印贸易额10年增长20 倍[EB/OL]新 浪 财 经 http: //finance.sina.com.cn/china/bwdt/20120116/1238112125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