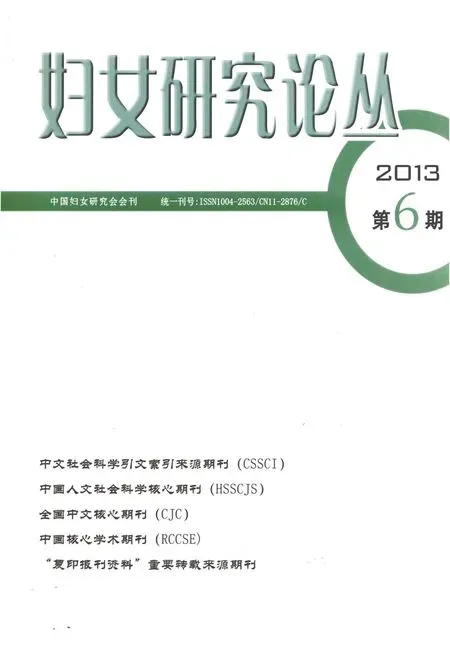当权力遭遇性别:近10年女村官研究综述与展望
曹荔函张克云
(1.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一、引言
伴随着国际、国内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重视农村妇女的政治权利,推动妇女参与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实施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民主选举给了农村妇女参与村级基层治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更多的妇女精英能够脱颖而出,走上村庄权力中心的舞台,成就了“女村官”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即女性参政、从政是妇女地位和作用发挥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民主真谛、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女村官首先是女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这种双重的角色体现了妇女的政治参与。诚然,女村官是妇女参政的成功典范,然而,成功进入权力核心圈子后,作为女性领导者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的从政道路是否顺利,有何障碍与阻力,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男性中心主义依然在很多方面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情况下,女村官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能否走得更远,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女村官的执政现状与发展得到了一些学者和机构的重视,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关于农村女性领导的研究,这些研究以实证为主,既有期刊文章,也有学位论文和出版成书的相关报告。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女村官的现状、制约或影响女村官发展的因素、针对女村官政治参与的措施等。本综述旨在从上述几方面对近10年来的女村官的研究进行评述,总结归纳农村基层权力核心结构中女性“一把手”的发展现状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女村官在村级治理中的现状
本文的女村官特指女村长或女书记。对于女村官参与村级治理的程度与现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数量上的衡量,即女村长、女书记人数所占的比例;二是女村官参与决策的影响力和质量,包括她们的实际地位、领导力评价等。女性主义政治学运用上述“数量的代表性”和“实质性代表”两方面内容考量妇女参政的程度,[1]旨在强调妇女参政不仅要有一定数量的妇女进入政治组织,这些妇女还应具备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应当代表妇女利益,积极倡导将性别平等纳入法律和政策。[2]
(一)女村官基本情况
1.女村官数量和构成
学者们一致认为,从数量上看,目前中国女性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比例还非常小,已有的统计数据显示,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仅占16%,女村委会主任、女村长更是凤毛麟角,仅占1%。[3][4][5](P122)[6]2007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后,这一数字达到了17.62%和2.71%,但依然不容乐观。[7]学者的研究调查也可以证实这一现象,即在村级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权力尖端缺损”现象。“权力尖端缺损”指的是女性参政任职高层次少,掌握实权、决策权少、正职少,女性在各级政治机构中所占比例越往上越是逐级降低,呈现出金字塔或类金字塔型参政结构,其边缘权力甚于核心权力。[8]目前农村女干部任职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闲职多、要职少。由此看来,能够走进村庄权力系统,掌握村庄优势资源的女村长、女书记目前还是一个数量极少、比较稀缺且特殊的群体。[3][9]
当选书记、村长的这些女村官们是农村妇女中的政治精英,通过学者们的调查,可以将她们的构成情况总结如下:第一,在年龄层次上以中年为主,40岁以上所占比例较高;[4][10]第二,受教育程度相较于一般农村妇女高,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4][5](P122)[11]
2.走进村庄权力中心的资本获取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女干部很多都是积极分子或者劳动模范,依靠入党等途径获取政治资源是农村妇女从“草根”走向管理者的传统路径之一。[12]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发生变革,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之下,大多数女村官们都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4][5](P121)[11][12]民主选举更看重管理者的个人管理能力和素质,这给了女村官们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机会。
通过总结女村官的权力来源,可以看出,她们走进村庄权力中心有很多一致的条件和资源因素,若没有这些过人的资源作为基础,女村官们难以在男性主导的村庄权力结构中脱颖而出。第一,女村官们从政前多从事非农产业,如村办企业管理者、小学教师、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经商)、村医等,[4]善于从事经济活动,是村里的经济能人,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素质、具有经营头脑和社会阅历;[5](P123)[6][10]正如王伊欢等所定义的农村兼性女能人就包括经济能人和政治能人兼容具备的群体。[13]第二,很多女村长、书记在担任村内核心要职之前,都担任过类似妇女主任、计生员的职务,或是担任过村两委的委员,有了与村民熟识的机会,锻炼了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并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支持。[4][5](P123)[11][14][15]第三,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娘家在本村,或者夫家是村中大姓,或者亲属、家族中具有有利的背景,如自己父母或者丈夫的家庭当中有干部、在外挣工资等,都会给女村官走入权力中心的舞台积累人脉,铺设道路。[4][5](P123)[10][16][17][18]
李琴、高涣清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以个案形式分析了在相同制度设计下两位女村官从政、执政经历差异的原因,揭示女村官通过网络建立共识,通过共识建立期望、取得权力、获得资源的行为。她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宏观社会资本即制度,中观层面包括宗族和派姓的力量、乡镇和村民偏好、妇女自组织的影响,而微观层次社会资本即人际之间的交往,比较难以衡量。[19]
徐兰兰重点关注基于“特殊主义”的关系圈而形成的“关系资本”,认为关系资本已经成为农村妇女获取村官这个稀缺性资源的一种非制度化方式。她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女村官如何成功突破以男系血缘为脉络的传统村庄运行规则,构建关系网络并形成关系资本,从而获取支持其参与村庄治理的各种资源。她得出结论,相比其他副职、虚职干部,女村长、书记这类正职村官的关系圈更多地带有“外倾”式的特点,其人际交往的对象和重点已扩展至非亲属血缘关系群体,后者构成其竞选和当选后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的主体。[16]周秀平从社会支持网络的角度得出结论,女村官要想崛起,发展的自身意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基础,家庭、家族关系、村内社会交往是前提,在半熟悉的村庄环境里,女村官村外异质化的社会交往是形成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的最终目标。[14]
3.参政动机与当选原因
了解女村官的参政动机可以剖析她们对于权力、村庄政治的认识,可以了解村级核心要职对于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想通过这个社会角色获得什么、实现什么,并且赋予这个角色什么。金一虹认为,女性管理者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想要改变女性农民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渴望“出人头地”,并获得社会的尊重和物质上的收入。[12]汪力斌等发现,“村民对自己的信任”、“为妇女争口气”以及“体现自身价值”是女村官参政的主要动机,其中村民的信任最为关键,虽然女村官们一开始并不是主动想担任村官,但她们认为村民的信任不能轻易辜负,激起了她们的责任感。[4][11]而陈福英和陈聪研究发现,女村官参与竞选主要是出于个人意愿和要求,属于自觉自主行为,单纯受他人推选或家人支持而参政的相对较少。她们从政的主要动机还有为村民服务,出于“为女人争口气”而从政的却很少。[20][10]总体来说,女村官从政的公益性和利他性心理比较强,一部分人也是出于自我价值的肯定而当村官,至于是否出于为女性同胞争口气而挑起村庄权力大梁,还存在分歧。值得肯定的是,女村官们的参政动机都比较成熟,多数皆是出于村庄利益的考虑。
因为大部分女村官都是通过民主选举胜任,所以群众基础是她们认为自己能够当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还有具有社会责任感,[4][11]无私、廉洁、正直,[4][12][20]了解人民疾苦,[20]能吃苦,可以带领人民致富以及活泼、泼辣、文化高等个人特质。[6][12][20]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相关制度和政策中对妇女参政问题有所规定,如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成员的比例、名额都有涉及。一些省市在政策中明确要求“村两委”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但一些研究显示,自认为由于国家政策支持或家族是大户人家而当选的女村官所占的比例非常少,这证明女村官更看重他人发自内心情感的支持、自己的人品以及责任感,对于国家的硬性规定或者家族背景这种策略性的东西考虑不多。关于“自身能力强”这一因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汪力斌、金一虹研究认为个人能力强是女村官成功的主要原因,而陈福英的研究发现则不同,她认为能力并不重要,女村官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才是最重要的当选原因。[4][12][20]
4.女村官执政特点
其一,一些学者首先肯定了女村官在执政中渗透的性格优势,如心思细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4][6][11][15]具有比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和观察力;[6]其二,女村官在执政中公心强、私心弱,比较廉洁;[4][5](P126)[11][20]其三,女村官为政舍得付出,实干且负责任;[5](P126)[11]其四,由于是靠民主选举取得职位,女村官比较重视民主管理、村务公开;[4][5](P126)[11]其五,女性群体意识得到提高。[11]
(二)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实际地位及影响力
对于女村官目前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状况,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都倾向于认为女村官执政的压力比较大,道路比较崎岖,会遇到一些不同程度的阻力和困难,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6][9][11][21][22]刘筱红、陈琼认为,目前的农村社会状况不利于女性进入村庄权力中心,要进入必然要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她们将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村民的关系作为3个变量,归纳出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3种不同的地位类型,即强势型地位、弱势型地位与均衡性地位,其中均衡型地位是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理想状态,但是目前还未实现。[9][21]王冬梅分析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认为从乡村社会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视野理解,女村官执政的权力系统与各种法律文本、规定出现了很大的变异。女村官执政在村务决策、村庄舆论及对村庄妇女的影响中并未体现出文本中规定的“有利于妇女的发展和提高”、“调动村庄妇女积极性”等话语,这说明外来文化与乡村本土文化的不适应,乡村固有的传统性别规范仍在制约着女村官权力的运行。[23]
女村官的执政质量有可能会出现“先天不足”的情况,有学者研究认为,很多女村官上任前村庄的条件比较落后,呈现出失序失范的状态,女性实际上是替代男性接了一个“烂摊子”。[3][5](P126)[12][21]由于性别的原因,女村官普遍对诸如出嫁女的土地问题、妇女参与选举等农村妇女问题比较关心。[5](P126)[11]但是,目前女村官还没有摆脱村务的拖累,仅仅停留在发展经济、协调邻里等事务上,脱贫致富仍是女村官最重要的责任,是村民们最大的期待,而对妇女自身的特殊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还没有提上重大日程。[11]王冬梅的研究发现,某村因为有了女村长,满足了“村委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的要求,不仅没有更加重视妇女参与选举的权利,反而取消了对妇女主任的妇代会直选。女村官执政没有冲淡农村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没有体现出有利于妇女的发展。[23]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妇女在村委会所占比例低,女村官往往是决策中的“孤家寡人”,她们所提出的代表妇女利益的建议,往往难以得到数量占大多数的男性领导者的认同,因此女村官影响力受到限制。[22]
在女村官领导力方面,高涣清、李琴认为村民自治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以及村民的参与性与自主性都适合以女性领导力为代表的“转换型领导”特征。然而,在村庄“力治”,即依靠个人能力、权力和暴力来进行治理的实际背景下,女村官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女性化”现象,她们进入乡村管理层是以牺牲自己的女性气质为代价的,女村官其实是以男性或中性领导力获得成功的。[24]刘筱红、陈琼对江西女村官的实证调查也发现,强势型女村官在男女村官的斗争中很容易倾向于男性化,采用男性策略;而弱势型女村官在男村官面前保持失语和恐慌状态,女性领导的特殊力量并没有表现出来。[9]
三、女村官参与村级治理的影响或制约因素
女村官群体数量很少,比例低,并且她们的执政道路并非顺利,领导影响力不同程度受阻,权力与性别产生冲撞,整体现状不容乐观。女村官数量的弱势更多地指向妇女参政力度不够、女村官后备军不足的问题,即走近或走进村庄治理的妇女数量少,是以广大农村妇女或“村两委”班子妇女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而在任女村官影响力受阻的原因则更倾向女书记、女村长执政之中的实际困难,是成功走进权力核心圈子之后面临的种种考验,这是两个既不相同又有联系的问题,应该区别考虑。因本文研究对象为女村官而非广义的农村妇女,因此主要综述女村官执政质量受制约的因素,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文化因素,第二是制度政策因素,第三是女村官自身素质因素。
(一)社会文化因素
研究者发现,综合心理素质对领导力的影响在两性的差异上并不显著,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女性领导者的晋升与发展往往具有不利影响。[20]
长期以来,有效的管理被描述为带有支配性、侵略性的男性形象而非女性形象,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经常被看作是无能力的。[26]传统性别观念是阻碍女村官执政与发展的主要原因。[3][4][5](PP123-125)[6][11][20][24]传统的性别观念建立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制下,把男女生理上的差异演化为“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女人被划分在私人领域,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更谈不上政治地位。在当今农村,男人掌权的观念以及父权文化的角色期待还比较浓厚。有学者认为,人们对权力的理解与文化中对女性的定义是相悖的,[5](P124)这种冲突一方面会导致村民不认可女村官的治理,尤其是其他男干部持偏见态度,排斥女村官,不支持女性领导的工作,也可能带来女村官家人的不理解。[4][5](P124)[11][20][27][10]另一方面,高涣清等认为,这种“历史劣势”的积累不仅影响着社会对妇女价值的评判,还影响到妇女自身的价值观念、成就动机、审美情趣等,导致了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并且,“历史劣势”使得女村官在执政时没有底气,“理性”地选择了“去女性化”。[24]也有学者认为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使女村官缺乏村内的社会资本积累,外籍女村官在工作时不太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可与支持,执政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19][20]
此外,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妇女没有职业这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再加上“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深入人心,妇女家务、田间农活负担比较重,女村官更是要“两头挑”,既要管理村庄事务,也要承担家务农活,承受事业与家庭两方面的压力,力不从心,这就产生了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4][5](P124)[11][28]
陈丽琴通过调查得出,农村公共空间呈现出萎缩的现状,这会导致女性难以凝聚广泛的社会资本和人际脉络,缩小了她们的信息来源渠道,使女性展示自身的舞台缩小。这种执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女村官的工作开展和发展道路。[29]
王冬梅认为,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别规则不发生改变,女村官权力的运作就难以摆脱传统的窠臼。在正式制度中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存在很大局限性的情况下,如果再不考虑文化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文化变迁过程的复杂性,而一味地靠强制措施自上而下地推行制度,就会出现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标相背离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23]
(二)制度政策因素
有学者认为,由于村委会选举程序的不规范,增加了女村官执政的困难。女村官的竞争对手失利后,往往会对女村官的执政怀有抵触情绪,在工作中进行刁难、不合作。[4][9]另外,相关制度和法律缺乏刚性,如《村委会组织法》第九条提出,“村委会成员中,妇女应有适当的名额……”,“应当”表达了一种建议性语气,法律效力不强。对于该政策,可被解读为无女性成员、只有一名女性成员或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30]由此可能导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的比例低,从而使得女村官进行决策时比较孤立,支持者少。[3][4][31]再者,女村官的收入较低,这既是她们执政的现状也是阻碍她们发展的原因之一。[4]也有学者把导致女村官“去女性化”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性别平等”制度的异化现象。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一种符合“集体理性”的制度安排,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提供的是一种机会平等,并没有考虑到“差别化”,没有体现“差别原则”,并非符合村级治理中女村官的个人理性。[24]陈聪研究发现,由于村级职务管理不规范,女村官往往身兼数职,多兼任妇女主任、计生工作,任务繁重、精力透支,不利于执政的效率和质量。[10]
(三)妇女自身素质因素
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文化素质不足、个人能力不够是制约女村官执政与发展的因素。[4][6][11][30]虽然女村官的教育水平相较于普通农村妇女高,但整体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大多数女村官没有学过管理方面的知识,因而执政能力受限。[4]还有观点认为女性的体力比男性弱,在生理身体素质上弱于男性。[6]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女村官领导力的特点不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社会造就的,是可以改变的,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在分析造成妇女自身素质偏低的原因时,多数研究者都能够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认为妇女表现出的对政治的冷漠以及能力上的缺憾并非天生的,而是整个社会文化传统、体制、资源以及村落的具体背景造就的。[28]
四、改善女村官从政现状的对策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文化、制度、经济、女村官自身素质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或对策,也有学者从领导方式、社会资本及关系资本的获取角度提出建议,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应加强社会性别立场的宣传矫正,鼓励女村官从政。[3][4][6][23[24]政府各级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各界应该积极宣传正确的性别观念,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为女村官的执政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支持。
第二,对女村官给予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健全有关农村妇女参政的法律、制度,加强制度的刚性,保证和加大村委会中女性的比例。[3][4][23]村级妇女利益诉求的传递须依托于妇女参政比例的扩大,尤其是进入“权力尖端”的妇女比例的扩大。如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有关妇女进入委员会的比例的规定比以往更具刚性,将以往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的内容改为“应当有妇女成员”的规定。“应当”二字在语序上的提前,强调了妇女进入村委会的必要性;而将“适当名额”改为“妇女成员”,也有利于防止在操作中限定妇女进入村委会的人数。[22]《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将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30%以上,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达到10%以上列为主要目标。这些政策都有利于未来女村官的决策执政,而且,要使农村妇女参政的法律政策得以实施,不受乡土文化中各种非正式规则的干扰而显示其权威性,那么农村基层妇联组织的密切关注和监督就是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23]
第三,有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从政女性的优势,在工作中有的放矢,扬长避短。[6]另一种观点认为,面对村治的复杂现实和力治的需要,领导方式的“中性化”是两种社会性别的“优势叠加”,是村级女干部的“理性选择”。[24]
第四,研究者认为,要改善农村女性从政现状,需积极发展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如食品加工业、商品零售业、社区家政服务业等,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参与社会事务、政务管理的意识、要求才会提高,政治地位也会随之提高。[4][6]王伊欢等认为,农村女性兼性能人的意义会呈现出政治兼其他方面的几何累积效应,这些女性由于经济或文化等其他方面的突出表现而树立威信,在政治领域的地位的话语权也多于纯粹的政治能人,政治权威也因此提升。[13]
第五,李琴等针对女村官社会资本的获得提出了4种策略,即在关系资本的基础上构建制度资本、在制度资本的基础上构建关系资本、没有关系资本的制度资本的建构以及没有制度资本的关系资本的建构。[19]徐兰兰也强调了关系资本的重要性,提出,各种对于妇女参政的保护性的政策和法律,只有作用于拓宽农村妇女社会关系网络和培育关系资本这一平台,方能真正落到实处。[16]
第六,对于女村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培训的对策。[3][4][6][11]一方面,培训是提高女村官执政素质、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公仆意识的有效途径;[11]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促进农村妇女参政、提升她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为女村官培养后备军的作用。[4][11]
第七,有学者强调参与式社区发展理念与方法对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意义,认为很多来源于海外投资援助机构的项目和当地妇联协同,通过一系列参与式发展的实践,如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当地官员、村民培训,部署女性社区领导等,用参与式和性别敏感的方法去思考治理,给农村妇女赋权,提升了她们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32]
五、对研究现状的评价与展望
(一)研究现状评论
虽然女书记、女村长的数量极少,全国83万个行政村中仅占约2%,但却是成功走入村级权力中心的精英者代表,是一个非常容易忽视却值得关注的特殊群体。女村官是村民自治的产物,是对父权中心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它的发展关系到妇女参政的程度,影响村民自治的代表性和民主进程,目前学术界对于女村官的研究在数量、深度和学者的关注度方面都滞后于对广义妇女参政的研究。
1.一些研究缺乏理论深度
女村官研究较多、较成熟的主要是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女权主义是研究妇女参政的理论基础,社会性别理论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意在揭示社会传统是如何塑造和规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有关女村官的很多研究都渗透了社会性别这一视角。[3][6][15][11][21][23][33][34]但问题是只限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对于理论本身的探讨不够,理论建树不多,特别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背景和农村女性参政的特点进行理论总结还实属少见。
2.调查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
女村官研究中实证调查很多,但其中一些研究比较简单,没有深入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大多数研究都是个案调查,缺乏系统和规范的阐释,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提升。如,有的研究者借助于类似“全国百位女村官论坛”等会议的机会对全国范围的女村官进行调查,调查的数据对于说明全国女村官的现状缺少代表性;一些女村官现状调查研究仅使用单变量描述分析,缺乏对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3.研究对象未进行细分
一些研究者对于“女村官”的概念使用混杂,没有清晰的定义和规范,往往会与“村两委”女性委员、妇女主任、计生员、女大学生村官等广义上的女村干部混淆在一起,或者直接用农村妇女加以分析,不少研究未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分。实际上,女村长或书记处在村级权力的核心要职,无论是其在村庄治理中的地位、其所承担的职责,还是政治参与的程度都与一般女村干部有区别,其现状、领导力和发展阻碍也不尽相同。比如妇女主任同样是女村干部,却处在虚职职位,位于村庄权力的边缘地带,决策地位不明显,她们的参政意识、行为特点和发展轨迹肯定不同于掌握实权的女村长,如笼统地放在一起分析则会忽略很多问题。
(二)今后研究中的重点关注
1.结合三农发展新趋势探讨女村官问题
如果抛开三农的新的发展趋势或者农村妇女的普遍问题来谈女村官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农业女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有数据显示,2001年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1%,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化滞后于男性,是否会对女村官的执政带来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其中以男性群体居多,由此产生了留守妇女这个新农村弱势群体。白南生以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为基数,推算出目前中国留守妇女人数已经达到4700万人左右。[35](P49)当女村官面临村中的留守人群,特别是留守妇女,如何发挥其女性领导者的优势,如何组织和发展这个群体,保障妇女的利益?如果女村官本身就是留守妇女,那么她又如何解决家庭婚姻问题,如何平衡角色间的冲突?
2.进一步细分研究对象
担任村长、书记的女村官是农村妇女里的精英,事实上农村妇女精英有3个类型,第一是徘徊在村庄权力圈子之外的农村妇女精英;第二是走进权力圈并有可能向权力核心靠拢的女村委委员,如妇女主任;第三是处于权力舞台中心的女书记、村长。要更好地研究处于权力中心的女村官,就应将研究对象细分,从这3个类型着手研究。关注在“村两委”中的妇女主任或负责妇女、计生的女干部,她们是最直接的后备军,这些人最有可能进一步走进村庄权力中心,而其他的农村女性精英也是女村官后备队伍,了解她们的参政意愿,挖掘阻碍她们进一步成为村庄核心干部的困难和诉求,有助于在总体上提高对村庄治理中的妇女参政的认识,让更多的农村妇女走向参政的道路。
3.注重质性方法的应用
有学者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尤其适合女性主义的研究目标,可以使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不是分离的和等级关系的,而是以整合的、同情的、平等的甚至合作的关系形式为特征。[36][37]个人口述史就是一个值得运用的方法,女权主义者主张不仅要由妇女来做研究,做有关妇女的研究和为妇女而研究,而且要和妇女一起研究。[38]从这个角度看,口述史作为一种自下而上、以被研究者为主体的方法,不仅是一种研究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手段。采用口述史的方式,可以肯定妇女的经历,增加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妇女。[38]因此,运用口述史等方法可以令我们纵观女村官的从政经历和内心真实感受,赋予她们更强的信心,并结合社会背景,加深研究者对农村妇女从政的主观认识。
4.进行一系列比较研究
为了使女村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有说服力,可以进行一系列比较研究。如女村官与男村官治理对村庄产生的不同影响;女村官与城市妇女领导在领导力和执政特点上的异同;女村官执政前后对村庄三农发展产生的影响;等等。可以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以是否是女村官执政为变量构建自然实验中的关键变量,分析其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探讨女村官的影响力和领导特点。
[1]Philips,Anne.The Politicsof Presence[A].王金玲,高小贤编.妇女发展蓝皮书 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4妇女与农村基层治理[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Dodson,Debra L..The Impact of Women in Congress[A].王金玲,高小贤编.妇女发展蓝皮书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4妇女与农村基层治理[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郑彩华.将性别视角纳入农村基层政治改革与发展[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9).
[4]汪力斌.女村官参政执政的过程、特点、困难分析[J].农村经济,2007,(11).
[5]宋美娅.女村官,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的光荣与困境[A].谢丽华,宋美娅编.女村官传奇[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6]左小川.论村级治理中的女性身影——湖南省岳阳地区“女村官”现状调查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0).
[7]陈至立.在全国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实践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J].中国妇运,2009,(7).
[8]辇雪妮.中国妇女参政中“权力尖端缺损”现象的成因与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09
[9]刘筱红陈琼.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5,(1).
[10]陈聪.新上岗女村官的政治参与行为分析——基于福建省女村官的实证调查[J],江西青年职业学校学报,2008,(1).
[11]任杰.全国百名女村官调查报告:社会性别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07,(4).
[12]金一虹.从“草根”阶层到乡村管理者——50例农村女性管理者成长个案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2,(6).
[13]王伊欢,张亚娟.农村女性能人对于社区发展的多元意义——30例农村女性能人个案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9,(4).
[14]周秀平周学军.社会支持网络与农村妇女发展——女村长与村落发展的案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1).
[15]毛先春.女村官领导力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三门县为例[D].华东政法大学,2011.
[16]徐兰兰.关系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参政执政思考——基于广东省潮汕地区女村官的个案研究[J].南方农村,2012,(4).
[17]仝雪,屈锡华.中国基层农村妇女干部现状分析——以河南省南阳市郭滩镇毕店镇妇女干部状况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05,(11).
[18]李慧英,田晓红.制约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相关因素的分析——村委会直选与妇女参政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2).
[19]李琴高涣清.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女村官:同途何故殊归?[J].晋阳学刊,2010,(5).
[20]陈福英.性别视角透视下的女村官政治参与——基于福建省的实证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2).
[21]陈琼.村庄治理中的女村官研究——以江西三个村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5.
[22]杜洁.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行动与研究[A].王金玲,高小贤编.妇女发展蓝皮书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4妇女与农村基层治理[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3]王冬梅.村落文化视野中“女村官“执政的反思——以河北H村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0,(4).
[24]高涣清,李琴.村级女干部的“去女性化”:性别、社会性别和领导力[J].妇女研究论丛,2011,(1).
[25]Wen-Dong Li,Richard D.Arvey,Zhaoli Song.The Influenceof General Mental Ability,Self-esteem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on Leadership Role Occupancy and Leaderadvancement: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1,22(3).
[26]Eagly,A.H.,&Karau,S.J..Role Congruity Theory of Prejudice toward Female Leaders[A].Psychological Review,2002,109(3).
[27]郑憬函.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领导力研究[J].学理论,2009,(14).
[28]唐华容.农村妇女参政不足的自身成因分析——以湖南维新村为个案[J].管理观念,2009,(4).
[29]陈丽琴.农村公共空间的退缩与女性的政治参与——对湖北省S村公共空间的分析与思考[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3).
[30]杜洁.以研究促进政策和法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与法律/政策项目的探索[J].妇女研究论丛,2006,(S2).
[31]刘筱红.支持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公共政策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2).
[32]Tamara Jacka.Women's Activism,Overseas Funde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and Governance:A Case Study From China[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10,(33).
[33]王金玲,高小贤编.妇女发展蓝皮书 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4妇女与农村基层治理[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4]付红梅.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4).
[35]叶敬忠,吴惠芳等.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6]Mies,Maria.Towardsa Methodology for Feminist Research[A].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J].社会学研究,2003,(1).
[37]Reinharz,Shulamit.Experiential Analysis:A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A].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J].社会学研究,2003,(1).
[38]鲍晓兰.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与思考[J].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1).
——参政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