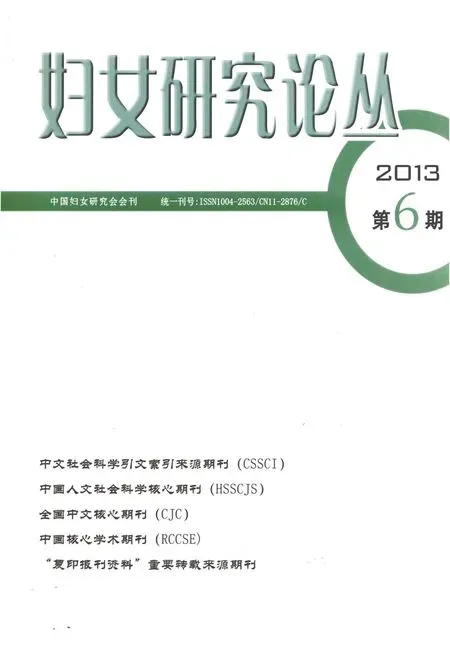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利的实践逻辑:南宁“出嫁女”案例研究
王晓莉李慧英
(1.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 100084;2.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问题的提出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后,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份文件《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掀起了中国妇女组织推动各级政府实施男女平等的高潮。男女平等的条款纷纷被写进相关法律中,包括《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以家庭(“户”)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方式得以恢复,妇女参与生产劳动重新回归到家庭的私人领域。在实践中,妇女因婚姻关系变动(出嫁、离异、丧偶等)而失地的情况一再发生,特别是土地第一轮承包(15年不变)以来,婚后妇女需等待若干年甚至始终得不到重新分配土地的情况时有发生;[1]第二轮承包实施之后(30年不变),这一现象变得十分普遍。[2][3]
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农地征用和土地股份合作等趋势加剧,土地的权属和经营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个体的土地权利再度引起关注。妇女在流转中的决策权受损,往往被家庭父权制下的“户”所掩盖,未能引起妇女自身足够的重视。而农地征用和土地股份合作是将土地由实物物权变为补偿或股权,在村或组集体层面进行以“个人”为单位重新分配。出嫁、离婚或丧偶的妇女(下文简称“农嫁女”①这里采用官方文件中的概念,主要是农村出嫁、离婚、丧偶的妇女,俗称“农嫁女”,也包括未婚且未离开农村的大龄女青年和入赘女婿等群体,见李建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0年5月。)由于脱离了稳定的婚姻关系,她们的土地权利在集体层面显化了。2000年,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损情况是9.2%,到了2010年则达到了21%,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10年间,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加速发展,并没有解决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损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全国妇联对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对“农嫁非”妇女,46%的村集体不给宅基地,35%的村集体不给承包田,38.5%和35.4%的村集体分别在土地补偿费和土地分红方面不予相应的村民待遇。目前多数法院不受理此类纠纷,“出嫁女”只能靠上访维权。2012年全国妇联系统受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投诉9970件次,比上年增长16.8%,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土地征用补偿分配阶段。妇女维权上访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维稳压力,耗资巨大,且得不到有效解决。权利的性别冲突从私领域转到了公领域,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农嫁女”群体的维权抗争。目前对于涉及妇女土地权益受侵的案件,绝大多数地区的法院拒绝受理,上访成了“农嫁女”维护土地权益的主要行政途径。[4](PP10-14)
自90年代起,以土地股份改革试验区广东为代表的“出嫁女”群体就开始持续不断进行维权上访,并促使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如南海、东莞、深圳的宝安区、龙岗区、惠州等地。但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此前研究多强化妇女作为被动受害者的角色,[5]且将妇女视为同质性群体。根据与男性的从属关系,本研究将“妇女”划分为两类集合性主体:一方为男性的妻女、母亲,另一方是男性的姐妹群体。只要婚姻关系稳定,前者的土地权利就可以依附于男性而得到保障;而后者一旦出嫁或者前者一旦婚姻关系发生破裂,她们即摆脱了(原)家庭中的依附关系,未建立新的家庭或者在新家庭中无法依靠男性重新获得土地权利,成为了土地权利受损最为普遍的群体。轰动全国的南宁“出嫁女”即属于后者,在涉及征地侵权的过程中,她们不但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且成功影响了当地决策,促使政府商讨解决方案,为全国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树立了典型。本文基于2013年2-3月笔者在南宁经开区实地调研的访谈资料,阐述征地过程中“出嫁女”合法土地权利遭遇全面剥夺的实践逻辑,力图动态揭示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后果与解决思路。
二、征地过程中妇女土地权利的实践逻辑
(一)事件的缘起
南宁市经开区成立于1992年,2001年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至2012年,经开区辖区面积504平方公里,下辖1个镇、2个街道、22个村和5个社区,人口约2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5万人。2005年经开区获批3000亩项目用地指标,其中包括那历村“整村征地”的2600亩。2005年征地前,那历村村民的经济收入以农业为主,村集体没有企业和土地收入,妇女对土地收益分配的个人权益从属于家庭,没有专门的个体利益要求。征地后,补偿安置费为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平均一个5口之家可获得补偿费120万元,另有“一户一宅”式宅基地安置的租金收入(人均年收入约3500元)和分红收入。据现任村支书介绍,“别的村都眼红了,盼着政府去征他们的地”。
2005年征地时,那历村有20名未迁出户口的“出嫁女”,主要是“农嫁非”户口无法迁出或是嫁到条件较差的外地农村不愿转户的妇女。1981年分包到户之际,时为“未嫁女”的她们都获得了生产队的承包地。婚后,只有二组依照“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的一般原则,按传统习俗将“出嫁女”的土地收回,但并没有书面记录。她们有的靠在外打工,有的靠耕种村里的开荒地维持生计。村民延续解放前的宅基地划线“老宅地不可侵”,并且认为“出嫁女”与娘家一起住会“克娘家”、“断子绝孙”、“带来霉运”。2000年后,已经生儿育女的“出嫁女”在外居住困难,有7户回到父母的开荒地建房。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征地和随之产生的经济收益,也没有在事实上产生利益纠纷。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快,那历村被卷入其中,征地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带来了纠纷。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涉及村民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和分配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这些“出嫁女”虽保持村民身份,但按习俗从未被通知参加本村的村民会议,当然也被排除在分配方案的名单之外。村干部的看法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并将这一决定诉诸集体同意而合法化。村民否认“出嫁女”的合法村民资格,实质在于少一人则自己能多分一份。其理由包括:“出嫁女”要么没有承包地,要么在外打工而没有耕种其承包地;“出嫁女”并未在本村居住,不算村内的常住人口;“出嫁女”没有履行村民义务,并未参与村集体集资,如教育附加费、维修道路水利的集资等。而这条理由恰恰利用了南宁市政府办[2003]150号文[6]的规定:“出嫁女”及其子女的户口仍在原村,但居住地不在原村又没有履行村民义务的,其待遇由村民会议确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国家法律政策相抵触,如有违反,由乡镇政府责令改正。经开区政府认为,那历村的分配方案不包括“出嫁女”明显违反政策,不予以审批,并决定扣留那历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两天后,80多名村民围攻镇政府。按照规定,经过村民会议决定的分配方案,政府没有审批权,也无权扣留补偿款。镇综治办迫于群众压力,发放了补偿款。事后,“出嫁女”请求镇政府到生产队主持调解会议。镇妇联主席受委派前往二队主持调解会议。会前一日,队长说,“谁同意给出嫁女分,就不给分你们的钱”。会上,妇联主席还未把有关政策法规宣读完,场面就开始乱了,村民指着她说,“你读的什么东西,你干嘛不把你的工资分给她们,反而帮她们回来争我们的钱”。有的甚至还想厮打参与开会的“出嫁女”,妇联主席手臂也被群众抓伤。村民大会表决通过“本村所有出嫁女不论户口是否在本组,一律不得参加本村的土地资金财产及各种利益的集体分配”。
(二)事件的进展与结果
为争取自己的权益,那历村的“出嫁女”组成了一个上访集体,6年间连续12次进京上访。与此同时,为维稳需要,经开区政府6年总投入近300万元,遭自治区政府3次通报,2次亮起平安建设的“黄牌”警告。“出嫁女”进京上访的次数之多使得经开区更换了领导。新领导上任后,提出“维权就是维稳”,他亲切的态度和冒雨去家访等做法让出嫁女对政府解决问题重新恢复了信心。
新领导上任后,首先改变过去的维稳思路,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是维稳”。并采取相应措施,使这一新的工作思路在经开区和街道办两级政府中得到贯彻执行,使得出嫁女问题在村队两级得到调节。第二,与出嫁女建立平等、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书记上任后的第四天就接见了出嫁女,承诺一定处理解决好问题,并留下手机号和家庭电话号码,出嫁女感动得当场落泪。第三,将“矛盾”或“问题”正确分类。按照户口、土地和居住情况等将出嫁女分为5类,逐户排查出嫁女在夫家落户及享受待遇的情况,缩小了出嫁女群体的范围,减轻了压力。第四,在与村队协商方面,采用“干部对干部”而非过去“干部对群众”的策略,有效避免了干部直接卷入冲突的尴尬局面。第五,真正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敢做敢为。新任书记反复对干部强调,要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不以逐利为驱动。书记亲自参加出嫁女公寓的奠基仪式,并带领出嫁女去外地参观养殖场,为出嫁女迈向新阶段的生活提供扶持和机会。
经街道办政府与村队协商,最终形成协议:一是村委会提供给出嫁女44平方米的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式建筑,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二是按照户籍人口情况为出嫁女提供自谋职业补助,即子女包含在内(一队标准是2.5万元/人,二队标准是3万元/人);三是鉴于当前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出嫁女可保留依法解决征地安置补助费的权利。同时要求,出嫁女不能再为土地安置补助费等问题上访。出嫁女考虑到毕竟政府为她们保留了走法律途径的权利,加之她们深为新任领导态度的改变所感动,同意“放弃上访”的条款,也接受了不能与村民享有同等待遇的现实,“毕竟走了6年上访路,我们也想回归正常生活”。在南宁市经开区政府新任领导班子的积极干预下,全区184名出嫁女的合法土地权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
三、讨论与建议
“出嫁女”土地权益问题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出现的农村集体成员内部利益分配问题,这一传统习俗和现代法制的矛盾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将越来越突出。现有的政策法规在制度上保障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中办厅字[2001]9号)等一系列政策法规,都强调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农村妇女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并对出嫁、离婚、丧偶等妇女群体的土地权益作出具体规定。但传统习俗加村民自治却使其不能落实。受传统习俗影响,农村社区通常以父系家庭为中心,村民代表大会这种民主管理的现代方式在涉及村庄内部利益分配时反而会强化宗族和父权话语权,导致妇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并使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方案显得合情合理。基层政府难以纠正村规民约中的违法规定。涉及村庄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以村民会议形式进行“民主决策”,一旦其产生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基层政府责令改正通常会变得无效和被动,甚至会激起农民的围攻和反抗。这也是“出嫁女”合法诉求难以解决所面临的传统和现代冲突的两难境地。
(一)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下,征地带来了“性别化”的身份认定,“出嫁女”的成员权在村、组集体层面遭否定
农耕社会“父系—夫居—养儿—儿养”一系列的血脉、姓氏、资源和财富的男系继承,[7]以及与之相应的婚丧嫁娶习俗,形成了一套不平等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出嫁女”并未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资源分配规则,村、组干部口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代表了村庄层面的主流性别话语。征地补偿收益权在村组集体层面的再分配,同样维护了父系为中心的财产和土地收益权、继承权等。[8]土地补偿费按照政策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那历村按照“村民表决”的名单实行人均分配,将“出嫁女”及其子女完全排除在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由政府直接补偿到农户账户,“出嫁女”的个体收益权又一次被归于父母“户”下。安置补助费各组按“一户一宅”式标准集体建设回迁房,“出嫁女”被集体排除在外。
(二)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表决”的决策程度为土地权利的性别化提供了一个合法化的条件
对“出嫁女”性别化的身份认定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得以合法化,它反映了一种公共权力,其核心在于将脱离了婚姻依附关系的女性排斥在村庄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之外,维护了传统农耕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度。村队干部和村民借以否认“出嫁女”合法村民资格的三条理由:一是“没有或没有耕种其承包地”,实际情况是,生产队按照“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的原则,将“出嫁女”的承包地非法收回;二是“在娘家村没有宅基地”,其实是,村民以“克娘家”、“断子绝孙”、“带来霉运”等传统性别不平等观念为由反对出嫁女在村内居住。“祖业权”也在挑战着国家土地政策的实践;[9]三是“没有履行村民义务”,事实上,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就村民义务作出具体规定,村民义务主要表现为承包土地上的义务及其他方面的义务。从1985年“劳动积累工”的取消到2006年“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村民义务集中在承包土地和政治参与方面。出嫁女从未被通知参加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会议,其结果是,更加固化了村民的性别不平等观念,淡化了村民的法治意识。
(三)基层政府难以纠正村规民约中的违法规定,且其维稳的政绩压力大于事关妇女维权的问责压力
首先,涉及村庄内部的征地补偿利益分配,以村民会议的形式进行“民主决策”,摆脱不了村庄既有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缺乏基层政府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缺乏弱势妇女代表的参加,迫于来自强势利益集团或宗族势力的压力,村民会议可能会产生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村规民约。而非法决定一旦产生,基层政府再责令改正则通常变得被动、无效,甚至激起多数群体的围攻或反抗。其次,当前法律政策多没有明确问责主体、问责程序和追究方式等,基层政府并没有面临来自“妇女维权”的问责政绩压力。那历出嫁女进京上访的次数之多、频率之大,造成了地方政府“维稳”的政绩压力。“自上而下”的上访路线迫使问题的责任主体由街道办(乡镇级政府)升为经开区管委会(县级政府),迫使经开区更换第一责任人,使得问题获得了“领导式”的处理方案,而非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途径和村规民约的完善来解决,且多数情况下,出嫁女最终仍不能获得同等村民待遇。类似的案例还有广东南海、[10]安徽霍邱[11]等。
“出嫁女”土地维权的有效长效解决,既需要从国家的整体制度安排层面进行推动,也需要逐步改变村庄(社区)层面传统的父权制规则与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为此建议:
第一,加强性别平等意识教育。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在农业和农村能力建设的培训中纳入性别平等内容,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妇女团体为农村妇女维权提供法律援助和制度化支持。重视组建妇女组织和开展妇女能力建设培训,提升她们的权利意识与改变自身从属地位的能力。推选特殊妇女群体作为村民代表,强化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第二,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规标准。确定“个人”的权利主体地位,保证征地补偿机制中的性别平等,保护妇女土地权利的独立性。对外嫁、离婚、丧偶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明确的规定,保障土地等集体经济利益分配时在村庄内部的公平性,并充分保障妇女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第三,强化对村规民约的法律约束。从土地权益入手,加强法制教育,树立婚嫁自由、婚居自由等体现性别平等的新观念,切实改变男娶女嫁的传统资源分配规则。废除与《物权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相抵触的性别不平等条款。保障基层政府对违反法律政策的村规民约的纠错强制力,将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相结合,强调在协商民主程序中,发挥基层政府的引导作用,宣传性别平等观念,引导村民依法自治。
[1]Yang Liand Yin-sheng Xi.Married Women’s Rights to Land in China’s Traditional Farming Areas[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6,15(49).
[2]张林秀,刘承芳.从性别视角看中国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公平问题——对全国1199个农户和2459个村的实证调查[J].现代经济探讨,2005,(10).
[3]钱文荣,毛迎春.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5).
[4]张笑寒.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问题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2,26(6).
[5]Sargeson S..Women's Property,Women's Agency in China's'New Enclosure Movement':Evidencefrom Zhejiang[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8,39(4).
[6]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妇联、市农业局、市民政局关于切实维护我市农村出嫁女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Z].南府办[2003]150号文.
[7]李慧英,杜芳琴,梁军.将性别平等纳入村规民约之中——怎样修订村规民约[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8]李慧英.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2,(2).
[9]陈锋.“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10]出嫁女权益保护如何突破重围[N].中国妇女报,2009-07-30.
[11]21年,出嫁女的土地之争[N].中国妇女报,2010-11-20.
[12]杜芳琴.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J].浙江学刊,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