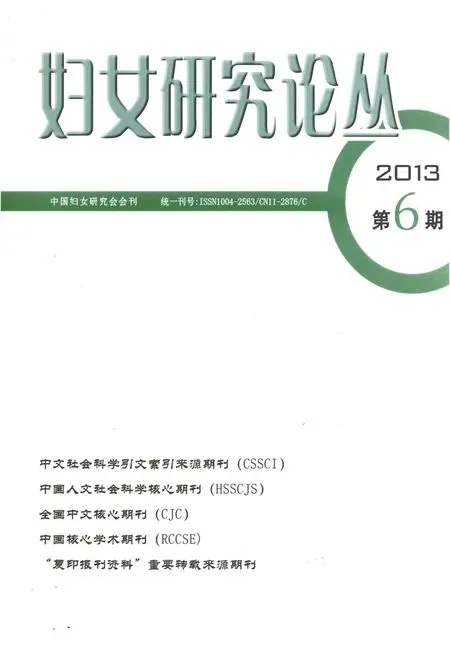性别与伦理*:重写差异、身体与语言
王楠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北京 100875)
性别是当代思想界的一面利剑。作为一种学术视角,性别研究中有关伦理向度的思考一直承载和刷新着几乎所有学科的不同层面。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对性别的思考采取理论“介入”的姿态,试图改写理性、言语、行为的惯性思维,在“生命于何处存在”这个基本伦理问题上,开启了因身体的物质性差异而引发的人类理性的讨论,包括关于语言、文化、社会和知识体系的讨论。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性的政治谱系学式的考证所示,在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视角下,生命已成为权力和知识干预的客体。思考性别也成了人类自我反思的一种方式,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伦理学母题,其中充满了困惑和矛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诸多学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奉行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立场,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盲视”。它或者坚守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术本位,排斥、贬抑乃至无视女性的视角、经验与价值;或者固守男性优势地位的假定,断言女性弱于男性,宣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是有益的或适宜的,排除女性能够成为“知识主体”的可能性。为了跳出学术研究中男性偏好的藩篱,当代诸多女性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性别”这一研究变量的引入和强调,来发出女性自己的不同声音,建构女性自身的理论话语,从而一改诸多学科中所存在的那种视男性及其相关议题为唯一正统与标准的偏狭。①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莲·肖沃尔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审西方文学价值观的“经典化”过程。她发现女性被排除在“知识主体”之外,女性被视作伦理的“他者”,而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接受、传播和延续男性至上的“思想基因”,诸如“才智”、“精神”、“强壮”和“抽象”。但是“铁板一块”的女性主义批评仍停留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里,追求差异并不能在平等地拥有根本善的这个概念上有突破。
同其他学科一样,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也引入性别的视角,拆解差异、重构身体和重置主体,打开了后结构主义视域内性别的伦理维度。拆解性别差异对二元对立的性别界线的超越,是我们对自身的新认识,即认识到自己是“被生产”和“被虚构”的文化产品,也是我们挑战人文科学中的伦理推理惯性的契机。而认识到性别是给定的物理身份,身体对这个身份提出的限制性条件使得身体成为伦理问题。同时对身体物质的认识引发了身体与历史、身体与权力、身体与文化实践的复杂纠葛。纠葛之一便是如何“接受”一个性别,如何“引用”这个性别,以及如何“成为”权力的行为主体。本文以性别伦理的核心问题——差异、身体和语言的晚近理论为中心,探讨性别研究中的伦理介入力量和透视效应,打开性别的边界,理解人性的善,以便促进人类接近认识自我的可能性。
一、重写差异
当福柯提出“为何19世纪末之前,男性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之后,性别成了“问题”。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做男人和做女人有何不同,为何不同,如何不同?是什么使得男性和女性能共同生活、相互交流,建立关系的?怎样在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之间区分性与性别?男女有“别”的身体在社会中究竟以何种样态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身体又如何促进了文化的形成和规制?
女权运动第三波之初,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的性别差异说就遭受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诟病。她所强调的性别二元对立学说因为划界的随意性和对女性主义内部差异的忽视成为批评的靶子。②女性主义第三波强调去性别化的政治主张,从语言、行为主体和身体的哲学思考维度提出反性别本质主义的策略,同时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因为性取向、种族、阶级、少数族裔和国别等差异,提出反对“铁板一块”的女性内部的霸权倾向。经典论述见Judith Butler.The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Routledge,(1990)1999;Monique Wittig.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C].Boston:Beacon Press Books,1992;Diana Fuss.Essentially Speaking:Feminism,Nature and Difference[M].London:Routledge,1990;Elizabeth V.Spelman.Inessential Woman: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M].Boston:Beacon Press Books,1988.21世纪,伊利格瑞坚持差异的性别主张,但是,她将两性看作并非对等的两极,而是考察认识论意义上的性别化差异(sexuatedifference)背后的伦理关系。[1](PP2-8)伊利格瑞认为女性和男性不能表达成对等的公式,并不是因为两性之间不平等,而是两性所代表的两极没有可以相互衡量的内容和方法。因为,女性“并非只有一种性。她至少有两种性,但不能把它们看作分开的两个。她的性征至少总是双重的,其实是多元的”。[2](P215)伊利格瑞实际上在彰显女性性征的多元性。“她”总是多于或少于“他”,或是总是身处别处,不可比。因为“他”是通过“她”的多重性和不在场,经由“他”自我授权的等式内,得以确定。所以,伊利格瑞论述的“她”拒绝设定的“等式”或常规,因为一旦跳入这个性别矩阵,作为他者的“她”就会被除名或丧失标注自我“异他性”的差异。伊利格瑞在《此性非一》(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之后,将有关性别差异批评的触角延伸为“两个人的伦理”(The Ethicsof the Couple)。这里的两个人并非仅仅指男性与女性,而是性别化之后作为行为主体的两个人,内涵包括异性恋的两者、同性爱的两者、母女、父子,外延可以涵盖跨文化、跨种族、跨宗教的两者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伊利格瑞认为两性所构成的家庭并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因为家庭中的两性(“丈夫—妻子”)是以“从属”或“屈从”为基础而维系的不平等关系,构成公民社会基点的应该是有着平等诉求的“公民—公民”关系,是以“我们”互称而形成的共同体,是以自身生物性差别而区分的两种生命形式的平等伦理吁求。伊利格瑞仍然立足于差异的生命体,但是延伸生理性的男女差异,而吸纳关于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lived beings)的公民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公民关系,才能维护和保护人类的身份和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共处”。[3](P65)伊利格瑞延伸了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首先提出的“变成女性”的性别政治,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作为公民的女性的伦理主体意识,呼吁经过性别选择的(sexed)“两个人”的公民伦理理想。
到21世纪,关于性别差异,伊利格瑞研究的焦点不再关注性别术语、二元对立或性别化文本问题的探讨。重新诠释“性别差异”对伊利格瑞来说,是将性别差异转化为“两个人的性别伦理”,从关于差异的概念出发,转向指涉性别关系背后更为深刻的知识的本质、起源和范围的哲学思考。伊利格瑞重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将她对性别的伦理思考带入考察黑格尔关于古希腊社会中人对自我认识的文化理解力问题。黑格尔对文化的现代解释产生过重要影响。黑格尔认为,当人类行为主体满足物质生活需求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的第一本质。当人发展为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时,行为主体的第二本质——对文化的表达得以产生。所以,伊利格瑞看到“历史是滋养第二本质的土壤,使得第二个本质生长:关于文化的、精神的本质,这个本质显然超越了自然的第一本质”。[4](P133)这个“历史的土壤”培育出,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公民的社会。但是这个“公民的社会”使得人性的第二本质消隐,因为公民认同于不可置疑的普遍外在世界规律,结果性别一元论的伦理制度在传统哲学体系中不胫而走。在对文化的表达中,男性的精神是征服自然、克服自然的主体,文化因此被解释为男性所创造的历史产物。男性是为文化与道德而造,女性无法获得。男性学着在社会生产和交换制度中工作,女性在家庭和婚姻制度中被教育履行社会职能和生育实践。女人从未获得第二本质,或者说作为男人的“影子”,用“普遍的单一性别”被“代表着”。[5](P53)伊利格瑞正是要赋予哲学话语系统的性别分析维度,正如语言学和符号学曾经做到的。
二、身体物质
伊利格瑞超越性别本体论,将“差异”性别化之后才论及“差异”。如果伊利格瑞探讨的核心是拆解或擦抹两性之间的界限,那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关注性别界限断裂之处的越界体验和因“此性优于彼性”的断裂处所受的压迫。不同于伊利格瑞,巴特勒把探讨性别的伦理惯性看作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探讨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知识主体”的单一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论问题。她强调,“女性”是一个需要通过批判性思考而不断解构和建构、冲突和融合的永恒的命题,性别差异伦理并非专属女性主义内部的命题,而是一种“如何冲出他者的牢笼,在保持政治立场同时永不停止的思考”。[6](P418)女性主义第二波的性别政治主张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巴特勒则认为这个区分没有意义。巴特勒所关注的性别问题并非性别差异,而是“以性别差异为背景探讨思维方式、言语行为和物质身体的性别呈现”。[6](PP416-417)
身/心差异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但身体物质的提出却似一记重创冲破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意识优先性的惯例,并从尼采开始将身体纳入哲学的思考范围。虽然哲学家各自揣度身体物质与世界的关系的切入点不同,但身体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哲学家不断进行着哲学式的思考。性别伦理中,对有差异的身体回归和言说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的焦点。性别差异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如何为人的伦理问题,在差异体制中如何理解身体的物质性。这部分论述将围绕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展开:性别是思想和选择的理性结果,还是盲从和给定的强加物?性别是我们为身体假定的一种身份还是身体对这种给定的身份提出的规制条件?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波伏娃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身体作为自由意志的载体是先于物质而存在的。萨特认为人实际上原来是个无,是在我们自身之外被世界塑造和制造的原料,即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等到后来才把自己塑造成了想成为的那种人。这个塑造和创作原料的过程是选择我如何在自在中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体就是那个纯粹自由的虚无,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所以,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实现自由的途径是人的自由选择,人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通过行动担负起选择的责任。人类由于选择时无据可依陷入困惑,在虚空中孤独挣扎,终身为了从自在自由过渡到自为自由而奋斗。萨特的自由哲学观提出了一个通往人类终极自由的路径/媒介——身体的物质性问题。到底身体作为自由的自为还是物质的自在而存在呢?这个问题又引出另外一个关于性别的具身化问题,女性/男性和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萨特似乎暗示以何种性别出现在世界上是个纯粹偶然的事件,“我生为女性或男性”只是“我”在他人的注视和解释的意义编码和解码中才具有存在意义。也就是说,我的性别取决于他人的存在模式对我的认定,但不能妨碍我在身体中存在的绝对自由。波伏娃步其后尘,但利用萨特的自由意志哲学揭示女性作为偶然被选择的存在模式所受到的压迫。这在女性主义运动之初作为行动纲领是必要的。妇女因“第二性”将自为意志转交给男性,被“变成女性”。身体在文化传统中被注视和被塑造的事实让妇女反思文化和社会规范的控制意图,反思在父权制度中所处的附庸地位和所受压迫,性别即是行动,寻找失去的自为的自由意志是波伏娃对萨特自由哲学的女性主义图解和具体化。
如果说身体是“我”的意志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具身化,那么“我”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安置我的身体。那么,如何安置我的身体?萨特认为道德存在于真实性之中,如是说,“我”在身体中成为真实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问题接踵而来,我怎样存在是否有道德可言?我的自由意志如何指导我的肉身,并以何种模式存在?在后现代理论图谱中,这种个人主义对身体物质的控制遇到了麻烦。身体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外部因素走到台前证明自在意识的虚无。身体物质的社会性、政治性、表演性和技术性的问题浮出地表。
身体作为自在的存在并非具有先天的生物本能,如萨特所说使身体实体化不是肉体本身,而是使身体物质成为一种伦理材料,那么这种伦理材料必然与形成它的社会相关,身体物质就相应变成社会的具体需求与利益的呈现体。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身体物质社会构成说、福柯的身体权力和政治技术说都在追问身体物质是如何为社会服务和如何被社会授予阶级和种群并提供场所的。自柏拉图以来,布迪厄作为超越身心二元对立思考的思想家之一,认为身体和社会是互相包含的场所,一方包含另一方是惯习使然。布迪厄所讲的惯习是行为作为社会习俗而固定下来的模式。身体作为实践的能动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内化这些惯习,无意识地承担了各自的角色,并不断复现包括性别观念在内的常识,在身体上得到“促进社会世界再生产的政治工具”的持久表达。[7](P71)不同于布迪厄,福柯把身体视为被动的客体。在福柯对身体的谱系学式的考察中,身体物质因其可利用性、可驯服性成为接受、反射社会历史事件的载体。无论是血腥的酷刑还是仁慈的惩罚,身体是政治、经济、权力施行某种惩罚制度和技术的场所。身体之外种种事件和权力铭刻在身体这个场所上,“事件使得身体这个场所不断地转换、变化、改观和重组”。[8](P148)
巴特勒将身体表述为一种表演,表述为自我的生命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物质呈现,表述为对变为性别的身份批判。巴特勒对主体的批判再次揭示出她对稳定身份的忧虑——这种稳定身份被假定是随着变为女性或男性而物质化的。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出,身体作为不同性别的表达欲望的媒介被给予不同的意义。身体被呈现为男性和女性而出现,且这一过程中,一种异性恋秩序形成。身体物质性外化于肉体性,身体在其中被提供场所,因此异性恋文化得以持续生产,而维持这种生产的根本动力是相互有意义的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的物质性。在这一秩序之外是被排斥的身体,它们因为其偶然性而被拒绝物质化。这个他者位置、这个外在、这个“非一”的位置正是巴特勒关心的越界体验。如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有某种原初的、创始的和深刻的创伤”。[8](P72)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实际上在阐释身体的建构过程和重建的可能。她认为生物性身体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性别或身体是各种社会规范规约和反复强制的结果,是引用自己的结果,并通过表演创造主体。但是不同于面具说,性别不是面具,可以任意摘戴,仿佛面具下面藏着一个演员(主体),而是在不断引用自己的性别,并被反复强制书写这个规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流动的主体。因此,作为文化规范制约的主体,一定有边界,而巴特勒关心的则是边界外的生存可能,如同性恋和双性人。这里的断裂和褶曲之处正是他者铭刻伦理思考与哲学生命的场域。然而,这个场域中的他者并非要与中心同质形成相对立的关系,也不是用距离、远近、亲疏标注自我,而是在无法标注的权力网络上、知识体系的幽微边界建构“保持移动”的主体。[9](P15)
三、语言主体
正是通过对关于身体的话语建构的谱系分析,巴特勒演绎了性别的表演性更深刻的内涵。在理想的性别二元形态下考察双性人和变性人的言语行为,以及它们与语言惯例的隐含关系和表演潜质。“消解性别”从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开始,而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和“自然的”的规范概念又是形成性别差异的源头。巴特勒将主体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在向文化规约的“服从”过程中进行考量。③巴特勒关于主体对文化规约的服从理论参见她的最近力作《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147页。在“身体的服从”和“拒绝认同”、“转回自身”和“渴望屈从”中,在权力压抑主体又生成主体的悖论中,提炼永远处于社会边界的主体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9](P26)巴特勒并非强调行为主体行动的性别化过程,而是揭示在被表演中实现性别身份的行动。因此,“性别是通过被维持的社会表演而被创造的”。[10](P141)
奥斯汀(John Austin)的“依言行事”对巴特勒的启发不言而喻。奥斯汀首先提出主体对语言具有某种表演力。主体意图与文化秩序的相互交织和渗透,而这种交织和渗透反过来又为语言的恰当表演提供了舞台和背景。奥斯汀的表演性理论为性别表演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学基础。而巴特勒的延伸阅读重点在于挖掘言语行为的性别意蕴。巴特勒认为性别语词的使用是一种表演、一种引用。语言的行事性通过主体的权力或意志,使得某种现象被命名而存在。人的身体从出生就落入语言的象征网络中,被语言命名、区分、赋予社会意义。“生理性别”的物质性只能通过话语来理解。例如,一个婴儿被“询唤”为“女孩”的过程中,女孩不是自然地接受她的女性性征继而成为女孩,重要的是“女孩”通过对性/性别规范的“引用”成为符合某一规范的主体。对规范和权威的“引用”使所有语言符号被置于引号之中,性别身份在对这些符号的引用、嫁接、重述过程中,循环往复地被征引,在征引中松动、瓦解而丧失稳固性。这类洞见使得巴特勒看到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表演的结果,性别不再被理解为自我的身份建构的基础,而是作为语言表演的结果,是语言特质在社会中的性别呈现:“如同在其他仪式性的社会戏剧中,性别行为需要被重复表演。这种重复同时是重新赋予与重新经历一系列已经确立的社会习俗;并且是合法的习俗与仪式性的形式。虽然有通过在性别模式中被风格化而实施这些意义的个体身体,但这一‘行为’却是一种公共行为……表演是在其二元结构中维持性别这一策略性目标而产生——这一策略性目标不能被归属于一个主体,但是相反,它必须被理解为用来确立和巩固主体的。”[10](P140)
所以,性别在这个重复“表演”的过程中产生,但巴特勒并没有停留在“表演”的结果和复现性上。作为复制和仪式性的沉淀产物,性别被自然化的同时,又遭到“消解”。巴特勒在《身体的重要性》中用大段脚注对约翰·塞尔(John Seale)和奥斯汀的表演理论以及德里达的可重复性行为进行了延伸阅读。[11](PP244-245)巴特勒的贡献在于,建构性别的复现表演是对当下行为的“暂时引用”,“引用”同时产生缺口和断裂,断裂之处正是“建构的不稳定成分”活跃之处,也是巴特勒要构建的超越规范的逃逸时刻。这种边界上的不稳定性是对“重复过程本身的解构,是对稳定化了‘性别’的效应进行消解的力量,是将‘性别’规范的稳定性转变为被激活的潜在危机”。[11](P10)巴特勒的落脚点放在试图摆脱未被命名的性别边界上,因为边界上充满包容和排除,被排除者在对源于支配性位置之外的“区域”建构话语的可能成为巴特勒消解主体重构性别差异的场域。巴特勒突破语言惯例框架下的性别身份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巴特勒看到性别是发生在空间、时间中表演的产物,性别的表演性的提出为动摇两性所具有的稳定性提供了哲学话语层面上的可能。
巴特勒正是在考察行为主体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体系和在这个体系中被赋权的行为主体自身,消解人本中心论。这个观点显然受到福柯的“精神管制论”的影响。但是巴特勒关注的不是犯人被囚禁的样式,也不是形成权力的管控和规训的政治制度,而是权力管制和生产发生过程中主体的形成,这个形成过程是因对规范的吸纳而形成,主体的形成反过来又支持管制的权力的部分形成。主体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对于规范和服从的欲望”的产生、创立、内化和外化的精神生活完成的。而精神的服从正是标志着服从的一个具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规范,因此,“这种规范的精神实施得自预先的社会运作”。[9](PP16-20)这个行为主体在参与社会事件中完成了它自己的服从,并渴望和精心制作了它自己的镣铐,将成为自己的“权力”交还给从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社会条款”——规诫和惩罚,并且行为主体的意义模式在个体行为中被表演和被强化,因此,最初的屈从就构成了存在的欲望。像巴特勒那样坚持自己的存在欲望,坚持异他性(alterity),④巴特勒有关异他性(alterity)是受到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思想的影响。巴特勒和列维纳斯都是犹太裔学者,他们对犹太人的“异他性”问题有共识。巴特勒在2012年最新力作《十字路口:犹太性和对复国主义的批判》(Parting Ways:Jewishnessand the Critiqueof Zionism)中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美国小说理论家多萝丝·霍尔教授也受到列维纳斯的影响,从叙事学的角度提出了新伦理批评(New Ethics),这是目前美国文学批评新的增长点之一。英文学术论著参见Dorothy Hale.Jamesian Aesthetics of Alterity.2013年即将出版,另见Robert Eaglestone.Ethical Criticism:Reading after Levina[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7.David Parker.Ethics,Theory and the Novel[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中国学者对异他性的研究参见刘文锦:《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他人的面容与“歌中之歌”》,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主体则以反对它自己的面目出现。“生成自我”不是简单地挑衅和反对主体的位置,而是将“我”暂时悬置,在不稳定的重复和危险实践中,在社会存在的边界上保持移动,反抗最初的性别“暴力”。正如巴特勒重新阐释的安提戈涅,她永远“保持移动”,并随时准备越界和逃逸。基于安提戈涅的不稳定的伦理边界,作为漂移的他者,巴特勒并非建构他者的伦理规范和实施规范的代理行为,而是让性属问题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从而向未来开放自己。因为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我之所以为我的存在事实在权力话语体系中无处安身。
通过谱系学式的批判解构性别,通过查找并揭示那些“不稳定性”或“不连续性”的文化性偶然行为,女性主义批评家挑战并揭露人(human)作为一个预设概念和“排他性”霸权政治。[12](PP179-208)齐泽克、拉克劳和巴特勒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有关马克思主义内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关于主体、霸权、普遍性的论战。⑤社会规约对这个概念的惯用标准和性别情景化的论述在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合著的文集:《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中给出了充分的阐释。他们站在主体的历史性改造层面上提出性政治学对性差异理论的挑战。这些观点延续了《性别麻烦》、《身体的重要性》质疑哲学范畴里提到的“人”所受的性别规约的讨论。[12](PP33-34)因为对性别的反复表演“预设了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没有起源的模仿”。[10](P138)在关于人的“意义增殖领域”的偶然性上重新标注性别和性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女性主义者重置主体身份、主体话语,使存在摆脱自我,使思想另类思考。
四、结语
性别理论源于对性别差异的预设性的质疑,而预设的物质身体差异延伸了我们作为人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预先被制造为存在,这首先就妨碍我们真正理解实际身体所揭示的人的本质。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结构女性主义批评家并没有拒绝对自己的认识和本体确定感的丧失,而是以“无暴力的名义接受其变化”,并且重新考虑这些性别预设蕴含的“偶然性”和“可变性”。⑥巴特勒所讲的“暴力”是指对变性人、双性兼具者以及携带HIV和艾滋病患者在公开自己身份时遭受的身体、语言和精神上的暴力,以及警察或政府对这些暴力的漠视。[13](P34)面对这些持有秩序规范的他者时,女性主义者容忍对“他者”(自己)的无知,因为“保持问题的开放性比预先知道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共性更有价值”。[13](P35)21世纪的批评家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思考差异,也就是向未来开放自己。新世纪新人文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提供给人类表达权利和价值的潜力和空间。
性别差异走向终结之后的身体何处得以栖息?伦理神学教授苏珊·弗兰克·帕森斯(Susan Frank Parsons)从性别神学的角度给出了可能的救赎,“在基督那里我不要重复先前的模式,但在未来按自己的信仰重塑自己。这让我变得神圣,因为在这里,上帝是鲜活的。信仰的召唤是某种与生活相关的诉说,一种表演、一种来自未来的生活召唤”。[14](P161)⑦苏珊·弗兰克·帕森斯根据西方妇女运动的实践,理顺了三种性别伦理模式:平等伦理、差异伦理和自由伦理。平等伦理关注女性与男性共同人性的参与平等。差异伦理强调女性和男性平衡与互补间的重构标准诉求。解放伦理试图冲出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约束和范畴,重塑人性的理性在消解性别后获得的自由。这样的划分大致与女性主义近代的三次妇女思潮的核心政治主张基本吻合。女性主义作为新人文主义建构之中的一种思考方式,从平等伦理到差异伦理再到解放伦理,伦理所试图解放的是社会建构范围之外的人性的一个维度,正是我们自己这个维度。作为性别伦理的女性主义在重新获得人性的共同之处的意义上,开显“不依赖于社会习俗而强加于二元模式的新生活,是超越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规约和范式的契机。这样,才有可能使人性中更趋完善的理性一面得到授权和解放。”参见其《性别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43页。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酷儿才有可能实现肉体的具体化。
[1]Yan,Liu.Feminism,Sexuate Rightsand the Ethicsof Sexual Difference:An Interview with Luce Irigaray[J].外国文学研究,2011,(3).
[2][法]露丝·伊利格瑞,马海良译.非“一”之“性”[A].收录于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Luce Irigaray.Towards a Citizen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A].Democracy Begins between Two[M].Transby Kirsteen Anderson.New York:Routledge,2001.
[4]Luce Irigaray.The Universal as Mediation[A].Sexes and Genealogies[C].Trans.Gillian C.Gill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5]Luce Irigaray.The Eternal Irony of the Community[A].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Hegel[C].ed.by Patricia Jagentowicz Mills.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96.
[6]Judith Butler.The End of Sexual Difference[A].Feminist Consequences:Theory for the New Century[C].ed.by Elisabeth Bronfen&Misha Kavk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7]Pierre Bourdieu.Outlineof a Theory of Practice[M].trans.Richard N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8]汪民安.福柯的界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张生译.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with anew preface)[M].New York:Routledge,(1990)1999.
[11]Judith Butler.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M].New York:Routledge,1993.
[12][美]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著、胡大平等译.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3][美]朱迪斯·巴特勒著,郭劼译.消解性别[M].上海:三联书店,2009.
[14][英]苏珊·弗兰克·帕森斯著,史军译.性别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原文译文笔者做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