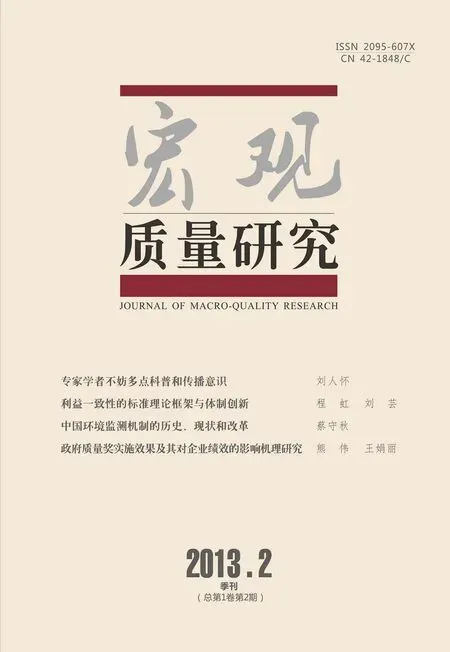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
——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国外研究综述
李 酣
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
——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国外研究综述
李 酣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产生的质量安全领域的风险需要政府规制来进行治理,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者们研究了政府质量安全规制和法律责任规则的共同使用下的社会效率状况,也分析了政府质量安全规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普遍承认政府规制在这一领域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和解释了质量安全领域的过度规制产生的政府失灵(规制失灵),以及在过度规制基础上形成的规制不足这一悖论。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虽具有利弊的两面性,但却是治理质量安全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需要采用信息规制、激励性规制措施、自我实施的规制等方法革除其弊端。
质量安全;规制;责任;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引言
Joseph Stiglitz(2009)写道,当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描述了美国屠宰场中恐怖的卫生状况的时候,美国人民和美国消费者开始放弃食用肉制品;而美国肉制品包装产业的选择却是恳请政府实施食品安全的规制,由政府颁发许可证,以重新恢复消费者的信心。美国今时今日的空气和水更为清洁、人民的寿命更长,原因就在于环境规制。而在当下,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食品、安全和环境规制的世界——争论的焦点仅仅是是否规制过多、能够用更低的规制成本获得想要的效果,而不在于是否需要规制(Joseph Stiglitz,2009)。
在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背景中,一些学者研究了生产厂商的质量安全责任问题。如Walter Oi (1973)认为:如果在产品市场中,交易双方及交易过程处于完全信息的状态下,采用严格责任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或者只要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自由选择能力,不需要直接的政府控制就可以实现质量安全的保障目标。但是Oi的这一分析受到了Victor Goldberg(1973)的批评,他认为产品质量安全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者的信息是否完全的问题,所以,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来分析这一问题并得出相关政策含义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在存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即使产权明晰,科斯定理的推论也不能成立,即市场自身不能够通过交易双方的谈判达成有效率的结果。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George Akerlof(1970)开创性地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他的分析建立在下面三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1)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确定商品质量;(2)高质量商品相对于低质量商品的价格更高;(3)对厂商而言,不存在进行品质担保的可能。如果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市场机制在提供质量安全产品上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除了早期的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研究会将背景设置在完全信息的环境中,其它大部分该领域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中。虽然在Stiglitz的描述中,美国的肉制品包装商人将回复市场均衡的希望一开始就寄托在政府的介入之上;但是在经济学家有关质量安全责任的早期分析中,即使是承认产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也不意味着他们都承认政府进行质量安全规制的必要性。在经典经济学中,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文献并不认为政府监管是解决这一市场运行障碍的可供选择的手段,而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和法律救济回复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Viscusi &Moore,1993);或者通过厂商对于产品品质的担保(Spence,1977);或者是采取保险机制等办法实现(Geistfeld,1995)。这些都可以在不需要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的情况下,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效率的市场均衡。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充分理论。质量安全中的信息不对称虽然也不必然要求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但是,正如Stiglitz所观察到的,在世界范围内,食品、药品和安全领域中的规制普遍存在,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也浩如烟海。本文从政府质量安全规制责任的作用及其存在的规制失灵着眼,对国外学者在这一方向的研究文献做一归纳和总结。
除引言外,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政府质量安全规制在应对这一市场失灵中的作用和范围;第三部分是在质量安全监管领域存在的政府失灵;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展望。
二、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质量安全责任
(一)政府质量安全规制与法律责任的共同使用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认识到,质量安全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问题。不对称的质量安全信息对各个主体会带来外部性影响,引发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因而质量安全领域需要政府规制。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文献探讨了政府规制和法律责任的共同作用下,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实现问题。Guido Calabresi(1970)认为,政府质量安全规制与法律责任规则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Steven Shavell(1984)最早指出,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控制过程中,企业所面对的产品质量法律责任制度和政府监管必须保持平衡。当然,在区分公权(政府规制)与私法(法律责任)调节的事前与事后选择的时候,他提出了四条理论依据:(1)规制机构和私人部门所掌握的产品风险信息有所差别;(2)生产厂商在造成质量安全风险之后并没有承担全部损害的可能;(3)生产厂商由于各种原因却有可能免于责任追究的可能性;(4)政府履行质量安全的监管责任可能存在管理和追究生产企业责任的成本。在以上四个条件,或称为假设前提的基础上,Shavell提出,符合社会福利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是找到政府规制与法律责任的结合点,这必然是解决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Rose-Ackerman(1991)界定了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规制和质量安全伤害的侵权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他认为前者是一种公法(Public Law),而后者是私法(Private Law)。法律上的侵权责任与政府质量安全立法规制互为补充,两者都是有效的。他提出了两者之间互补的三个条件,普通法的侵权责任只是在规制不够严厉时候的权宜之计,限于政府规制立法没有涉及的领域。质量安全规制应该尽可能退出侵权责任能够以更严厉的方式管束的领域。总而言之,在质量安全领域,绝大多数导致质量伤害的行为应该还是由经典的侵权责任加以约束。质量安全规制应该选择直接的、事前规制的,具有严重危害的产品责任领域,如健康、汽车和药品等极小的范围。在这些领域,侵权法律责任规则或者法院系统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人员缺乏等原因,无法处置这些带有一定技术性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Alessandra Arcuri(1999)指出,在Goran Skogh于1989年的一篇文献中分析了法律责任规则、政府规制、私人保险和公共保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优点和缺陷,因此,不同规则的混合使用可能更为有效率。同时,Arcuri认为,作为不完全信息控制与调节机制的质量安全规制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式,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制定有效率的质量安全的规则,比如规制政策制定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用有效的方式向消费者交流质量安全的信息。
在Shavell(1984)的分析范式基础之上,很多学者对于政府规制和法律责任机制的共同使用的福利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Charles Kolstad等人(1990)指出,之前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采用安全标准及庇古税这样的事前规制和侵权责任这样事后措施,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但他们证明,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单独使用侵权法律的疏忽责任规则效率低下,而事前规制可以矫正这一无效率。Patrick Schmitz(2000)同样认为这两者存在互补,共同使用会带来更好的福利效应。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财富在质量安全的受害者那里的分布不是一致的,那么并不需要假定政府规制存在执行失误,同样可以得到以上的结论。Robert Innes(2004)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政府事前规制和法律事后责任对于企业履行责任,以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上产生的不同作用。他认为即使政府观察企业履行安全责任努力程度的成本显著高于监测事故的成本,直接的事前政府规制也可能比事故损害的事后责任规则要有效。而Yolande Hiriart等人(2004)证实,如果预防努力不能被验证(Verifiable),在进行如上所述的这些分析的时候就要考虑道德风险所带来激励机制失效的问题。Sebastien Rouillon(2008)理论上分析了政府规制与法律责任体系如何共同作用,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路径,而且证明两种规则的共同使用要优于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治理风险的方式,而且这时,这些规制都大可不必规定得那么严厉。Bharat Bhole和Jeffrey Wagner(2008)的分析建立在假定企业可以通过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两种方式来履行质量安全责任的假设条件下,政府规制和严格责任法律规则的共同使用在缺乏法官的证明的情况下依然是更优的。这一推论在企业面临惩罚性赔偿的时候依旧是成立的,只要社会福利与企业的期望履责成本负相关。
(二)提供信息是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有效路径
Arcuri(1999)指出,纠正信息不对称的质量安全信息规制是各种安全规则中能够保障消费者自由选择的首选政策措施。纠正不完全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首先的方案是提供缺失的信息,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Schwartz和Wilde(1979)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而Viscusi、Magat和Huber(1986)提供了安全规制领域消费者有效利用信息的一些例子。
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应该通过何种手段予以提供,这些信息手段何时是有效的,何时是无效率的,选择哪一种信息规制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呢?Nelson(1970)认为商品按照其包含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差异,可以分为搜寻品(Search Goods)、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Darby和Karni(1973)则主要分析了其中的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例子。Nelson(1974)指出,厂商会自觉地向市场发布产品质量的真实信息,质量安全的政府规制反而可能会扭曲市场对于信息的正常传递渠道,这时Akerlof所定义的柠檬市场的市场失灵并不会出现。Klein和Leffler(1981)认为Nelson提出的信息机制能够解决Akerlof的柠檬市场问题。
在Milgrom和Roberts(1986)提出的声誉机制模型中,声誉具有品质担保的作用,价格本身就具有额外的质量信号的显示功能。这些文献强调了质量安全规制中的信息披露机制,监管规制不应该限制真实信息的披露。在所有的商品当中,信任品的欺诈最有可能,也是危害最严重的,信息规制在这方面的效果最好。Rubin(1990)发现声誉机制对于那些希望在市场上立足,进行重复销售的厂商而言,有品质担保的作用。
质量安全规制在这里,主要是一种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有效机制。如果是消费者对风险的无知,或者对有关特定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确定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低估,或者高估风险,从而导致某种无效率,这是Asch1988年提出的观点。Bardach和Kagan(1982)认为如果消费者的信息不完全来自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时候,过多的信息披露反而会导致消费者不能阅读或者消化,这时候,信息的强制披露可能产生负面效应。Pildes和Sunstein(1995)指出,消费者的这种不完全信息只能通过相关环境的改善得到弥补,如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增强消费者的信息处理能力等。
除了信息规制之外,在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中,增加质量安全规则的严格性、修正广告涉及质量或者安全的内容、赔偿、罚款等补救或者救济措施也在使用。比如,在对生产厂商质量安全方面违规行为的罚款上,Feistein(1990)认为,政府的罚款措施应该只限于真正的欺诈行为;其次,最优罚款金额应该设定在保证厂商在质量安全上的努力产生适当激励的关键点上。Shavell(2005)附带谈论了事故责任中直接规制、矫正性税收和法律禁止方法,即禁令(Injunction)的作用,不过他也承认在到底是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还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Marcel Boyer和Donatella Porrini(2011)的分析发现:如果提高司法体系的效率,能够提高被规制者的安全履责的水平,进而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这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要求会降低,也会减少企业在责任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比例。
三、质量安全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规制失灵或者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多种,例如George Stigler(1971)提出的管制俘获理论认为,对于社会经济中的每一个行业来说,政府规制可能是一种管制的挑战,也可能代表着一种“机遇”。在规制立法和规制执行两个层次上都可能存在着“政府规制市场”,在利益驱动下,被规制者总会千方百计对监管机构进行“寻租”,企图影响甚至收买规制立法者和执法者。此外还有公共选择学派所提出的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等等。质量领域广泛存在的各个主体之间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和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所带来的社会负外部性是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理由,但是“诺斯悖论”也告诉我们,“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道格拉斯·诺斯,1994)。政府本应从公共利益出发,提供公正公平的质量安全监管政策,但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干预行为也会出现失灵,监管效率低下,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市场失灵下的政府过度规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而政府失灵对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扭曲作用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亚于市场失灵本身,甚至更为严重。
(一)过度规制
要探讨质量安全领域的过度规制,首先需要引入规制强度这一概念。规制强度(Regulation Intensity)现在环境和金融领域的政府规制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采用的概念,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在国内外都很多。有一些学者建立了规制强度的相关理论模型,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实证研究方面。市场主体进入营业领域的时候所受到的在资格、机会、条件和程度等方面的限制条件的严苛程度就可以被定义进入规制强度,秘鲁经济学家De Soto(1989)比较了在秘鲁首都利马和美国佛罗里达州Temple市设立一个小型成衣工厂需要花费的时间的对比,结果是289天比2小时。后来的Zylbersztajn和Graca(2002)以及Djankov,La P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2)对不同样本国家的进入规制强度都进行了测算,尤其是是后者,使用进入管制的程序数、办理程序花费的时间和支付的货币成本衡量了85个国家的进入规制强度。
西方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放松规制的潮流,许多学者从环境、安全生产、电信和金融等不同的行业领域出发,研究了这些产业中政府过度规制(Overregulation)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过度规制的表现或者测度方法有多种,例如美国2010年的Dodd-Frank法总长达到了848页,是Glass-Steagall法案的23倍。更为严重的是,每隔一页都要求规制者填入更为详细的内容。这就体现了“过度规制”。Frederick Sawyer(1979)认为环境领域的政府规制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许多规制行为的制定基础是在将粗略的研究结果做了简单的外推,忽视了生态过程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常会造成产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立,反而使得规制措施实施后弊大于利。John Mendeloff(1986)分析了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规制过程中的健康标准设置(Health Standard-Setting),这一过程当中规制过度和规制不足并存,过度规制是源自于用成本高昂的方式去实现过于严格的标准,规制不足是由于标准设置过程滞后,导致很多风险根本没有得到应对。OSHA的很多标准制定过程同时存在这两种问题。而且设置过于严格的标准拖累了标准设置的进度,换言之,是过度规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规制不足。产生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工会和产业组织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标准设定被上诉到法院,标准的效果通常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需要规制机构去证明标准的必要性,而这些机构的资源都是相当有限等等。按照他的计算,在OSHA的规制中,十之八九的相关规制政策都成本过于昂贵,可能花费几百万元美元都不能解救一两个人,特别是OSHA制定的关于氯乙烯(Vinyl Chloride)的安全标准,要耗费4千万美元才能拯救一条生命。在他看来,只有有关石棉的标准还算成本合理,40万美元的成本可以救一个人。他认为OSHA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规制的范围扩大同时将规制的严厉程度降低,这样,政府规制的社会福利效果会更好。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被规制者给定的遵守规制的成本,能够防范更多的疾患,这种策略性的变化会带来成本的下降,拯救更多的生命。
当然,Mendeloff的计算纯粹是从成本-收益分析的比较,没有考虑过多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这种计算受到了Sidney Shapiro和Thomas McGarity(1991)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计算存在错误。比如过于依赖事前的成本估算,可能不太准确,另外在估计和测度健康和环境规制的收益的时候,也难以把握那些过于复杂的因素。
国外此类文献已经探讨了政府过度规制与被规制的微观个体之间的激励与约束关系。Gary Cacciatore(1997)推断美国的医药业受到的管制程度是最高的,不仅体现在数量庞大的规制措施,还体现在这些规制措施详细地决定了医药业提供服务的具体细节。结果导致这些专业人员将更多的“注意”放在了如何满足政府规制措施的细节要求上,反而忽视了自身的职业判断,很多规制措施不必要地介入了医药行业的实际操作层面,导致职业精神的削弱。Haring和Rohlfs(1997)的研究认为,美国采取重要的步骤和措施想推进区域电信行业的竞争,但是,采用的却是更多管制的方式。理论上电信运营商之间的接入费率应该是通过企业之间的谈判议定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规制者自己决定了。美国在航空、汽车运输和铁路等行业对于竞争的规制都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导致了这些行业价格过高,而服务的质量却在稳步下降,政府最后不得不自己接管部分产业。他们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的区域电信市场没有过度的规制,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结果可能更有效率。Curtis和Schulman(2006)认为美国的医药规制影响了医疗健康部门的创新,对其成本费用的降低起了副作用,导致了美国医疗成本增加过快,患者面对的医疗成本过高。复杂而过于繁琐的规制措施导致了成本的上升,也带来了服务创新的停滞不前。以上这些研究分析的对象虽然分处环境、医药等不同的领域,但是这其中的政府规制对微观规制对象行为的过多干预,都对被规制者的行为选择产生了负面效应,甚至可能使得规制的结果与设定规制手段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过度规制与规制不足的悖论
中国古语云“过犹不及”,在规制领域也是如此。对于过度规制和规制不足(Underregulation)之间悖论的研究最先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Joshua Aizenman(2009)认为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的平静期,会导致规制强度的下降,甚至如果这一时间段比较长的话,规制强度甚至可以降低到零,但是这时社会合意的规制水平是正的。如果金融危机带来比较高的成本损失的话,又会看到过度规制。如果要解决这一悖论,就需要采取改革规制的结构、使用信息披露方式、增加规制机构在政治中的独立性和采用“最小谨慎”监管(Minimum Prudential Regulation)的国际标准等等方法。Cass Sunstein(1990)认为这种悖论的形成其实是规制策略的自我失败(Self-Defeating Regulatory Strategies),也就是规制策略导致的结果和其设计的初衷是相反的。他举例说道,空气清洁法案(Clean Air Act)的实行会导致空气更脏。这种分析其实在公共选择和福利经济学的文献中相当多,出于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规制机构结果大都成为花费公共资产而服务私人利益的无谓作用。但是Sunstein也强调,改变这种规制悖论的解决方法并不是恢复到自由放任的阶段,而是从这些规制失灵的实例中汲取经验教训。
正如Sunstein所提到的环境质量的例子,关于规制过度和规制不足的研究在美国的环境规制中有较多的体现。Markusen等(1993,1995)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企业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作用下,美国国内不同州之间的地方竞争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在环保标准的制定上走上不同的极端。Colin Scott (2012)认为现在政府的规制总是雄心勃勃,似乎要规制一切(Regulating Everything),但在爱尔兰,虽然规制机构的数量和规制的范围增长显著,但是其规制能力也被显著耗散了,这些规制机构组织上和执行规制形式上的碎片化,导致其权利被分散,被弱化,但是责任反而加重了。
四、结论和展望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是政府干预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满意的结果,其原因有很多。首先的一个理论解释可能是政府规制在设立规制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方面存在较大的误差,将政府视为无所不知的全能者来纠正市场失灵,而忽视了政府实施规制的成本,这种规制本身可能产生的失灵却被忽略。其次,规制作为政府行为,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拥有必要的信息,但是在常态下,规制者关于规制对象的信息一般要少于被规制者,这种信息约束限制了政府规制的效率,被规制者往往会采取逆向选择行为。除了这些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关注规制过程中的政府规制强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质量安全的政府规制当中,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原理,在垄断市场结构中,如果垄断厂商生产的是经验品或者信任品,那么为了弥补垄断厂商提供产品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数量上的差异,政府规制是必要的;但是政府采取的规制政策和手段的“强度”可能存在“过度规制”也可能存在“规制不足”,这两种状况下都会导致政府规制的失灵。
规制过度会影响被规制者自身的积极性,规制不足自然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对于消费者的伤害。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加强规制和放松规制的不同呼声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来临和消退而转换。可以说,西方国家中存在经济领域中规制放松和社会性领域规制加强两种并存的态势。从美国来看,其政府从18世纪末期开始,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在不断加强,而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在涉及卫生、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日渐高涨。在英国、法国等国家,也出现了大规模解除对航空、铁路、能源和电讯等行业经济性规制的浪潮。
在我国,可能存在相反的态势。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在后续的进程中,我们在解除对于市场经济的统制之后,市场领域的相关规范还没有完全的树立,在经济性规制领域,可能需要更多的规制方式和手段。例如,在反垄断领域,虽然已经颁布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但是在执行上还存在很多不完备的情况。但是,在环境和安全等社会性领域,原本就基本上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一直以来就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总体而言,目前依然处于一个过高程度的规制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放松规制,而不是加强规制。程虹和李丹丹(2009)指出,在质量安全领域,政府对于微观市场主体的过多规制会导致这种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失衡,进而形成规制失灵。程虹等(2012)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质量管理体制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这种困境的出现。政府在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规制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董志强等(2007)认为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形成“政企合谋”,并对这一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聂辉华等(2011)利用中国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数据对此进行了面板数据检验。林闽钢等(2008)则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规制失灵。可以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内规制领域的政府失灵现象,借鉴了国外的相关规制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用中国的数据做了计量检验。
正是因为规制失灵的出现,学者们提出了几种治理规制失灵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要取消政府规制,而是改变政府规制的做法,改变规制过程中规制机构和被规制对象之间的关系,让被规制者面对正确的激励机制。Laffont和Tirole(1993)创立的激励性规制理论就指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率和信息租金是一对共生的矛盾,实施规制可以避免企业得到垄断利润,但必须以效率损失为代价,将激励机制引入政府规制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在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质量安全规制领域,激励性规制是给予市场主体正确激励的有效方式。另外,Porter和Kramer(2006)指出自我规制是一种涉及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标准与规制过程的制度安排,其标准与规制过程大多由一个组织的成员共同制定,目的是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这是一种介于政府规制和市场规制之间的中间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规制的不足。与政府的强制性规制不同,自我规制是由被规制对象自行设计并自我执行的制度安排,而且不是比政府现行规制更加严格,就是在缺乏政府规制或标准的领域建立新的标准。再有就是放松规制。由于规制失灵的日益明显以及规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放松规制”的潮流。Marjit等人(2008)认为,高度规制的环境造成了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等是扭曲的,因此最好将规制保持在最低程度。
[1] 程虹、李丹丹,2009:《我国宏观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中国软科学》第12期。
[2] 程虹、范寒冰、罗英,2012:《美国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及借鉴》,《中国软科学》第12期。
[3] 道格拉斯·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4] 董志强、严太华,2007:《监察合谋:惩罚、激励与合谋防范》,《管理工程学报》第3期。
[5] 聂辉华,蒋敏杰,2011:《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
[6] 林闽钢、许金梁,2008:《中国转型期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规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7] 张朝华,2009:《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下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重构——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
[8] Akerlof,G.A.,1970,“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4,pp.488-500.
[9] Aizenman,Joshua,2009,“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aradox of Under-and Over-Regulation”,NBER Working Paper,No.15018.
[10]Bardach,E.and R.A.Kagan,1982,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1]Bhole,Bharat and Jeffrey Wagner,2008,“The Joint Use of Regulation and Strict Liability With Multidimensional Care and Uncertain Convic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8,pp.123-132.
[12]Bouckaert,Boudewijn and Gerrit De.Geest,2000:Encyclopedia of Law and Economics,Cheltenham,Edward Elgar.
[13]Boyer,Marcel,and Donatella Porrini,2011,“The Impact of Court errors on Liability Sharing and Safety Regulation for Environmental/Industrial Accident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1,pp.21-29.
[14]Cacciatore,G.G.,1997,“The Overregulation of Pharmacy Practice”,Pharmacotherapy:The Journal of Human Pharmacology and Drug Therapy,Vol.17,pp.395-396.
[15]Calabresi,Guido,1970,The Costs of Accidents: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Yale University Press.
[16]Curtis,L.H.and K.A.Schulman,2006,“Overregulation of Health Care:Musings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y”,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Vol.69,pp.195-206.
[17]Darby,Michael,and Karni Edi,1973,“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6,pp.67-88.
[18]De.,Soto,and Hernando,1989,The Other Path,Harper and Row.
[19]Djankov,Simeon,Rafael 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2002,“The Regulation of Entr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pp.1-37.
[20]Feinstein,Jonathan S.,1990,“Detection Controlled Estim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3,pp.233-276.
[21]Geistfeld,Mark,1995,“Manufacturer Moral Hazard and the Tort-contract Issue in Products Liabilit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5,pp.241-257.
[22]Goldberg,V.P.,1974,“The Economics of Product Safety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5,pp.683-688.
[23]Haring,J.and J.H.Rohlfs,1997,“Efficient competition in Local Telecommunications Without Excessive Regulation”,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Vol.9,pp.119-131.
[24]Hiriart,Yolande,David Martimort and Jerome Pouyet,2004,“On the Optimal Use of Ex-ante Regulation and Ex-post Liability”,Economics Letters,Vol.84,pp.231-235.
[25]Innes,R.,2004,“Enforcement costs,Optimal Sanctions,and the Choice Between Ex-post Liability and Ex-ante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4,pp.29-48.
[26]Klein,Benjamin and Keith B.Leffer,1981,“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ssuring Contractual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pp.615-641.
[27]Kolstad,Charles D.,Thomas S.Ulen and Gary V.Johnson,1990,“Ex Post Liability for Harm vs.Ex Ante Safety Regulation: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pp.888-901.
[28]Laffont,J.,and J.Tirole,1993,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Regulation and Procurement,MIT Press.
[29]Marjit,Sugata,Biswas,Amit K.and Beladi Hamid,2008,“Minimize Regulations to Regulate-Extending the Lucas Critique”,Economic Modelling,Elsevier,Vol.25,pp.623-627.
[30]Mendeloff,J.,1981,“Does Overregulation Cause Underregulation?the Case of Toxic substances”,Regulation,Sep./Oct.,pp.47-52.
[31]Mendeloff,J.,1986,“Regulatory Reform and OSHA Policy”,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Vol.5,pp.440-468.
[32]Milgrom,Paul,and Roberts John,1986,“Price and Advertising Signals of Product Qua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pp.796-821.
[33]Nelson,Phillip,1970,“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8,pp.311-329.
[34]Nelson,Phillip,1974,“Advertising as In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2,pp.729-754.
[35]Oi,W.Y.,1973,“The Economics of Product Safety”,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4,pp.3-28.
[36]Pildes,R.H.and C.R.Sunstein,1995,“Reinventing the Regulatory St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62(1),pp.1-129.
[37]Porter,M.E.,and Mark R.Kramer,2006,“Strategy and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84,pp.
[38]Rose Ackerman,S.,1991,"Regulation and the Law of Tor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1,pp.54-58.
[39]Rouillon,S.,2008,“Safety regulation vs.Liability with Heterogeneous Probabilities of Sui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8,pp.133-139.
[40]Rubin,Paul,H.1990,Manag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Free Press.
[41]Sawyer,F.G.,1979,“An overview: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Water,Air,and Soil Pollution,12(1),pp.37-45.
[42]Schmitz,Patrick,W.,2000,“On the Joint Use of Liabi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20(3),pp.371-382.
[43]Schwartz,A.and L.L.Wilde,1979,“Intervening in Markets on the Basis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27,pp.630-682.
[44]Scott,Colin,2012,“Regulating Everything:From Mega-to Meta-Regulation”,Administration,60(1),pp.61-89.
[45]Shapiro,S.A.and T.O.McGarity,1991,“Not so Paradoxical,the Rationale for Technology Based Regulation”,Duke Law Journal,pp.729-752.
[46]Shavell,S.,1984,“A Model of the Optimal Use of Liabi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5(2),pp.271-280.
[47]Shavell,S.,2005,“Liability for Accidents”,NBER Working Paper,No.11781.
[48]Spence,A.Michael,1977,“Consumer Misperceptions,Product Failure and Producer Liabilit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44(3),pp.561-572.
[49]Stigler,George.,1971,“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2(1),pp.3-21.
[50]Sunstein,C.R.,1990,“Paradoxe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57(2),pp.407-441.
[51]Viscusi,W.K.and M.J.Moore,1993,“Product Liability,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Innov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1(1),pp.161-184.
[52]Viscusi,W.K,Wesley A.Magat,and Joel Huber,1986,“Informational Regulation of Consumer Health Risk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Hazard Warnings”,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7(3),pp.351-365.
[53]Zylbersztajn,Decio,and Carolina T.Graca,2003,“Costs of Business Formalization:Measuring Transaction Costs in Brazil”,Revista de Economia Institucional,5(9).
■ 责任编辑汪晓清
From Market Failure to Government Failure: A Literature Survey on Qua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
Li Han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Wuhan University)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s needed to regulat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issues under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which is a common view between scholars.Economists analyze the joint usag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statutes,also,the domain and mod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re defined.However,those scholars discovered the government failure resulted from overregulation in qua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s given to explain this paradox.Although there are two sides of government’s qua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it is still the necessary method to cure the market failure in quality and safety governance.Nonetheless,informational regulation,incentive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self-enforcing regulation are required to overcome its drawbacks.
Quality and Safety Responsibility;Regulation;Market Failure;Government Failure
*李酣,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lihan@hotmail.com。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58)、“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K06B06)、科技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210117、201310202)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2YB048)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