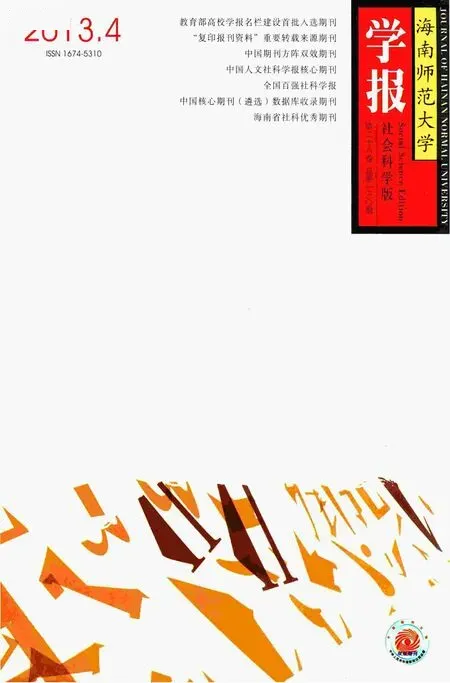鲁迅研究的扎实成果与可喜收获——评赵歌东《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谭五昌,马媛颖
(1.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文化时代,谈论“现代性”问题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时髦与紧跟“潮流”了,毕竟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甚至“后后现代”了。时下一切有关鲁迅的话题,似乎颇为“不合时宜”,因为鲁迅及鲁迅话题与当今社会的整体精神氛围与思想状态存在内在的冲突与不协调。然而,作为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绕不过去”的经典性作家,鲁迅始终存在着,并且至今仍然在参与并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现实及文学意识。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与评价鲁迅呢?鲁迅研究的价值及新意何在?赵歌东的学术新著《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鲁迅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是言说不尽的,其现代性体系所涵盖的各类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亟须我们去进一步发掘、审视与评估。
回顾近百年的鲁迅学术研究史,我们看到,每个时代由研究者们所建构的鲁迅形象均呈现着不同的时代性风貌,这一现象既建立在时代发展的客观基础之上的,又受研究者主体研究意识、研究方法等主观因素影响。大致说来,1920年代的鲁迅是作为启蒙者的“文学的鲁迅”;1930、1940年代的鲁迅是“民族魂”和文化战线的“斗士”;1950 至1970年代的鲁迅是被极端政治化的、“革命的”化身,甚至一度成了政治大批判中的“尺子”或“棍子”;1980年代的鲁迅是“思想的”、“批判的”、“文学的”;1990年代以来的鲁迅,则是“文化的”、“矛盾的”、“历史中间物”等多元化的。[1]由此可见,无论是研究者对鲁迅形象的建构,还是人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接受与解读,都经历了一个变化与起伏很大的历史过程,而这种情形还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说,关于鲁迅的思考和界定仍然处在嬗变不居的“未完成”状态。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鲁迅研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历程:李长之在1930年代撰写的《鲁迅批判》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普遍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角度来感受与评说鲁迅,否定了鲁迅思想家的地位,突出了作为文学家和精神战士的鲁迅形象,相比较同时期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知识分子稍显政治化的鲁迅研究,李长之具有自己的独特研究角度,那就是他通过文本细读深刻感受到了鲁迅内心的孤独,体悟并把握了鲁迅的思想性格与精神状态,努力复原鲁迅的真实面目,因而影响深远。建国后,王瑶和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影响较大,王瑶的专著《鲁迅与中国文学》从宏观角度对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性研究,以揭示鲁迅文学世界的面貌。曹聚仁曾与鲁迅交往密切,其于1937年编著的史料汇编《鲁迅手册》对鲁迅研究而言颇具价值;建国后,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一书,该书从多角度、多侧面对鲁迅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与评价;1967年,曹聚仁又出版了《鲁迅年谱》。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以其资料的翔实可靠和评述的客观公允在海内外的鲁迅研究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仍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19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界人才层出,成果丰硕,陆续涌现了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孙郁、张恩和、孙玉石等著名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论著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生平思想、文化意义等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与研究,其有关论著视野开阔,理论方法新颖丰富,研究成果斐然。例如: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以鲁迅的《野草》为论述重点,寻找“历史伟人与平凡的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对鲁迅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予以全方位的揭示;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对鲁迅思想及鲁迅小说的文化意义作了深刻的阐发和高度评价;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鲁迅与孔子》,围绕着鲁迅的爱情及鲁迅与“国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剖析;孙郁的《被亵渎的鲁迅》、《对话鲁迅》,论述并探讨了鲁迅在不同时代所遭遇的严重误读,提出了鲁迅被边缘化的悲剧性命运的等沉重话题……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论著,是新时期以来多维视野中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些著作对于纠正以往对鲁迅的误读和歪曲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也为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进一步走近鲁迅、理解鲁迅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参照。
在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界,“回到鲁迅”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其目的是要求研究者能够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要还原历史的、真实的鲁迅,当然离不开对鲁迅原始资料和文本的认定和梳理,因此,在“回到鲁迅”的口号声中,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早期的创作原典(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呐喊》、《彷徨》、《野草》为标志性文本) ,藉此重新发现作为启蒙思想家和“反封建思想革命”先驱者的鲁迅,回到一个有着独特心灵世界的“孤独者”形象鲁迅那里……在这些阐释和解读中,大多数研究者把视野集中到了鲁迅个人身上,或者把目光聚焦在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或者把目光聚焦在鲁迅生命的孤独感和悲剧性,并以此为基点,从启蒙运动的起源意义上追寻鲁迅启蒙思想和生命意识的源流和嬗变,从而把鲁迅与“现代意识”和“现代性”联系在了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痛苦的启蒙主义者形象。近些年来,研究者们重提“回到鲁迅”的口号,力图让曾经被高度政治化、符号化了的鲁迅回到个性化、感性化的“文学鲁迅”的层面上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往对鲁迅的认识主要侧重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主要关注点是对其启蒙思想的客观效应的阐释,对作品的解读也主要集中在文化评判层面,对其文学作品本身的诠释及其“现场”效应关注不够。因此,再度强调回到“文学鲁迅”的层面看鲁迅,一是要回到“五四”文学的原生态环境看鲁迅,一是要以鲁迅创作的原始文本为依据看鲁迅,再者是要在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及其相关的现代性思想流变的意义上看鲁迅。这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构成鲁迅创作和思想的“历史现场”,由此才能真正地还原和彰显鲁迅创作和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关于鲁迅的接受和阐释是一个不断积累又不断超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形象及其价值和意义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单一、感性,到整合、全面、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不断突破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盲区或文化盲点,不断对鲁迅创作和思想进行重新发现、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下简称《启蒙与革命》) 可以说是近年鲁迅研究一个扎实的成果和可喜的收获。
《启蒙与革命》以“启蒙”和“革命”这两个中心概念为理论原点,展开对“鲁迅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述。不难看出,作者对鲁迅文本的细节和鲁迅相关历史事件的原始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逻辑清晰、层层推进,行文隐含着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情感立场,理性的分析中时时透露出“知人论世”的理解与感悟。全书围绕着鲁迅对“现代性”的选择与坚守透析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矛盾冲突,力求还原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的独立姿态和历史形象。赵歌东指出:当前一些论者在使用“现代性”概念的时候,往往“在没有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种种歧义做出历史分析的前提下,简单地从传统性、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角度质疑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合法性,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质疑和否定包括鲁迅创作在内的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2]1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从“现代性”意义上还原鲁迅的真实面目,首先要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上,对“现代性”的辞源与词性进行历史的梳理,划定出“现代性”扩张从西方到东方的概念内涵和历史外延,才能对鲁迅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恰当的定位分析。这样的理论视角展示了作者稳重的现代性历史观和严谨、负责的学术态度,为全书奠定了历史的、理性的学术品质。
赵歌东对“现代性”概念作了综合性的历史分析:“现代性”谱系是一个以“现代”为词根的复杂话语系统,这一复杂的话语体系包含着“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后现代”等多重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知识谱系的主体结构。[2]1在书的绪论部分,作者从“现代性”最初的辞源与词性开始,讨论了现代性在审美、社会、文化和技术层面上的涵义,回溯了“现代性”的历史和历史中的“现代性”,区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以“天才的个性”为表征的现代性,和以对理性的崇慕为表征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显示了作者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素养,这也使得《启蒙与革命》一书的立论坚实而富有历史感。
正如赵歌东所言:“现代性”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首先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次是欧洲历史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界标,再次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文化属性。西方的“现代性”以“人的觉醒”为历史背景,并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进步理念之上——“人的觉醒”需要建立健全的理性,而确立健全的理性需要一个以“现代性”的认同与扩张为源动力的启蒙过程。赵歌东所阐述并加以肯定的“现代性”,是一种建立在此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基于“现代性”认同与扩张基础上的理性主义和进步理念的历史载体。在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外源型现代化”范式内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人的解放”这一中心论题,得以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追求接轨,加入到世界现代化变革的进程当中去,进而形成了以“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认同为源头的现代化追求。在赵歌东看来,这种现代性认同和现代化追求在鲁迅创作和思想中得到了最集中、最持久的实验,但最终并没有实现鲁迅所坚持的现代化目标。这是鲁迅个人的悲剧,也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悲剧。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从物质变革到制度变革再到思想变革,后者是从思想变革到物质变革再到制度变革。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外源”与“内源”双重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从内需要进行思想启蒙;从外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一点上,《启蒙与革命》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鲁迅创作和思想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以“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为内涵的现代化程式。由此,鲁迅的文学史意义与文化形象得到历史的定位与确立。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作为“内源”的传统性与作为“外源”的现代性的冲突,而这一冲突的焦点在于“人”的观念的转变。赵歌东认为:鲁迅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他为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确立了“立人”的目标,并在此基点上从内源、外源两方面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启蒙与革命的现代性选择。这个结论并不完全是赵歌东个人的发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以往历代鲁迅研究者反复论证而确认的一种历史共识。但应该看到,在21 世纪的今天,自觉地认同这一历史共识仍然具有艰难的现实性和挑战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歌东的结论并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简单重复,而是对一种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历史共识的严肃重申和艰难的持守。
在赵歌东看来,作为个体的鲁迅是一个体现着矛盾冲突的综合体——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标志的矛盾实体都在他的内心与形象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些印记又恰恰体现出“现代性”冲突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的个人启蒙及生活经验就遭遇了文化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他站在“中学”与“西学”之间,从两者的不断碰撞与冲突中,对晚清的思潮做了现代性的理论整合:从“中学”方面,形成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思维方式;从“西学”方面,则确立了“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主张,由此完成了其思想上的现代化启蒙,并为其后发出划时代的“呐喊”奠定了思想基础。
赵歌东指出:从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变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期,也是鲁迅思想逐步深化、发展、成熟的时期。辛亥革命所倡导及确立的“民族—国家”观念印证了鲁迅早期的“立国”思想,而革命的失败促使他从“立国”转向以“立人”为根本的现代性追求,并最终确立了以“改良国民性”为基准的启蒙主义文化思路。鲁迅将眼光聚焦于“人”这一根本性因素,确立了“立人”这一论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由此而言,鲁迅思想及其创作是连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层政治变革与深层思想变革的一座桥梁。
从历史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这个运动本身。在思想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五四”精神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持守成为鉴别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立场的一个重要标志。赵歌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问题”与“主义”,鲁迅自己也有过“彷徨”与挣扎,但他始终坚守着“五四”的启蒙主义立场,他对知识分子的左翼和右翼同时保持着批判姿态,同时又通过与左翼与右翼的冲突和论争使“后五四时期”的文坛保持着对立统一,因此而使其思想和创作成为“五四”之后的“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现代性事件”。鲁迅的存在对“五四”之后启蒙与革命的转型、左翼与右翼的转换与融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启蒙与革命》一书对鲁迅的现代性思想与启蒙与革命关系的论述是其学术用力点,围绕这一命题,作者对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认识与分析的不同结论进行了简要梳理,从中我们看到了傅斯年、张定璜等人如何从启蒙意义的角度对鲁迅创作进行分析,肯定了鲁迅创作的启蒙主义特征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在理论上确定了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品质;看到了刘一声如何从革命的角度肯定鲁迅杂文创作的价值,却又因为狭隘的革命立场而对鲁迅“改良国民性”的现代性追求做出错误判断,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五四”之后的鲁迅研究不可避免地背离了鲁迅创作的现代性方向;我们也看到了“文革”结束后,人们在“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声中重新确立“立人”思想和启蒙主义立场在鲁迅创作现代性追求中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作者在对各历史阶段鲁迅创作现代性研究成果进行框架式梳理的同时,还呈现了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五四”精神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理解,描述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在启蒙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不断矛盾冲突中得以发展、深入的过程。这些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澄清了鲁迅研究史上的某些盲点,对于还原鲁迅的历史形象无疑是有益的。
《启蒙与革命》的论述对相关史实和史料条分缕析,史论结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例如,在分析鲁迅思想现代性追求的发生过程时,赵歌东指出: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使鲁迅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创办《新生》的经历使鲁迅初步确立了“立人”思想并重新发现了自己;加盟《新青年》使鲁迅思想由种族意识演进为民族意识,再进入到“改良国民性”,最终确立了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些论述层层深入,清晰地展现出鲁迅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启蒙与革命》一书的后半部分,作者着眼于“革命”这一关键词,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还原了鲁迅与“后五四时期”的文艺论争、鲁迅与“左联”关系始末、鲁迅与“左联”五烈士、鲁迅与“两个口号”论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再现了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路”上的矛盾与挣扎,使我们重新发现了作为革命“同路人”的鲁迅在左翼文学阵营中不得不“横站”的历史姿态。
历史地看,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鲁迅是被塑造、被阐释出来的。不论是“同路人”还是“圣人”,是“主将”还是“小兵”,甚或是历史的“中间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片面性,正如《启蒙与革命》的“结语”中所显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鲁迅形象是一个一再被误读的“先驱者”。鲁迅不是什么“圣人”,但他的思想是崇高的——鲁迅思想的庄严与神圣取决于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原创性与先驱性。对鲁迅形象“解构神圣”是要回归或还原“先驱者”鲁迅的历史本色,而不是“打倒”鲁迅。鲁迅思想是复杂的、多元的,却也是简单的——简单就在于,鲁迅确认并坚守的“立人”目标及其相应的“人的觉醒”的现代性诉求始终没有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目标没有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作为启蒙先驱者的鲁迅完成其思想涅槃并成为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固定标志。历史上许多伟大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的选择和姿态往往远远超出他们的时代。鲁迅既是时代的先驱者,又是时代的先觉者,他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还要别无选择地继续走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我们的文学还没有完成“人的觉醒”的历史使命,鲁迅思想及其创作就依然有继续存在并被讨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21 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连续性过程,我们依然行进在20 世纪以来“追求现代性”的历史道路上。因此,今天谈论鲁迅及鲁迅的意义仍然是必要的,我们需要通过阐释历史的鲁迅而重新发现我们自己。这也许就是《启蒙与革命》这本书值得我们关注与重视的理由所在。
[1]徐妍.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0.
[2]赵歌东.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