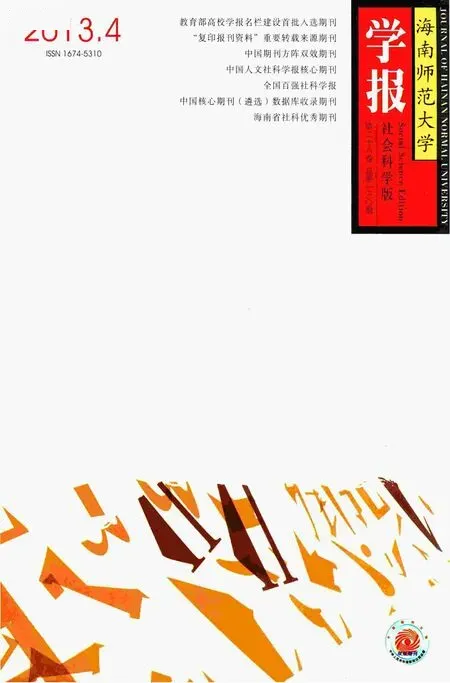杂糅与裂隙:海南本土作家地域书写侧记
王瑞瑞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
海南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自古以来都是备受冷落的偏远之地。黎族文化深远地隐藏在这个安静的角落里默默无闻,直到贬谪的苏东坡在这边隅之地留下了些许文化馨香,使中原的气象略略有所存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足迹使海南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红色娘子军”的革命想象在这片土地上萌生,也意味着海南文学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建省到目前国际旅游岛计划的实施,海南这片弹丸之地不仅成为人们捞金淘银的“福地”,也成为知识分子争相奔赴的热土。外来文化随移民作家的加盟携尘而来,与本土文化成对照之势,在两者形成的张力推动下,海南文化自身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但整体上讲,外来作家仍受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影响,海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积淀并没有很好地在这些移民作家身上实现血液的替换——他们要么在椰林小径里继续构思着故土的故事,要么已经放弃地域的想象而实现思想性转型,又或在网上开拓另一重写作空间。总之,海南的地域文化在他们的小说中终归是浅唱低吟,即便是80年代所形成的“大特区文学”也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书写场域而已。
即便如此,文化也不是凝固的“神话”,而是持续性地处于交汇生成之中。海岛于80年代加速进行的现代化,既吸引了外来人才,也带来了以现代性为根本特征的外来文化。当外来事物登陆特定地域,必然会与之产生相互碰撞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可以有效地辐射在本土作家身上,使他们产生对故地新的文化想象,并灌注于作品之中。以现代性为总体特征的外来文化与海南本土文化相交汇,形成了一种风格独异的文化杂糅。这一进程给本土文化带来新鲜血液,也带了撕裂性的疼痛。因这一进程还在继续,本土作家很容易就可以感触到这种对抗性的融汇与紧张。
海南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其具有“天生人天养人”的优势,正因此,人们也就相对散淡。正如斯达尔夫人对法国南北文学区别的比较中提到的,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影响颇深。古代各个时期从广东、福建及大陆各地迁移至海南的人,同本地的原住民在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浸润下形成了共同的生活习性。三三两两闲散的海南人,在椰子树下成天地喝着老爸茶就是海口最简约传神的素描。经济与文化的边缘状态使岛民们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理性与进取精神,这有点符合外地人对海南人的夸张想象,即类似于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山野村夫一样不谙世事。这一想象可能疏于考虑地理、民族、历史、经济等诸因素所造成的海南文化的杂糅状态,但它起码暗示了本土作家书写实践具有的在地性。相比外来作家,他们对城市和乡村的书写无疑更能体现海南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崽崽,就是当代比较执着于海南书写的作家,对海南人的了解可谓深到骨髓,因此可以成为分析的标本之一。他的一些文本提示我们,海南人的生活仅从基本需求层面上看是富足的,“醒了就吃食”,饭桌上一定要有荤腥,吃的不好被人笑话,“吃肉好过吃药”。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席卷之前,他们是只在吃食上打转的,后来商品经济之风刮过海南,股票交易、彩票、发廊、房地产等灯红酒绿的东西也进入他们的生活。不过,现代意识与理性精神始终缺位。崽崽在小说中就塑造了许多此类底层海口人形象。海南湿润的气候及临海多水的地理优势造就了一批从事渔业的买卖人,而80年代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优化了职业结构,随之诞生了一批出入公司的小职员。即便在后者身上,也鲜有内地大都市那种快进的节奏。他们日常生活散淡,流连于街头巷口、老爸茶店或夜晚的宵夜摊椰子铺,这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场所与海口人懒散的气韵共同构筑起世俗化、生活化的文化景观。相形之下,外来移民则带着与本地人截然相反的性情踏足这片慵懒的城市,他们不管是刚刚起步的创业人还是成功的企业家都带着激情与渴望,不想让生命中的分秒浪费。这种差异有着文化的根源,但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影响作家的文化杂糅。
二
文化杂糅以地域为前提,它已经成为海岛本土作家的生存处境,成为他们无从逃离的书写宿命。因海南经济起步较晚,这种以现代性进程为主要动力源的文化杂糅的出现也是最近的事。尤其在海口这座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差不多成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他们与本地居民构成了有趣的对照。从整个海岛来看,现代性进程则是一个“野蛮”的闯入者,它“蛮横粗鲁”地破坏了原生地域文化生态。海南一些敏感的本土作家,对这些文化“痛点”有着深切的体会。
尊严问题就是文化杂糅情境下海南本土作家常涉及的一个文化“痛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重塑人的尊严的巨大力量。尊严与自我认知有关。也就是说,它与身份认同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在慢半拍的海岛上,人们捍卫尊严的方式带有浓烈的泥土气息。不过,在杂糅的文化处境中,身份认同容易出现错乱,自然容易导致尊严观的错位与混乱。《不识字的阿辉》中的阿辉去鱼塘偷鱼,被警察逮到时,“他转过身,一只右手在裆里掏,那些人又笑,我不知他们笑什么,却见阿辉从裤裆里拖出自己的家伙来,用手握着戮了三几下,那家伙蓬勃起来,像剥了皮的眼镜蛇,嫩红赤亮狰狞吓人。”[1]阿辉最终用猥亵的姿态和愤怒的目光逼退了警察,赢回了些许自尊和生存的权力。而《谷后街》中瘫痪年迈的奶奶舍弃老脸将裤裆中的“老母毛”贴在了追赶孙子的汉子的嘴唇上。这些为生存的尊严而做出的举动令人震撼,它与粗鄙、下作、自辱相伴而行。行为无形中已消解了尊严的本来意义。福柯曾谈及尊严问题,他更为关注尊严中的自我因素,即有自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尊严。也就是说,应通过“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2]关注自我(涉及身体、灵魂、思想、存在方式)是“自我技术”的关键,只有关注自我才能实现人自身的尊严。这在崽崽的小说《我们的三六巷》中有着很明显的体现。外地人“闯海”是穿插小说的一条主线,文本将外地人与本土人放在同一故事空间中进行对照,他们性情各异,但大多缺乏一样东西:尊严。卓金在其小说中俨然是一个完美的人物,本地男孩吉仔经由卓金的引导,在接触社会的一系列事件后逐渐地完善了自身人格,并有了一种更加健全的社会尊严观。这不妨说是崽崽的刻意为之,外来文化价值观在与本地的互相试探冲突后达成了完美的融合,而吉仔则是这一过程后的理想构型。我们从饮食文化上看出海南人朴实率直的品质,“我们海南人吃东西就讲一个鲜字,吃东西就吃一个味。……就是清水白煮。……你们大陆人就爱自己骗自己,花椒、辣椒、八角。”[3]海南人原汁原味,没有大陆人的精明与圆滑。对吃早茶也特别重视,穷的喝茶吃包,富的啃鸡爪,下猪肚牛杂,无论福穷,总要在茶店折腾一上午,谓之吃“韵味”,甚至公司、单位开会也要挪到茶楼,边啃鸡爪边领奖状。在茶楼里吹天谈地,在行动上却畏缩不前。外来的闯海人则充满了奋斗精神,三六巷人每天吃茶逗乐看着卓金、琼生、星星等外地人从穷困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奋斗目标,却只会说“小富在俭,大富在天”,或者为邻居盖房子几平米地之类的芝麻小事争得面红耳赤。当然,崽崽更着重于对“原住民”人性的思考。他谈到吹牛时说,海口人某些人吹牛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某些外地人吹牛,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只是一个台阶一个序幕,一场好戏跟在后头呢。[4]只有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获得自尊,也才是赢得尊严的关键。但我们从福柯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奉行功利主义也许会一时成功,但人却异化了。所谓的“成功人士”无不处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笼罩中。经济社会人往往沦为物的奴隶,譬如琼生的金钱至上,李梦莲的沉沦物欲世界。很多闯海人最终都成为被物质操控的提线“木偶”,而吉仔则实现了精神的升华,阿霞也从三六巷狭隘自私中逐渐通达了敞亮的境界。
显然,面对物欲重围,人的品格还是要留存那“原汁原味”的素朴才好。海南本土文化中特有的慵懒、散淡,有时或可成为现代性急躁冒进的一剂解毒良药。探讨人的尊严和精神的缺失,这是崽崽城市叙事的重要主题,也是很多本土作家持久关注的。如韩芍夷的长篇《驿动的年轮》、吉君臣的《丽人出城》,都力图在物欲横流的都市寻求精神重建的可能。显然,这些本土作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回望乡土,希望从那里重寻灵魂的力量之源。
三
现代性进程席卷了海南的城市,这里的霓虹灯又引诱了它大大小小的县城和乡镇,五光十色物质生活的背后是欲望的持续性发酵。准宗教的巫文化一向是中国人值得信赖的精神依托。但在现代性的洗礼中,这一巫性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当天上三尺不再有“神明”时,乡民们的精神该寓居于何处呢?这些乡民们的精神苦恼,正是作家想挖掘的。本土作家林森的小说《关关雎鸠》以带有地方特色的笔墨呈现了小镇人人生的困境,揭示了海南人的情感和精神危机。军坡节装军、看婆祖、拜五海公是瑞溪镇人历来非常重视的事。军坡节是为纪念女英雄冼夫人而举办的民间节日,在这天装军是振奋人们精神的重大仪式。凡谁家有病有灾让六角塘村的婆祖想个解救之法必定有效,五海公则是全镇人的神明。很快,小镇开始有了新生事物,白小姐的彩票、吸毒、永发镇嫖娼、啤酒机赌博、色情录像厅和迷情脱衣舞,花花绿绿,应有尽有。总之,一切都变了。老潘家祖孙三人平凡无奇,但生活却已波澜迭起了。宏亿吸毒不能自拔,宏万买偷来的摩托车连累父亲坐了监狱,老潘则在老伴和儿媳妇的逝去中一天天愁苦终老……现代性的消极力量强力地挤压着人们的精神空间,并惩罚性地将他们抛到了神性荒芜的“世俗之城”。军坡节取消,年轻一代美好的记忆不在,尽管后来发掘民俗,又恢复了装军,甚至增添了许多莫须有的文化节,但小镇民俗传统的精魂早已丧失殆尽。婆祖的解救已经无效,五海公也再不显灵,没有根的人们散若飘萍。小镇的年轻人想逃离小镇走向都市,而老一代人依旧缅怀有着祖屋的乡村,像老树一样枯守着那片精神的废墟。
乡土一向是当代作家纵情书写的对象,也是作家寄托梦想的地方。单纯的乡村,不含任何杂质的田园意象,成为作家当然的文学想象。海南本土作家如符浩勇、郑庆杨、符兴全等,有许多反映乡村生活的小说。它们着力于描绘海南农村独特的风俗民情,挖掘乡下人纯洁朴素的品质,并批判了商业文化和城市文明,体现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比如符浩勇的《金嗓子》。不过,乡村并不是一个宁静封闭的恒久结构,它从来就挟裹在历史时空的变化中,受到现代性持久的挤压。逃离还是回归,似乎是作家永远的心结。
这当中,林森的小说具有代表性。它体现了一种弥合裂痕的冲动,即将过去和现在,乡村和城市汇通起来表达的诉求。[5]这勿宁说是文化杂糅的别一种文学想象。它力图超越审美现代性的单纯批判,去获得一种更广阔、深远的文化境界。但现代急速前行的列车显然无心为此停留,它并没有为这幽怨的文化美人单设驿站。小说奏响的仍旧是一曲忧伤的文化挽歌。它不仅表征了一种自我确认文化身份的困境,而且恶化为生存意义的完全缺失,逃离已成为惟一的出路。[5]在《风满庭院》中,“我”一个体弱多病的大学生回到乡村家里养病,却无法得到安静。村里的牛相继死去后,人们请“师傅公”作法驱灾辟邪。这显然无法遏止村里接二连三的灾变。修路造成村里人的分裂,而与邻村的冲突升级成血案,“我”不得不匆匆逃离。乡村生活的沉寂表面看似令人向往,但这个曾经“有安详宁静有美丽有灵魂归属的村庄,也同样有丑陋、愚昧和粗俗”。[6]先祖和师傅公的做法无法阻遏历史和时代生活的变化,老潘也回不去心灵的乡村,惟有布满尘埃的祖先祠堂静静地守候着。
[1]崽崽.不识字的阿辉[J].山花,2002(11).
[2]汪民安.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1.
[3]崽崽.我们的三六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104.
[4]崽崽.海口人[J].天涯,1995(6).
[5]林森.序[M]//小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6]林森.风满庭院[M]//小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