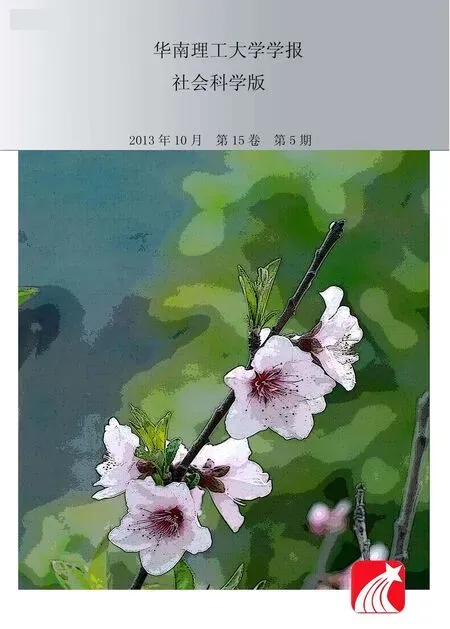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蔡元培与郭秉文办学理念比较
韩立云,张 燕
(1.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2.陆军航空兵学院,北京 101123)
北京大学之父蔡元培与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是中国近代两位著名的教育家,两位先生分别主持了20年代的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使两校在短期内均有了快速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是风格迥异的两所国立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与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也有所差异。但考察其深层的理念,二人在办学中又具有许多共同的内容,这些共性是办好一所大学所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所有大学理应具备的基本办学理念。这对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蔡元培办学理念
蔡元培一生教育论著颇多,对于大学办学理念有其系统的理论,他的这些理论最重要的体现是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改革,这次改革使北大从“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同时也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教育自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如杜威所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蔡元培的办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完全人格,五育并举
蔡元培对培育学生的国民意识和完全人格非常重视,认为“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2]14他的这一思想在教育方针上体现为“五育并举”。他在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指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并在其后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对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个方面,“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他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核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来培养具备完全人格的人。
(二)教育独立,教授治校
蔡元培主张教育应超然于政府与教会之外,他于1922年3月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全面阐述了他的这一主张。他从“完全人格”教育理念和教育自身规律出发,倡导“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由于政党扼杀个性、急功近利与不稳定性,“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同时,教育也应独立于教会。因为,“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具有许多共性,是自由的,而各种不同的宗教之间则具有巨大的差异,彼此对立而不相容,“若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3]337在北大改革中,他力倡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北大设立评议会,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是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构。
(三)昌明学术,重视科研
蔡元培几度到德国留学、出访,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坚持“学术本位”,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5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进一步明确大学的性质:“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4]6他强调“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5]627蔡元培认为学术不仅与大学发展有关,与国家昌盛也有密切关系,“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6]330因此,他首先在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作为研究学术和培养研究生的专门机构,同时,亲自或协助创立了各种学术团体,开展各种学术演讲。
(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不仅重视学术研究,更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1919年8月,在《传略》(上)中,他在回顾总结人生经历时,对这一方针进行了概括性表述:“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4]332因此,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等各种思想“樊然并峙”;各类人物如提倡白话文者、主张文言文者、复辟论者、西化论者等“汇聚一堂”。正如马寅初先生所言:“当时在北大,……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7]62
二、郭秉文办学理念
作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学博士,留学美国的郭秉文深受美国大学办学思想和管理体制的影响,他将当时较有活力的美国办学模式引人中国,在南高基础上创办东南大学,并使20年代的南高—东大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重镇,以至孟禄博士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8]232-233由此可见,当时东南大学的地位和影响。郭秉文的办学理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持诚至善,三育并举
郭秉文主张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他坚持“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主张通过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而使学生的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各方面都得以“相当的发达”。他以“诚”为训,提出“中庸言诚,包智、仁、勇三德。希腊人恒言健全之心寓健全之身,盖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9]56-57“诚”便成为郭秉文三育思想的根本,“诚”育德、智、体,以“诚”为训,即“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10]60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将校训改为“止于至善”,要求师生的言行品性臻于完美。他借东南大学所在地南京的地理环境,期望学生具备“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这样一种国士的风度和气节,惟真是求,惟美力修。[11]3在持诚和“止于至善”校训的熏陶下,形成了南高—东大诚朴勤奋的学风。
(二)三会一体,自动自治
郭秉文坚持教师、学生“自治自动”的方针,在就任南高校长后,便对校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撤销了学监处,组织各种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实行校务会议制度。东大成立后,1923年4月《国立东南大学一览》中进一步明确教授会、行政会和评议会 (三会)的组成人员及其职权。教授会由校长、各科、各系主任及教授组成,主要负责教务教学事宜。行政委员会是全校的行政总枢,由校长及由校长就本校职教员中委任委员组成,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评议会由校长、各科代表 (各科主任)、各系代表、行政各部门代表、附属中小学代表组成,负责全校重大事务的议决。由此可见,学校教务和重大事务的决定是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和评议会来做出的,体现了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三会一体制”加上校董事会,形成了仿效美国的大学模式,兼具民主与效率。
(三)学术中立,教研并重
他素来主张“学者治校、学者不参与政党和政治”,推崇学术自由。各种学说、主义、问题,只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均可以在大学里讨论、研究、讲授。正如吴俊升所说:“公治校方针,对于延揽人才,确能兼容并包,无政党及学派之分。其时国民党在校任教者有陈去病、顾实诸教授;讲学者则有研究系之梁启超、张君劢,社会主义者江亢虎诸先生;学生中有国民党员、青年党员,亦有共产党员。但在校内只许作纯粹学理研究,不许作实际政治活动。”[12]9-10由此可见,郭秉文是秉承学术自由理念的。
郭秉文对于大学的见解与蔡元培有所不同,他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非仅办一二科即可以餍学者之望”,[13]99一所综合大学,应该既包括偏重学理的文理科、教育科,又包括偏重应用的工、农、商等学科。郭秉文非常重视教育教学,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同时与蔡元培一样,重视学术研究,坚持学术自由。尤其在考察了欧美教育状况回国后,他更强调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学术之研究,应特别提倡,为国家根本计,学术不精,则凡百不能进步。我国杂志书籍,大都译自东西洋,自著者甚少,现象如是,自己固自进步,而对世界毫无贡献,安望能得列国之信仰。”宜“多设研究会,尊重发明家,则学术自有发达之望。吾人纵不能有所发明,而尊崇学术固应尽力提倡是之。”[14]
(四)四个平衡,注重科学
郭秉文晚年将平生办学体验,归结为《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1、通才与专才平衡,即大学培养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又不能截然划分”,这样才能“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才能使大学生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15]12、人文与科学平衡,即人文与科学平衡,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兼具科学素养的复合型毕业生。3、师资与设备平衡,即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这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南高—东大培养人才的最成功之处,便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同时建成了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及实验室等,为教学和科研创设当时国内一流的硬件条件。4、国内与国际平衡。郭秉文之所谓国内与国际的平衡,一是要使东南大学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中心,二是要使东南大学成为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的窗口。
三、两位校长办学理念的比较及启示
蔡元培与郭秉文办学理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蔡元培对于大学的定位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认为“学” (学理研究)与“术” (应用科学)应当分离,郭秉文则认为综合性大学应学科齐全,“学”“术”结合;蔡元培在北大期间对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使北大以“人文”著称,郭秉文则将科学社迁入南高—东大校园,使东大以“科学”名世。然而,深入考察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其中包含诸多的共性:第一,在人才培养方面,不论是蔡元培的五育并举还是郭秉文的三育并举,都是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具有“完全人格”的人。第二,对于大学的任务,都注重学术研究,学术的进步是科技进步的前提,也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源泉。第三,学科建设方面,均注重基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论是北大只设文理法科,还是东大学科较多,但都非常强调文、理科的发展,而且均把文理科合并,强调基础学科建设和通才教育。第四,主张教育独立方略,实施“教授治校”,顺应教育民主化潮流,北大和东大均按照教育部规定设有教授会和评议会,而作为其组成成员的教授拥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教学事务均由教授会议决。
在对两位校长办学理念的比较中,我们找到了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第一,每所大学理应有所有大学都具备的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具有自身的特色,应当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需要创建综合性大学,但并不是要每一所高校都成为综合性大学,学校发展也并不是只有大而全才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盲目扩大学校规模,纷纷设立各种学科,不顾自身条件都要建设成为综合性大学,结果是新的学科没有发展好,原有的优势和特色受到冲击而消退,致使现在很多大学不管大小,“五脏俱全”,“千校一律”现象严重,失去了学校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学校发展要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学科,不能贪图大而全。世界一流的大学也不都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是一所小而精的大学,她没有最热门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却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中有31位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
第二,大学应当是独立自治的,政府应当是“无为而治”的。随着大学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日益紧密,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也更加完善,但大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其发展应按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应当维护它的独立自由,大学必须是独立自治的。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教育资源多半来源于国家和政府,二者不能不存在某种关系,问题的关键是二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申素平认为,政府是“公立大学的举办者”,是“所有大学的管理者”,但“不是大学的办学者,对公立大学不是,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大学也不是”。[16]为此,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成为“有限的政府”,作为举办者,为学校制定大学章程,任命学校决策机构成员,为大学提供必要的办学条件和稳定的办学经费;作为管理者,主要为调控和服务,包括制定教育标准,保证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发展,规范教育活动的行为,做好教育服务工作。[17]113政府需要转变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职能,给予大学应有的自主权,这是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
第三,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完全人格”的人,而不是把人培养成“工具”。教育应当服务于人本身,而不是经济或者政治,教育一旦受制于经济或政治,便失去了教育自身。然而,受实利主义影响和服务社会的需要,专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教育过分重视其工具价值,而忽略人文素质和价值理性,人的发展走向了片面。单纯的专业教育还远远不够,“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激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和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18]310因此,大学教育要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来进行,使受教育者懂得人之为人的价值,明白人的生存价值和追求目标,并创造各种条件,进行素质教育,使学生发展成为人格健全、人格诸要素协调发展的“完人”,同时培养其健康品质和创新意识,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使其成为复合型新型人才。
第四,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当注重学术研究,坚持“学术本位” “学术自由”,恰当处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这三大职能之间的关系。教学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学术研究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而服务社会是教学、科研的最终目的,三者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的。学术科研的发展要求自由,“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算不上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的神圣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19]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实用主义兴盛时期,大学成为了社会的中心,成为了社会“服务站”,致使是否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了评价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的标尺,大学不再是一块平静之地,不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象牙塔”,这无异于舍本求末。因此,高等教育改革尤其应当提升教学和科研的地位,还大学其本面目,正如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所讲“建几所象牙塔又何防”?
第五,大学应由真正懂教育和学术的教授来管理教育教学事务,坚持“教授治学”。教授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教育又有学问,让他们直接参与决定学校大事,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又能使学校管理走上民主化轨道,为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学校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当前,我国大学学术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学术行政化,这一方面是受“官本位”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术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资源配置方式是行政化的。[20]要保证学术权力的正确行使,就需要政府给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大学赋予教授更大的学术权力,并注重学术研究相关制度建设和校园学风建设。
第六,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的创新是长远大计,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教育如果过分关注应用,那么最终会导致核心创新能力的匮乏,影响到应用学科和前沿学科的发展。“基础学科是大学发展的基石,是应用学科开发的前提和后盾,是催生高科技成果的源泉。”几乎所有一流大学都以建设强大的基础学科为核心。[21]人文素质的提高是高素质人才必须具备的,而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建设是建立高水平大学必须具备的,然而目前我国大学学科发展的问题是科类结构失衡的现象严重,自然科学“重应用轻基础”,人文社会学科“重经管轻人文”,文理学科“重理轻文”;学校建设方面却是重视物质建设轻视精神文化建设,“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研究或学术水平的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如何创建一种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22]因此学科建设在突出优势和特色的同时,要加强基础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建设;大学总体建设要注重学校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建设。
[1]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版),1998,(2):42-55.
[2] 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 [M]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3]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M]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蔡元培.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 [M]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M]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6]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M]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7] 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陶行知访罗钧任后致郭秉文函 (1922年11月4日)[M] //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 (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 (1918年10月)[M] //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 (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12] 吴俊升.业师郭鸿声先生教泽追思录 [M]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13] 国立东南大学缘起[M] //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 (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 郭秉文.战后欧美教育近况 [J].新教育,1912年第2卷第4期:395.
[15]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16] 申素平.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政府角色的转变[J].高教探索,2000(4):50—53.
[17] 董云川.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18] 爱因斯坦文集[M].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9] 谢泳.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J].东方艺术,1997(4):20-22.
[20] 纪宝成,胡娟.关于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 [J].中国高教研究,2010(1):1-4.
[21] 陈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学科建设[N].科学时报,2009-6-2.
[22] 陈维嘉,洪成文.耶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和借鉴[J].中国高等教育,2004(23):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