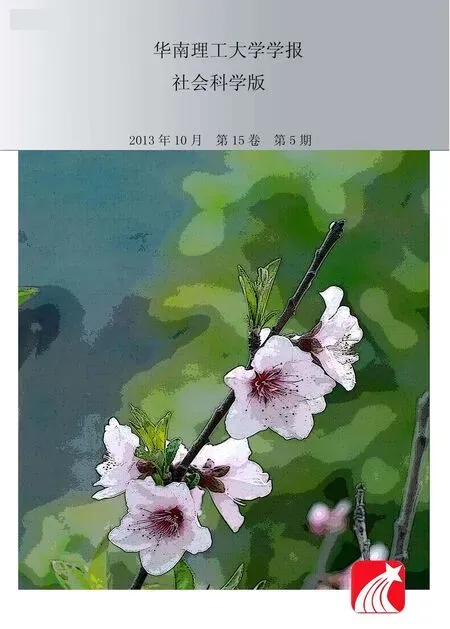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苏全有,李伊波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新军开始大规模逸轨的重大事件。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多取自下而上视角,着重从革命党人的角度进行剖析,且多拘泥于革命情结,如王在民《广东新军的“庚戌起义”》[1],方忠英 《庚戌广州新军起义》[2],黄大德《从新发现的庚戌新军起义资料谈起》[3]等,然自上而下探究庚戌起义时政府作为的研究却较乏见,清政府成了忽视的对象。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政府视角出发,考察清末广东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失策之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
自近代以来,广东以其独特的海陆位置、密迩港澳的便利条件及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省界观念”[4],屡次成为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发难之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所策动的十次起义,除1907年12月丁未镇南关之役、1908年4月戊申河口之役外,其他八次起义均发生在广东。在庚戌新军起义爆发前广东大地上已发生过1895年10月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10月庚子惠州之役,1907年5月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6月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9月丁未防城之役,1908年3月戊申马笃山之役六次起义。如此高密度的起义纷纷在广东一省揭橥而起,势必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然事实上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之际,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上却存在诸多失策之处,欲弥患于未萌,当难以实现。在庚戌起义未萌之前,清廷广东当局主要存在如下失策之处:
(一)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
《大清光绪新法令》中关于新军军制的条款“募兵制略”格式四、五载:“来历必须土著,均有家属,应募时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品行:犯有事案者不收。由各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各举合格乡民,开具名册,偕赴该选验处所听候点验,勿许滥保游民溃勇。”[5]4然此次新军起义的领导者“倪映典为安徽合肥人,与熊成基等进行革命活动,已升任至管带,后因有人告密,乃改易姓名,出走广东,仍投入新军。初为见习官,后任排长,在新军中具有很高的威信。”[6]68且倪映典不会说粤语,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报刊《一三专号》载《倪先烈映典传略》记云:“兵士上讲堂时,烈士因言语不通,大书‘汉亡二百六十余年’粉字于黑板上,兵士皆首颔,烈士心喜。”[5]130另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编的《一九一○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载,“映典是安徽人,为人慷慨激昂,做事勇敢,常自誓为革命牺牲。到广州后因为语言不通,革命活动很感困难。”[7]86倪映典外域特征当甚明显,清廷广东政府募兵官弁之不察失职如此。
此外,粤督袁树勋上奏称,“窃查近年新军滋事,不仅一省,就粤论粤,有总因焉,有远因焉,有近因焉。上年八月间,宪法编查馆会奏覆核陆军部筹备事宜,单开‘城市游惰之民则不宜征,广西等省匪党夹杂可虑,则不便征’等语,实为洞见症结之论也。粤省从前仓促征兵,所谓游惰而夹杂匪党者,不敢谓其必无;此总因也。既有游惰及夹杂匪党之虑,故投营之时,军心即不甚固,逃亡之报告,既月有所闻,而港、澳密迩,匪徒乘间煽惑,防不胜防。”[5]152-153亦从侧面道出新军征募时的敷衍塞责。
(二)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
清末政府为控制军队,强化统治,遂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欲在全国建立36镇。在编练新军的同时,为适应其对人才需求,在练兵处督导下与之配套的军事学堂在各地亦纷纷兴办起来。军事学堂做为新军官弁的生源之地,对其学员进行严格的招募考核、思想教育自为清廷创办学堂的题中之义。然观诸其成效,犹如清廷倚新军为干城卒成其掘墓人一样始所未料,各军事学堂学员多为革命党人所煽动,暗中加入同盟会,况且有大批党人屈身应募,潜入新军及军事学堂,布满革命种子。作为镇压新军起义的清军管带李景廉的同乡及旧友陈景吕在《我所知道的庚戌新军起义之役》中说道:“现在革命潮流,日渐高涨,草泽英雄,类多参加革命……李景廉说:我们陆军同学,多数暗加入同盟会,时机成熟,自当联同反正。”[8]34
此外,革命党人徐维扬编的《庚戌广东新军举义记〈革命之远因〉》中载:“未几,雨平与张醁村、刘古香等因倡革命,触当局之忌,被革退,乃在广州暗集同志,与朱执信、邹鲁等联络进行,各因所知,分途运动。陆军速成学堂、虎门讲武堂学生多表同情,而陆军学兵营尤为活动。盖是时清吏派黄士龙设模范学兵营,遣人至恵、梅及北江等处征兵,维扬投笔应征,而各属党人亦多屈身应募,赵声为陆军第一标统带,又从而提倡之。陆军之中因而布满革命种子。”[9]306-307同盟会元老莫雄在《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将弁学堂与新军〉》中亦有类似记载:“将弁学堂以韦汝聪为指挥官。上校营长黄士龙,第二任营长王体瑞,学兵营步兵第一队少校队官陈昌言、第二队队官邓拔,炮兵少校队官杨其伟、邓锵、李济深、叶举、伍冠球等人都是学兵营的排长,张文、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徐维扬等都是学兵营的学兵。上述将弁学兵营的队官和学兵,多是同盟会员,而陆军速成的学生姚雨平、张醁村、张我权、何克夫、林震、刘古香等人也是同盟会员,他们参加新军之后,新军的革命运动逐渐扩张活跃起来。”[10]81-82
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及新军营中,势必会引起新军的思想失范,造成政府对新军控制力的极大削弱,其亦是广东新军逸轨的重要原因。清末广东政府对新军捉襟见肘般的控制力一大表征为广东新军中的基层军官及士兵的纷纷入盟。
革命党人“经常利用星期假日,邀约官兵去白云山附近地方集会,演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山东黄海之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王入粤等惨痛史实”,其目的在于揭发清廷腐败,辱师丧国,必须推倒。这样的演讲,效果极佳,“常常感动得新军们抱头痛哭”。[11]86
党人莫纪彭在《由庚戌新军之役到黄花岗之役》一文中亦载道:“倪秉章主持新军运动,军官们奉他为革命大师,广州城内外设有四五个革命机关,自天官里、联胜里、清水濠以迄同庆坊。机关里每当星期日燕塘军官穿皮靴带长剑来听秉章演讲三民主义。半年工作,把燕塘军官由见习官级、连排长级,百分之八十向同盟会宣誓,加入同盟。士兵百分之百加盟,更不在话下……这时驻燕塘全部新军,已尽是革命党了。全部新军力量变成了革命力量”。[5]85-86
同时,革命党人在营队中成立“党代表”组织,架空了新军官长对军队的控制,使其失去对新军的军事指挥权。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编的《一九一零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载:“倪映典恐有疏漏,于是改变方式,先向各营队代表讲述,再由各代表向各目兵传达。因为那时的革命运动已经组织起来了,营有营代表,甚至排也有代表,负责传达指挥和联系。(新军)为预防宪兵到来收缴枪机便纷纷自动携枪离营,择要防守,并声言如宪兵敢来燕塘收缴枪机,即予迎头痛击,并禁止官兵入城。各营营长无法制止,也没有权指挥,指挥的权已属于各营队革命党人代表。”[7]
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在新军动员中成效卓著,与新军自身思想状况有关。正如孙中山说道:“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业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队;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12]494此外 《袁树勋增祺会奏新军酿变剿抚情形折》亦载云:“综此案始末言之,其总因由于无教育或自以为受军国民教育,而自由独立之说深中乎其心,如病者然,肌理不密,外感乃得而乘之,此不惟粤省为然,各省军人,滋事比比,非无意识之冲突,即受外来之诱惑,不从根本上改弦而更张之,难未已也。”[5]155袁树勋的奏言亦从侧面道出新军官弁受党人影响之深,粤省政府对新军控制近乎无能为力的窘状。
(三)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
新军军纪废弛、军官玩忽职守,亦是造成党人屈身应募、进入军队、散发盟票、鼓动思想以致新军失控的重要原因。同盟会员胡毅生、朱执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两月在《致孙中山函》中向孙中山言道:“前年倪君在粤省运动时仅费数月工夫,实因赵任标统时已种下种子,不可为例。且当时防闲极疏,外人可任便入营住宿、演说,今断不能。”[13]清廷倚为干城的新军军纪废弛如斯,昭然若揭,新军岂有不乱、不受策动之理!
军纪废弛之另一表征为着装不严。新军士兵于除夕日进城未着军装,因口角微嫌同城内刻字铺店主发生龃龉,致警兵干涉,发生军警交哄。“初二以后,暂勿放假即假亦需由官长率领,不准穿着便衣,以重名誉”。[5]153-154于此可知,新军士兵当素有入城不穿军服之习惯,军警交哄后粤督始禁不得穿着便衣,为时已晚。
莫雄在《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中述道:“清廷腐败无能,军队颓废不堪,国防设施是有名无实的。军队的服装也不像样,简直可以说没有军服,每兵只有一件传统式的红布镶黑边前后书‘勇’字的号褂一件。官兵平日均不穿军服,出兵出差或者有军事行动,才穿上勇字的号褂。军风纪尤为败坏,不少官兵在营盘之内,公开吸食鸦片,有的官长公然贩卖鸦片和开设赌局赚钱。至于在防区内包庇烟赌,收受规费,甚至借剿匪而掳掠,借捕盗而抢劫的事情是常见迭出的。这种军队腐败透顶,与其说卫国的,毋宁说是害民的。广东新军是1903年张之洞奉清廷命令,在武备军、武匡军的基础上整编而成的。但官兵的旧习惯重,质素很差,名为新军,实与旧军无异。”[10]69
广东新军将领平日提备不严、抚驭无方,亦是导致广东新军军纪松弛、失去控制走向起义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是年六月陆军部对广东新军协领张哲培等的审判意见《陆军部军法司驳会审拟判张哲培等呈稿》奏曰:“被告张哲培对于本案犯罪之要点如左:(一)平日提备不严,抚驭无方,致有所部军人反叛。案此。该被告于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大理院所呈递之亲供内,已供有治军无状,罪不可逭等语。虽探求此次致叛原因,在与巡警寻仇及为要求放假二者,然世未有以平日抚驭得法之兵,而能以小故激之使叛者。”[14]61-62审理标统刘雨沛亦如斯。
(四)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
在庚戌广东新军逸轨前的1908年冬,由时任安徽新军混成协马营和炮兵队官的光复会党人熊成基发动了新军起义,时隔仅一年有余,广州亦发生类似事变,且规模与影响远甚于前。党人在清廷倚为干城的新军中策动起义,不可谓影响不大,作为腹心之患,清廷不得不予以重视,然广东地方政府的惩毖之心可谓疏忽。粤督袁树勋在致军机处、王大臣、军咨处、陆军部的《电奏讯办黄洪坤等犯情形稿》中言:“抑树更有请者,新军与逆党勾结,皖省酿变于前,今粤省又煽乱于后。其主动者,多由该军各级官长。一经获案,亦昌言不讳。”[15]
且作为庚戌新军起义的指挥者倪映典亦曾参与安徽新军起义,失败后易名潜入广东新军。莫纪彭在《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一书中写道:“满洲政府所以训练此新军,名目上系强兵对外,其实只是严防‘家贼’——制倒革命。操军事上的绝对优胜之权,一切平民草泽式的革命,从此消灭,固属满洲政府唯一的上算,即于吾辈党人也岌岌然引为隐忧,认做难与争锋了。谁知自安庆新军,给熊成基先生这一变后,把我们这一隐忧打破。一打破这个疑迷,彼练新军以制我,我便可用新军以制彼,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于我人革命的前途,反多出一条捷径了。故此我们从前的革命途径,多是向绿林土匪上用功夫,此时已改转方向,从新军上努力,放弃绿林土匪的运动,这是革命史上一个很大的转动的,这个转动不得不归功于熊先生,尤不得不归功于倪先生了。”[16]324-325清廷没有及早汲取安徽新军起义之教训,以作出应对措施,反被党人抓住机会,加以利用,成功地推动了革命动力的转型,未几便策动了亦由新军发动的清政府的掘墓之役——武昌起义。
(五)政府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
广东新军能成为清末革命的动力,从清廷之干城向掘墓人转变,虽其自身原因如“农民为主的下层群体及会党本质;海外军事留学生群体的阅历;新军知识化;学生青春期的叛逆倾向”[17]外,同盟会员的宣传、鼓动无疑起了莫大的作用。如革命党人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载述:“倪映典运动新军方法,初有香港《中国日报》代印同盟会小盟单万张,每逢假日,即邀各兵士齐集白云山濂泉寺,由巴泽宪、王占魁、甘永宣、黄洪昆、梁耀宗等演讲革命真理。兵士听讲后,纷纷取盟单填写宣誓。故进行不满一月,三标兵士入党者占大多数。”[18]204
党人不仅进行秘密宣传,而且还采取半公开的宣传方式,广东政府终未能拿出治本之策,以致新军中革命形势高涨,如干柴烈火般几欲一发不可收拾。莫雄《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庚戌新军起义〉》一文中写道:“同盟会组织在新军中的发展和新军士兵群众的革命倾向日益加强,广州附近各地的民军活动又颇活跃。从己酉 (1909)十月间开始,姚雨平、倪映典就密锣紧鼓地策动新军起义,并从香港中国报运来很多宣传品和盟单在军中散发,甚至半公开地征求士兵加盟革命,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使新军群众的革命气氛更加浓厚起来,党人尤为意气风发,恨不得立即开炮打垮清朝。”[10]75党人在节假日邀集士兵进行演讲,宣传排满保汉、进行种族革命的思想,任由盟单在军中恣意传播,足以彰显出清廷广东当局对舆论捉襟见肘般的控制力。
被捕革命党人黄洪昆供词中记载:“那总头子孙文,派人在各界运动,政界、报界取其消息灵通;学界取其智识高尚,商界取其资助钱银;军界取其胆量、人格,器械便利;绅界无用,故少运动。革命党的宗旨,专主排满,如诱得人多入党,则分别给予优等特别勋章,所领票布,系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保我汉民、矢忠矢信’等字。倪映典煽动人入会,时常言说,系分步、炮、工、辎等营,分日到白云山脚的不记名寺内,或在寺外,每次或三几百人,或几十人,多少不定。伊立在台上,各弟兄站在地下,演说是革何命,因汉人如此之多、满人仅有二成,我们多数人,受此少数欺压,轻汉重满,全无道理,专以压制手段,外国人则不然,何以我汉人专为奴隶。嗣后务须同心同德,苦志操练,听候机关命令,大众当要排满,保我汉民!言至忿际,拍案几烂,各人则鼓掌赞和。说毕,各人饮荷兰水、食饼而散。”[15]3-8
党人在军队中的恣意活动充分暴露了清廷的无能,对士兵的集会、演讲引导不力。清廷中枢于宣统二年正月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密谕,如“有聚众开会演说情事,是已越乎范围,无论藉辞何事,皆宜一体查禁,以重纪律而靖嚣张。”[5]145虽不能以今日眼光来视清廷对待聚会、演说之草率急躁态度,然亦足以窥探出处于日薄西山之际的清廷对于新军思想控制的无能为力、捉襟见肘之窘态。
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
从除夕日兵警交哄,至初一、二日的冲突升级,兵警互殴、砸毁警局,此次起义的导火索至此最终形成。初三日倪映典进入军营枪毙齐管带后,哄乱之际的新军已势如骑虎,难以收手。此时或剿或抚,清廷广东政府当取果断之策,掌握主动权,控制局势的发展。然综览此次起义爆发后清廷在应对方面却存在如下失策之处:
(一)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
此次广东新军起义爆发后,清廷广东当局的最大失误莫过于新军协统、标统等将领的临阵脱逃,以致军心涣散,造成军队指挥失灵,局势进一步走向失控。该年六月清廷陆军部军法司进呈对张哲陪等人的审判奏章《陆军部军法司驳会审拟判张哲陪等呈稿》载:“因闻所部军人哄溃变 (起),仓皇无措弃营托故走避。案此。该被告于初二日早,接到一标及协部报告新军哄溃情形后,既未能率二、三标未溃之兵,亲往镇抚。其行抵茶亭后,远望见有乱兵,并不前赴协司令本处,或带一标设法收抚;或用兵力弹压,又未向一标及炮、工辎营各官下一命令,亦未知照二、三标应付,即驰入城内等情。业由该被告于本会审中供认不讳。虽据称进城系欲向制台请示,但该被告身为协统,标营溃变,协部被劫,则镇抚是其专责,即欲进城报告,或打电话,或派弁前去可矣。其即亲身驰入城内者,显系弃营托故走避。奉令出营,观望不前。案此该被告于初二日进城后,到下午四点多钟,偕吴参议、李军门见袁督,由袁督面交大令一支,并缴械免死牌两面,一面嘱李军门派兵接应。该被告先行,吴参议随后出来说:制台教你先出城。李军门接说:你先出去罢,我兵就来。该被告于行到东门时,因想防兵随后要出来,我何不同他们一同去更好。故又折回水师行台过夜等情。业由该被告于本会审中供认不讳。是制台本意,原意抚事责之该被告,抚恐无效。又命李军门派兵接应,并非命该被告带兵同去。乃该被告一味畏葸,必欲等候防兵同出,失此可抚之时机。延至初三,遂成逆党倪映典闯入炮营及步一标杀官胁变,并率死党数十人,与巡防队抗拒之局。”[14]62
标统刘雨沛亦存在同样问题。“初二日,第一次临事仓皇无措,弃营走避,前一标执事官刘祥汉供述书上载,当乱兵冲入标本处来,声言欲杀标统,情甚危急,因保该被告穿过二营,向后营门出走。是该被告于乱兵向标部冲来,登即离营走避无疑。更按诸该被告于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自己详报督练公所内文载,由三营后方营门避脱等语,亦是情形恰合,并查该被告于初二日离营时,既未向在营各官长告明去向,亦未下有命令,致全标官长无所禀承。是其出走时之心慌意乱,历历如绘。又该被告于此十八点钟之长时间内,并未派人向标营内各官告明,自己现在何地,以后当到何地,又未向该官长等下有命令,竟将自己所统之标营,弃置度外,尤属不应。初三日,当该乱党向标部冲入时,该被告仅令卫兵闭门,未令开枪抵御,亦未下令将该逆拿住。标营兵士被胁,纷向大马路及广九铁路行去,该被告亦即离营等情,业于本会审中供认不讳”。[14]63-64
陆军部军法司对张哲陪、刘雨沛的会审可谓证据丰赡、翔实,其作为广东新军的主要领导人临阵弃营,致使失控局势进一步加剧,责任不可谓不大。
起义被镇压后,新军步队第一标第一营管带胡兆琼向粤督袁树勋报告,“迨至事机发现,又无维持办法之命令,自初二上午起事,至初三下午息事,未受张统领一字命令,亦不知张统领在于何处?以至官长无有主脑,不知何去何从?欲施之法律以抚之,则无命令不能行事 (无命令管带无杀人之权,即无安抚之力),管带只得始终在营尽力维持,以期挽回。但此次变乱,共有七营,管带亦有七员,究竟各员不顾生死尽力维持,某员逃遁退缩,致大局于不问,已在各上宪洞鉴之中。”[15]21胡兆琼的报告虽不免有为自己粉饰脱罪之嫌,但也足以明悉起义爆发后新军协统、标统不知去向,军中无主致局势至难以维继的局面。事变发生后,清廷特派遣两江总督张人骏彻查广东新军滋事情状,该大员于奏折《张人骏奏查覆广东新军事变情形折》中奏曰:“迨衅隙已成,而协统、标统等官又不善抚驭,始则一味操切,严申不准放假之令,继则相率畏避,弃营而逃。人心一摇,军情遂涣。兵士既误于报复之说,更受倪映典之煽惑,以致一旦横决,酿成惨劣之现象。”[5]221将帅弃营逃遁,导致危机的进一步升级。
(二)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
弹械的充足与否直接关乎一场战役的胜败,起义后,各界舆论对之多有评介,因新军有枪械弹药之便利,即为革命党运动之绝佳对象,如新加坡《星洲晨报》中历庚戌年一月十五日 (1910年2月24号)载文《粤垣之兵变与党人运动军界之进步》言称:“大抵凡革命党人之所抱以为恨者,即为军械之输送,盖自近年来革命风潮,日增剧烈,而清政府之防范党人,其计亦渐而愈工,彼既明知党人必藉军械以为命脉也,故对于严拿私运军火一事,殆不遗余力。然因是而党人之行动,亦未尝不为之少阻。党人知之,乃一改其方针,而趋向于军界之一方面,起事时既不虞军火之缺乏,而于平日复可稍免官场之嫌疑,使一朝反戈相向,询可谓事半而功倍,彼党人之所以不惮身入虎口,而图运动军界者,要不外夫此也。”[5]301
此次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即为枪械弹药的缺乏,起义于萌芽阶段时,广东新军当局即采取将士兵枪械弹药收缴,各营仅留一千颗子弹以防不虞之难的举措。此本清政府面对可预知的新军逸轨之灾所采取的极有效之手段,然收缴不力,终至起义爆发,但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究其所以失败之由,不过以去年底粤督得接秦提电,称军界恐有变事,各标统接密札后,于廿二九日先将枪械扳机,并子药解缴军械局,只留每营常备子弹一千,计七营共不过七千粒,以二千余众,而仅得此七千粒之子弹,且各枪亦多失去扳机,至归无用,其所以失败,有由来矣。”[5]301-302
此乃该计策得售之效,若无此计,局势失控之形势当难料想。然而广东当局未能彻底落实,即未能尽缴工程、辎重两营军械,致党人发动新军用兹作为反清之利器。起义后陆军炮队二营管带林金镜报告:“管带因即献议,一、二标子码枪机既饬呈缴,所有炮、工、辎重各营枪机子码刺刀等项,似应一律饬令呈缴,以免会党借此利器乘机滋事。张前协统允嗣初一日后再行饬缴。初二日早五点钟,管带与炮队一营齐管带各派军械长及看守城门之官长,押解枪机刺刀呈缴。因见工程、辎重两营未将枪机刺刀缴回,即速飞报张前协统。讵意令竟不行,后竟将协司令部军装器械毁坏一空,并往二标哄闹。若当时张前协统严饬工程、辎重两营,将枪机、刺刀、子码一并呈缴,则会匪何至如此猖獗?此皆未将枪机、刺刀、子码全数饬缴之过也。若严饬工辎两营将枪机、刺刀、子码悉数缴清。则无以资寇。一标乱兵已乏利器,声势自减,亦不致酿成抢夺枪码,逼胁炮、工、辎重各营哄闹二标之患。平心而论,会党无枪弹可恃,虽煽惑亦属徒劳,则工辎未缴子码枪刀,实张前协统之失计也。”[15]39-42
(三)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
至初二日,新军兵士在抢枪毁坏协司令部后,督练公所吴督办、吴参议等向粤水军提督李准推荐曾任学兵营及第一标标统、现任陆军小学堂总办、深得军心的黄士龙前往安抚、解散起哄的兵士。黄士龙沿路招劝,抚回大批兵士回营,然又至城东门继续招回散兵,不料却遭城上旗兵开枪误伤,终引起兵士再次哗变成骑虎之势,遂一发不可收拾,致功败垂成,实可惜也。起义被镇压后黄士龙对舆论声言的《黄总办士龙与各界函》称:“此次为劝谕新军,误受枪伤,以致事败垂成,大局糜烂。”[5]269
当时舆论界亦多认定旗兵的仇汉心理及官长的猜忌而激化新军的情绪,终成新军逸轨,有一定道理。如太仓在新加坡1910年4月14号《星洲晨报》登文《粤吏所谓预防军界革命者技止此耶》称:“此次广州之兵变,就其事后报纸所载之诸情形,及黄士龙之口供而论,实由官吏及仇汉之旗兵,所节节激成,而绝非由革党所主动,已为多数舆论所公认。然而政界之对于此事也,其意见乃悉与舆论成反比例,一若兵变之起,纯为革命行动,彼激变之罪,绝无可言者”。又有“夫袁督于宣示新军酿事情形之札文中,既语语认定为革命党所运动,且据被拿者之供词,亦有新军大半已入革命之说,则自政界一方面而言,其必以为新军多属革党,可不言而自明矣,益以今日袁督既有饬督练处,于星期日多派侦探,前往各山附近,密查新军有无演说革命之事,则其急于筹防军界革命之心,亦即为外界人士所尽悉矣。”[5]303-304故旗兵仇汉、总督猜忌使新军兵士情绪激化,使消弭起义最后希望亦告破灭。
(四)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
记述党人在广东组织机构之一的《广州宜安里黄寓》载:“当新军举义时,徐等即放火为号,火息后,被警察搜获革命军旗多面,警吏明知为党人机关,不予查究,亦异事也。”[18]204另革命党人冯自由《中华民国国旗之历史》载:“徐宗汉探悉所贮藏国旗之被褥为警吏移至区署,乃托女友庄汉翘取回原物,讵该被褥为火毁去一角,红布外露,警吏已查悉为党人用旗,时汉翘尚未入党,绝不知被褥中藏有危险物,茫然投警局报领。警吏谓必须物主到署亲领始可发还,宗汉至是始知事情败露,乃契汉翘逃亡香港。于此可知当时警吏不欲遽兴党狱,否则跟踪探索,徐、庄何能免耶!”[5]53警吏之玩忽职守,放任自流,对当时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党人活动置以不管不问、敷衍塞责的态度,当非一朝一夕之情状。政府机构面对危机敷衍若斯,岂能弥患于未萌。作为此次庚戌起义导火索的兵警交哄,亦是政府应对不力的重要表现。
三、善后措施之不足
此次新军起义,虽一起一蹶,仅三两日而已,然而摆在清廷广东当局面前的善后问题却纷繁复杂:溃散新军安抚、遣送问题;阵亡及伤病冻饿致死士兵的抚恤问题;遗失枪弹的召回问题;被焚营房、警局的修复问题等。其间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
在庚戌新军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广东当局不得不面对如何稳恰地处理众多参加起义的新军士兵的问题,对此清廷采取不辨良莠,不论是主动参加起义还是被胁从参加,所有降兵全部遣散回籍之策。粤督袁树勋草定善后处理意见《两广总督札行善后草章》云:“宜即由督练公所会同协、标等官,点名造册,至其解时,则一同送回原籍。”[15]33党人马锦春《庚戌之役》称:“清吏善后之策,除照例敷衍文牍外,即假退伍之名,遣回征兵甚多,新军势力因之减去大半。及至下半年重行补征,始渐次回复原状,革军亦因之略有起色。”[19]98如此不辨不分、一律遣散回籍,虽耗帑颇巨,实徒劳之策,非治本之计。第二年秋季广东第二次征兵,新军又完全改换姓名,应募入伍,重新做革命的种子,终于在武昌起义胜利来临之日,在广东起义响应。[1]48-50此外新军的过剧解散亦引起舆论界的诟病、谴责,如《小吕宋华侨致自治会函》谴责曰“虽或新军未必呼将伯之助,然当征招时,招之使来,不惜巨万教练之。遣散时挥之使去?即使投闲置散之。岂非赏罚悉成儿戏?”[5]264
新军起义失败后,广州士绅各界对遣散新军亦表深感痛惜,宣统2年正月十九日,广东方便医院、九善堂、七十二行商董郭仙舟等致军咨府、王大臣等电:“初不遽剿,驱散全军。新军于民,始终无扰。指为革命,叛迹毫无。现官绅商民,皆知铸错。今复资送回籍,新军痛苦,无面还乡。素练军人,弃之可惜。知误仍误,实难索解。乞请旨派员抚慰,招集回营。俾速成镇,大局幸甚。”[5]275宣统2年正月20日,香港华侨全体、冯爵臣、谭少及等致军机处、军咨府等电:“良好新军,四民挚爱。忍令回籍,无辜陷之!久练弃之,縻款不足惜,如成镇无期何!如征兵无望何!”[5]275《共言报》署名梁玩恭的撰文《对于军警交哄后之慨言》:“吾于是为军界惜,尤为吾国前途危,作而叹曰:可怜哉新军!可怜哉中国!夫罄国民之脂膏,费政界之擘画,以练此新军,方谓养成军队,可以称雄海外,张我国威。而乃九州铸错,因小故之不戢,遂轻掷为沙虫。”[5]277舆论对新军之同情可谓溢于言表,对其被遣散回籍亦深痛惜,对政府之行为感到遗憾、不满。
(二)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防营等旧式军队素日军纪败坏前已有述,然作为此次起义的镇压者,在变乱纷起的特殊时期清廷广东政府依旧未能加强对其的约束,以致产生许多毁坏军人名誉之事,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与对民众秋毫无犯的新军形成鲜明对比,为各界舆论所指责。如《东方杂志》载文《广东新军作乱与官兵大战枪毙百余人阵斩十余人余众悉溃》言:“初四日,(官军)是午并将一标内二营烧去,以免藏匿。”[5]284港商学界亦撰文《港商学界为新军事公致自治会函》论证焚烧军营乃防营所为,非新军所为。“以如虎如熊之水提亲军在营,乃能被新军窃入纵火,由一而再,所烧者止营房,营房以内之行李辎重军装,悉无损失。明日由巡防营从容雇夫挑运来城发卖。又报纸载初四日两点又烧三营,亦若防营与新军宜搬清物件,然后令其纵火者。又知焚烧西关六局亦是新军所为,与民间所见所闻,则大反对;烧营者实防营,烧六营者实由营兵枪毙平民公愤所致。”[2]262新军营房的焚毁对已捉襟见肘的清廷广东当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时《广粹旬报》载文《营房一炬又去五万九千余两》称:督练公所“以粤省新军亟筹续征,所有日前被焚之梵生寮营房,亟应勘估修建。共沽价,除用回砖石外,须费工料五万九千余两云。”[5]291防营军队焚毁营房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旧军的厌恶情绪及对清政府的不满。
此外,对防营的缺乏约束还表现在防营对获得的新军军装公然估卖,时舆论《公言报》载文《卖军衣》言:防营“获得新军衣装,有三五人在东较场排列估卖,人多挤拥,如故衣圩场,怪现象也。国帑制军衣,军人壮颜色。军士今溃逃,遗衣殊可惜。我军旧纪律,掠夺非越职。较场作市场,招买人如织。”[5]278防营的纪律松弛、无约束,造成舆论之诟病,政府不可谓无责。
综上可知,庚戌起义作为清末广东政府面对的一次重大军事、政治危机,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的应对方面存在诸多欠妥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事前的失策、事发时的失误和事后处理之不足等三个方面。事前的失策之处主要有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等五个方面。这其中又尤以“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方面为显著,党人“不惮身入虎口,而图运动军界”致使新军思想转变,革命动力成功转型,成为炸开清政府统治堡垒的重磅炸弹,被誉为清政府的掘墓之役——武昌起义亦是此“逸规新军”之“杰作”。清廷广东当局欲弥祸于未萌当难以实现。事发后的失误主要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这其中对局势关系至大当属“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从除夕日兵警交哄,至初一、二日的冲突升级,兵警互殴、砸毁警局,初三日倪映典进入军营枪毙齐管带后,哄乱之际的新军已势如骑虎,难以收手。此时或剿或抚,清廷广东政府当取果断之策,掌握主动权,控制局势的发展。探诸此过程政府官员及军队将领之作为,不难发现其首鼠两端、临阵弃营之表现。事后处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为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清末广东政府在危机初步结束、社会秩序亟待恢复期间,尽管采取不少善后措施,但其中存在诸多弊端,为舆论所谴责,且“不分良莠,一律遣散降兵”的举措虽耗帑颇巨,实徒劳之策,非治本之计。总之,庚戌起义事前、事发中及之后,清末广东地方政府均存在应对失当之处,一年后武昌一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走上土崩瓦解,以上原因当加以深思。
[1]王在民.广东新军的“庚戌起义” [J].学术研究.1958(7):48-50.
[2]方忠英.庚戌广州新军起义 [J].广东史志.1995(4):70-73.
[3]黄大德.从新发现的庚戌新军起义资料谈起[J].学术研究.1997(2):42-47.
[4]苏全有.论清末的省界观念 [J].安徽史学.2009(1):17-23.
[5]仇江.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6]陈铭枢.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M]//民革中央宣传部.陈铭枢纪念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7]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一九一○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J].近代史资料.1955(4):86-89.
[8]陈景吕.我所知道的庚戌新军起义之役[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 (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9]徐维扬编,邓慕韩订.庚戌广东新军举义记 [M]//丘权政,杜春和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莫雄.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 (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 (辛亥革命前后)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陆军部军法司驳会审拟盼张哲培等呈稿[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15]刘悲庵编.广东新军叛变本末[J].砭群丛报.1910(6):47.
[16]莫纪彭.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M]//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7]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思想失控 [J].史学月刊,2009(6):82-87.
[18]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19]马锦春.黄花梦影[M]//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