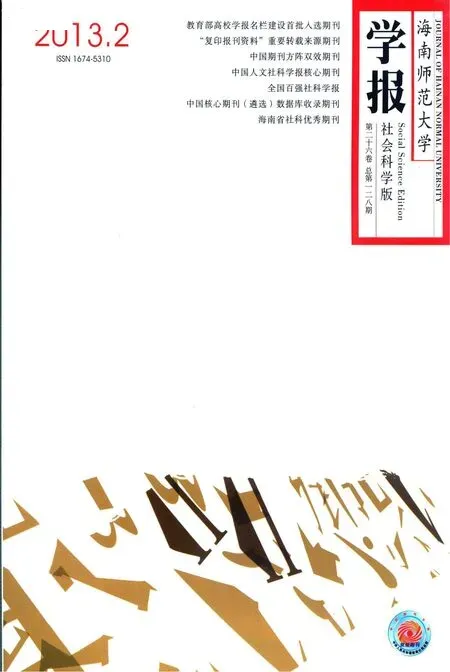回忆与死亡——《呼兰河传》忆乡模式下的死亡意识
杨碧薇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作为萧红晚期的重要文本,《呼兰河传》的死亡意识较之早期的《生死场》而言,还有待研究者的更多发现。《生死场》中对“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的死亡描写深入人心,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呼兰河传》死亡意识的开掘。而《呼兰河传》在死亡意识的表现上,的确呈现出诸多与《生死场》不同的面貌。格非就曾指出,“《生死场》里面写到的生死是非常难、非常狰狞的,但是《呼兰河传》里面的生死就变成了日常化的。”[1]确实,《呼兰河传》中在忆乡模式统摄下的死亡意识更为自觉,也更为成熟。
一 乡土记忆:东北地域文化
乡土记忆是现代作家割舍不去的精神食粮,“对于漂泊的中国作家而言,乡关之恋已是深入骨髓的情感。”[2]作为一名逃离故乡的现代游子,萧红的乡土情结既具有与东北作家群相通的共性,又深含在经历人世冷暖沉浮之后的个人化体验。在《呼兰河传》中,乡土记忆的高度释放,重现了作家曾生活过的东北故乡的地域文化,也与萧红的死亡意识互相指涉,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作为表现死亡意识的承载体,《呼兰河传》的乡土记忆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呈现。
(一)自然
与《生死场》的开篇描写了格调较为缓和的麦场自然景观不同,《呼兰河传》的开篇第一章,作者就通过车夫、卖豆腐的人、卖馒头的老头等人在寒冬里的语言和行为,着力介绍了呼兰县城特殊的自然环境——严酷的天气:“严寒把大地冻裂了”、[3]347“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3]348“远望出去是一片白”。[3]349第一章末,又对这样的自然环境作了对应的渲染:“冬天,冻掉了人的耳朵,……破了人的鼻子……裂了人的手和脚”,[3]376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描写手法,将呼兰县城的寒冷与荒凉像泼墨一样一览无余地淋漓渲染,由此展开了故乡呼兰独特的表征:在这个极为寒冷的场域里,自然生命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东北大地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最明显的地域特征,离乡若干年后,萧红对故乡的回忆仍然是被“寒冷”首当其冲地充满。隐去了明确的时间叙述,仿佛她的回忆是顺着“寒冷”的线索而展开,“寒冷”便是故乡留给她的最为强烈的印象。
这样寒冷的回忆,也影响了萧红晚期的死亡意识。当她的回忆被大片的严寒所占据,生活在背井离乡之中,忍受着颠沛流离的痛苦之时,人的生存以及对死亡的思考,便作为首要的话题,以严肃而自觉的形态呈现在文本中。
另外一笔浓墨重彩的自然景观描写,出现在第一章第八节。这一节主要回忆了故乡的火烧云。与别的地方火烧云不同,“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3]373萧红的回忆很细致,不管是火烧云的颜色,还是火烧云的形状,甚至是人们在吃过了晚饭后的日常活动,均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如果说,东北大地的严寒气候映衬的是小说“生的残酷”的情感基调,隐喻了死亡的悲苦,那么,回忆火烧云这一自然景观则映衬了《呼兰河传》中的另一条情感基调,即“生的快乐”。“生的残酷”与“生的快乐”,又构成了生命形态的两个方面,在对立而统一的生命形态中,死亡意识的内涵得以更深化的挖掘与扩展。
(二)民俗
在第一章里,作者便以扎彩铺如何扎纸人作为起点,展开了对呼兰河地域民俗风情的回忆。这样的回忆,在第二章里最为密集: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其中,对“跳大神”这一民俗活动的回忆首先重现。“大神是会治病的”,[3]377大神若被二神冲犯便会打鼓乱骂,大神天黑起跳等等。在对跳大神活动的回忆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呈现出一种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思考:跳大神活动往往吸引众多男女,“若是夏天,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3]378“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3]379这种民间狂欢性质的众人看热闹,是对正在进行着的“生”的选择性遗忘;在无意识的狂欢......之中,也隐含了民间对死亡的恐惧:大神若被冲犯,便会降灾于人,人们必得烧香点酒、挂红布杀鸡消灾,以避免不愿面对的死亡。这种对东北跳大神仪式的回忆,“被置放在所有仪式书写的首要位置,即可看出跳大神在本书中所隐含的重要性,很有纲纪的作用”,[4]它对应了第一章里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立足于民俗人文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超越于人类自然肉体死亡威胁之上的
故而,这种回忆对萧红而言并不是快乐的,她已经从中洞察到了故乡人对死的认知状态:一方面,死亡在这个东北小城里是容易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们往往在跳大神、放河灯这样的集体活动中消磨自己的生命,就像一代代人习惯了忍受酷寒的天气一样,死亡烙印在呼兰人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另一方面,死亡又会不时激起人们的恐惧,这些东北民间萨满教仪式给人们带来直观的死亡表演,他们借助各种消灾弥祸的办法,对自身惧死的心理进行形式上的安慰。由此可见,故乡这些为鬼而做的民俗,给萧红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在她对故乡的回忆中,诸多隐含死亡意义的民俗活动就占据了一整章笔墨。在童年时就亲历了这些民俗活动的萧红,死亡意识也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为此,回忆起故乡的往事时,萧红一再说“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3]379
(三)人事
在《呼兰河传》这幅浩繁的东北画卷中,人事是作者描写的重头戏。小说集中塑造了“我”、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莫不与死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和祖父都在见证着呼兰河人民的死亡,后来,“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3]528小团圆媳妇被婆家迫害致死;有二伯既怕死,又多次寻死,最后“听说有二伯死了”;[3]529冯歪嘴子则经历了妻子王大姑娘的死。因为这般诸多的死亡,《呼兰河传》的格调从整体上来说,注定不是活泼明快的——尽管萧红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也展现出儿童的天真无邪;呼兰县城的种种人事莫不统摄在死亡的阴影下,死亡使《呼兰河传》具备了深沉的重量。
所以,在萧红对故乡的回忆中,死亡是一个绕不开的重大主题,“目睹死亡,是童年的萧红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她人生启蒙重要的一课。”[5]面对东北故乡人们的无知与麻木、残虐与冷酷,萧红在回忆时已显克制,童年的她亲历了这一出出死亡的闹剧与死亡的悲剧,但当她回头审视时,却又与她的回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她在对故乡漫无边际的深切回忆中,又秉持了一种清醒的理性,由此她才能透过回忆的表象,触摸到震撼人心的生与死。
小说第五章写了团圆媳妇遭婆家迫害致死的故事。这个事件在萧红的回忆中应是颇具分量的,所以她才不惜花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来怀念这位小团圆媳妇。其中,她所能回忆起的,更多的不是小团圆媳妇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而是她遭受迫害走向死亡的这一过程。如果说祖母的死只给萧红留下一个粗浅的丧事的印象,“等人家把我抱了起来……屋子里的人,……都穿了白衣裳”、“家里继续着来了许多亲戚……请了和尚道士来,一闹闹到半夜”,[3]417那么,到了小团圆媳妇这里,萧红所目睹的死亡,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死亡结局,而是惊心动魄的死亡过程。
12岁的小团圆媳妇,本有着孩子的纯真天性,初到老胡家时,她笑呵呵的,吃饭就吃三碗。但是随着婆家的逼迫,她天天挨打,“一直哭了很久,到了冬天,这哭声才算没有了”,[3]447被折腾出了病,于是老胡家又开始了跳大神,在一群瞎出主意的乡民的建议中,孤立无援的小团圆媳妇逐渐被推向死亡边缘。最后,她被迫接受了开水沐浴消灾,而滚烫的开水却夺去了她生命光景的最后一丝希望。她“烫一次,昏一次”,[3]474不久以后就死了。在团圆媳妇死亡的过程中,萧红作为一名见证者,亲自目睹了团圆媳妇的婆婆对她的虐待、呼兰河人民充当愚昧的不自觉的帮凶的种种行径。人们的这些行为与东北地域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初,日本、沙俄开始侵略东北,东北长期处于战乱与动荡之中,与此同时,萧红的故乡呼兰县仍然封闭、保守、落后,虽然曾有“北满谷仓”、“江省邹鲁”之称,但是文化教育与现代文明的动力仍然匮乏,人们依然生活在麻木愚昧之中。①参见包天亮:《流亡者的乡土叙事——论萧红小说中的乡土世界》,汕头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同时,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外界压力的双重胁迫下,人们丧失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他们对生活无动于衷,对死亡又怀着超乎寻常的淡漠。呼兰人民的这种在地域浸染与封建束缚中长期积累起来的“集体无意识”,无形中充当了逼死小团圆媳妇的帮凶。在小团圆媳妇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乐于充当看客,“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只是不能够前来看老胡家团圆媳妇大规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3]470另一方面,在满足了观看的好奇心的同时,却没有谁真正意识到老胡家的做法是在无情地戕害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没有谁站出来帮助解救小团圆媳妇,甚至是说一句公道话。小团圆媳妇的惨剧给萧红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对于萧红来说,这一事件给她造成的深刻记忆,既来自于小团圆媳妇本身的死,也来自于乐意观赏并不自觉地推动其死亡的看客。这种记忆,使得萧红的忆乡与同时期的一些乡土作家有所不同,当他人在通过追忆故乡的美好而试图躲避尘世之时,萧红的忆乡却注定不是对纯粹的美好的感怀,她站在“五四”启蒙者的角度,反观东北老家愚昧落后的方方面面,描写前现代时期的人世环境,在讽刺与揭露的同时展现出一种悲悯的人间情怀,因而更显高度。
小说第六章则具体塑造了有二伯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名普通的家佣,有二伯的身上却有着比别人更为明显的死亡意识。萧红回忆了有二伯上吊、跳井的种种琐事,上吊的导火索是有二伯遭到主人的责打,他感到委屈与无望,“先是骂着,后是哭着,到后来也不哭也不骂了”;[3]499跳井,却“在那柴堆上安安稳稳地坐着”。[3]499作者对有二伯这一人物是灌注了充分的同情的,他身份低微,对生与死却比一般人敏感。当呼兰县城里别的人时刻处于遗忘死亡的状态中时,有二伯却通过他朴素的话表达了对死亡的思考:“到阴间,阴间阳间一样,活着是个穷人,死了是条穷鬼”,“死,死不了,你别看我穷。穷人还有个穷活头”。[3]497因为生的艰难,有二伯产生了死的念头;而面对死亡时,他却又眷恋起生。他既忍受着生的煎熬,又惧怕着死后的万事皆空,最后,他选择了活。这种矛盾构成了有二伯的死亡意识,也贯穿在萧红的回忆中,成为《呼兰河传》死亡意识的一部分。其中,“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漠视依然是最底层的人们苦苦挣扎而没能摆脱的命运之网。”[5]
比起《生死场》中剧烈的死亡描写来说,《呼兰河传》中对王大姑娘的死,却处理得异常平静。这个时候的萧红,已经能从年轻时激进的控诉中抽身出来,站在更为理性与更为超脱的位置上,去看待人的死亡。如果说以《生死场》为代表的《王阿嫂的死》、《哑老人》等小说都更多地把死亡的表达集中在死亡场景的描摹上的话,那么《呼兰河传》中王大姑娘的死,却是一种去场景化的写法,小说规避了对王大姑娘的死时场景的介绍,只简单地提到“冯歪嘴子的女人是产后死的”,[3]525将记忆的重心放到冯歪嘴子身上,从王大姑娘在世时冯歪嘴子的奋斗写到王大姑娘去世后冯歪嘴子的顽强生活。在冯歪嘴子这一人物的塑造上,萧红逐渐隐匿了激愤的态度,情感趋于内敛,虽然这片古老封闭的东北大地上的人性是病态扭曲的,但民族的生命力却在冯歪嘴子的身上出现了复苏的闪光点:面对艰辛的生存与至亲的人的死亡,冯歪嘴子并没有消极逃避,他“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3]526在凛冽的死亡气息中,他仍然对生活怀抱希望。“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的那份责任。”[3]526冯歪嘴子是萧红故乡回忆中的亮点,这个时期的萧红已经远离了中国大陆战火的硝烟,辗转到了香港,经历了几次情变,她的抗死精神中增添了更深沉的力量。故而在处理王大姑娘的死亡这一题材时,萧红已经站在了超越封建批判与阶级批判的高度,对人生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深层观照,表达了对死亡意识的深度思考,同时,也在死亡的光景中看到了人的力量,赞美了人性的温暖与坚韧。
“在外漂泊多年的萧红已经在时空尤其在心理上和故土产生了距离感,所以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是零碎的、片断的。”[6]抗婚出逃的萧红在早年并没有在文本中呈现出浓重的思乡情结,她曾说“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7]但随着阅历的增长与人世的浮沉,旅居香港的萧红更多地感受到了孤独与寂寞,生活的困扰、感情的伤害、国家的危亡都折磨着她,这个时候,家乡成了她情感释放的一个载体,她开始了对故乡的绵绵不尽的思念与回忆,完成了不朽的《呼兰河传》。
总的来说,《呼兰河传》中的忆乡模式是循着以上三条明显的线索展开的:一是对家乡自然景观的回忆,二是对家乡民俗习惯的回忆,三是对家乡人事活动的回忆。这三条线索凝聚了萧红对故乡的深切回忆,互相联系、互相佐证,展现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东北地域文化特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忆乡模式体系。在这一基础上,萧红晚期的死亡意识得以展开。
二 死亡意识:发现与超越
《呼兰河传》在忆乡模式下死亡意识的呈现过程,应是从直观感受入手,再深入到理性思考,最后进入到对死亡价值的评价中。故这里采取“死亡情感(对死亡的直观体悟)—死亡本质(从直观体悟进入到对死亡的本质思考)—死亡价值(通过本质思考,完成对死亡的价值判断,并以价值判断指导人生)”的研究线索,以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细致梳理《呼兰河传》的死亡意识,以期对萧红晚期死亡意识的发现与超越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死亡情感
陈思和认为,凡高与萧红的创作,“都不是预设一个艺术形式,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感情世界寻找一个表达存在的方式。”①转引自文贵良:《〈呼兰河传〉的文学汉语及其意义生成》,《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感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特征,在萧红淡远的文字中,隐藏着无数情感的冲创,她对故乡的回忆是为了给自己的感情世界寻找存在的方式。而童年时目睹的故乡人民的桩桩死亡事件,带给她最初的情感体验,也给她的生命蒙上了挥之不去的死亡影像。
在回忆故乡人的死亡时,萧红是带着情感的;她对不同人物的死亡的书写,带有不同的情感体验。萧红的祖母不像她的祖父一样,给过她深厚的爱,相反,她用大针去扎5岁的萧红,这种生理上的疼痛体验使萧红记忆犹新,“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3]404所以,对祖母的死,萧红并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在她临死之前,病重的时候,我还会吓了她一跳”,[3]404萧红并没有写到祖母死时她是否流下眼泪,只是说丧事让她觉得好玩,“所以就特别高兴起来”,[3]417之后便再无闲笔。由此可见,祖母的死给萧红带来的是一种解放,因为从此后,她不再被人用针扎,在行为习惯上也少了诸多束缚,儿童的自由贪玩的天性得以释放。
对于团圆媳妇的死,萧红也未用过多的笔墨去宣泄自己的情感,但是从占据整整一章篇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对团圆媳妇的死是抱有强烈的同情心的。章末用大白兔的意象来隐喻团圆媳妇的冤屈,字里行间透露出强烈的凄凉感。可以说,团圆媳妇的死真正地震动了萧红幼小的心灵,在这整个事件中,乡人邻里的“无事者”的看客行径也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占据了她对故乡的人事记忆的一角。这一死亡事件让萧红过早地目睹了东北老家人民腐朽、无意识、残忍而麻木的精神世界,由此,“她更多地感受到东北大地的沉滞、灾难和人生的悲苦苦难与温情。”[8]
如果说,团圆媳妇的死直观地冲击了萧红的心灵,使她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了同情心的话,那么,冯歪嘴子夫妇形象,则促使萧红对活在麻木愚昧中的人民产生更深刻的同情心与敬佩心。她既对王大姑娘的死感到悲哀,同情他们一家不幸的遭遇,又敬佩鳏居的冯歪嘴子坚强生活的勇气。由此,同情与敬佩构成了萧红的死亡情感的两个方面。在她成年后对冯歪嘴子夫妇的追忆中,包含着无尽的唏嘘与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暗含着对冯歪嘴子及其孩子的美好祝福。
由此可见,在写作《呼兰河传》并对故乡进行回忆时,萧红的死亡情感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对祖母之死的近乎无动于衷,又有对团圆媳妇及王大姑娘之死的哀叹与同情,更有对敢于直面死之惨淡的冯歪嘴子的坚强意志的赞美。死,在呼兰县城已经成了日常的事,但是当死亡真正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时,这种死亡又会激起人对自己命运的同情。萧红对他人死亡的同情与观照,也是对自身生命的同情与观照,从中流露出对死的无奈与抗拒。
在祖母去世时,萧红年仅5岁,她对祖母的感情停留在片断式的、以肉体疼痛(被针扎)为核心的印象上,也就不难理解她的“无动于衷”。而对团圆媳妇及王大姑娘之死,她则采用了不同的笔调,灌注了深厚的情感,与对祖母的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者的一种写作策略,目的在于抑制恶的事物,褒扬美好的事物,由此,在忆乡模式下,萧红表达了自己独有的死亡情感。
(二)死亡本质
作为人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死亡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作为一位对生命有着高度自觉的作家来说,萧红没有停止过对死亡本质的追问,她对故乡的回忆,莫不被种种死亡所充满。“凝视死亡、追问死亡成为萧红小说的的基本主题;也可以说,死亡是萧红艺术地把握世界、认识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是萧红小说切入现实、品评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9]从死亡情感的表达到死亡本质的追问,萧红实现了由童年时的感性情绪到成年后的理性思考的飞跃。她在早期的创作中,便把生命的体验推向死亡的极致,但到了晚期创作中,不管是《小城三月》还是《呼兰河传》,死亡都不再聚焦于“非常态”的状态,而是趋向常态的死。这契合了萧红死亡意识的一个转向,也体现了她创作的一个转向:她不再通过惊心动魄的肉体死亡来表述“死亡”这一主题,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随时发生的死亡事件,去表达死亡情感、思考死亡本质。《呼兰河传》中,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走向死亡的过程的揭示是生动而丰富的,而她们死亡的结局,萧红却只几笔带过,在言不尽意的散淡笔触之外,凝结了萧红对死亡本质的具有存在主义性质的思考。
首先,在萧红看来,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它甚至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由此萧红对死亡怀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亡不是尚未现成的东西,不是缩减到极小值的最后亏欠或悬欠,它毋宁说是一种悬临。”[10]这种“悬临”,也是萧红生存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她既要躲避战争,又要经历生育之苦,还要承受感情上精神上的熬炼与社会的白眼冷遇。“悬临”就是死亡的无处不在,就是死亡的随时随地发生的可能。
其次,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与躲避,萧红也不例外。在惧死本能中,萧红却试图战胜恐惧,以儒家式的人生努力对抗死亡。面对死亡,她并不认为人生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人生的意义在于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生活,以无悔的姿态应对死亡。萧红不停地在求生、在抗死,这种死亡意识也贯穿到了她对故乡的回忆中,倾泻在了她的作品里。
最后,个人可以选择对待死亡的态度。出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萧红并没有提出“死亡不是人生终极”的命题,未对死亡之后的生命问题展开思考。但是,她对死亡之前的人生选择却有着深入的探索,她自己的生命历程就是一部抗争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选择逃避与消极,也可以选择对人生持有高度自觉。面对死亡,人们可以选择蒙昧、软弱的生活,也可以选择明智、坚强的生活。
总之,《呼兰河传》在忆乡、表达思乡情怀的同时,也熔铸了萧红对死亡本质的思考:死亡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不可避免的,是悬置于人生的;每个人都无法对死亡说“不”,却可以选择对死亡持有不同的态度。
(三)死亡价值
死亡的价值,根本上在于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完结性与毁灭性能对人生产生影响与指导。除却舍生取义的少数个体,死亡对普通人的价值正在于此。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在活着时就在领会着死,就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他将如何对待自己的死亡。”①转引自陆扬:《中西死亡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在《呼兰河传》中,死亡成为人生常态。小团圆媳妇的死与王大姑娘的死,都给萧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充斥她回忆的同时,也驱使她对死亡价值进行主动的思考。
死亡的第一个价值,即促使人从“死”的境地来反观“生”的状态,审视“生”的选择。《呼兰河传》第一章第五节回忆了一群死去了亲人的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3]366这样的人群,对死亡是缺乏深刻的认识的。而对萧红这位接受了“五四”教育的作家而言,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促进现代思想的传播,以期人们对“生”与“死”产生更自觉的认识。当“死”的恐惧与悲哀真正深入人心后,人们对自身“生”的状态的审视才能更彻底、更清晰,从而检验自己对“生”所做出的选择是否合理,是否有价值。
死亡的第二个价值,在于敦促人珍惜生命、把握生命。在《呼兰河传》的时代,东北大地上人的生存还是极不自觉的,人们活在为生而生的生中,宁愿做唱大戏的看客消磨日常时间,却对个体生命的宝贵缺乏基本的认识。而死亡能将生命带入虚无的境地,由于生命的尽头有了死亡的存在,所以人更应该珍惜生命、把握生命,以清醒的人生态度,过好短暂的生命中的每一天。
死亡的第三个价值,在于反抗死亡中产生的悲剧力量。《呼兰河传》中,有二伯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低微,搞出了自杀的闹剧,却依然顽强地活着;冯歪嘴子虽然经历了丧妻之痛,却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有盼望地生活着。人固有一死,意识到应该珍惜生命的人,总是在与死亡进行着抗争。“死亡给生者带来更大的生存勇气”,[9]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存哲学所体现的,是一种明知固有一死却不愿轻易向命运妥协的人生态度。人生因为有了死亡才显得可贵,人也因为有了对死亡的抗争才显得可敬。个人反抗死亡的行为,往往会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他人自觉地活着、顽强地生存。在人必将死亡的宿命中,反抗死亡始终作为一股强大的悲剧力量而存在。这就是死亡对人的最大启示。
总之,《呼兰河传》在对具有东北地域特征的故乡的回忆中,以人对死亡的直观情感切入死亡意识,通过对死亡本质的,彰显死亡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的精神对人生的。以死亡情感、死亡本质、死亡价值构成的死亡意识,其意义的展现最根本的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呼兰河传》带入了作者童年时期自我体验的回忆,凝聚了作者丰沛的情感与现代性的理性,通过感情抒发与理性判断,萧红完成了对死亡意识的探讨,表达了对死亡意识的态度。文中也暗暗汇贯着一股坚强的求生力量,留下了对美好的生之期待的阐释空间。
三 忆乡模式下的死亡意识建构
《呼兰河传》是一部以回忆为源而展开的小说,而小说中莫不充满了死亡意识。其中,“忆乡”的独特性在于对东北老家呼兰县城特有的自然景观、民俗人事的挖掘,而死亡意识的独特性则在于建立在特定的乡土景象之上,使得对死亡意识的思考具有更多的地域文化色彩。忆乡模式下的死亡意识建构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忆乡模式是死亡意识赖以展开的文本环境,是承载小说织体的基础。现代作家中,鲁迅、沈从文、废名、王鲁彦、许杰、台静农、梁遇春等都写过回忆故乡的乡土文学作品,他们在忆乡的模式中展开叙述,主题通常是怀念故乡、揭露故乡的愚昧落后,表达对传统文明失落的哀叹、表现在现代生活中的失落感、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困境、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心态等等。其中虽有涉及到死亡主题,却往往处理有限,极少有像萧红《呼兰河传》这样大面积地观照人的死亡、精细而复杂地呈现死亡意识的作品。而萧红将死亡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置放于忆乡模式的统摄下,使忆乡模式成为统领死亡意识之展现的情感环境与文化环境。这种以忆乡模式来承载并完善死亡意识的手法,在现代文学中并不多见,颇具开创性。
第二,忆乡模式是隐去了时间叙述的。《呼兰河传》的第一章写自然地理;第二章写民俗;第三章写“我”与祖父的后园生活;第四章写“我”家的荒凉、我的玩耍活动;第五章写团圆媳妇;第六章写有二伯;第七章写冯歪嘴子一家。作者的回忆是一种散点透视,她抓住了记忆中最鲜明的七个点,整合成七章,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书,章与章、故事与故事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读者无法断定文中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这些事件不是以时间而是以概念而呈现的。时间意义上的含混是《呼兰河传》叙事的一大特色,在隐去了时间叙述的忆乡模式中,团圆媳妇、王大姑娘死亡事件的概念能得以集中的呈现,死亡意识得以突出的彰显。
第三,忆乡模式承载死亡意识的同时,死亡意识也拓展了忆乡模式的书写空间与意义空间,使文本获得了更多的阐释的可能。死亡意识的深度挖掘与思考,增添了忆乡模式的书写厚度,使《呼兰河传》不再停留于简单的故乡抒怀层面,它超越了同时代甚至后面时代的一些文本,通过对死亡意识的思考,体现出一种终极关怀下的永恒乡愁与文学张力。
总的来说,忆乡模式下的死亡意识建构,使《呼兰河传》表现出与其他现代乡土小说不同的特质,这一建立在独特的东北记忆的忆乡模式上的文本,凝结了萧红个体人生经历中的现代性死亡思考,感智交融。就这样,死亡意识通过忆乡模式,在《呼兰河传》中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建构;忆乡模式也因死亡意识的探讨而更具意义。《呼兰河传》文本的这一层阐释空间无疑是巨大的,其文化意义的含量也不容轻视。
[1] 徐健.坚守文学创作的本真 探寻萧红的当代价值[N].文艺报,2011-06-08.
[2] 席建彬.关于现代小说诗性存在形态的历史思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 萧红,乐齐.萧红小说全集——一代才女的艰辛跋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4] 林幸谦.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5] 蒋书丽.不动声色的文字下面——也说萧红的《呼兰河传》[J].名作欣赏,2008(7).
[6] 刘艳梅.异乡人 故乡情——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谈萧红作品的“回乡”模式[J].名作欣赏,2008(9).
[7] 刘丽华.鲁迅与萧红的故乡情结[J].鲁迅研究月刊,2004(11).
[8] 宋扬,许宁.苦难与温情——萧红、迟子建死亡意识之比较[J].社会科学辑刊,2008(6).
[9] 郝庆军.论萧红小说的死亡主题[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
[10]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