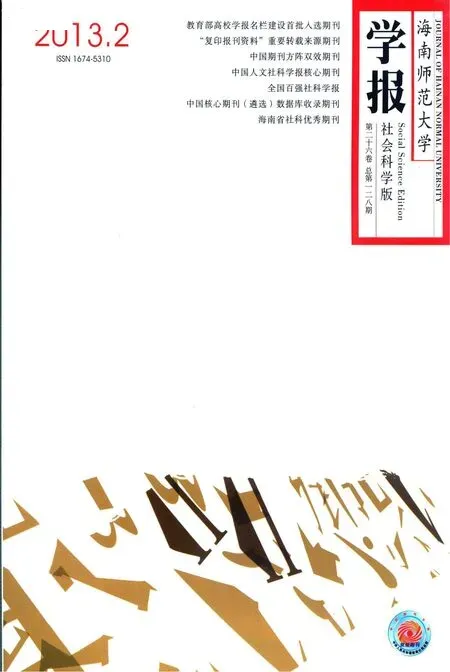对中国乡村的“小历史”叙事——读毕星星的《坚锐的往事》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12)
毕星星在《坚锐的往事》的《自序》中说:“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宣布:他要把非虚构文体打磨成一种利器,为人类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纪实,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学现象。2001年,也是‘诺奖’设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各路巨匠提出,希望文学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历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以意识形态来叙述的历史和政治谎言。”毕星星说他因此“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暗暗坚定了自己的选择”。[1]
我不能判定纪实是否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学现象,但我却分明地能够感觉到,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思想标高、精神深度,是通过民间性的“小历史”对历史的纪实性思想性文字来体现的。所谓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一对概念。西方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化的文本有两种,一种是单数的大写的历史,一种是复数的小写的历史。譬如说,占统治地位的正史属于“大历史”,集中的统一的对历史的阐释属于“大历史”,基于某种观念形态下对历史的阐释属于“大历史”;各种野史稗说属于“小历史”,分散、零碎的对历史的阐释属于“小历史”,私人性经验性的对历史的叙说属于“小历史”。之所以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思想标高、精神深度,是通过民间性的“小历史”对历史的纪实性思想性文字来体现的,从远里说,是因为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学不分的传统,如《史记》等等;从近里说,是因为面对今天的价值失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需要通过忆旧来寻求新的价值资源以支持自己失衡的价值天平,这就是今天忆旧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无论是红色文化的再度出场,还是对历史真相的重新打捞,抑或对旧闻旧事的兴趣,或是百姓、坊间普遍的怀旧情结等等。而民间性“小历史”对历史的纪实性思想性文字之所以在这其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是因为时代性的原有价值大厦崩塌之后的普遍的不信任、怀疑而导致的重新认知事实真相的冲动、需求;一是因为作为单数的“大历史”对历史的叙说无以满足上述的冲动、需求之时,“民间”作为复数的“小历史”对历史的叙说就得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浮出历史地表”。于是,我们看到了种种“非虚构写作”的盛行,于是,我们看到了种种“一个人的历史叙事”倍受读者的欢迎。
一
毕星星的《坚锐的往事》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努力,就是这其中的一项硕果。它偏重于对中国乡村历史真相的重新打捞,而在这种打捞时,又因为作者亲身体验的真切,加上作者理性认知的深刻,从而修正、重建着我们的乡村记忆,让我们有了“去蔽”之后得以“澄明”的快意。
说起来,像我这样的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的一代人,我们对中国乡村的记忆,最初是通过那些写土地革命、土改、合作化运动、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而得以完成的。我们对这些“文本的历史”曾经深信不疑,而没有看到这些“文本”的书写,是为“权力”所“制约”,是“历史的文本”。直到我们下乡插队,面对真实的中国乡村时,我们也还在时时怀疑自己真实的所见所闻,这样的认知“病症”,在原本就在乡间生活的农村青年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宁愿相信“文本”而不相信自己亲历的真实。倒是不怎么识字的作为我们上一代的乡间老农,他们只立足于自己私人性的切身的生存利益,从而能够“本能”地去除“文本”对“真相”的“遮蔽”,说出类如《皇帝的新装》中小孩子所说出的真话来,并因此每每让我们这些被“文本”“遮蔽”了双眼、不相信自己双眼的人,大吃一惊,目瞪口呆。直到多少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知道了“悬搁一切价值判断”“直观事物本身”时,当我们知道了一切历史都是“文本的历史”而“文本”又因为“权力”的“制约”而是“历史的文本”时,当我们知道了“修改教科书”能够修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历史记忆时,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我们作为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我们应该有责任重新回望我们的乡村历程,我们应该有责任重新书写我们的乡村记忆。因此,我们愿意伴随毕星星,重新开始我们对中国乡村的回望与反思。
或许是因为毕星星是文化人的缘故,或许是因为文化是乡村变革的最为深刻的标志,总之,毕星星的这本《坚锐的往事》主要是以文化特别是以文化的直接载体——文化人为主线,写在“权力”的规训下,写在城乡文化的冲突中,乡村文化的种种表现形态,进而来揭示中国乡村的历史真相。
《特级教师南岩之死》被多家选本选入,并曾获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在毕星星的作品中,最受文坛好评。在几十年的农村政治革命中,原有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村民间文化及文化人最受摧残、蔑视,被伤害、改造的程度最重,即使是在“十七年小说”这种被规训了的“历史的文本”中,我们也时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印痕:譬如这些小说中的一个主题范型就是,作为新的政治文化载体的青年农民与作为原有的乡村民间文化载体的老一代农民的冲突。但乡村的文化人却在这种劫难、坎坷、磨难中,默默地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位置,从而使乡村文化的长河得以在田野的大地上延伸、流淌。乡村教师是乡村文化人的典型,在新的政治性的教育体制内,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最难以归属:一方面,他们在名义上是现行体制中人,是现行体制认可的文化形态的承传者,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们又沿袭着传统乡村文化人的社会角色,在实际的教学生涯中,又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隐形层面上,传承着乡村的固有文化。南岩作为特级教师,就是他们的典型,他们的代表。毕星星的这篇文字,写了南岩由于参加革命的父亲与在乡间的母亲的离异而得不到父系家族的认可,那其实就是政治文化与乡间文化的断裂而给南岩带来的身份归属的无着,是上述乡村教师身份归属的隐喻,这种无着使南岩一生饱经困苦、坎坷、屈辱,但南岩却在这样的境遇中,因了自己在语文教育中的突出贡献而成为省级著名的特级教师。作者在讲述南岩的一生时,借助自己与南岩的亲属身份,使全文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充满了感染人打动人的情感的力量,使我们不由得不沉浸其中,在对乡村教师的深刻理解时,深受感动。
《特级教师南岩之死》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纪实文字,但在毕星星的纪实文字中,它却远远不是最好的一篇,如在这本《坚锐的往事》中,比它胜出一筹的文字随手就可以举出几例来。我猜想,《特级教师南岩之死》之所以被多家选本选入并获散文界、山西文学界大奖,多半是因为这篇纪实文字中情感的动人力量,还因为南岩的教师的社会身份——而又是从一般的重视教育的这一层面上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可。在获取殊荣这一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把《特级教师南岩之死》视为一个“历史的文本”,只是导致其成为“历史的文本”的“权力”,来自于文学界的判定能力。于此,我们不能不感叹于文学界判定能力的历史局限性——它们还更多地生存于“大历史”的阴影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奇妙的错位:文本的“小历史”叙述与对这“小历史”叙述文本的“大历史”的判定。这样的一种奇妙的错位,或许也是民间性“小历史”对历史的纪实性思想性写作潮流在其发展中,所应该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吧。
话题似乎有些扯远了。回过头来我们接着来谈毕星星的这本《坚锐的往事》。
在我看来,《最后的乡绅》是一篇要远远高于《特级教师南岩之死》的杰作。诚如作者所说:“在封建时代以至民国,乡绅都是乡村社会一个重要的阶层。‘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乡绅成为基层政权和底层民众联系的中介,决定了它在村落视野里的乡土权威地位。”但“自民国以后,乡绅的社会地位日渐滑落。土改一举将原来的乡村精英请下了历史舞台……由于乡村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居多,对读书人心怀一种天然的文化歧视,乡绅日益成为零畸者和多余人”。然而,“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我们的乡村终于又开始向自治回归。一旦少了自上而下的权力干预和强制,这些乡村知识分子的作用立刻突显出来了。”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最后的乡绅》中的主人公“师傅”这样的一个机会,他“生不逢时,在乡里制度的承袭变革过程之中错了位”,只能成为一个上述的“零畸者和多余人”。读《最后的乡绅》,在主人公“师傅”“受尽奚落和嘲笑”的种种可悲、可笑、可叹的言行举止中,我们时时都可以看到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面影,他们都是作为某种文明的承载者,却生活在这种文明的没落时代,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零畸者和多余人”。这里有着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偶在的无奈、悲凉,也有着在历史长河中必然的言说不尽的丰富的时代与社会的内涵。鲁迅多次说过,《孔乙己》是他写得最为满意的最好的小说,《最后的乡绅》也可以说是毕星星目前写得最好的纪实性文字。与《最后的乡绅》相类似的,还有毕星星对已然被今天这个影视时代所淹没的乡村戏曲蒲州梆子的叙写,还有对乡村戏曲传人《剧坛怪才墨遗萍》的叙写。
二
《谁还知道李希文》、《毁誉参半说浩然》也是两篇意蕴厚重的纪实文字。
这两篇文字都写了在一个时代权力规训下的乡村文化人及通过他们而体现出的乡村文化的呈现形态。李希文是代表一个时代文化风尚的农民快板诗人,他曾经红极一时,如郭沫若所说:“我是郭老八,陕西有个王老九,你就是李老十。”但诚如作者所说:“李希文其实并不是一个农业从业者……他应该是一个游民无产者。这个成分的因子浸透在血脉里,他的成功失败,和这个职业赠与的心性息息相关。游民的革命性和游移性、投机性潜伏着,气候合适一定要萌发的。山西好多农民领袖,在这一点上都和李希文相似。”其实,并不仅仅是山西,中国的农民领袖也大多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文化中也多有这种基因潜伏其中。早在中国革命的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其经典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以“痞子运动”有着精彩的描写与论说,当然,毛泽东是从“好得很”的对此的赞扬来批驳对方对此“糟得很”的指责的。不能否认的是,类似李希文的这种游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在革命的初起之时,他们的言行也是代表着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的真正利益的,因为在革命初起之时,如毕星星所说“道地的农民没有能力代表农民”,而类似李希文这样的人的身上“有农民式的淳朴,也有游民式的狡黠”。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格局、构成,在孙犁、赵树理的小说中,都有着十分深刻与精彩的揭示。孙犁、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先后成为文坛主流的代表,又先后退出时代的文学主流,与这种游民性及对其的评价的历史浮沉关系甚大,这是个用许多专论也难以说清的问题,是一个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说清的问题,我在这里自然不能给以展开,但我们也因此能够感受到毕星星写了李希文这样一个“典型”及这一“典型”被我们今天所遗忘的历史的沉重性。再多说一句的是,李希文退出历史舞台与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明星,作为一个时代话题,有着同样的深刻与沉重,诚如毕星星所说:“一个农民厕身于国家的政治博弈里,该是多么危险的赌局和游戏。”李希文这一代游民的民间性、底层性及其所曾代表的农民利益与政治规训的脱节,是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
浩然则可以作为李希文之后的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是李希文之后的一代在政治规训下的农民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流淌着李希文的血液,但在这一文化谱系的成长中,已然更多地脱离了民间、底层与农民本身,而更多地符合了规训的标准。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他也仍然还是被规训的对象而不是规训者本身,对规训迎合的真诚,在被规训时本身所自然带有的民间、底层、农民群体的风貌,都让后人对此一言难尽。如此,我们也就会明白,毕星星为什么会在说浩然时,会“毁誉参半”了。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不是毕星星一个人所能破解得了的,它需要时间和更多的人对此的努力以及新的价值资源的引入。毕星星能够深入地参与、丰富这一论说,已经是非常地难能可贵了。我对此还非常赞赏的是,毕星星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层面,对此给以揭示、论说,而不再局限于我们所习见的从人格、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臧否人物,这样的一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尺度,在我们回望一个历史时代的风云人物时,特别是政治人物时,是非常必要与及时的。
三
当然,我说我们在回望一个历史时代的风云人物时,要更多地从历史的角度、层面而不再局限于我们所习见的从人格、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臧否人物,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人物人格及道德品格的评价。当我在批判政治规训给民间文化带来的负作用时,也并不是就对民间文化有着一种完全的肯定。事实上,由于传统的老中国是以群体性的道德伦理作为社会价值本位的,特别是在民间,道德伦理的力量往往是作为统治性的力量存在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特定的具有历史内涵的尺度上,而是从一个一般的具有普泛意义的尺度上使用“规训”这个概念,那么,如何评价、用什么去规训传统的乡村的民间的道德伦理,如何重建新的民间的道德伦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紧迫的时代性的社会问题。正因此,毕星星的《大匠野史》颇值得文坛给以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这篇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乡村建筑匠人的领袖,因之,被称为“大匠”。“大匠”带领着自己的乡村建筑队征战南北,功绩赫赫,但却引起了自己养母之子即自己堂弟的妒嫉之心,而这位堂弟“在村子里就是有名的惹不起,惯以死缠烂打制胜”。于是,他的这位堂弟以莫须有的对自己的母亲不孝为长期攻击“大匠”的利器,终于使“大匠”心气郁结,积郁成疾,绝症致死。毕星星说:“大匠的死,是一个非常耐人解读的现代人死亡文本。”下面,我试着来解读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现代人死亡”?
大匠之死,首先死于“纯粹的恶”。毕星星对此分析说:“堂弟谋害大匠,并不希图自己得到什么。他没有利己的动机,纯粹为了害人。与必要的恶相比,这是一种纯粹的恶,恶意的破坏属于没有意义的破坏。他一般针对对象的优势地位,如荣誉、社会地位甚至审美方面的优势评价等。”这样的一种“纯粹的恶”,是社会差别对人性扭曲之后的人性的“恶疾”,这种“恶疾”在底层在民间普遍存在且历史悠久,其破坏性的能量骇人听闻。十年浩劫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纯粹的恶”在起作用。汉娜·阿伦特在论述西方的德国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时,将“平庸的恶”归结为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我要说,中国的十年浩劫能够形成的一个原因,则来自于这种“纯粹的恶”。
大匠的死,还死于民众对这种“纯粹的恶”的软弱与无力,还死于民众缺乏公众意识公德意识:“当初堂弟挑起事端,狂热地攻击大匠的数年,小城一直把它当作一件私事。”说到底,是因为民众没有看到这种“纯粹的恶”对自己利益所带来的伤害因而袖手旁观。这样的一种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冷漠”,在鲁迅的笔下,我们可以时时看到。这样的一种“冷漠”所带来的实则对“纯粹的恶”的鼓励与放纵,也是十年浩劫能够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喜的是,当市场经济让民众对个人的利益有了自觉的维护意识之后,民众终于“如梦方醒……他们开始失悔,在大战胶着的时候,在大匠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小城没有出手助战,小城没有救护自己的功臣”。也许这种“失悔”,正是鲁迅笔下的“庸众”在今天开始觉醒并建立自己的现代公众意识公德意识的开端吧。
大匠的死,还死于如何看取传统的民间的道德伦理。事实上,“纯粹的恶”,往往也是假传统的民间的道德伦理或这种道德伦理的“革命化”外衣而大行其道的。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看取传统的民间的道德传统,这在“五四”之后本已经不成问题,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以批判“五四”以弘扬传统为盛事的时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又一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因之,毕星星在《大匠野史》中所坚守的启蒙立场,就显得难能可贵。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确如毕星星在文中所引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一再主张的:中国人应“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正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以传统的道德伦理作为社会价值本位的国度,所以,“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对于我们就格外重要,否则,永远如毕星星所说:“玩‘技术’的耍不过玩‘道德’的”,“大匠的惨败惨死,无疑是现代生活中道德又一次战胜技术的可悲的范本”。所以,毕星星大声疾呼:“社会对人的技能评价和道德评价要区分”。
“大匠当然也要为自己的死负责任。他的愚忠愚孝,使得他仿佛还生活在两百年前。”在大匠身上,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中国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负与曲折。毕星星呼吁:“这种小人的挟嫌进攻还能遇到,巨人们,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才是。”这可以视为现代之声对传统乡村的呼唤。这种呼唤,在“反思现代性”的时潮中,如果我们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大地,特别是不要忽视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的现实实际,我们对这种呼唤,就会倍感亲切。
《大匠野史》之所以称为“野史”,是因为上述大匠之死的真正原因,在对大匠的“正史”中,只字未提。大匠之死的真正原因“私下议论是可以的,形成一种公开书写,那是断不可行的”。“推测纪念碑的碑文,正面呢,肯定是永垂不朽、鞠躬尽瘁、功高盖世、能工巧匠之类,阴面呢,简略介绍生平,比方全国优秀企业家啦,世界杰出人士啦,荣获鲁班奖啦等等。”毕星星为此悲愤地说:“有人制造了大匠的死,我们又乐于修改大匠的死,大匠便只能这样死去。”这样悲愤的声音,我们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曾经听到,在鲁迅悼亡体的《伤逝》中也曾经听到。正是不满足于大匠“这样死去”,有了毕星星的这篇《大匠野史》,也让我们由此看到“野史”高于“正史”的价值,看到了当今民间性的“小历史”对历史纪实的价值。
四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乡村走向都市,是百余年来中国的民族期待,也是这一群体中每个个体的个体期待。这种期待,在实现这一期待的历程中的坎坷,在刚刚开始实现这一期待之后的对乡村失落的失落感及对乡村的亲情忆念,还有那对现代对都市的不满与反思等等,所有这些,都生动地通过毕星星的个体性的人生记忆的《走出乡村》而得到了生动而又深刻地体现。
这种体现是通过毕星星写自己家族从其爷爷开始到其子女一代共四代人才走出乡村的家族轨迹来完成的。
毕星星的家族聚居在山西的晋南地区,也称为河东地区,那里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的转折处,传统文明的成熟之地率先走向现代文明,也是历史的必然,如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认为的,当一种历史形态成熟之后,它就会在自身孕育出一种埋葬自身的对新的历史形态的渴望与期待。如是,我们看到了毕星星的爷爷在科举中成为秀才之后,又顺理成章地循着历史的脚步,成为北京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而毕星星的爷爷不明原因的死亡而导致的毕氏家族在走出乡村的历程中的受挫,简直就犹如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一波三折的众说纷纭不明就里的一个隐喻。毕星星的父亲没有走出乡村,就像毕星星所说,是从乡村走向都市的一个“顿歇”;毕星星的大哥一代,在民国时期,通过读书、参加革命而伴随新的政权进入城市;毕星星的姐姐一代,在“文革”前通过读书进入城市;毕星星本人在“文革”初中断学业,又通过参军提干而走出乡村;毕星星的儿女一代,在新时期随父母入城读书而进入城市:一个家族走出乡村的历程,真真是犹如我们民族从乡村走向都市的一个缩影。从这样的“小历史”中,或许我们可以借此来窥探“大历史”的某种真实,进而窥探真实的历史本身。
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毕星星的父辈在“整天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三年困难时期,也仍然不惜拆房来支撑儿女通过读书来走出乡村的苦撑苦熬。这个走出乡村的梦想“是那样诱人,以至于后人累断筋骨,受尽艰难,那个梦想也能够支持他们付出最惨烈的牺牲”。这是一个乡间家族的梦想,从文化形态上来说,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梦想,以致我们不惜牺牲乡村成就都市,牺牲农业成就工业,牺牲百姓的日常的物质人生而成就原子弹那灿烂的蘑菇云。
在这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分隔制度,有了城市户口的优越性、优越感,有了农村户口转入城市户口的“难于上青天”的艰难,有了毕星星在城乡之间像“搬运工”一样,年年将城市的物品“从大米、挂面,水果糖,到肥皂,火柴,碱面,作业本,圆珠笔”周转、搬运到乡下的家中。
在这其中,我们还通过那诸多的丰富细节,看到了毕星星在从乡村走向都市的途中,对都市近于偏执的敌对情感,对于乡村近于偏执的怀恋。诸如作者在写到自己扣上门锁告别家乡时的感受:“我对准门扣,搭上锁身,按上锁簧。拇指和四指一合。啪嗒……我所在的闹市,日日夜夜铺排着声音的盛宴,混合成震耳欲聋的巨响。他们厚颜无耻地展示着自己的速朽,倒是那一声‘啪嗒’成为永恒。每当‘啪嗒’一声,我的心就感到刺痛,也感到温甜,它指示我,这才是真正触动灵魂的声音。”毕星星还写道:“由乡村到城市的道路上,数不清的脚印,带着各色的泥土,密密麻麻踩到了城市的水泥地面……这一支迷失了家园的队伍里,也弥漫着我们一家无可奈何的惆怅和苍凉。漂泊,是现代人永远的宿命。乡村,却是我们烙印终生的胎记。”听到毕星星这样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也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真情的感叹,我就不由得要说,我们民族其实从实质上并没有“走出乡村”,我们民族“走出乡村”的路还十分十分地漫长,还要经历非常非常的曲折与坎坷,中国学界当今对现代性的反思,也还是移植的、平面的、肤浅的。或许,我们在对乡村的回望与反思时,还需要重新确立我们的价值立足点。这,或许也是今天民间的“小历史”对历史进行叙说时所应该有所警惕的吧?
《坚锐的往事》值得评说之处还有很多,引发的问题也还有很多,诸如那一时代乡间的民谣,那是比那一时代主流诗歌更为真实的对历史的记忆;诸如那一时代乡村婚姻生活与性生活的民间的个人性记忆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记忆等等。总的说来,毕星星这种基于民间的“小历史”的对乡村历史的回望与反思,对于唤醒、修正我们对中国乡村的记忆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因为诚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说:“数十年间,国人的集体记忆也早已经损毁得不成样子……1949年以后的生活,历史已经书写涂改又书写几经轮回。走过的日子,穿越的事件,翻开书,大惊失色,白纸黑字早已不是你经历的记载。”无论对于历史“民间眼光与精英判断”怎样地“竟然如此互相抵牾,互相哂笑”,但“一个完整的记录”毕竟“有待各色各样的记录去丰富补充”。《坚锐的往事》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及时的现实性极强的丰富与补充。
[1] 毕星星.自序·坚锐的往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