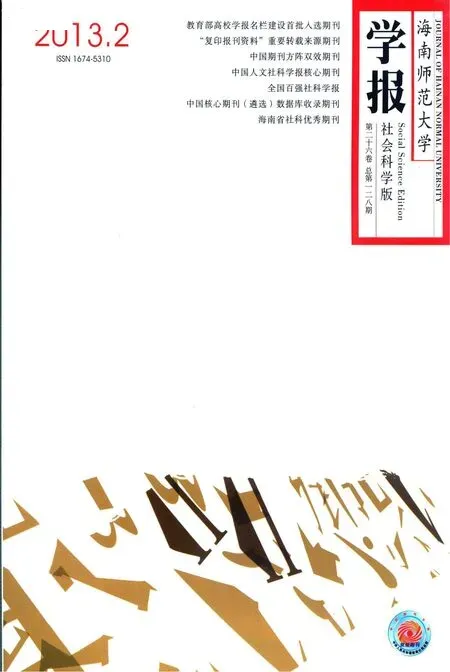现代性社会的疾病隐喻——评王刚的长篇小说《关关雎鸠》
李彦姝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
一
王刚在《关关雎鸠》的创作谈《关关关关》中指出:“当今作家都对历史题材更感兴趣,我总是看着社会现实问题,中国的大作家都是农民问题的专家,我只关心城市。”[1]毋庸置疑,就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历程而言,乡土叙事和历史叙事占据了小说家的大部分精力(就严肃文学而言这样讲是大致不差的,通俗文学则另当别论) 。当把视线拉回到城市和当下的时候,小说家们则显得力不从心。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直视当下、不愿意干预现实,而是说由于“身在此山中”的迫近距离,生活在城市中的作家(当今文坛绝大多数作家都生活在城市中)不易廓清城市生活的真实面目和复杂内涵。或者说他们对于当下种种“社会病”、“城市病”,因缺乏揭示的勇气和智慧而显得无从下手。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缺少距离感的城市书写往往是危险的尝试。王安忆就曾指出城市叙事的局限:“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2]城市书写容易流于单调和肤浅,严肃而深刻的城市书写对于作家是一种巨大挑战。当怀揣着这样的判断来看王刚的长篇小说《关关雎鸠》(以下简称为《关》)的时候,就不得不赞叹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用严肃文学的态度揭露世俗问题的智慧。
王刚认为自己的写作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英格力士》,一种是《福布斯咒语》。我会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写下一部小说。比如我现在在美国开始写的小说《关关雎鸠》就走在《英格力士》那股道上。”①见孙小宁:《作家总是千疮百孔 矛盾重重》,《北京晚报》,2011年4月18日。
由此看来,王刚在《关》创作之初,即有着明确的主题意识和创作意图——即创作一部与《英格力士》存在精神继承关系的严肃文学作品,而非《福布斯咒语》那样迎合大众审美品位的通俗文学作品。事实也大致如此,《关》所描写的校园/教育题材与《英格力士》十分接近,都体现了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
这两部小说中,师生/教师关系、校园生活、教学事件等均构成了主要的叙事对象,甚至在人物关系的建构上,两者也颇为相似。《关》展现了戏文系教师兼戏剧艺术家闻迅古典浪漫的心灵气质,这个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格力士》中独具个性且气质不凡的英语教师王亚军。王亚军与闻迅都是富有激情、怀揣理想、期望在讲台上实现人生价值的师者,阿吉泰和岳康康都是高贵、宁静、享受孤独的单身女教师,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间均彼此倾慕,也都穿插了苦涩的师生恋情节,但所有的爱情尝试最终都无果而终。纵观故事主题和人物设置,可以说两部小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事实却不尽然。《英格力士》讲述的是“文革”时期发生的故事,仍然具有历史叙事的种种特征,但是,到了《关》这里,历史就彻底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现实的焦虑和批判,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关切。现实书写无疑出自对于历史的继承,但是现实所衍生的种种新问题,却是历史所未曾遭遇过的。闻迅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境,很多是王亚军所无缘面对的。
二
苏珊·桑塔格曾说过:“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3]5《关》中,几乎每个社会有机体都是疾病王国的公民,都处于一种自知或不自知的“带病生存”状态。
《关》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揭示了病症所在,更在于揭示病症时所采用的方法,即“感伤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将那些普遍的、棘手的社会病症置于反讽性、戏剧性的叙事策略之中,从而营造出一种悲喜交加的荒诞感。
“疾病是一种惩罚,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他就是该疾病的病因。”[3]52按照这种说法,小说中谢达所患的癌症,无疑是对他“文革”时期懦弱表现的惩罚,进而,疾病也是他对自己在特殊年代所欠下的历史债务的清还。那么,大学生刘元的病症和病因又是什么呢?刘元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性格敏感,情绪多变。按照外公柳先生的旨意,进入到戏文系这个他丝毫不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从刘元创作的剧本中可以判断,他生活在一个母爱缺失的家庭,他对女老师岳康康变态式的跟踪、偷拍或许正缘于潜意识里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 。当刘元发现岳康康和闻迅已经陷入爱河时,他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突然爆发,不计后果地将不堪入目的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给当事者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刘元最后死于自杀,而能够解释他自杀原因的日记内容被作者有意识地遮蔽起来。疾病?失恋?忏悔?……人们只能去猜测他的死因,最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因为看不到希望”。刘元是当代90后一代大学生的缩影——外表阳光时尚,思想前卫叛逆,但是内心脆弱敏感,他们在年龄上已经跨入成人的行列,却无法以成人的心智支撑起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也不善于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压抑与他人沟通,最终导致自我的毁灭。刘元以他无常的命运为当代青年人的心理病症作了一个注脚。
疾病缠身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和城市的普遍境遇。首当其冲的城市病是“人际病”,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韩少功将城市定义为“隐者之城”:“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4]的确,城市人乐于彼此保持距离,各行其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朴素的交流成为了奢侈品,在大学里也不例外。学生与老师是不同世界中的物种,缺乏对话,难于沟通,“老师是猫,却真的不知道在老鼠洞穴里的学生们每天在怎样过日子。”[5]因此,当闻迅走进学生宿舍时学生们的惊讶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之前从没有老师走入过他们的私人空间。老师缺乏对学生应有的同情,他们无法理解学生失去父爱的痛苦,学生对父亲亡灵的怀念竟成了老师冷嘲热讽的对象。教师之间的关系同样不堪一击,他们是泛泛之交的同事或学术上的竞争对手,却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同道。
现代性社会的另一种病症是“速度病”。速度是衡量现在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现代化的城市规划、通讯设备、交通方式都在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生活速度。古典的生活方式不复存在,舒缓的心灵生活成为了历史。闻迅和岳康康不愿自己的主体性被销蚀在繁冗疾速的现代都市中,“希望一切都慢下来越慢越好”。[5]于是,他们解脱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捆绑,采用互致手札这种古老而浪漫的沟通方式,对于信件的漫长等待无疑放缓了人们对于速度的想象,重新确立了心灵的节奏并寻觅到遗失已久的主体性。当整体性的都市不再成为人类心灵家园的时候,个体内在精神的寻觅和重建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无疑成为缓解人与城市紧张关系的重要自我救赎手段,以此成功地抵制了都市生活对人性的异化和工具理性对心灵的摧残。
除了互致信件,他们还在漫游北京城的过程中,寻求心灵的滋养和伸展。密集拥堵的现代化都市中总会存在一些适宜人类自由呼吸的夹缝,漫无目的地游走于旧街区、老胡同、古城墙,在深街小巷中回味记忆的芳香,在传统小吃中品咂岁月的精华,用单车和脚步绘制出一幅充满怀旧气息的心灵地图。但是,在忙碌紧张的都市人眼中,闻迅和岳康康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闲适惬意,却又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
在《关》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来书写的莫过于“大学病”。而揭示这一病症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直击要害,而是十分巧妙地采用了婉转迂回的叙事策略。《关》多次提及皮兰德娄的荒诞剧——《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令人拍手之处就在于“戏中戏”技巧的娴熟运用,将戏剧镶嵌于戏剧之中。《关》成功地将这一策略借用过来,将戏剧因素移植到小说文本中,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了紧张的互文关系,使小说充满了荒诞感和反讽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戏中戏”的策略对于小说有着何种叙事伦理上的意义呢?我以为,《关》中主要关涉两部大戏:艺术的戏与人生的戏。当闻迅以戏剧家的话语方式和处世姿态闯入古板、严肃的大学体制丛林中时,即艺术的戏以一种“不自然的”的方式镶嵌在人生的戏中时,巨大的错位感便显现了出来。
三
伽达默尔说:“戏剧是文学本身进入此在的活动。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Gespieltwerden)。”[6]也就是说,剧本本身并无生命力可言,剧本必须被演绎、被呈现、被释放,通过与人的“存在”发生关联来彰显生命力。《关》中,闻迅就是一个敢于在现实生活中大胆呈现、释放戏剧魅力的剧作家。他通过自身戏剧化的生存方式,将戏剧复活在现实生活中,构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事件。
按照人类表演学的观点:“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当做表演来研究。”[7]人类表演学有两个分支——艺术表演学和社会表演学。在艺术表演学当中,“戏剧”是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戏剧表演必须发挥激情、营造高潮,强调戏剧冲突和自我表现。而社会表演学则“强调社会的规范:表演既有向社会展示的一面,也有受制于社会的一面”。[7]社会表演必须要从艺术表演中吸取经验教训,它追求和谐、讲求原则,目的是化解冲突。也正是基于对艺术表演和社会表演的划分,《关》才显示出它的特别的寓意。
闻迅是一位成功的剧作家,他对戏剧的理解、对艺术的执着令人钦佩和赞叹。他热爱戏剧,热爱与艺术相关的一切,戏剧、音乐、诗歌等等。默念、吟诵、赞叹那些经典的剧本台词成为他生命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以至于与戏剧相关的各种专业词汇,每天如影随形。闻迅是一位心无旁骛的艺术家,他十分了解艺术表演的规律,却不太懂得社会表演的规则,不慎将戏剧表现的方式移植了在人际交往、课堂讲授等场域。从进入大学任教成为“体制中”人以后,他的境况急转直下。他内心清楚艺术家和大学教授的区别,懂得“才华真的可以在任何地方展示,只是除了大学校园”这个道理。但是知易行难,他无法翻筋斗般地立刻从一只高歌的雄鹰变成一只沉默的羔羊,于是注定要在如一潭死水的大学体制内,做一个疯子般的越界者。
首先,闻迅“错误地”把艺术表演挪用于人际交往中,频繁地在与同事、领导交往过程中制造摩擦和冲突。他接二连三地挑战学术权威柳先生,他强烈呼吁对本科课程进行改革,重视剧本写作实践,删减没有必要的课程……而这些提议恰恰触动了很多教师的切身利益。社会课堂的复杂远远超乎艺术家的想象力:大学人际关系的盘根错节、招生过程中暗藏的猫腻,学生家长无奈而违心的行贿……这些都使他感到惊愕,但在他心底仍怀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坚守。柳先生、周大同无疑是社会表演的成功范例。柳先生作为大学里的元老级人物,已经年近古稀,仍然稳坐戏文系的第一把交椅。虽然他自称“性情中人”,实乃固执保守,不逾规矩,十分懂得谨言慎行的生存哲理,深深地把自己埋藏在“中国电视剧艺术概论奠基人”的面具之后。周大同早已厌倦了了无生气的大学体制,但是身为戏文系主任,他也只能任凭岁月逐渐消磨掉自己的个性,机械麻木地做一位称职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
再者,闻迅“错误地”把艺术表演搬进了大学课堂。殊不知,他的灵感、激情和先锋式的授课方式,在当下的大学课堂同样失去了合法性和有效性。学生们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头脑被形形色色的概念、理论浇注,并认为这种方式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正当途径。所以,当闻迅以特立独行、热血沸腾的姿态站立于讲台的时候,他们反而兴趣索然,表现得无所适从。似乎课堂上师者的“灵魂出场”,变成了一件十分怪异、令人费解的事情。课堂的失败经历,使闻迅痛下决心完成他的蜕变,最终他被大学体制所驯服,开始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传声筒”——这不仅成为了他的授课方式,也成为了他的生存法则。“让一开始很清醒的人最后变得很迷茫,这就是现实。”[8]
王刚通过他的大学校园叙述,向我们抛出了一系列问题:究竟是平庸的老师驯化出了愚钝的学生,还是愚钝的学生炮制出了平庸的老师?当下,为什么在生产思想的大学校园,随处可见的都是“思想上的失踪者”?而为何像闻迅这样既有新思想又有真性情的知识分子却成了大学校园中的怪物?当然,小说只是向我们抛出了这些蹩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和解决路径,只能去小说以外慢慢寻找了。
《关》“很像是一首伤感的诗”①《人民文学·卷首语》,2011年第10 期,第1 页。源自席勒对“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分类。。它讲述的是“一个理想的遥不可及的故事”[8],讲述的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如何被现实刺伤灵魂、屡屡受挫终致无家可归的故事。题名“关关雎鸠”充满了对古典浪漫情怀的想象,而小说所感喟的恰恰是古典浪漫情怀的失落;“关关雎鸠”传达了对于理想和爱情的期许,而小说所指涉的恰恰是理想的迷失和爱情的虚无缥缈。
我们同情闻迅的同时,更同情这个身患顽疾的社会和时代。面对着钢铁般坚韧冷峻的外部世界,理想主义者内心深处的激情与伤感尽管有时会显得十分苍白,但又恰恰是一剂自我疗伤时所不可或缺的安慰剂。
[1]王刚.关关关关(创作谈) [J].长篇小说选刊,2012(2) .
[2]王安忆.生活的形式[M]//茜纱窗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76.
[3]〔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韩少功.扑进画框[M]//山南水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48.
[5]王刚.关关雎鸠[J].人民文学,2011(10) .
[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译者序言[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
[7]孙惠柱.人类表演学和社会表演学——哲学基础及实践意义[J].戏剧艺术,2005(3) .
[8]白烨.《关关雎鸠》:像一面镜子[J].长篇小说选刊,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