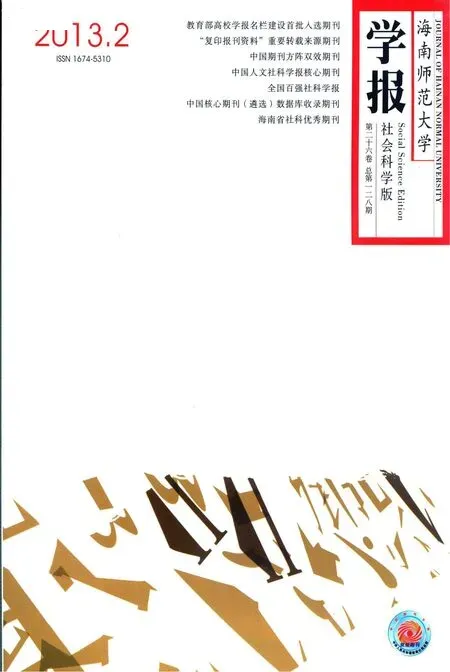诗性批评与诗史建构——评张德明《新诗话·21世纪诗歌初论(2000-2010)》
史习斌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在诗歌告别昔日的辉煌进入自处自适,诗歌批评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和学理化的今天,诗歌和诗歌批评离关注它的人的距离也在渐行渐远。好在还有另一批人,或是诗人,或是学者,或是诗人兼学者,他们用内行人的姿态进入诗歌,用内行人的语言进行表达,以诗的规律对待诗歌的写作、批评与研究,克服着读者对诗的畏惧感和头痛症,展示着诗之为诗的魅力。张德明教授的新作《新诗话·21世纪诗歌初论(2000-2010)》(九州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下简称《新诗话》)便是这种努力的成果。这部35万字的新诗研究专著,在代表文本细读和重要诗人扫描的基础上,以“现象”、“地域”、“诗群”为关注点,通过“结构”和“本体”的论述实现理论构建,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不乏真知灼见和理论深度,在当下诗歌批评精神和新世纪诗史建构方面具有探索意义,对处于生长期的21世纪诗歌的写作、评价、整合和再生等都具有重要的建设价值。
在一个诗歌源远流长、诗教的历史悠久并早已形成传统的文化结构中,主流的诗歌与诗歌批评担负了太多诗歌甚至文学以外的东西。在当代批评领域,理论的“爆炸”固然能够为解诗提供参考资源或思考路径,但过分倚重理论的花样翻新和分析技术则忽视了对象的审美特殊性,无疑会掩盖甚至淹没诗歌批评的诗性特质,使得从诗教的重压下勉强解放的诗歌与诗评再次步入诗性遭受干扰的陷阱。采用“诗话”的形式展开诗歌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即为古代诗话经典。这些诗话著作讲究知人论世、注重直觉思维,具有精短的篇幅、精炼的语言和灵活的形式,大可为诗性不足的当代诗歌批评吸收借鉴。有鉴于此,张德明教授向当下诗歌批评界发出了“重启诗话传统”的呼吁,试图以“新诗话”形式来重构新诗批评的话语模式,从而振兴新诗批评,促进当代诗歌发展。《新诗话》正是张德明教授所倡导的“新诗话”诗歌批评话语模式重构的一次实践。其重点不在学术观点的“四平八稳”,而在智慧与灵动的交织。它在尊重诗歌固有特质的前提下,拓展了当下诗歌批评的视野。它在将西方诗学思想作为理论储备的基础上,借鉴和继承了传统诗话式诗歌批评微言大义、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发现了被诗歌研究的科学性屏蔽了的丰富而生动的个体生命感受,吸取了古代诗歌批评采用的不同于西方分析诗学的感悟诗学,复苏了诗歌批评的诗话传统,是当下诗歌批评诗性回归的成功范例。
《新诗话》的诗歌批评在态度上真诚率真,绝不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包括理论与创作的对话,诗人与诗评家的对话,古今、中西批评理论自身的对话。在全球化的当下语境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论的冲击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几近“失语”的尴尬状态下,如何吸取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长处为我所用,如何复活和甄选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的优势,重建符合国人习惯而又尊重艺术审美规律的诗歌批评“话语模式”,是一个时代课题。而对话的姿态对改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紧张关系,真正重建大家认可的批评模式至关重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理解创作的甘苦,知人论诗,从诗人的角度与处境理解文本,挖掘那些关乎心灵和生命的独特体验,是对诗歌诗性的尊重,也是诗歌批评诗性特质的体现。
《新诗话》的诗歌批评在语言、体式上有亲近感,富有诗性美,而不像一些艰涩难懂的八股式论文那样让人敬而远之。其对诗人的批评和诗歌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印象批评的意味。《新诗话》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而不以理论为鹄的,没有理论术语的堆砌和炫耀但却不乏理论的深度。正是因为如此,《新诗话》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诗性特质。该著所提到的潘洗尘的理想色彩和生命情绪、李少君的“草根”与“自然”、毛翰网络诗歌音、画、诗相互交融的立体美、潘维江南印记的韵味、陈先发桐城余脉的味道等,都绝非纯粹的逻辑分析思维方式所能理解到位,而只可能借助敏感的诗性感悟方能领悟。此外,“片言居要、见微知著”也是诗性批评的智慧之功。《新诗话》能从年轻诗人博客链接的称谓窥探出“主编诗人”面临优势与陷阱并存的“现象”;从安琪的诗中读出她的人生遭遇,从而悟出“性别”对于北漂女性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公正待遇;从郑小琼的“幸运”背后看出了“时代的悲哀”和引人注目之下掩盖着的沉痛的血泪史……这种从主观心灵出发的诗性感悟,注重可读性与生动性的诗性灵动,饱含形象蕴藉的诗性韵味,使得《新诗话》的诗歌批评具有不同于纯粹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研判的西学色彩,而具有独特的东方思维特色,其整体性观照、直觉型运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想象力、形象性和创造性,是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说的“诗性思维”、“诗性智慧”的直接体现。
表面看来,诗话的“精炼”与“零碎”像是对新世纪诗歌众声喧哗现状和大部头诗评阅读危机的妥协,但从深层次来看,这一选择既是碎片化、快节奏的文学审美的时代需求所致,更是对当下诗歌批评现状与模式的反抗。波德莱尔曾经说过,最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新诗话》是“有趣”的,也是“诗意”的,它以“诗话”的方式实现诗歌的批评与研究,既是对诗学研究者灵光闪现的瞬间记录,又是对当下诗坛普通读者接受兴趣的尊重,此二者对于诗、诗人、诗评和诗歌研究都十分重要。在我看来,写诗应该是诗的,读诗应该是诗的,评诗应该是诗的,甚至诗歌研究也应该是诗的!因为文学是诗性的,诗歌是诗性的。在批评的“诗性”这一点上,拥有诗人与诗评家双重身份的张德明教授与他的《新诗话》给人的印象无疑是深刻而难忘的。
诗歌批评不仅应该是“诗的闪耀”,蕴涵“思的智慧”,持续系统的批评还应该有利于“史的建构”。《新诗话》贡献给21世纪诗歌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为生长中的当下诗歌提供的诗史价值。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一个开放的叙述性存在,诗歌史自然也是一样。当然,诗史的撰写应该有一定的积淀和距离,这样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并有利于观点和立场的客观公正。这一点张德明教授当然是清楚的,正如他所说,“为当下诗歌写史是危险的”,真假并存、泥沙俱下。正是这种显在的“危险”,要求研究者要具有“史识”,能够透过权力干扰和利益诱惑看清众多“现象”甚至“乱象”背后的本质,辨别诗歌与诗人的真假与品味,从而挑选出真正执著于诗歌写作的优秀诗人,筛选出有可能流传成为经典的优秀诗作,对这些有可能“入史”的诗人、诗作和诗歌流派进行分析研究,为专业诗歌史的编撰提供丰富的史料、有价值的观点和可供参考的论述。
《新诗话》在诗史建构方面突出了同时代人的优势,这表现在现场对话的真实性。这本著作所选取的论述对象是新世纪的诗歌和诗人,这种直入文坛前沿的当下性对主体和客体而言都有不可替代的在场感。在不断变化生长的诗坛现场,作者和对象之间是平等对话和双向交流,而不是面对封闭的材料所进行的想象性“还原”与“复活”,也不是对象缺席而进行的单方面审判,这就为“史论”的公正客观提供了前提。也正是研究对象自身发展所具有的动态变化性,使得论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掘它的多方面特性。对于当下诗坛尤其是新世纪的诗人,张德明教授有着刻意的关注和持续批评的勤勉,加上自身诗歌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双重身份,他与所论述的诗人之间是了解或者熟悉的,诗坛的大小事件他也基本亲历过,这种零距离突入当下诗坛现场的姿态和身处其中的同理心,让他对诗歌自身、诗坛语境和时代大环境的理解少了几分常见的“隔阂”,为其真正做到“知人论世、知人论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此出发,《新诗话》选取了李少君、安琪、郑小琼等十位诗人及其各自代表的诗歌现象进行分析,精选了执着于江南书写的潘维、江汉平原风格浓郁的阿毛等七位地域色彩浓厚的诗人为研究对象,同时选择了“中间代”诗群、“打工”诗人群、“新红颜写作”诗群等九个有代表性的诗群为考察对象,加上“结构论”和“本体论”中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总共有上百位诗人,近200首诗作。这种初步筛选和重点用力暗含着著者的选择和判断,为诗史的撰写补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源和参考。在“现象论”中,潘洗尘的理想主义追求与诗愤情绪力量,李少君的“草根诗学”倡导与“新红颜写作”命名,毛翰的学者型诗人身份、诗歌超文本实验和诗歌教育争鸣,安琪对“中间代”的贡献以及这一群体的特殊性,都具有不容忽视的诗史价值。此外,《新诗话》还将目光投向了主动避离现代社会的诗人杨健的“隐士”生活与诗歌写作,喜交诗友的诗歌热心人、诗界“义工”黄礼孩以及他的诗歌具有的温情、和善与宗教精神,在一片伐挞声中肯定了赵丽华“梨花体”之外作为一个诗刊编辑的“专题化”办刊理念和口语化诗歌写作的客观价值。在“地域论”中,选取了江南、云南、桐城、川陕、新疆、江汉平原、甘肃等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浓郁的地域及其代表诗人进行分析,初步绘出了一幅地域视角的诗歌地图。如果说“现象论”和“地域论”还只是间接影响诗史的建构,“诗群论”则直接涉及到诗歌发展历程的核心问题。“中间代”诗群、“70后”诗群和“80后”诗群的代际划分及其相关论述概括了当下诗歌的创作主力军和相互衔接的时间历程,“下半身写作”诗群、“低诗潮”诗群和“神性写作”诗群代表了几种不同的诗歌主体姿态和文化精神诉求,“打工”诗人群是市场经济浪潮下底层写作的代表,是新时期以来诗歌现实主义的强势回归,“新归来”诗群表现出在物质生活之外对精神生活和心灵渴求的特殊性,“新红颜写作”诗群则突出了网络时代和女性人格与艺术自觉的时代诗人性别特征的新变化。这些重要诗群的轨迹追踪和核心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当下诗歌的诗史建构都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所在。
《新诗话》发挥了著者零距离接近诗人和长时间文本细读的优势,不仅有来自诗坛一线的资料趣闻,帮助读者发现诗坛的边缘与隐秘,而且不乏深刻闪光的诗性智慧,有现象描述及其背后的本质探讨,有地域观照的特殊视角,有对当下诗坛力量代表的重要诗群的分析,有对作为诗歌成长土壤和平台的诗歌刊物的关注,加上诗歌“结构”的探索和诗歌“本质”的探讨,《新诗话》以借鉴却又不同于传统诗话的“新诗话”形式,呈现出诗性批评的鲜明特色,具有诗史建构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