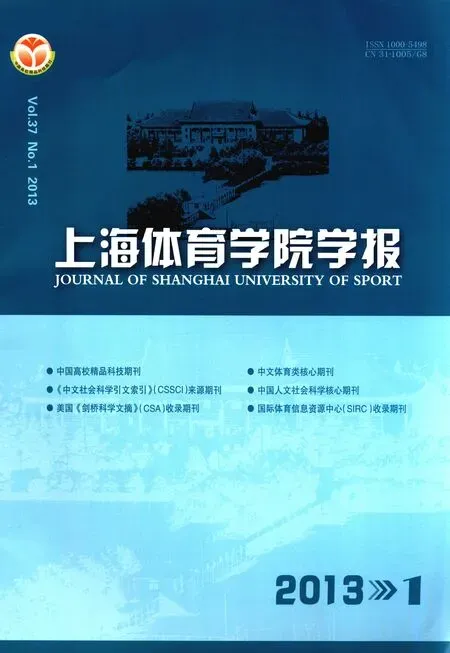彝族村寨火把节“火-祖-摔”的文化解读
花家涛, 戴国斌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200438)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火把节被认为是彝族的重要标志和象征符号。彝族之所以敬火,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起源于天、燃烧于地的火是人类诞生的前提,而与人生相关。彝经《勒俄特依》这样记载他们对火的崇敬:“远古的时候,天庭祖灵掉下来,掉在恩杰杰列山,变成烈火在燃烧,九天烧到晚,九夜烧到亮,白天成烟柱,晚上成巨光。天是这样燃,地是这样烧,为了创造人类燃,为了诞生祖先烧。”《吕氏春秋·义赏》这样评论彝族人(羌为彝族先民[1]):“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同样,《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记:“羌人死,焚而扬其灰。”在彝族人眼中,不仅祖先归天要借火“净化”[2],而且他们也通过火向住在天上的祖灵祈祷[3]。作为原始宗教信仰制约彝族生活各个方面的“祖先崇拜”,与“火崇拜”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彝族火把节[4]。也将“摔跤”作为沟通祖灵的媒介嵌入火把节仪式之中[5],形成了彝族火把节的“火-祖-摔”三元素。研读彝族火把节的传说与史志资料,梳理彝族火把节三元素的文化复合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是解读彝族火把节摔跤文化实践的新窗口。
1 远古时期:“生殖崇拜”下“火-始祖-摔跤”的文化复合体
彝族先民将“火崇拜”与“图腾始祖崇拜”相结合,形成了火把节源头的“火节”,并在祭祀“火节”的仪式中,通过摔跤的仪式性动作来表达“生殖崇拜”的意向,组成了远古时期“火 -始祖 -摔跤”的文化复合体。
1.1 火崇拜 “世代传承、少有变更”的“火崇拜”源于原始宗教信仰[6],是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先民看来,火一方面带来光明,驱走黑暗、猛兽与寒冷,可增强其生存能力;另一方面烧毁森林,烧死人畜,吞噬生物,而生恐惧感,视若神灵。“火崇拜”观念一旦形成,人们对“火”的自然实体崇拜就过渡到对“火”的灵物虚体的崇拜,产生相应的祭祀仪式[7]。“火崇拜”祭祀仪式寄托的是彝族先民对“火”既崇敬又敬畏的矛盾心理。
1.2 始祖崇拜 在母系氏族公社前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生活与畏惧自然现象而产生的自然崇拜相结合,形成了物、神、人三者关系杂糅交错,把部分自然物神话为与自身有血缘关系亲属的图腾始祖崇拜[8],这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自发性原始结合,也是彝族祖先崇拜的源头[9]。从现今存留痕迹来看,彝族先民的图腾始祖有竹子、葫芦、虎、树等,尤其是虎图腾。对图腾始祖的祭祀,目的在于祈求生命母体给予永不衰竭的生殖力、生命力。“火”也有化育万物的特点,是万物生长之源,是再生之神。在彝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火崇拜、始祖崇拜与生殖崇拜(种的繁衍[10])有着深层的关联。
1.3 “生殖崇拜”中的“扭结滚摔” 远古时期的彝族先民以“生殖崇拜”联系其“火崇拜”与“祖先崇拜”。通过“仪式交流传播”的方式[11],将祭祀的身体动作仪式化为“扭结滚摔”的摔跤意向,以此祈求始祖之灵来抗拒自然压力,表达生殖繁衍的需要[12]。
远古时期“生殖崇拜”信仰下“火-始祖-摔跤”的文化复合体,仍存留于云南双柏县者柯哨村彝族的火把节习俗之中。首先是毕摩唱“六组分支”经历,其次是代表始祖的“草人”唱《哭母调》,再次是烧“草人”仪式(身披草衣的“草人”作为祖先的“化身”,烧“草人”意为“火化归天”“火化返祖”),最后是成对男子扭结在一起从山坡“滚摔”到山下。整个仪式以代表始祖的“草人”为中心,在唱《哭母调》时高举男性生殖器“拟状物”,表达种族绵延的渴望,在“火化返祖”后其祖先的生殖崇拜又具象为“扭结滚摔”的动作(一名男子头部顶在另一男子胯下,另一男子将其脖子紧紧夹住,两人同往坡下“扭结滚摔”),寓意获得祖先强大的生殖力,“由山坡滚下”降临人间,表征“种族绵延”意向[13]。
2 汉唐时期:“鬼神信仰”下“火-祖先-摔跤”的文化复合体
与源自汉时的“羁縻”政策相适应,汉以后中央政府根据彝族先民的鬼神信仰特点,对彝族实行“以夷制夷”的“鬼主制度”[14]。作为集政权、神权以及军事于一身的部落酋长——“鬼主”,也通过彝人“鬼神信仰”与“祖先崇拜”的关联,针对其“除秽禳灾”之求,实现阶级统治之目的[15]。
2.1 火神信仰 汉唐之际,远古时期“自然实体火的崇拜”在彝族先民的“鬼神崇拜”(凶死者灵魂转化而来的“恶鬼”会致病成灾,正常死亡者或祖先死亡后转化而来的“善鬼”能保佑生者、使家族兴旺。如果“祖先鬼”因得不到祭祀、子孙违反行为规范就会惩罚子孙)[16]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灵物虚体的火崇拜”,“火”成为“神”。火神不仅是“清洁的源泉和象征”,具有“使一切东西纯洁的能力”,而且也是家庭保护之神,可以避邪、除秽、驱赶各种魔鬼[17]。由“火节”发展而来的“火把节”,正是彝人燃烧火把,用袅袅青烟迎接祖先回来享祭赐福之举。
2.2 鬼神信仰 汉唐时期,在保持对始祖尊崇和敬畏、得到始祖保佑的基础上,还在“鬼神信仰”的作用下“世俗化”“工具化”为“部落酋长”祖先崇拜[19]。“遐稽我(祖),肇自汉朝……汉封神,宋封佛,祀重千秋”[18],“汉封神”尊酋长之先为神,强化了酋长的权威与控制,唐朝形成了“鬼主”制度(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原始宗教活动)。《唐书·南蛮传》载:“夷人尚鬼,请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唐代樊绰《蛮书》载:“乌蛮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这样,集政权、军权与神权于一身的“鬼主”,通过信服“口咒、驱鬼、还魂、招魂、占卜、禳解”等仪式活动,预防或驱除灾害[19],同时强化了地方控制。
2.3 鬼神信仰中的“人神扭打” 火神崇拜与部落酋长祖先崇拜相联系,形成“鬼神信仰”下的村寨火把节的新的祭祀方式。“火”成为寨民与“祖先”的沟通媒介,一旦瘟疫传播、灾害降临,便“建坛打醮”“燃火求祖”。在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眼中,为了人畜安康,而在火把节举行摔跤比赛,“在摔跤中多跌几跤才痛快!才能把病魔统统从身上摔掉”[20]。这样,远古时期“生殖崇拜”的“扭结滚摔”转换为“驱鬼、扶畜、免灾”的“禳解”,表征为祈求人畜平安的“人神扭打”之意向。在火把节中,不仅彝人汇聚跤场,摔跤成为他们向“祖先”献祭的“贡品”,而且,他们还规定,“同寨人之间不摔跤,获胜者须是他寨人,且当晚必须离开举办地”,在他们看来,只有别寨英雄战胜或带走恶魔,才能佑护本寨人畜平安。
3 明清时期:“祖灵崇拜”下“火-祖灵-摔跤”的文化复合体
祖先崇拜发展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宗族祖灵崇拜”,在彝人看来,人死不仅灵魂不死,而且神界以“祖先之灵”最为重要,自己宗族的祖灵只佑护自己的子孙。这样,彝族宗族一切事务均受“祖灵”控制[21]。《普兹楠兹》载:“祖把牲畜护,牲畜得兴旺;祖把庄稼护,粮食堆满屋。子孙在世间,祖宗来保护。”[4]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带来的民族融合,其“宗族祖先崇拜”不仅与英雄崇拜相联系,而且还与农业生产及民族关系有关,彝族村寨火把节之中的“火-祖-摔”文化复合体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民俗事象。
3.1 以“一跤定胜负”占卜农业生产之丰歉 在明清凉山彝族传说中,人们认为天王不希望人间过上好日子,不仅派十大力来彝山踏坏庄稼,而且在彝族小伙子包聪战败了十大力之后,天王又撒下一把香灰面,变成数不清的吃庄稼害虫[22]。彝族人在6月24日点火把烧死害虫,并将这一天点燃火把、除恶灭害、摔跤扭打、共祈丰收的活动节日化为火把节[23]。这样,原来祈求“种族绵延”与“除秽禳灾”的彝族火把节摔跤,在祈求丰收期望中,又新添了预测农业丰歉之功能。嘉靖《寻甸府志·风俗》说:“(彝族)六月二十四日杀牲祭祖。夜以高竿缚火炬,以明暗占岁亩丰。男子以力相搏者,谓之跌四把腰”。在彝族人们看来,得“祖灵”所赐“神力”而获胜者,其村寨来年的收成必定胜出一筹[24]108。
同样,汉唐人希望别寨英雄战胜恶魔、佑护本寨人畜平安的“人神扭打”,变成了明清人对本寨胜出的企图,摔跤行为也由原先的象征性逐渐过渡到竞技性——不仅形成了扯抓对方腰带对抱抵肩的“跌四把腰”技术,而且形成了“一跤定胜负”的裁判法(以“第3点着地、被对方提抱起腾空旋转3转”作为输赢标准[25])。另外,一跤定胜负的“占卜”如同“神判”,不仅由“人神沟通之中介”的毕摩主持赛事活动,火把节摔跤成了神灵监督下的“神圣的比赛”[26];而且彝族摔跤也移作村寨间山林纠纷、地盘争斗的裁决法,“胜者是、负者非”乃神判之果,具有了无可争议的神判性[24]163。
3.2 以“战无不胜”崇尚护卫寨民的英雄 凉山布拖县流传的火把节由来的传说认为:远古时,天帝时常派兵侵扰人间,每每败北后又派天上大力士到人间挑战,并宣称若有人能打败大力士则永不再犯人间,否则人间将永归天帝统治。在这场“人神之摔”中,为了纪念战胜天庭大力士的人间大力士,彝人每逢节庆都相聚摔跤而赛[27]。这种传说折射的社会现实是,元明清时期彝族社会封建制发展与奴隶制变化中汉族大姓与彝族奴隶主及部落贵族的势力争夺、“冤家打斗”以及“赋重役繁”。这样,火把节摔跤传说成了现实压迫的隐晦叙述,祖先崇拜也“神化”为护寨英雄,火把节摔跤活动成了“演英雄故事”的仪式。
首先,通过“全胜”体现英雄的勇猛,比赛不分年龄、体重,以三战三胜或两战两胜者为赢,胜者为擂主,继续比赛,直至无对手的全胜;其次,全面展演英雄的全能,不仅赤膊上阵展雄健身姿,而且以“摔、掼、挑、仰、侧翻、侧甩”等技巧而演英雄精湛之技,通过强者将弱者轻轻举起后慢慢放下而展英雄之武德;最后,在场上激烈角逐、场外热烈呐喊与助威中,组建了“展英雄之姿、寻英雄之影”的仪式[28]。
3.3 以“谦逊礼仪”表征“夷夏互化” 滇东南彝族撒尼人为人畜安康而摔的传说是,一名叫“若格帕”的撒尼青年在犁田时遇见了流亡的建文皇帝,两人话语投机,结拜兄弟,生活在一起。一天,他俩在医治一头病倒的牛后,高兴得跳起来,并拥抱着在地上不停打滚……路过牧羊人以为打架,上前劝解,在弄清原因后说:“这样的好事,应该高兴,你们就互相抱着使劲地摔吧”[29]。将摔跤起源说成“明朝流落皇帝与彝族青年因治好牛喜极而摔”,折射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演绎了彝汉关系的新图景。
从汉唐时期的“羁縻政策”、元时的“土司制度”到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越来越直接化,也在以军事移民打破土司独霸一方、叛服不定之后,以设置卫所、军事屯田、推广儒学等“改土归流”政策,实践其“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的治理理念,出现“以夏变夷”现象[30],造成滇东南彝族比较普遍的“大分散小聚居”以及“汉彝杂居”的村寨结构[31]。这时,火把节摔跤也添加了许多表征友谊的礼节。以滇东南石林与弥勒等地火把节为例,不仅在“前伸双手上下挥动”开始比赛前,先要热烈拥抱、互相致意,后各退半步、双手往上举、俯身弯腰双手翻掌下落,示意互相学习;而且比赛结束后,胜者要把对方热情地扶起来,擦掉对方肩背上的灰尘,拥抱对手到本村座处,休息、畅谈、交流[32]。这样,与天斗、禳灾害的摔跤,也演变为和睦礼仪的文化实践。
4 结束语
彝族火把节摔跤文化的“火-祖灵-摔跤”3个元素,在历史发展中“既不断增添新内容,也将原先的内容逐渐消解”[33]。首先,远古时期的彝族先民关注“种的繁衍”与“火的崇拜”,在“火神”与“祖灵”的祭祀中通过“扭结滚摔”的仪式表征“生殖崇拜”,“扭结滚摔”成了摔跤的动作意向。其次,面对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保持彝人发展规模以及健康的需求,使汉唐时期的摔跤意向转变为“人神扭打”,作为“除秽禳灾”的文化解读。再次,明清之际彝族火把节的摔跤又添新内容,摔跤成为占卜农业丰歉的活动,“展英雄之姿、寻英雄之影”的文化表演,散发表征民族融合的“谦逊礼仪”气息。
正如中国武术以社会作为发展阵地,在社会化、政治化中推进发展一样[34],从游牧迁徙、演化而来的彝族摔跤,通过与其宗教、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关联而得以传承,也在“火-祖-摔”文化复合体中(在生殖崇拜下作为增强体质的活动,在鬼神信仰中产生平安意向,在祖灵崇拜下展演英雄形象、占卜生产丰歉、表征“夷夏互化”)得以发展。
[1] 《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0
[2] 吉郎伍野,阿牛史日.凉山彝族送灵归祖仪式“尼木措毕”及其价值[J].毕节学院学报,2007,25(2):24-30
[3] 杨甫旺,杨琼英.彝族火葬文化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2(6):65-70
[4] 马廷中.彝族古代原始宗教信仰浅论[J].贵州文史丛刊,2000(1):37-42
[5] 曲比阿果.凉山彝人火文化的传承与变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53-57
[6] 应骥.从火崇拜民俗看夷越文化传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2(5):66 -70
[7] 何星亮.火崇拜略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1):73-80
[8] 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2
[9] 程雅群,景志明.彝族祖先崇拜对婚姻习惯法的制约刍论[J].宗教学研究,2009(1):119-124
[10] 杨甫旺.彝族生殖文化概论[J].楚雄师专学报,1999,14(2):18-24
[11] Mary D.Implicit Meanings:Essays in Anthropology[M].London:Routledge & Kangan Paul,1975:2
[12] 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博”交媾巫术与生殖崇拜[J].民族艺术,2007(1):88-92
[13] 杨知勇.火把节源头的新材料和新思考[J].民俗研究,1993,28(4):48 -54
[14] 张泽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鬼主制度研究[J].思想战线,2012,38(1):115 -119
[15] 陈筱芳.周代祖先崇拜的世俗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296-299
[16] 蔡富莲.论凉山彝族的魂鬼崇拜观念[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3):138-142
[17]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375-380
[18] 何耀华.试论彝族的祖先崇拜[J].贵州民族研究,1983(4):153-168
[19] 段伟.攘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1
[20] 伊藤清司.传说与社会习俗:“火把节”故事研究[J].日本研究,1993(1):51-58
[21] 徐铭.凉山彝族祖先崇拜及其社会功能[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18-23
[22] 谢沫华.火把节的文化含义研究[J].云南学术探索,1998(2):77-81
[23] 葛永才.弥勒彝族历史文化探源[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07-108
[24] 柳田国男.民间传承与乡土生活研究法[M].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25] 朱文旭.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143-160
[26] 张伟岱.云南武术与宗教[M]∥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评审委员会.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0:190-191
[27] 苏呷此色.摔跤:布拖彝人的最爱[N].凉山日报,2007-01-18(7)
[28] 余鸣.火把节记事[J].民族工作,1999(9):42-43
[29] 王建中.论彝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功能[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21(3):97 -101
[30]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2010:43-45
[31] 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54-62
[32] 番丽玲.从传统的游戏到表演:石林彝族摔跤文化的变迁[J].体育世界:学术,2009(2):64-66
[33] 施爱东.“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减法[J].民俗研究,2011(3):5-22
[34] 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