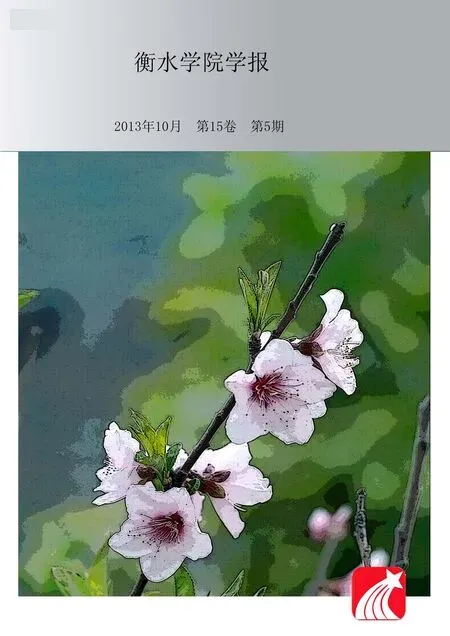董仲舒思想外儒内法考论
杨德春
董仲舒思想外儒内法考论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董仲舒《贤良对》《灾异对》《春秋繁露》所言表面上是儒家的思想,细按之,其本质上皆为法家之思想。董仲舒思想的本质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董仲舒;儒家;法家;外儒内法;《贤良对》;《灾异对》;《春秋繁露》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思想研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董仲舒研究的重要方面。关于董仲舒思想的性质和本质是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就此问题研究之。
一、董仲舒《贤良对》的外儒内法本质
董仲舒《贤良对一》云: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董仲舒主张人君而欲止其乱,应当强力疾作,即硬干或奋力而为,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但大亡道之世则另当别论。这与法家的当今之世竞于气力而主张强力疾作是一致的,大亡道古来有几?可见,这是主张放胆干,止乱或拨乱反正可以不择手段。
董仲舒《贤良对一》又云: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敎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倈,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敎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敎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孔子曰:“不敎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敎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认为人或仁或鄙,不能粹美,良莠不齐,必须自上而下进行改造,与孔子所不同的是孔子主张以君子改造小人要潜移默化,董仲舒之德化是依靠政权之力量自上而下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造,而且是大批量的改造。所谓“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其中“唯甄者之所为”“唯冶者之所铸”简直不把人当人看,一如对待自然物一般对待人,根本不考虑被改造者的反应和感受。这就背离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忠恕而已,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文思想而归于黄老刑名的自然思想。
董仲舒《贤良对一》又云:
臣谨《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倈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君主即位之第一年称元年本是史文之常,《春秋公羊传》以为重事,唯天子乃得称,于是有黜周王鲁之说。以天子之权予鲁。董仲舒为治春秋公羊学的学者,故其对策云: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以下改元为大事,皆《春秋公羊传》所开启。称元年、示大始而欲正本就是为了主张更张更化,即从根本上施行社会变革,而不是进行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这是与孔子的思想相左的。下面之引文董仲舒就提出了更张更化的主张。
董仲舒《贤良对一》又云: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茍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倈,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董仲舒认为统治的对象——人民与工匠施工的对象一样。孔子认为宰我如朽木粪墙不可教,就不教了,并不主张对宰我施行肉体消灭或从根本上进行强制性改造。董仲舒主张更张更化,依靠政权的力量,通过包括杀戮在内的强制措施自上而下地正不正而反之正,从根本上施行社会变革。这与董仲舒《庙殿灾异对》之主张杀戮宗亲以正不正而反之正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庙殿灾异对》明言诛杀,而《贤良对》较为隐讳。《庙殿灾异对》与此有关的文字如下,可对读。
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周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
董仲舒《贤良对二》云: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敎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董仲舒主张贤者的迅速提升,毋以日月为功。反对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这是主张社会等级结构的迅速变化和根本变化,都是激烈的革命化的变动,与社会等级结构渐进式的改革格格不入,故这与儒家的基本思想相去甚远。另外,董仲舒主张贤者的迅速提升,毋以日月为功。这也是反对礼治的,即反对制度政治。这与儒家的基本思想也相去甚远。
董仲舒《贤良对三》又云:
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敎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敎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圏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二、董仲舒《灾异对》的外儒内法本质
董仲舒贤良对虽也说“故《春秋》变古则讥之”,但董仲舒更强调“义”和“权变”,由近及远,抓大放小。这样一来,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被冷落了,董仲舒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下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一《王道》云: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夫人以适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党。亲迎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何休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提出三科九旨之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侯,内诸侯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由近及远,抓大放小。这一套理论的指导思想就是“义”和“权变”。这样一来,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被冷落了,董仲舒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下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宋洪迈撰《容斋续笔》卷七“董仲舒《灾异对》”条云:
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本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
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剌,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
洪迈认为董仲舒《灾异对》“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使汉武帝最后下决心派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汉武帝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洪迈认为董仲舒首劝汉武帝杀骨肉大臣,与其平生学术大为乖剌。洪迈没有看出董仲舒平生学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系统性,这是洪迈的局限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宗庙考二天子宗庙云:
西山真氏曰:仲舒对策言天人相与之际,以为天心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又谓人君所为美恶之极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皆药石之至言也。至火灾之对,则传会甚矣!况又导人主以诛杀,与前所谓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邪也。夫亲戚之骄僭,近臣之专横,夫岂无道以裁制之?岂必诛杀而后快哉?史称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其后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谋反,迹见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死者数万人。夫谋反,不过数人,而坐死者若是其众,岂非仲舒前言有以发帝之忍心与?
真德秀认为董仲舒贤良对策言天人相与之际,以为天心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又谓人君所为美恶之极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皆药石之至言。至《火灾之对》,岂必诛杀而后快?真德秀与洪迈一样,没有看出董仲舒平生学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系统性,这也是真德秀的局限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三刑考二刑制云:
按汉儒如贾谊、董仲舒最为醇正,然至其论诸侯王,则皆主于诛杀。仲舒此对(指董仲舒《灾异对》)与天人三策议论迥别,真西山亦谓太史公言贾谊明申韩,今读《政事书》,蔼然有洙泗,典刑未见,其为申韩之学,至诸侯王皆众髋髀等语,然后知太史公之说不缪。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圣贤处事固不同也。盖诸侯王虽汉初之深患,然根连株逮而诛锄之于后,固不若建法立制而防闲之于初也。孝文时淮南济北亦尚构逆,讨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尚深竟党与,亦不闻复有后患,何必诛及二万余人哉!
马端临读《政事书》的感觉很有代表性,初读《政事书》,蔼然有洙泗之气象,典刑未见,至诸侯王皆众髋髀等语,然后知太史公之说其为申韩之学之不缪。马端临认为董仲舒《灾异对》与天人三策之议论迥别,没有看出董仲舒平生学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系统性,这也是马端临的局限性。
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外儒内法本质
董仲舒主张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俞序》云:
故予先言《春秋》详已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为民除患之意也。
可见,董仲舒主张先发制人,以防患于未然为仁之大者,可见董仲舒主张仁义的虚伪性。防患于未然,即所谓诛心,没有犯罪之人,以防患诛之。董仲舒之前,萧何所定法律虽严酷,但尚有法可依,人没有犯罪,刑罚不加其身。董仲舒主张先发制人,讲究诛心,董仲舒弟子以《春秋》断狱,以诛心为断,以防患为口实,专杀于外,无需请示武帝,可谓无法无天。韩非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法家还有法可依,董仲舒的外儒内法可谓无法无天,比法家还可怕。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已,公子牙卒。”《春秋公羊传》云: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季子之遏恶奈何?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焉致乎鲁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不从吾言而不饮此,则必为天下戮笑,必无后乎鲁国。于是从其言而饮之,饮之无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然则善之与?曰:然。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酖之,行诛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竟然以季子杀母兄为善,主张大义灭亲,根本不顾及血缘亲情。在杀戮亲人的具体手段上,以不见鲜血而自欺欺人地逃避伦理道德之困境,《春秋公羊传》以此为亲亲之道,则《春秋公羊传》所谓之亲亲之道实为大义灭亲之一块遮羞布,完全是表面文章,没有任何伦理道德之实质。董仲舒教武帝大义灭亲的思想与《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完全一致。
董仲舒迷信政权的力量,以政权的强制力量务除天下所患,实行强力急作式的或曰暴风骤雨式的更张更化。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符瑞》云: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百官同望异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董仲舒特别强调人君之权的重要性。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四《王道》云:
故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观之,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这都是强调借助于政权的强制力量以实行激烈的社会变革。
最能代表董仲舒外儒内法思想的著作当是《春秋繁露》卷六《保位权》。
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六《保位权》云:
民无所好,君无以劝(杨德春按:劝原作权,据文意改。)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劝(杨德春按:劝原作权,据文意改。),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驳,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得过也。所好多则作福,所恶过则作威。作威则君亡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亡德,天下相贼。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声有顺逆,必有清浊;形有善恶,必有曲直。故圣人闻其声则别其清浊,见其形则异其曲直。于浊之中,必知其清;于清之中,必知其浊;于曲之中,必见其直;于直之中,必见其曲。于声无小而不取,于形无小而不举。不以著蔽微,不以众揜寡,各应其事以致其报。黑白分明,然后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后可以致治,是为象则。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声出于内,响报于外;形立于上,影应于下。响有清浊,影有曲直,响所报非一声也,影所应非一形也。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其行赏罚也,响清则生清者荣,响浊则生浊者辱,影正则生正者进,影枉则生枉者绌。击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施,罚不虚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圣人由之,故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
这就是董仲舒从《春秋公羊传》总结出来的统治术。对民无须施以教化而要使民有欲,民有欲则君可以以奖赏制之,使民有所畏而以刑罚制之。设官府爵禄是为了施赏罚而不是为了施教化,以赏罚二柄治国,这是韩非治国的基本手段。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这是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因而尊卑之制、贵贱之差完全是物质利益的差别关系,这就使礼制完全物质利益化了。在孔子的思想中,礼制是人的道德价值的体现,礼制的核心是仁,由仁开辟价值之源,所以自天子以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在求仁,设官府的目的在施教化、行仁政。可见董仲舒的统治术是外儒内法,是与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董仲舒《贤良对》之思想被前人称为醇正,董仲舒被前人称为醇儒,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前人皆失之。董仲舒思想的本质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由此入手便可洞察《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的本质区别。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305.
[4]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452.
[6] 十三经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2242-2243.
Dong Zhong-shu’s Thought: Being Ostensibly of Confucianism but Essentially of the Legalist School
YANG De-c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dan University,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The thought in Dong Zhong-shu’sis ostensibly of Confucianism but essentially of the Legalist school. The essence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is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Legalist school with Confucianism as its form and the Legalist school as its content. With the excuse of “righteousness” and “tact”, one can attain his end by hook or by crook and do whatever he likes.
Dong Zhong-shu; Confucianism; the Legalist school; Ostensibly of Confucianism but Essentially of the Legalist School;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5.004
B234.5
A
1673-2065(2013)05-0018-05
2013-05-21
杨德春(1968-),男,河北遵化人,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