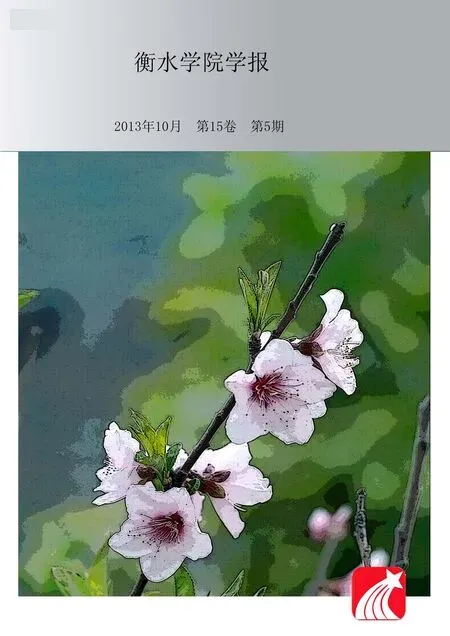说“樑”字
石立善
说“樑”字
石立善
石立善(1973-),男,吉林长春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申江学者”特聘教授,台湾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朱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古代经学史、敦煌学吐鲁番学、日本汉学史。
樑;袁文;《甕牖闲评》;笔记;文字学;俗字;俗文化

博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1c832f0101dn2n.html
今日翻阅南宋袁文(1119-1190年)的读书笔记《甕牖闲评》(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7年10月版),此书卷四有一条是这样说的:
米元章写《遂州圣母庙碑》,“梁”字更加“木”而作“樑”字,“梁”字自有木,何用更加木也!
袁文批评书法家米芾多此一举,在已有木的“梁”字上再加一个“木”旁,他在同书“昔字古作㫺”条也说过:“昔”加月成“腊”、“莫”加日成“暮”、“暴”加“日”成“曝”等都是殊失前人之意。依他看来,米芾似乎也不能免所谓“尺二先生”之讥(语出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九《文说》)。其实早在唐代,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仙韵·燃”字条就已说过类似的话:“上‘然’从火,已是烧,更加火,非。同‘梁’加木,非。”
这个“樑”字的确很有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历代字书是如何讲的。《说文解字》有“梁”无“樑”,该书《木部》“梁”字条说:“,水桥也。从木从水,刄声。”“梁”为本字,“樑”其实就是“梁”的俗字。金代的字书《四篇声海·木部》云:“樑,音梁,栋梁也。”明人梅膺祚编写的《字汇·木部》云:“樑,龙张切,音梁。见释藏。”张自烈《正字通·木部》:“樑,俗‘梁’字。旧注樑‘见释藏’。”《正字通》引的“旧注”就是《字汇》。释藏即佛教大藏经中的“梁”字多写作“樑”,而收录佛经字音的《大藏音·木部》也收录了“樑”字,音梁。诸书中的“音梁”,是传统的注音方式之一,即用正字给俗字注音。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木部》“樑”字条云:“《淮南子·主术训》:‘大者以为舟航柱樑。’不独见释藏也。”《康熙字典》认为“樑”字不仅仅出现在大藏经中,外典《淮南子》也用了这个字。事实果真如此吗?《康熙字典》举出的书证,很容易让人误会《淮南子》的成书时代即西汉就有了“樑”字,斋主觉得有必要加以说明。刘安《淮南子》的传世刊本源自于宋代的刻本,宋明清历代刻本或多或少保留了前代的一些书写习惯(有的宋本也保留了之前的写本时代的文字样貌),同时更多地反映了各自刊刻时代的文字形态,一部书的流传是屡经传抄刊刻的,用字的情况复杂,我们岂能依据《淮南子》刻本的文字形态来判断汉代是否有“樑”字!斋主浅见: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并未用过“樑”字,两汉碑刻简册不见此字,“樑”这一俗字应当诞生于六朝,这一时代的石刻碑版多见此字(参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67页),隋唐五代亦沿袭用之。今检明正统《道藏》本及影钞北宋本等《淮南子·主术》篇皆写作“梁”,管见所及,唯有明代万历茅坤(字一桂)批评本作“樑”,可知《康熙字典》所用的很可能就是茅坤批评本。茅坤批评本的影响不小,日本江户宽政十年(1798年)刊刻的宇野成之标注《改正淮南鸿烈解》的底本用的就是茅坤本。
关于“梁”字加“木”的缘由,台湾学者张文彬说:“‘梁’已从木,‘樑’字就‘梁’再加木,其义仍同。此如‘然’已从火,后世又加火成‘燃’,‘莫’已从日,后再加日成‘暮’等,皆同也。”(《异体字字典》“樑”字条研订说明)这一解释并未讲到问题的关键,其实说破了也很简单,“梁”字常与“栋”“柱”“桥”“榜”等木旁的文字合为一词,加“木”旁实出自汉字孳生的规律之一——类化,即同类相化。如敦煌出土的中古写本中,“栋梁”“柱梁”“桥梁”等词语的“梁”字很多都写作“樑”。不仅是俗字,一些后起字(今字)也是如此,“燃”“莫”“曝”都是出自这一演变生成规律。“木”与“水”已是梁字的表意偏旁,再加上一个“木”旁,确实是“床上叠床”“屋上架屋”。这样的字并不太多,除了“樑”“燃”“暮”“曝”等常见字外,斋主还可以举出几个例子:“焦”加火写成“燋”,“绵”加丝写成“”,“架”加木写成“【木+架】”,“婴”加女写成“”,“柰”加木写成“【木+柰】”等,不过这些字样并没有推广开来,传到今日。由类化增加偏旁而产生的文字很多,一些字我们现在仍在用,例如“媳”字《说文解字》不载,“媳”是“息”字的后起俗字,“息妇”连用,“息”本指子息,由于类化增旁,俗写加“女”旁写作“媳妇”。汉字的同类相化功能强大,上下文字的形体或者上下文义的影响,都会改变某些汉字的形体。中国人的思维是物以类聚,对于词语也是如此,同时也相信“字以类聚”,一个字因为上下文字或文义的“感染”和“同化”,会变成与上下文字类似的字形,比如“石桥”,民间写作“石【石+乔】”,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袁文好古勤学,《甕牖闲评》于经史制度、天文地理等皆有涉猎,对于文字音韵也很关注,与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等宋代笔记的性质相似,读此书有读清人考据笔记的感觉,无怪乎俞荫甫瞩目并加以点评(《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卷三十《评袁》)。《甕牖闲评》洋溢着强烈的正字观念和正统意识,对于俗字严加批斥,这个看法也代表了主流学者的声音,如清人汪德容也说加了木旁的“樑”字乃俗字,不可用(《六艺之一录》卷264引)。钱大昕曾指斥一些俗字“妄诞可笑”(《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宋时俗字》),记载俗字的专门字书“污我简编,指事、形声之法扫地尽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龙龛手鉴》)从正字或正统的角度判断,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但从文字的使用与实践、承传的立场来看,则未免失之偏颇。
不止米芾,唐宋书家落笔,本不避俗字,我们看唐宋时代的碑刻俗字就多得不得了。无论用“梁”还是用“樑”,貌似无关紧要,它们表达的意思不变,不过“梁”与“樑”一正一俗,恰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类型——雅与俗,亦即主流(正统)文化与俗文化。唐代以前的写本时代包括“樑”字在内的俗字是屡见不鲜的,但宋代以后的刻本尤其是经史类正统典籍都将俗字改作正字,偶尔也可见少数漏网之鱼,比如《旧唐书·李晟传》载录唐德宗手书的吊唁文:“大厦方构,旋失栋樑”,又如《通典·兵典》“轉關橋,一樑,端著橫檢”,这些是改而未尽的俗字。古代碑刻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六朝隋唐五代的写本和明清刊刻的小说等都使用大量的俗字,这些无疑都属于俗文化系统。俗字是俗文化的主脉,虽然违背六书造字原则,但约定俗成,民间喜用乐见,况且正俗文字的地位也处于不断地转换和变化的动态之中。虽然“樑”字最终没有取代“梁”的正字地位,但唐代变文、元杂剧直到明清小说都大量使用此字,而且到了近世给人感觉有由俗转正的倾向,如这一时代的人名就不避讳这个俗字,明代有“王国樑”,清代有“杨朝樑”“张国樑”“陶樑”“王樑”等。人名对于文字的采择是非常敏感的,也具有时代性,说明明清时代“樑”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认,当然这与其文字自身含义具有的“正能量”(栋梁、桥梁等)有密切关系。现在这个“樑”字已十分罕见了,但仍有人在用,斋主认识的一位台湾学界前辈的名字就用了这个字,记得当初看到名片上的“樑”字不禁为之一怔,印象深刻。
米芾书丹的《遂州圣母庙碑》反映了北宋时代俗字的使用情况,可惜这块碑和拓本都没有传下来。“梁”字写作“樑”,看似画蛇添足,实则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真可谓“一字一中国”!由一个文字的偏旁或笔画的增减变化,可以看出民间日常的习惯和风俗,这难道不就是汉字的魅力所在吗?
(本文经作者稍作修订)
(责任编校:耿春红)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5.007
1673-2065(2013)05-00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