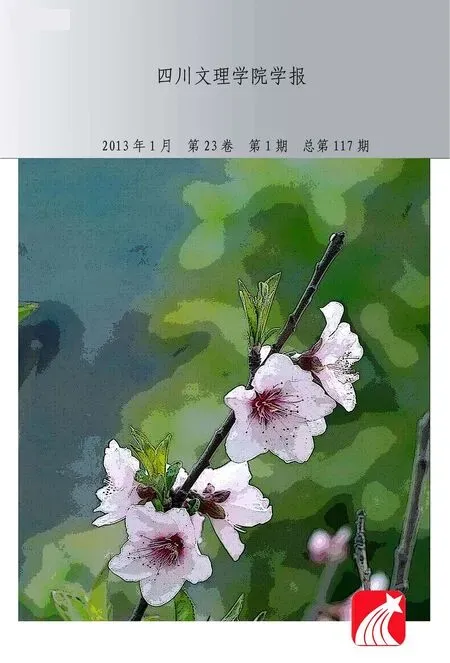渐变的胎记,矛盾的心态
——论《缅甸岁月》中奥威尔的殖民情结
高明玉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渐变的胎记,矛盾的心态
——论《缅甸岁月》中奥威尔的殖民情结
高明玉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缅甸岁月》中,主人公弗洛里脸上的胎记是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象征,胎记使得弗洛里在心理上处于“既非纯白人,又非缅甸人”的尴尬境地,胎记由暗变淡的过程则体现了奥威尔对殖民主义的暧昧态度。
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殖民主义;矛盾性
大多数的评论者认为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是一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小说。诚然,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愤懑,但是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小说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主人公弗洛里脸上的胎记,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象征。评论家哈蒙德认为:“对奥威尔来说,胎记明显是个强有力的象征,他感觉一些人被烙上了耻辱的印记——无论是贫穷、胆怯、负疚、还是失败——它会缠绕着你一生,无法摆脱。”[1]93弗洛里脸上的胎记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其中关键性的描写有三处。
弗洛里出场时,奥威尔强调他左脸上那块呈月牙形的丑陋的胎记,从眼睛一直拉到嘴角,“从左侧看上去,他的脸上一副受尽折磨、愁容不堪的样子,仿佛胎记是一块伤痕似的——这是由于它是暗青色的”。[2]13对于自己面容上的缺陷,弗洛里总是不时侧转身子,不想被别人看见。第二次描写是在弗洛里冒着生命危险找来宪兵队驱散了叛乱的人群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教堂仪式上,弗洛里显然以英雄自居,做着与伊丽莎白结婚的美梦,平生第一次大胆地把自己的胎记冲着伊丽莎白。这时,他的缅甸情妇马拉美闯了进来,扯碎自己的衣服,以自辱的方式无情地羞辱了他。弗洛里“眼神直直地盯着圣坛,表情僵硬、面无血色,以致那块胎记就像一条蓝漆似的,非常扎眼”,伊丽莎白也开始因为他的胎记而痛恨他了。[2]290最后一次是弗洛里恳请伊丽莎白的原谅无望后,他心灰意冷,绝望地饮弹自决,“人一死,胎记也随之慢慢褪色,成了一块淡淡的黑斑”。[2]299胎记使得弗洛里在心理上处于“既非纯白人,又非缅甸人”的尴尬境地。胎记由暗变淡的过程体现了奥威尔对殖民主义的暧昧态度。
一、奥威尔的反殖民主义意识
奥威尔与缅甸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他的祖父、外祖父以及父亲都曾在印度工作或经商。特殊的家庭背景铺就了奥威尔的人生道路。中学毕业后,奥威尔在缅甸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警察职业生活。然而殖民地生活的严酷现实超出了他的忍受能力,1928年,他顶着来自家庭的压力,递交了辞呈回到了欧洲。英属印度地区以其异域的景致、情调和习俗为奥威尔提供了理想的创作背景。他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写了《绞刑》、《射象》和《缅甸岁月》。评论家认为:“《缅甸岁月》是奥威尔最为传统的小说,也是最成功的小说。”[1]89
最初,奥威尔打算紧随《巴黎和伦敦的落魄生活》的成功之后推出该书,然而遭到了出版商维克多·葛兰兹的拒绝,理由是印度殖民政府的官员担心该书中反帝国主义情节会对印度和缅甸产生负面的影响。1934年10月纽约的哈泼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才使得葛兰兹改变了主意并于第二年出版了该书。桑顿在写于6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奥威尔是公学人的典型代表,身上体现了公学精神,却对帝国观念和帝国使命深感怀疑。詹姆斯·莫里斯在他撰写的大英帝国的兴衰三部曲中把奥威尔看作是一个帝国公仆的代表,但对他所供职的体系已不再信任。此外,奥威尔是一个“弱化了的或是不坚定的”帝国主义者。[3]侯维瑞在其主编的《英国文学通史》中也写道:“早在写作生涯开始时,奥威尔就在他的小说《在缅甸的日子里》等作品中表现出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谴责。”[4]
奥威尔本人在谈到他放弃警察职业的原因时也说过:“我放弃它部分是因为那儿的气候毁坏了我的健康,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要创作的模糊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无法继续为帝国主义服务,我认为它是一种欺骗。”[1]15奥威尔十分憎恨他所为之服务的帝国主义,因为它给他带来的是无可名状的痛苦。奥威尔感觉自己是大英帝国主义机器上的一部分,参与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压制,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必须为之赎罪的负疚感。谈到创作《缅甸岁月》的动机时,他说:“缅甸的景观,当我身处其中,是那么的恐怖,仿佛就是一场恶梦,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不得不写一本小说去祛除它”。[1]14后来,奥威尔在评论《缅甸岁月》时说:“这是一本卑微的作品,但它异乎寻常明确地展现了我们这个帝国的官员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每一个驻印的英国官员当他在处理欧洲和土著利益冲突的案件时都处于虚伪的境地。理论上,他代表着司法公正;实际上,他却是保护英国利益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经常要在放弃自己的诚实和毁掉自己的事业中做出选择”。[3]当然,他选择的是后者。多年以后,奥威尔又写道这本小说包含了他反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5]
评论家认为:“弗洛里当然就是奥威尔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弗洛里显然就是他想象如果选择继续留在缅甸的自己”。[6]由此,弗洛里脸上的胎记对奥威尔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暗青色的胎记象征着弗洛里的自卑,使得弗洛里在心理上感受到“非纯白人”的尴尬。他总感觉低人一等,“每当他做了什么感到可耻的事情后,就会想起自己的胎记”。[2]54就连在伊丽莎白对他一往情深的时候,他也谨慎地“忽然将脸侧向一旁,尽管胎记本就远离她,他可不要让她太靠近自己的脸”。[2]84其次,胎记也象征着他的孤独。欧洲人出于对土著居民的鄙视,不肯与之交往,整天在俱乐部中打牌饮酒,闲扯漫谈,无知自大,迂腐之极,这一切都令弗洛里感到厌恶。虽然他本人也酗酒狎妓,但也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他选择住在操场最高处,紧贴丛林边缘。他有个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医生,但是后者却无法与之沟通,他同医生的交谈就像是自言自语,因为“医生是个大好人,对他所讲的话却知之甚少”。[2]70所以,当他遇到来缅甸物色丈夫的伊丽莎白时,内心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当伊丽莎白最后拒绝他时,他甚至乞求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娶你,并答应从不碰你一个指头。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即使这样我都不在乎。但是我无法继续一个人生活,老是一个人”。[2]294其实,他只是在精神上,或者说是在情感上爱慕伊丽莎白,渴望得到的是她的同情而不是爱抚。他要的只是白人的认同,驱散心头的孤独。遗憾的是,“他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到一个根本不能理解自己、同自己有着完全不同追求的女人身上,指望对方能帮助自己驱走可怖的孤独感,而幻灭之时,孤寂犹在,除了死,也实在别无出路”。[2]4
正是因为弗洛里的孤独才使他能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帝国主义的事业。他感受到整个大英帝国的堕落和道义上的耻辱。弗洛里对英帝国在缅甸的统治十分不满。他发现并不像殖民主义者鼓吹的那样,殖民者带给缅甸的不是文明、进步和秩序。他们都是一些骗子、窃贼和酒精的过滤器,满嘴谎言,他们来到缅甸只是为了掠夺资源和压制当地土著人。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只是喝酒取乐,“酒精是整个帝国的粘合剂”。[2]37弗洛里对他所接受的“崇高使命”产生了怀疑:“我所反对的,只是令人作呕的欺骗,说什么白人的负担,这纯属白人老爷故作姿态,真让人厌烦。”[2]37与其他殖民者格格不入的弗洛里内心总有一种远离白人的企盼。
二、奥威尔的殖民倾向
虽然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表现出较强的反殖民主义态度,但他不经意间也流露出“白人优越”的殖民主义意识。这首先表现在奥威尔(通过弗洛里)对缅甸人的态度上。尽管弗洛里对帝国充满了怨愤,但是他却并没有融入当地的土著社会,而是处于白人与土著的夹缝中。虽然他和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是朋友,但是后者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他者”来衬托自己的白人身份。维拉斯瓦米医生是典型的“自卑情结”的体现着。法农认为:“自卑情结是通过对本土文化原创性的埋葬而建构出来的。每一个被殖民的民族,换句话说,每一个拥有自卑情结的民族都会发现自己要面对文明国家的语言,也就是宗主国的文化。自身地位的提高与他对宗主国文化的接受成比例。当他对自己的黑色、丛林谴责时,会变得更白”。[7]18听到弗洛里批评他的殖民同伙,维拉斯瓦米极力为英国人辩护,声称“他们彼此之间忠诚磊落!……在他们粗狂的外表下面,是一颗金子做的心”,“你们的商人开发我国的资源,而你们的官员则出自纯粹的公德心,使我们得以教化,将我们提升到同他们一样高的水平”。在他眼中,东方人“冷漠、迷信”,英国殖民者带给他们的是“法律和秩序,”“始终不渝的英国公正,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2]37-40当他听说白人俱乐部要吸收一名土著会员,加入这个俱乐部就成了他最大的目标,他认为“一个印度人一旦成为欧洲人俱乐部会员,他的声望能提高多少。进了俱乐部,你几乎就变成欧洲人了,任何流言蜚语也不能把你怎样。俱乐部会员是神圣不可亵渎的”。[2]45-46医生的“自卑情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衬托了弗洛里的“白人优越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白人身份及权力,所以他才不顾埃利斯的极力反对,想方设法帮助医生加入白人俱乐部。
此外,弗洛里在缅甸还拥有一个情妇——马拉美,是他两年前花了两百卢比从她父母那里买过来的。但他与马拉美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后者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情欲。法农认为:“由于白人男子是主人或更简单地说是男人,他可以奢侈地和很多女人睡觉,这在每个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都是如此。”[7]46在弗洛里心中,马拉美永远只是妓女、玩物,他总是对她说:“我跟你完事之后就不需要你在这儿了”。[2]54-55所以当他遇到了从巴黎来缅甸物色丈夫的克莱斯蒂恩先生的侄女伊丽莎白后,他对马拉美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暗想:“自己以前从未发现马拉美的脸有那么黑,她那又瘦又硬的身子有多么古怪,笔直得就像士兵的腰杆,除了水瓮班的臀部那儿,周身没有一处曲线”。[2]89并且用一百卢比把马拉美赶出了家门。通过弗洛里对马拉美的态度,弗洛里骨子里的白人意识可见一斑。
再者,奥威尔的殖民意识还体现在小说中对缅甸的刻板描写中。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写到:“东方主义是一种基于东方和(大部分时间是)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别之上的思维模式。由此相当多的作家,无论是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还是帝国官员,都把东西方这种基本的差别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来指导自己关于涉及东方及其民族、风俗、思想等的理论、史诗、小说、社会描述及政治刻画的创作。”[8]鲍尔德文总结了后殖民话语中东西方的差别:东方充满异域情调、专制、邪恶、神秘、感性、落后等;西方则体现了理性、民主、自制、实际、强大等。[9]
对奥威尔来说,缅甸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以五大特产而出名,均以P开头,“即佛塔、流浪汉、猪猡、和尚和妓女”。[2]301此外,水牛、黑森林、舞蹈都是那么令人着迷。缅甸人更是物化或动物化的存在。例如缅甸的男人的“脑壳向上倾斜,就像公猫一样”;女孩则体格敦实,“古铜色的皮肤,头顶着水罐而身体笔挺,健硕的臀部向外突出,有如母马一般”。[2]123-124维拉斯瓦米医生是个体格很小、黑白分明的人,他的出场很滑稽,“活像一个盒子里弹出来的木偶”。[2]34而中国移民李晔“罗圈腿,穿着蓝色的衣服,留着一条辫子,黄黄的脸上没有下巴,净是颧骨,就像个和善的骷髅”,他的孩子,一个光屁股的小孩,正在满地乱爬,“活像一只大个头的黄色青蛙”。[2]134此外,缅甸人还充满了迷信,例如,马拉美相信“淫欲就是一种魔法,能够赋予女人控制男人的神奇力量,直到她最终把他变成近乎白痴的奴隶”。[2]54缅甸的车夫很少给车轴上油,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尖尖的声音可以驱邪避鬼”等等。[2]58
与缅甸人的负面形象相对应,欧洲人则是权利的中心和强者的形象。他们所在的地区人口约有四千,包括两百印度人,几十个中国人和七个欧洲人。虽然欧洲人只有七人,但是他们的俱乐部——一座破旧的独层木制建筑——却是全城的真正中心。“在印度的每座城镇,欧洲人俱乐部都是其精神堡垒,是不列颠权利的真实所在,是土著官员和百万富翁们徒然向往的极乐世界”。[2]14弗洛里虽然是个孤独、懦弱的灵魂,但在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在驱赶水牛、林中猎豹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敢,尤其是努力涉过积满淤泥的河,搬来援兵驱散了暴动的人群,他一夜间成了所有白人心目中的“英雄”。新来的宪兵队军官维拉尔更是独领风骚,二十五岁左右的年纪,身体修长而笔直,具有英国军人的兔脸,淡蓝色的眼睛,双唇间看得见几颗三角形的门牙。“在随意间却透着一股刚毅无畏、甚至冷酷——也许的确是只兔子,但却是一只坚韧、勇武的兔子。他坐在马上,就好像自己同马儿是一个整体,而且他看上去年轻矫健得逼人。[2]193就连他的名字奥威尔也赋予了寓意,维拉尔在英文中是生殖力的意思。他的风流倜傥,加上高超的骑马和马球技术,很快俘虏了伊丽莎白的芳心。
三、奥威尔殖民意识的根源
奥威尔的缅甸之行,除了家庭和经济因素外,还受到当时殖民话语的影响。殖民统治者除了以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为主要手段外,经常利用殖民话语来鼓吹西方是给未开化的东方带来文明之光的火炬手,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是白种人的责任。如吉普林所描绘的那样,开化、教导、帮助东方人是“白人的重担”。吉普林1899年2月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了诗歌《白人的重担》,督促美国人像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担负起“白人的重担”。吉普林还是第一个广泛并深刻论述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作家。他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30年代及以后。吉普林由此被誉为英国殖民主义的旗手,大英帝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吉普林是奥威尔非常喜爱的作家。据奥威尔回忆,在他年轻时,吉普林是“真正‘家庭供奉的神’,他在中产阶级中的威望当时尚无其他作家匹及”。奥威尔曾这样描述他对吉普林不断变化的态度:13岁崇拜他,17岁讨厌他,20岁喜欢他,25岁蔑视他,而在30多岁又仰慕他。奥威尔在缅甸的五年(1922年-1927年)正是他最容易接受影响的年龄。在吉普林的影响下,为帝国效命的责任和荣誉以及对东方浪漫情调的幻想使奥威尔对东方充满了热情,正如斯蒂文·茹恩思曼所回忆的那样:“他经常谈及东方,我一直有个印象,他十分渴望重返东方……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
此外,奥威尔幼年时所接受的教育也对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一岁时随母亲回到英国,八岁入读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这是一所殖民意识浓厚的学校,是“英帝国学校的一个摇篮和托儿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会到海外殖民地做官,定居或者当兵”。正如考纳里所描绘的那样,圣塞浦里安要求学生具有高度的坚韧力。它向学生灌输一些殖民理念,诸如“个性、个性、还是个性”,“责任之路就是光荣之路”等。吉普林和亨利·纽博尔特的诗歌是他们主要的教材,要求学生为到印度、缅甸、尼日利亚和苏丹等地任职做好准备。[10]16奥威尔传记作者戴维森认为“奥威尔初到缅甸时,他内心充满了帝国精神和帝国主义意识。”他说:“无论如何,奥威尔在圣塞普里安所接受的帝国主义教化是如此强大,直到他在缅甸亲自经历并实践帝国主义时都无法摆脱。”他还表示:“无论奥威尔在多大程度上拒绝帝国主义(他当然也是这么做的),我都坚信圣塞普里安的影响会终生深入到他的无意识之中。”[10]17-18
《缅甸岁月》的创作背景适逢二十世纪20年代缅甸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时期。虽然奥威尔对缅甸的民族运动的动荡深表同情,然而他对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指涉是一贯的蔑视,对土著人的刻画传承了殖民小说的传统模式,是一种漫画式的讽刺。耐人寻味的是,奥威尔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了弗洛里的死,他脸上的胎记也由此变淡,成了淡灰色。胎记颜色的消退意味着弗洛里向白人的回归。这既是奥威尔替弗洛里的选择,也是他本人的选择。
小说中奥威尔对殖民主义的矛盾性主要是通过他的主人公弗洛里以及自己的口吻表现出来的。一方面奥威尔赋予了弗洛里敏感而沉思的性格,使得他与白人俱乐部的“迟钝的愚人”不同。弗洛里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其孤独、渴望被理解的一种体现。但另一方面,弗洛里的胎记象征着他的身体及心理上的缺陷,每当他开口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胎记,从而使得他的语言苍白无力,充满负疚感,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也就不那么底气十足。最终通过印度医生善意的谎言,谎称弗洛里是不小心擦枪走火导致的“意外身亡”,奥威尔帮助弗洛里在基督徒墓地找到了最后的安身之处,因为基督徒墓地象征着“殖民者的团结”。奥威尔的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所接受的教育是殖民主义的,他的态度和倾向又是反殖民主义的,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是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矛盾性的主要原因。
[1] Hammond J R.AGeorgeOrwellCompanion:AGuidetotheNovels,DocumentariesandEssays[M].New York:Macmillan, 1982.
[2] 乔治·奥维尔.缅甸岁月[M].李 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 Keck, Stephen L.TextandContext:AnotherLookatBurmeseDays[J].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2005(1):27-40.
[4]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643.
[5] Rai, Alok.ColonialFictions:Orwell’s“BurmeseDays”[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83(5):47-52.
[6] 陈 勇.论乔治·奥威尔缅甸殖民生活的政治观[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9):74-80.
[7] Fanon, Frantz.BlackSkin,WhiteMasks[M].New York:Grove Press, 1967.
[8] Said, Edward.Orientalism[M].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2-3.
[9] Baldwin,Elaine.IntroducingCulturalStudies[M].Bei Jing:Bei 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5:171.
[10]Davison, Peter.GeorgeOrwell:ALiteraryLife[M].New York:Macmillan, 1996.
[责任编辑邓杰]
FadingBirthmarkandAmbiguousAttitudes:Orwell′sColonialistComplexinBurmeseDays
GAO Ming-yu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China)
The birthmark in Flory′s face is an important clue throughout Orwell′s Burmese Days, which makes Flory in an embarrassing position of “nonwhite and non-Burmese.” And the change of the birthmark from dark to pale indicates Orwell′s ambiguous attitudes towards colonialism.
Orwell; Burmese Days; colonialism; ambiguity
2012-12-28
高明玉(1974—),男,安徽灵璧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A841
A
1674-5248(2013)01-0082-05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