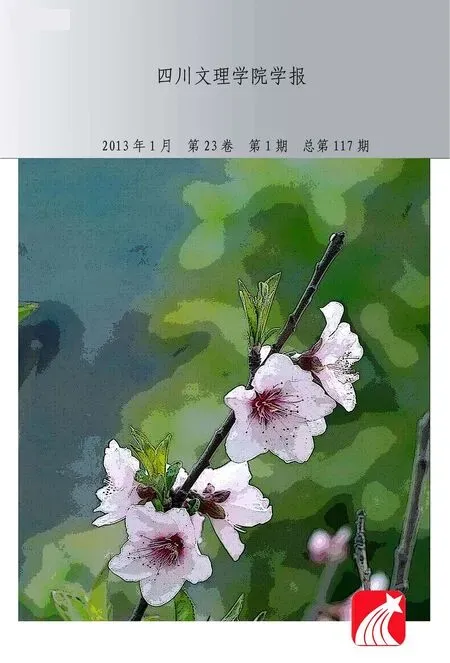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比较研究
宋 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 成都 610031)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比较研究
宋 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 成都 610031)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前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后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两者的斗争实践各有千秋,同时又具有相通之处,对中国革命也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
川陕;陕甘边;根据地;比较;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其斗争形式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各有千秋。深入进行二者的比较研究,对于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深化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两个根据地的基本情况
川陕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至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嘉陵江放弃川陕根据地止,一共持续了三年零两个月。在这三年多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建立绥定、巴中两个道委和赤江、赤北、红江、南江、巴中、长赤、江口、苍溪、广元、嘉陵、恩阳、仪陇、阆南、长胜、营山、宣汉、达县、渠县、万源、红胜、英安、陕南、城口等23个县委和县级苏维埃政权,区苏维埃政权16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9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3900多个。全盛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在全国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84000平方公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辖区共有人口500多万,拥有人民武装共有10万余人,其中正规红军有12个师35个团8万多人。
陕甘边根据地从1932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至1935年2月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止,持续三年时间。西北根据地从1935年2月至1937年2月被中共中央正式改称为中共陕甘宁特区持续了两年,合计在一起就是持续了五年时间。这还不包括寺村塬根据地建立前的武装斗争,而且是持续到土地革命战争结束依然存在,并未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消灭,从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到1935年2月,“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至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7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1]257陕北根据地辖区最大的时侯“设有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神木等九个苏维埃县治,形成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神(木)府(谷)两块苏区。佳吴绥清延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的大部农村,靖边、安塞、米脂县东部和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府谷县的大部农村,佳县和榆林市结合部的农村”。[2]到1935年2月,两个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北迄长城沿线,南抵北山南缘,东临黄河,西接环江的30个县,其中包括陕西省25县,即府谷、神木、米脂、佳县、绥德、吴堡、横山、靖边、定边、保安、安塞、安定、清涧、延川、延长、延安、甘泉、宜川、高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潼关、耀县、旬邑、白水。甘肃省陇东5个县,即宁县、正宁、合水、庆阳、环县”,[3]辖区共有民众近100万,巩固和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武装约有14000余人,其中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9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
二、两个根据地干部地缘特征不同,工作开展方式各有侧重
两个根据地因斗争环境、斗争情况不同,主要干部骨干地缘特征不同,在工作开展方式上也各有侧重。
首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骨干大多是“外来户”,在整个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干部始终存在主客籍之间的分歧和摩擦,这大大局限了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和持续。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前,川陕边曾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如王维舟、杨克明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百折不饶,辗转苦战,是一支很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旷继勋同志曾率邓锡侯部第七混成旅发动蓬溪起义,建立起四川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南部也爆发了升钟、保城起义,在陕南开辟了西乡游击区,创建了红二十九军。但这些本地武装和干部在川陕根据地创建后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并没有很好地整合这些力量,而是不信任乃至猜忌这些干部,在使用上进行打压、排斥,甚至迫害。川东游击军虽然改编成红三十三军,但屡遭歧视、削弱,最终被取消了番号。王维舟后来回忆:“自从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处处受到张国焘的歧视。我军人多枪少,武器、弹药缺少补充,而我们担任战斗的任务很重,防线又长,万一有所失误,要以军法从事,处境相当困难。”[4]本地干部在川陕根据地创建后大都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里,而以张国焘为首的主要领导在军政关系上对苏维埃政权重视不够,始终将政权看成是军队的办差机关,且用“改造政权”为借口多次打击和撤换地方政府中有能力的干部,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本地干部王维舟、杨克明、张逸民、罗海青、余典章等均有过这样的遭遇,旷继勋、张逸民等更是在“肃反”中惨遭杀害。反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都是土生土长的干部领导,具有本土作战的优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主要领导骨干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制上级指导机关的“左”右倾错误,同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因而历经数次重大挫折却能屡仆屡起,最后成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其次,两个根据地斗争方式也各有侧重。川陕根据地在红军入川时有1万多红军主力,最盛时发展到8万多正规部队,其军事斗争工作是十分有成效的。徐向前同志后来总结川陕根据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为扩大武装力量,根据地先后召开木门会议、毛浴镇会议和清江渡会议,大力扩红,并加强军队建设,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川陕根据地持续三年多的斗争中,有两年多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先后进行了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战役、“反六路围攻”、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等。然而,连年战争的破坏使根据地得不到有效的休养生息,因此其斗争也难以持久维持下去,最后不得不放弃。尽管也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但整个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始终是围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展开的一系列战争。诚如徐向前所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北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5]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则更侧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陕甘边根据地拥有的武装力量不是特别多,最多时也不过1万多人,却能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正是得益于其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陕甘边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有着明显的主场优势,“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6]陕甘边主要领导人大多是从事兵运工作出身,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深刻。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7]7习仲勋后来回忆:“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8]早在1929年,刘志丹就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方针,决定采用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白色(派共产党员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三种斗争方式来创建革命武装,后来这三种方式使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毫无疑问,陕甘边根据地能够成为中国土地革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两个根据地的斗争具有的共同特点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lt;共产党人gt;发刊词》等文章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和规律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的川陕根据地,和“硕果仅存”的陕甘边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中华苏维埃建设的典型实践,它们与其他根据地互相支援和配合,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基地,为人民政权道路的开辟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共同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般规律。
首先,两个根据地都是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地理优势建立起来的,符合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特征。川陕根据地这样的地利十分明显:“在地势上有巴山之天险,扼汉水长江之咽喉,向南发展可以截断长江,虎视武汉,向北发展可以据汉中而制西安,向西发展可以打通甘肃、新疆与苏联联络,向东发展可以联系湘鄂西及鄂豫皖赤区”。[9]徐向前同志对红四方面军能在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原因归结为两个:一是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之间和四川军阀本身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发生混战;二是川北地形条件十分有利,山高林密,地形险要,许多关隘都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利于大部队的集结,而有利于小股部队的隐蔽与穿插。“拿各方面条件看,川陕边都是较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讲的那些条件差不多”。[10]陕甘边党和红军也是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地理条件,开辟和巩固了陕甘边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它的东、西、北面都被黄河天险所包围,成为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以此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十分利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同时由于地域偏远,地广人稀,加上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行政和军事控制力相当薄弱。[11]陕甘边将领王世泰后来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断,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3省18个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特别是早年刘志丹、谢子长即在这一带发动革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是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方”。[12]
其次,两个根据地的斗争实践都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光辉典范。
川陕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制定土地革命方针政策时,党组织深入调查研究川陕边实际,详细分析当地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素质和阶级属性,制定符合川陕苏区实际的土地政策。先后颁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1932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1933年2月)、《怎样分配土地?》(1933年2月)、《农村阶级划分》(1934年9月)、《平分土地须知》(1934年12月)、《平分土地办法》(1935年)等一系列法令政策,既坚持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又根据川陕实际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在可以分得土地的主体上,不仅包括工农大众,也包括雇工、兵士、失业者、寡妇、商贩、市镇平民甚至社会边缘群体;在土地分配时,将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及附在土地上的所有财产都列为被分对象,但将不可分的如“大的矿业、林业(如盐井、煤矿、铁矿和大森林……)收为国家共管,作为国家财政基础。因为这些大产业,就是分给农民,也不能开发,而且也不便于分”;[13]在土地分配标准上,则按田地出产量和劳动力多少来分,以当地惯用的“背”为单位(背:通南巴一带以产谷子100斤的田的面积为一背);在政权结构和体系上,川陕也没有直接搬用中央苏区的省、县、区、乡四级制的苏维埃政权模式,而是保留了村一级的苏维埃政权,还创造性地采用十家代表制,从而实行省、县、区、乡、村五级模式,大大夯实了苏区基层政权的施政基础。
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也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路线。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14]这不仅是中共中央对刘志丹同志个人革命实践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是对陕甘边根据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肯定。陕甘边根据地最有成就的是创造了武装斗争的陕甘模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根据地接连受挫的过程中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15]后来决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临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狡兔三窟”的战略,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先后开辟以陕北安定、隆重南梁和关中照进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后又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几个根据地互为犄角,相互照应。“狡兔三窟”的创造性战略布局,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要发展。“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7]7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并称之为围棋中的“做眼”。正是这种到处做“眼”的战术,把中国革命这盘大棋在西北下活了。习仲勋后来回忆:“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1]16
再次,两个根据地都十分注重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事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川陕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川陕根据地在贯彻执行土地分配政策时,党员干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先是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充分发动人民群众都来参与土改,然后带领他们打土豪、分浮财,并根据土地政策和川陕省党代会、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决议精神,将苏区民众按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经济地位和剥削关系分成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六个基层,作为土地分配的依据。在分田地时,由分田委员会的党员干部和当地群众一起去踩田地山场,和所有分田者一起来分配土地。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对土地的诉求,苏维埃政府尽可能将土地分给群众,只留了不到3%的土地作为红军公田,而且还制发土地使用证给农民,从法律上规定分地农民对土地具有归属权。同时,党和政府还鼓励积极生产,引导他们种植经济作物,并直接出面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等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根据地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良作风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敌人围剿时死心塌地地支持红军作战,拼死捍卫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自幼生活在贫苦人民之中,对当时边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在革命实践中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党和红军的行动准则,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他们采用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法,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牛羊、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一待时机成熟,就召开工农兵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保证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从而大大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还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普及文化教育,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陕甘边民间流传的“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陕北出了个刘志丹”等歌谣从侧面反映出陕甘边根据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融洽。正是因为两个根据地的党组织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来制定方针政策,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才赢得了根据地人民至死不渝的支持和拥护。
四、两者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南和西北的重要实践,两者在中国革命事业中都占有其独特的地位,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3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16]川陕革命根据地不仅在川陕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成为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进行了苏维埃建设的典型实践,创造出全国第二大苏区,其斗争和其他苏区的斗争遥相呼应;它的创建和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削弱了四川军阀的军事实力,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民众运动的发展,同时使根据地人民经受了革命洗礼,在川陕边播撒下革命的火种;尤为重要的是它还积极配合和接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及军事行动,支援和配合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在全国红军完成长征战略转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对陕甘边根据地,七大前后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没有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和长征的红军,就下不了地,……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7]562湖南话里“下不了地”是无法想象、不可设想、后果相当严重的意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的情况下,红旗巍然不倒,为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后来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其他根据地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这两个根据地都为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领导骨干。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栋梁之才。除张国焘后来妄图分裂党中央、最终叛党出逃外,众多在川陕根据地奋战过的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披肝沥胆,立下赫赫战功,不少同志建国后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如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傅钟、王维舟、许世友、程世才、魏传统、刘瑞龙、郑义斋、张琴秋等。而在陕甘边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过、后来成长为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领导人的也为数众多。除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外,较为人民所熟悉的有高岗、马文瑞、贾拓夫、王世泰、习仲勋、汪峰、刘景范、马锡五、张秀山、阎红彦、郭洪涛、郭述申、朱理治等人。“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时,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至少有50人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过”。[17]
由此可见,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一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两者的斗争实践各有特色,其共同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各自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高原革命征程——回忆陕甘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2] 陈永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阵地[N].庆阳论坛,2010-10-19(02).
[3] 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276.
[4] 邓金德.四川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4):53-55.
[5]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279.
[6] 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939.
[7]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刘志丹纪念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8] 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16.
[9]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0-51.
[10]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J].星火燎原,1984(1):48-50.
[11]张智全.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必然性[J].中共党史研究,2011(10):26.
[1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334.
[1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20.
[14]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N].解放日报,1943-04-23(01).
[1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60.
[16]唐 琼.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2(3):52-56.
[17]李 蓉.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J].中共党史研究,2009(11):18.
[责任编辑邓杰]
ComparativeStudyontheChuan-ShanandShan-GanRevolutionaryBase
SONG Jian
(Party History Research Division of Sichuan Province Party Committee, Chengdu Sichuan 610031, China)
The two revolutionary bases, Chuan-Shan and Shan-Gan were typical practic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rmed independent regime” and the Soviet Campaig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former was the second big base of China Soviet Republic and the latter was the only base in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War whose fruit was preserved today. Their revolutions were different yet common 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revolution respectively.
Chuan-Shan; Shan-Gan; revolutionary base; comparison
2012-08-24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青年项目(SLQ2012C-02)
宋 键(1977—),男,湖南双峰人。主任科员,主要从事川苏陕苏区研究。
K269 .4
A
1674-5248(2013)01-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