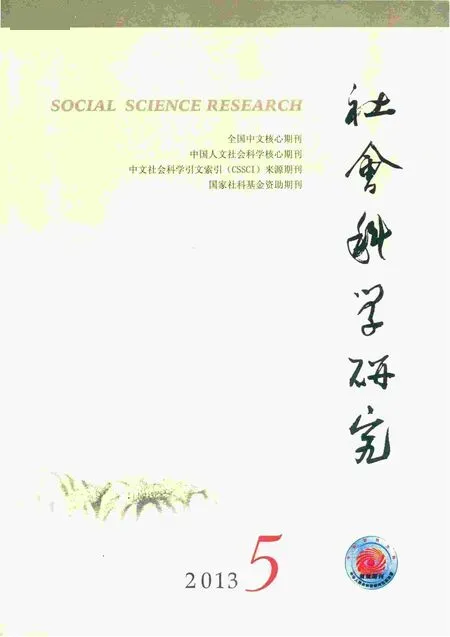历代注疏对 《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以 “三危”为例
汤 洪 黄关蓉
中国古代典籍从上古传说时期的“三坟五典”算起,到殷周时期正式出现文字记载的各类文化图册,再到春秋战国被后世学者经典化的诸子百家,经籍的流传浸染了两三千年的漫长历程,其所载内容也为后世不断传诵、阐说、注解、疏证,由此而形成一种积学深远的注疏传统。求真求实,彰显本源是任何一部经典注疏的基本诉求,然而,阐释学的基本规律又告诉我们,任何注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意义不断流变的过程,原有经籍的最初语义总会经由不间断的注解、阐释而发生讹变、翻新以及内容更替等,以至于有时年代越后,我们会发现经传解说的结果距离当初的内容事实竟然越发地遥远。最为常见的就是古人与近人之间就同一个地理名词的认识,由于政治时代与历史条件的不同,就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这在辞采瑰奇的《楚辞》的训释中特别明显。《楚辞》中出现的多个地理名词,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历代注家对于这些名词的注解认识,一直处在不断流变、指代游移不确甚至于前后矛盾龃龉之中,俨然形成了一个空间地理舆图的时代演变观念史。本文试以《楚辞·天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1〕一语中的“三危”为例,讨论其在先秦以来各种典籍以及各家注释中的确切演变流程,以管中窥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历程,揭示其背后的种种历史文化原因。
一、先秦汉初文献典籍关于“三危”的记载
“三危”作为地理名词并非仅仅出现于《楚辞》中,作为先秦时期广泛出现在人们文化视野中的词语,如同我们今日社会视野下的“东方”、 “西方”、 “特区”、 “沿海”、“西部”等熟词一样,原本有着为社会所认可、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和对象指代的特殊名词。
(一)“三危”作为特定地理名词所指为何,我们可以依据西汉前期的文献资料《淮南子》中的多条记载来加以界定:
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淮南子·俶真》)〔2〕
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在乐民西。(《淮南子·墬形》)〔3〕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淮南子·时则》)〔4〕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淮南子·主术》)〔5〕
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兠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淮南子·修务》)〔6〕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杂糅百家之说,其言语说辞虽然有涉神怪荒诞,但是通过其记载有关“三危”的内容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做出一些简单明了的判定:“三危”正是《淮南子·时则》所言的西极之山,这座山在昆仑之西,从昆仑经流沙、沉羽 (按:即《淮南子·墬形》所谓弱水),一直向西,方达“三危”。这座山又是传说中神农氏治理天下的最西之处,同时也是尧帝西窜三苗的地方。《淮南子》的记载并无歧义,就连高诱在注解此书上引所有材料时,从头至尾始终坚持认为“三危,西极之山名也。”〔7〕
不独《淮南子》,《山海经》、《尚书》、《史记》、《吕氏春秋》等典籍的记载也可印证此说。
(二)《山海经·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8〕这正与《淮南子·时则》所述一致,《山海经》“三危”也位于昆仑之西,那么这一认定显然与我们今天的地理学常识就有明显的不同了。
(三)《尚书·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9〕伪孔传曰:“三危,西裔。” 《尚书·禹贡》又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10〕伪孔传曰: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11〕伪孔传为《尚书》两处三危所作的注解,都只是说此山当为西方极远之山,并没有将它指实为具体的某座山峰。
(四)《史记·五帝本纪》也有“迁三苗于三危”句,裴骃集解引东汉马融的话说:“三危,西裔也。”〔12〕看来,马融和伪孔传都是这么认为的,三危只不过是一个西方之山的通称。
(五)《吕氏春秋·本味》记载:“水之美者,三危之露。”〔13〕高诱注谓:“三危,西极山名。”〔14〕可见直到高诱生活的东汉中期,三危尚为西方极远之山的通称,并不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被具体化为中国西境某座实在的山峰。
二、《楚辞》各家注疏对“三危”语义的多种阐释
然而,我们仅仅通过历代注家对于《楚辞·天问》中“三危”语义解说的变化即可察觉,“三危”作为先秦典籍中一个较为常见且固定的历史地名在后人的观念世界里发生了怎样的游移变化。在这里,我们大致发现了后世对于屈辞注解的一个整体性趋势:一个语词在先秦典籍中本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不确定的指称,经过历代注家学者孜孜不倦的考证与补经工作,这个语词就会被注疏成一个十分确定的、实实在在的、可稽可查的、且具本土化特色的事物了。而经典也就是在这样不断累积叠加过程中,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远离了它原初的面目,以人们所需要的内容呈现在世人面前。总体上看来,后世楚辞注家大多援引《地记书》所言甘肃渭源境内鸟鼠山之西之“三危”以及《括地志》所言敦煌东南三十里之“三危”以解说屈辞“三危”,此外,也有定“三危”为不姜之南、乐民之西、昆仑之西、酒泉之西、敦煌东南、鸟鼠西南、卑羽山、西藏、黑水之南、云南、南海、黑水下游的,不一而足,现略陈之,以备参考。
(一)西方之山。东汉王逸曰: “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15〕王逸解三危为西方之山,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漏洞,但他并没有指明这三危到底为西方哪座大山。或许正由此模糊注解所造成的空白,遂让后世楚辞注家不断寻觅这座位于西方的三危山的具体位置,从而形成异说而彼此争论不休。
(二)黑水之南。唐柳宗元《天对》曰:“黑水淫淫,穷于不姜。玄趾则北,三危则南。”〔16〕柳宗元据《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认为黑水最后流入不姜之山。常识告诉我们,河流一般皆导源于山,流入湖泊或江海,世上可能很少有河流最后注入大山之中的。况且,柳宗元所引《大荒南经》与《山海经》其他有关黑水的记载相牴牾,比如又有材料说黑水南流入海等,故《山海经》中关于黑水的记载我们并不能全然尽信。柳氏又说玄趾在黑水 (也可能是不姜山)之北,三危在黑水 (也可能是不姜山)之南,这个推断不知源出何典。由于不姜之山历来无解,所以,我们也就无法确定三危何在。总之,柳宗元所言三危似乎在黑水或者不姜山的南面。
当代学者金开诚《屈原集校注》曰:“三危,神话中山名,传说在西方黑水之南。”〔17〕金开诚的解释源于柳宗元《天对》。金开诚认为三危为神话地名,因而《禹贡》所记三危也当全为神话,那么,后世的一切考证似乎都是白费气力,这是一个需要以专论来探讨的另一重要话题,此处只好暂时按住不表。
(三)鸟鼠之西。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曰:“《书》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张揖云:三危山在鸟鼠之西,黑水出其南。”〔18〕洪兴祖依据《尚书·禹贡》,并援引张揖的注解,认定三危在鸟鼠之西。鸟鼠在甘肃渭源境内。楚辞学界,洪兴祖第一个将三危具体指实为实实在在的地名,并精确指出了三危的地理所在。
洪兴祖的注解看似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实则疑窦丛生,有偷梁换柱之嫌。《禹贡》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19〕按照《禹贡》的记述,黑水导源之后,途经三危,最后流入南海。也即是说,三危只是黑水的中程,并不是起点,但三国时人张揖的说法似乎认为黑水导源于三危,故洪兴祖所引两则材料本身就存有矛盾。清人毛奇龄《天问补注》就曾注意到这一关键问题:“三危,山名,黑水所经地。”〔20〕毛奇龄说得十分清楚,三危只是黑水途经之地,并不是黑水导源之山。总之,洪兴祖引《尚书》以证《天问》,有着诸多不合理因素。
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承洪兴祖说,认为“黑水、三危,皆见《禹贡》。”〔21〕明人李陈玉《楚词笺注》亦承洪说:“黑水、三危,《禹贡》治水之地。”〔22〕
(四)乐民之西。明人黄文焕《楚辞听直》曰:“《淮南》谓三危在乐民西。”〔23〕《淮南子·墬形》谓:“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在乐民西。”〔24〕乐民位于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又在乐民之西,历来注家对“乐民”本也不甚了了,再加上弱水本也如黑水一般,在中国以弱水为名者当不下十处,历来说法更是不一,所以,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推测出三危的具体地理方位。故黄文焕的解说也未能给我们一个所以然,乐民比三危或许更加让人迷眩,以乐民解三危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清初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承黄文焕说,认为:“《淮南》云,三危在乐民西,又自昆仑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山。”〔25〕周拱辰虽承袭黄说,但黄文焕仅引《淮南子·墬形》,而周氏又引《淮南子·时则》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26〕作为补充,在楚辞学界,三危第一次有了比较具体的方位,那就是位于乐民之西,也位于昆仑之西,然乐民与昆仑的方位关系如何,我们仍不得而知。但若以此为坐标,去检测关于三危的诸多说法,如鸟鼠山之西 (昆仑之东)等说法皆无法立足。
(五)肃州塞外。清初王夫之《楚辞通释》曰:“三危在今肃州塞外。”〔27〕肃州大致为今甘肃酒泉。依王夫之的解说,三危当在酒泉以西之塞外,但酒泉以西如此渺远,三危到底是哪座山峰,我们依然迷雾一团。
(六)敦煌东南四十里。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楚辞集注二》曰:“《括地志》曰: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此《禹贡》黑水之三危也。郑康成曰: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汶山相接。《水经注》:渭水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故有苗谷,此则放三苗之三危也。而近世儒者混而一之。或三苗始迁苗谷,后又徙于沙州耳。”〔28〕徐文靖这段文字注《天问》“三危”,《天问》“三危”与黑水相关,故笔者认为徐文靖主张《天问》“三危”是沙州敦煌东南四十里之三危。徐文靖认为有两个不同的三危,一为导源于敦煌县东南四十里的也即《禹贡》所记的黑水所途经的三危,一为《淮南子·修务》里所记载的窜三苗之三危,此三危则在甘肃渭源县西南之鸟鼠西南。徐文靖为我们提供别开生面的视角,他或许已经洞察到经籍中有关三危一语的混乱现象,所以他提出不同典籍的记载可能指代不同三危的新说。这确实能为我们提供更大阐释空间,让后世注家不必再为经籍中前后矛盾的记载而搜肠刮肚、强为其说。但是,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却要用同一个三危来命名,徐文靖没有答案,因而谜团终未能得以彻底破解。
清人丁晏《天问笺》与徐文靖的说法大致相同,一为敦煌三危,一为鸟鼠三危:“《西山经》: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郭注:今在燉煌郡。《尚书正义》引郑玄注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叔师谓在西方是也。”〔29〕丁晏的注解正好照应前论,王逸 (叔师)说三危在西方,后世楚辞注家们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断找寻这位于西方的山峰,先有探寻到甘肃鸟鼠之西的,后又有探寻到沙州敦煌东南的。从古人注书的这一范式来看,我们不难体察到中国士人传不破经、努力为经传缝合的良苦用心。
(七)卑羽山。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通鉴前编》:沙州燉煌县卑羽山,三峰峭绝,人以为三危。”〔30〕蒋骥把沙州敦煌东南的三危再一步具体化,明确坐实卑羽山为三危,且把三危解为三峰峭绝之义。在楚辞学界,蒋骥或许是第一个将三危具体化为一座实实在在的山峰,并且对三危作出三个危峻山峰的文字训诂。
(八)荆、梁、雍之边。晚清王闿运《楚词释》谓:“三危今西藏,其地连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当荆、梁、雍之边。”〔31〕王闿运所定范围极大,三危在西藏,又连接着桂、云、贵、川、甘之地。是横断山脉吗?但横断山脉似乎与广西和甘肃又扯不上多大关系。是岷山吗?但岷山和云南、贵州、广西关系也不紧密。是秦岭吗?但秦岭与云南、贵州、广西似乎也缺少直接联系。是大巴山、大娄山、云贵高原或者其他什么山?但这些山统统都不能满足王闿运的这几个条件,无论如何也找寻不到,所以附和者寥寥。
(九)藏卫滇越之间。近人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问》谓:“黑水、玄趾、三危皆西南地名……此之地皆在藏卫滇越之间。”〔32〕姜亮夫解楚辞,多以庄蹻入滇为说,但姜氏不顾《山海经》、 《淮南子》等典籍的记载,让读者觉得“三危”等诸地名皆为楚人独创,这似乎带有偏见。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姜亮夫的解说,或可自圆其说:《山海经》等典籍为楚人作品,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记三危,说三危在西北方向,楚的西北方向正是现在四川、云南一带,也即是现今中国的西南,故定三危在中国西南,似乎也有些道理。不但如此,《尚书》也说导黑水入三危,注南海,注入南海的河流在中国西南方向是很多的,而注入南海的河流在西北方向似乎很难找到。看来,姜亮夫说三危在西南也并非空穴来风。
(十)南海附近。近人林庚《天问论笺》谓:“黑水、玄趾、三危均近南海。”〔33〕林庚此说可能源于姜亮夫,将三危从西南藏卫滇越间再南移至南海附近。问题是,这个南海为何,如果是现今南中国海附近的一个什么山,既不在中原的西方,也不在楚国的西方,那么,林庚的结论还不如姜亮夫有理。
(十一)黑水下游。今人程嘉哲《天问新注》曰:“三危,地名。古三危也是一个无从考实的地方……它位于黑水下游,也坐落在西方或西北方。”〔34〕如同黑水,三危杳不可求,倒是直截了当。既然无从考实,程氏又说三危在黑水下游,为什么非要是黑水的下游,而不是上游或中游,程氏所据何典,我们不得而知。程嘉哲无从考实之说正可作为这个问题的结语,三危到底在哪个方向?又是哪一座山?这个问题,历来楚辞注家似未能言说出究竟。笔者罗列诸多异说,旨在表明三危是怎样的恍惚迷离。
三、“三危”在阐释中的讹变历程
由此可知,“三危”一语,先秦乃至汉初本为模糊语义之大地极西之山,后世不断演化为“有三个山峰之山”。三危承载着自身语义的流变乃至讹变,对三危释义的具体讹变历程,我们可从历史的进程中再进一步展开考索。
《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唐孔颖达正义引汉人郑玄语曰:“《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35〕《史记·夏本纪》“三危既度,三苗大序”〔36〕,唐司马贞索隐引郑玄语曰:“《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37〕唐人孔颖达和司马贞所引汉人郑玄关于“三危”的解释大体无异,此似为将“三危”具体化为中国政治版图境内实际地理称谓的第一案例。从郑玄经学化的注解中,“三危”已然具备大致地理方位。如果认定鸟鼠山在甘肃渭源县境,那么,《地记书》所言“三危”即当在此附近,这是汉人的观点,由此可知,汉代经学家正是依照汉代政治版图来索求“三危”的。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大人赋》有“直径驰乎三危”句,唐颜师古注引张揖语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书》曰:‘导黑水至于三危也。’”〔38〕三国时人张揖对“三危”的注解与东汉郑玄相差无几,同引《尚书》来证明三危,其与郑玄的偏误同出一辙,《尚书》借用了一个域外地名来记录一段治水传说,两人皆将此域外地名经学化、历史化、本土化,误解由此而生。
《左传·昭公九年》 “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39〕,西晋杜预注曰:“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40〕在杜预看来,三苗与允姓都被流放于三危,允姓流放后居于瓜州,瓜州又为敦煌,故三危即位处敦煌。这似为三危从鸟鼠西移至敦煌的第一案例。
托名桑钦所著之《水经》比附更为具体。《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三危山在燉煌县南”〔41〕,此时,“三危”已从甘肃渭源县境之鸟鼠山之西推演到了敦煌县南境,与今日我们所认识的“三危”地望已经相差无几。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往往有着相似的认识,《水经》作者与杜预对三危即有着相同看法。虽然《水经》作者与杜预生活时代孰先孰后尚难判定,但至少可以推测他们所在时代应相去不远,杜预大致生活于3世纪中叶,这为我们探索《水经》成书年代提供了意外的旁证。
承续杜预和《水经》之说的,尚有郭璞。《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东晋郭璞注三危谓:“今在敦煌郡,《尚书》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也。’”〔42〕顺带提及,郭璞这段重要的注解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中漏录。郭璞将“三危”划定在敦煌,并同张揖一样,引《尚书》为证。郭璞有两个明显失误:一为把本指极西之山的“三危”本土化,以注者当时所在的中国版图范围来诠解先秦意义上的三危概念;一为误解《尚书》,把《尚书》所言“三危”固定化为中土西境之敦煌。笔者认为,《尚书》此条记载,或有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将三苗流放到了极西之“三危”,要么就是《尚书》作者借用大家熟知的极西之地的“三危”来作夸张表达,意为将三苗流放到很远很远的西方去了。
至迟到唐代,“三危”所指即已定型。《史记·五帝本纪》“迁三苗于三危”,唐人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43〕《括地志》为唐初李泰所编,《括地志》这条材料在“三危”的讹变进程中与郑玄所引《地记书》同为转捩点,《括地志》在《地记书》的基础上,不但对“三危”词义作了解释,而且还将“三危”具体地望指定在敦煌东南三十里。李泰的这一比附遂成后世公论,这也即是后世一般地理志书及辞书所给出的三危确解。但是,李泰注解本身就疑问重重。位于敦煌东南三十里的所谓“三危”山,在唐朝当地人口中尚称“卑羽山”,“卑羽”应为音译,有的史书如《太平御览》也称“升雨山”〔44〕,“卑”与“升”之繁体“昇”形近而误。我们似可如此推测,当地人不只在唐代,甚至在远于唐代的更遥远年代,他们皆以“卑羽”名此山,而不是以“三危”名之。问题似已然明晰,李泰在《尚书》及前代注家们所划定的地理范围内,作了进一步探寻,终在敦煌东南三十里找寻到一个当地人称为“卑羽山”的山峰,又因此山恰好有三峰突兀之势,遂望文生义解“三危”为三座耸峙之山峰。乍一看,此解似天衣无缝,完备无缺,但经过笔者前面的考索,最终发现这一注解历程充满着极大的讹误与附会。
四、历史意识的变化是导致“三危”注解歧义的根本原因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大致已看出“三危”这一语词的流变历程。在先秦典籍中,“三危”以一种神话意蕴相对浓厚的指称方式指代“西极之山”,这座山位于大地中央“昆仑”之西方,若想从昆仑抵达此山,尚需经过流沙、沉羽等地。先秦时代的典籍撰写者似乎都没有混淆这一概念,当然屈原《天问》“三危”也毫无疑问承载着这一语义。《山海经》、《尚书》、《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典籍所记“三危”无一例外皆是此种语义的印证。甚至直到东汉,“三危”都还没有产生太大歧义。自郑玄注《尚书》和张揖注《汉书》后,“三危”便逐步走上了“中原化”、“本土化”的阐释历程。再经杜预注《春秋左传》、《水经》以及郭璞注《山海经》的进一步演化,“三危”从鸟鼠山之西不断向西推进至敦煌,但此时的“三危”尚只是敦煌境内一个模糊的并不确定的山名。到唐代《括地志》认定敦煌卑羽山为“三危”后,“三危”就正式定型,成为后世不刊之论。从遥远的西极之地到九州临近中土之域,从一个半神话半传说半历史性的飘渺悠远所在逐渐坐实为一处实实在在的中国山峦,“三危”最终形成了我们今日地图册上可以查阅的西部山峰。事实上在先秦典籍尤其是以浪漫幻想见长的文学典籍《楚辞》之中,这种原本带着相当浓厚的神话虚幻色彩和渺茫空阔的指代特征的词汇,往往在后世的注解中都在不断经历着具体化、实证化、明确化的过程。“三危”如此,《楚辞》中其它地理名词也大多经历着这样的命运,“流沙”〔45〕、“赤水”〔46〕、 “不周”〔47〕、“西海”〔48〕、 “悬圃”〔49〕、 “崦嵫”〔50〕、“西极”〔51〕、“昆仑”〔52〕等,无不具有此种特征。
客观说来,这种历史性地理名词在后代阐释史进程中的讹变,我们已经很难准确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及社会因由,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同时也少不了更深层的主观因素。先秦典籍流传时间久远,从而客观上难免形成所谓的“训诂茫昧”〔53〕。于此之外,由于不同时代的学者受到各自时代知识储备度、思维方式、观念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权威话语模式的影响,由此而导致人们主观上对于古代典籍及其内容的不同认识与评价,乃至于对于同一个概念、名词、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可能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归根结底,这便是一种人类历史宏观地演进变化着的历史意识,即对于人类演进着的观念意识本身的意识演变状态。这种历史意识与人类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根本方式有着深刻关联。借用西方当代阐释学的观点,世界、历史与文献的存在首先是,而且也只能是在人类的“认识”与“理解”中的存在。“三危”也好,“昆仑”、“崦嵫”、“西海”、“流沙”也好,所有屈辞文献中的地名、概念和语言形式只有经由人们,经由学者的理解、阐释和流传才能获得自身的历史命运。而在每一个学者的理解与阐释的背后,都本质性包含着对于阐释对象的某种误解和成见,或者说某种特定“前见”或“前理解”。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就认为:“一种诠释学处境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前见所规定的。就此而言,这些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因为它们表现了那种我们不能超出其去观看的东西。”〔54〕西方阐释学前驱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角度奠定了这种阐释学的理论根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55〕中国历代学者注释先秦典籍,毕竟都处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语境之下,这种特定的时代文化条件必然决定了不同的屈辞学者对于屈辞研究与理解的特定“文化视域”与“文化前见”,这是任何一个学者都无法超越的思想界限与历史界限,由此自然形成整个屈辞注疏传统流变的特定“效果历史”。中华文化在先秦以及更早时期的神话创始时代获得奠基以后,经由先秦以儒家为主的实践理性精神和道德理性精神的洗礼,远古时代人类遗存的诸多色彩瑰丽的浪漫性文化信息和历史信息逐渐经受着后世的改造和选择。汉代以后,特别是像汉唐明清这样的盛世王朝时代,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以及中华文化自身的统合性内在驱动力也必然要求将一切异域之物、神怪之说、不经之谈、迂阔之论整合到一种严整通透的言说秩序之中,甚至于使之成为一种权威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而任何经典文献的注疏阐释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正是这种国家意识和历史意识自足流转演变的具体显现。由此而令我们看到,原本神话传说中虚幻迷离的“三危”这座“大地极西之山”,最终如何演化成了中华九州域内的“鸟鼠之西”或“敦煌西南”的“峭绝三峰”,如何成就为“普天之下”的“王土”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作为后世学者和阐释者,作为文化的传递者和耕耘者,如何尊重原典,如何从文献本身出发,从原初的历史事实与历史情境出发,尽量剔除所有主观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尽量接近最初屈辞道说者和阐释者的原始意义,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和文献本身的面貌,或许是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思考的又一重要问题。
〔1〕〔15〕〔18〕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96,96,96.
〔2〕〔3〕〔4〕 〔5〕 〔6〕 〔7〕 〔24〕 〔26〕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6,361,434,609-611,1312,361,361,434.
〔8〕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55-64.
〔9〕〔10〕〔11〕〔19〕〔35〕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刻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8,150,150,151,150.
〔12〕〔36〕〔37〕〔4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65,66,29.
〔13〕〔1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741,761.
〔16〕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374.
〔17〕金开诚.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336.
〔20〕毛奇龄.天问补注〔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集2〔Z〕.济南:齐鲁书社,1997.147.
〔21〕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8.
〔22〕李陈玉.楚词笺注〔M〕.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
〔23〕黄文焕.楚辞听直〔M〕.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52.
〔25〕周拱辰.离骚草木史〔M〕.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Z〕.117.
〔27〕王夫之.楚辞通释〔M〕.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Z〕.216.
〔28〕徐文靖.管城硕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276.
〔29〕游国恩.天问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5.
〔30〕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4.
〔31〕王闿运.楚词释〔M〕.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Z〕.631.
〔32〕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294.
〔33〕林庚.天问论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4.
〔34〕程嘉哲.天问新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69.
〔3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98.
〔39〕〔40〕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刻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56,2056-2057.
〔41〕郦道元.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594.
〔42〕山海经〔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
〔44〕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244.
〔45〕〔46〕〔47〕〔48〕汤洪.流沙·赤水·不周·西海—— 《离骚》地理再探索〔J〕.中华文化论坛,2010,(3).
〔49〕汤洪.《离骚》“悬圃”新释〔A〕.中国楚辞学:第11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205-222.
〔50〕汤洪.屈辞“崦嵫”再探索〔J〕.文史杂志,2012,(3).
〔51〕汤洪.屈辞“西极”再探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6).
〔52〕汤洪.屈辞“昆仑”再探索〔J〕.中华文化论坛,2013,(5).
〔53〕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
〔54〕〔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95.
〔5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06.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