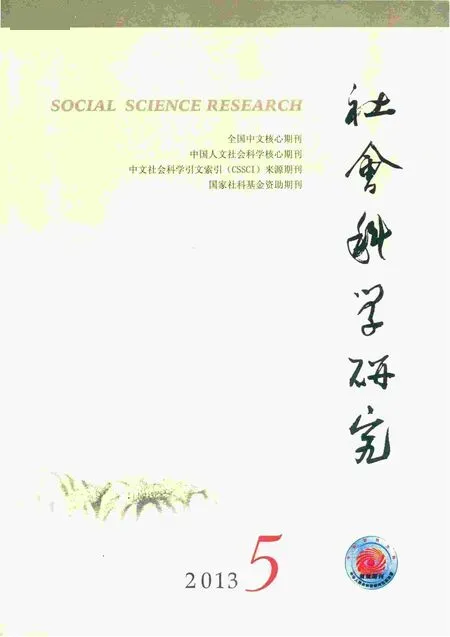“百药”、“百病”学说的生命伦理与美好社会
苏 宁
早期道教经书《玄都律文》(据《道藏提要》考为“唐以前正一盟威律文”)在其《虚无善恶律》、《戒颂律》、《制度律》、《章表律》等分册之后,列出专章《百药律》、《百病律》,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百药”、“百病”理论,独具特色地就善恶报应观以及戒律制度的执行提出了详尽的阐述。实为道教借医家之名与世俗伦理共同塑造的生命性理、玄理,同时也是事理与情理,在其宗教的信仰里阐发出生命的思想。其中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借助独特的思辨特征、叙述方式,从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建立了道教以神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之学,是对道教生命伦理的鲜明阐释,表现了宗教与人文“疗治社会”的多维性思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应道教“贵生”理念。
一、何谓“药”?
何谓“药”?在《玄都律文》中的“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药物,而是指道德、行为,而戒律则为处方。此“药”是基于对人类行为不健康的预设。经曰: “夫德以除灾,药以愈病,不知律者,为国则无延祚之期,为家则无子孙,为身则刑兆虚乱,正气不居,年命为衰。故非道而治,非法而言,亡算夺纪,司过言罪,司命削籍。律曰:德为医也,行为药也。”〔1〕显然,这个“医”、“药”以清净无为、积善修德作为基础,是与信徒共同创造的宗教伦理视野。故文中又曰“柔弱去欲,宽和恭逊,药之道德府。”〔2〕道教从《太平经》开始,就确定了“内以至寿,外以至理”的养生与积善并重的原则。与其他经文注重将救人济世之善行作为个人修炼成仙的条件不同,《玄都律文》中的“病”与“药”的道教伦理实际功能是指向社会的,要求信徒遵行用以维系世俗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
经中说道:“尊天敬地为一药,钦奉三光为一药,恬淡无欲为一药,仁恕谦让为一药,好生恶杀为一药,不多聚财为一药,不犯禁忌为一药,廉洁贞信为一药”。显然,在此经中,“病”与“药”也是分层级的:较低一个层次即视为指向基本道德规范的“药”;较高层次则为有精神规范作用之“药”。在“百药”理论中,人们生病,并非外邪侵入人体,而是人们日常行为的失范,由各种各样的不善恶行造成的。可见此经借助伦理的逻辑进入而上升到宗教逻辑,生命是与德性相联系的。经文中关于生病有如是论: “夫人有疾病者,坐于过恶,阴掩不见,故应以病。因缘非饮食风寒温气而起也,由其人犯法违戒,神魂拘谪,不在形质,肌疏藏虚,精气不守,敢为利焉。虽居荣服,不敢为非。度形而为衣,量腹而为食。虽富且贵,不敢恣欲。虽贫自贱,不犯戒律。是故自然外无残暴,内无疾病也。”〔3〕将生病直接等同做恶(“坐于过恶”),在其他宗教以及哲学思想里是不多见的。我们知道孔子有“不忍人”之说,孟子有“不安”之说。《玄都律文》则直接称“病”。要治疗身体疾病就要用药,但是这个“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药,一般的医药不但治疗不了疾病,还有使病情恶化的危险。“人不修其德行而广求医药,藏罪而多求章表上,而所行不改,其罪更凶。”〔4〕所以《玄都律文》为众生治疗疾病开出了它特有的药方,即“百药”。那么究竟“百药”是什么呢?文中已一一列出,这里征引如下:
“不烧山林为一药,空车助载为一药,志弱性柔为一药,不自尊大为一药,行宽心和为一药,不好阴私为一药,动静有礼为一药,阴德树功为一药,起居有节为一药,不论诉人为一药,近德远色为一药,灾病不干为一药,施不望报为一药,为人慕愿为一药,推恩义让为一药,慈愍怜爱为一药,好称誉人为一药,心静意定为一药,为人愿福为一药,祛邪弼正为一药,不干豫人为一药,教化愚暗为一药,戒敕童蒙为一药,解散思虑为一药,因贵为惠为一药,内修孝悌为一药,为人起利为一药,蔽恶扬善为一药,以力助人为一药,好饮食赐人为一药,怜贫伤危为一药,救日月蚀为一药,言语谦逊为一药,恬淡宽舒为一药,不负宿债为一药,思神念道为一药,质俓端正为一药,立功不倦为一药,不争是非为一药,除情去欲为一药,受辱不怨为一药,不取非财为一药,推好取丑为一药,虽灾自受为一药,称扬贤良为一药,好相引用为一药,不自彰显为一药,救祸济难为一药,不自伐善为一药,谏正邪乱为一药,劳苦不恨为一药,开导迷误为一药,覆蔽人过为一药,因富布施为一药,进胜己者为一药,扶接老弱为一药,惠与穷乏为一药,誓不駡詈为一药,为人严净为一药,智德不退为一药,位高接士为一药,好言善语为一药,恭敬卑微为一药,生无懈怠为一药,至诚笃信为一药,不駡畜生为一药,推直引曲为一药,心平意等为一药,进退可否为一药,不念旧恶为一药,推善掩恶为一药,听谏受化为一药,推多取少为一药,忿怒自制为一药,见贤自省为一药,闭门恭肃为一药,推功救苦为一药,尊奉耆老为一药,好人有功为一药,清廉贞分为一药,听经实行为一药,助人执力为一药,富有愍无为一药,远嫌避疑为一药,安贫不怨为一药,尊奉圣文为一药,好成功德为一药,宣扬圣化为一药,得失自观为一药,劝人学道为一药,愿礼拜三宝为一药,以言为善为一药。”〔5〕
相对应而言,百药善为首,百病恶起端。对于一个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世俗权威和社会组织的群体来说,道教不能绕过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正是从仙道到人道的道教的伦理化趋势。对于当时对道与神充满了信赖和依从的民众来说,“药”的指称所能起到的权威意义超过其生物属性,如此言说方式能使道民绝对奉行。善行是有生命、有意志的,把握生命就不仅是生物学的把握或了解,而是一个道德律令的把握。《玄都律文》一再讲“受辱不怨”、 “至诚笃信”、 “劝人学道”皆为药,在如何调护生命这一点上,使宗教伦理意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历史化、具体化,开辟出精神领域、心灵世界及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何谓“病”?
此经认为,“病”大多是因为人们的行为不端,对神不敬、多行不义而造成的。行恶造成生命之滞。这样一来,便将道教信仰与生命之义在道德理性的逻辑中打通。个人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连属在一起。“人能除此百病,即无灾无患”。关于“百病”,文中详述说:
“喜怒无常是一病,不好耆老是一病,好色无德是一病,舛戾自用是一病,憎之欲死是一病,从贪弊恶是一病,擅变自可是一病,鬼黠谀谄是一病,快祸遂非是一病,两舌无信是一病,乘权纵横是一病,駡詈风雨是一病,侮易孤寡是一病,教人堕胎是一病,威势逼勒是一病,孔内窥人是一病,借不念还是一病,背向异端是一病,曲人自直是一病,调戏异同是一病,恶人自喜是一病,探巢破卵是一病,愚人自贤是一病,水火败人是一病,以功自与是一病,教人去妇是一病,以劳自怨是一病,合祸睽爱是一病,喜说人过是一病,唱祸导诽是一病,以贵轻人是一病,见物欲得是一病,以贱耻贵是一病,亡义取利是一病,以德自显是一病……”〔6〕
《道藏提要》曾指出此类经文为:“按善恶多少计数报应之律文”。不过文中没有局限在具体论述善恶报应的层次结构,而是推衍出如何罚恶的伦理规范与标准作用。善恶观念自有道家起即为道教伦理的一个核心观念。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重视运用戒律来规范信徒的日常行为,无论佛教的五戒、八戒、十戒还是道教的“老君五戒”、“初真十戒”等,都体现了扬善抑恶的道德原则。善恶报应的观念在道教中起源已久,《太平经》中已有云: “但当赏善罚恶,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7〕《抱朴子内篇》中也对修善能够有助成仙、为恶与人的寿命长短有关做过如下论述: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本数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多者,则纪算速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8〕
《玄都律文》经文承继和发展了道教原有的灾福承负的思想,强调善恶报应不仅与修道有关,也与人的生命长短有关。这个思想在《玄都律文》中论述得更加详细。经文明确指出“千善”之后世出神仙真人。
应该看到,“百药”“百病”是有道教神学基础和宗教功能的。《玄都律文》继承《太平经》五脏有神、存思可以除病的思想,同时延续《赤松子章历》司过之神的思想。在这里,有“司过”、“解过”之神,他们乃是“百药”、“百病”的司职之神。文曰“常思病来之罪,所犯过恶,司过神、解过神、司过君、解过君,当解除之一切罪过、世间所犯诸恶,则病消除。”〔9〕解过祈福,即当思过悔罪,上章进表,以求神真宽恕。经曰:“轗轲衰耗,数得飞祸,绝无子孙,疾病痿厄,所求不谐,牢狱闭系,血气虚赢,贫贱困极,残年夭死,痴狂聋僻,或出妖臣逆子,破家癫厉,刑人市死”〔10〕种种厄境,皆当依律上章,以解罪业。由此看来,《玄都律文》在承继前代已有各种善恶报应论述的基础上,更将其细化,为善与作恶受到的奖罚更加量化。用“百药”、“百病”这种通俗的形式表达祈神解过,使灾福承负成为有具象原型的思想范畴,是对道教传统的奖善罚恶思想的一次提升。这样一来也就具有了社会功能,它努力把人和神、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信众惧怕神明的惩罚因而产生了相应的内在动力,自觉地以“百药”、“百病”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日常行事更加有根可据,不至越出范围而遭灾受难。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善恶报应的思想是建立在道教清静虚无的理论之上,故谓之“虚无善恶律”。宇宙的“生生”建立在“道法自然”的演化中,善恶的显化,也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中。道教实践者的目的是超越自我而与神的规范、教诲相联系,它不是个人的或人格性的美德伦理,而是超越了人的现实性而与神圣的永恒性相联系。普遍的伦理规范成为神的戒命,平凡的道德准则变成了超凡的道德律令。这既内涵了宗教伦理的世俗性又包含着宗教伦理的超越性。
经曰:
“一者遗形忘体,泊然若死,谓之虚,二者损心弃意,废伪去欲,谓之无;三者专精积神,不为物集,谓之清;四者反神服气,安而不动,谓之静;五者深居宴处,功名不显,谓之微;六者去妻离子,独与道游,谓之寡;七者呼吸冲和,滑泽细微,谓之柔;八者缓形纵体,以奉百事,谓之弱;九者憎恶尊荣,安贫乐辱,谓之卑;十者遁赢逃满,衣食麄竦,谓之损;十一者争作阴阳,应变却邪,谓之时;十二者不饥不渴,不寒不暑,不怒不哀,不迟不疾,谓之和;十三者爱视爱听,爱言爱虑,不费精神,谓之啬。律曰:凡此十三者,混沌为虚无。行道守真者,敬奉师法,顺天教令,穷极无为之道,虚、无、清、静、微、寡、柔、弱、卑、损、时、和、啬。夫为道者,气炼形易,民和国宁家吉,灾不起,寿命延,家国昌。违律者为天所刑。”〔11〕
百病”、“百药”作为一个有效而又完整的祈神解过体系,将善行神化为解病之药。其解过的宗教基础是祈神修炼,这就将伦理判断转化为对信仰价值的服从,将现实的社会行为上升到宗教对命运的把握,是向生命处用心,对命运正德。人的尽性已是“生命”上的事,如《尚书·大禹谟》所说:“正德利用厚生。”这样的伦理目标具有道教信仰力量的超越性。将对现实的祸福转化为宗教体验,转换的中介是祈神存思。把人伦关系的调节权和伦理目标的决定权交给了绝对律令。《玄都律文》在虚构出的一系列病与药的循环体系中,将“仙境”具体化为人类的道德理想,要求人们通过行善等方式来彻底摆脱物质和情欲的诱惑,实现成仙、得救。
同时,“百药”、“百病”说也有宗教美学的共享基础。与善恶对治的“药”、“病”这一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经特殊化的组织构成宗教审美符号。它给抽象概念赋予具象原型,人间的世俗社会行为转化成特殊的人神关系,最终体现为符号化的宗教共享关系。“百药”也好,“解过祈福”也好,同美、善有共同的谱系、逻辑、思维方式,主张通过道德理性来润泽、调护生命。每一种伦理选择、戒律操守的选择,或“药”,或“病”都是一次美与善的判断。审美经验越丰富,品味越健全,道德视点越清晰,道教的教规约束便越自性。人的审美本能融合在道教伦理价值本能中,使向善行为成为超越个人道德约束的人格本能与内在能动,从偏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和道德实践到注重社会的精神境界,随着其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的递升,社会也将可能变得愈加美好。这也许是“百药”、 “百病”之说给予我们的启示。
〔1〕〔2〕〔3〕〔4〕〔5〕〔6〕〔9〕〔10〕〔11〕道藏:第3 册 〔Z〕.457,457,458,458,457,458,458,461,456.
〔7〕王明编.太平经合校〔M〕.中华书局,1960.39.
〔8〕王明撰.抱朴子内篇〔M〕.中华书局,198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