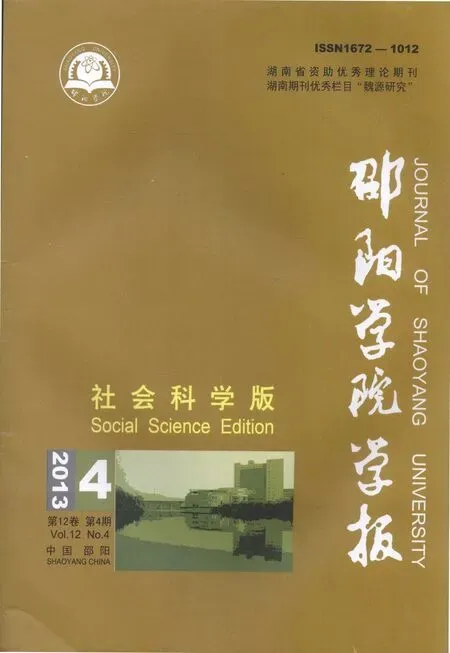论两汉文艺论著中“丽”的语义场和审美范畴
吴明刚
(四川民族学院 中文系,四川 康定 626001)
一、先秦时期“丽”的语义场和审美内涵
检校“丽”字在先秦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丽”字使用情况相当复杂,含义也比较丰富,大概有七种:①“华美、华丽、美丽”;②“依附、依据”;③“施政、施教、施刑罚”;④“数”;⑤“两、偶”;⑥“楼、屋栋”;⑦通“罹”,意为“遭遇,陷于”,但其被纳人们审美视野,表现出审美质性的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作形容词,意为“华美、华丽、美丽”
先秦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首先表现为“重质轻文”,先求“实用”,后讲“美丽”,先崇尚物质享受,后诉求于精神愉悦。此期人们审美视野中的“丽”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有联系,表现为服饰、建筑之华丽与容貌之漂亮,后来有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文丽之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由品物到评人再到品文,反映了当时人们审美视觉的变化。
(二)作数词,“两、偶”含义
“对偶”、“和谐”、“对称”、“均衡”是中国最传统的审美心理,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作为数词的“丽”并不具审美质性,不过它暗含和联系着中国人的这个最普遍的“审美感觉”,故它在修饰名词的时候也带上了审美的色彩,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三)作动词,意为“依附、附着”
作动词的“丽”有“附着、依附、著”之意,因此就有“突出”的意思,同样也潜蕴着一种“依附性”的美学意味。当然,这种美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美。
先秦时期,“丽”作为一个概念开始有审美意识萌芽的表征,历史语境赋予它独特的审美内涵,在奠定了“丽”审美范畴基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丽”范畴未来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1]
二、两汉文艺论著中“丽”的语义场分析
两汉文艺论著中,“丽”被广泛使用来评论文艺作品。《淮南子》:“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淘朗奇丽激扮之音”,“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者”。这里谈到了歌、舞的“丽”特性。“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丽也”“西北曰丽风”,这里认识到风“流动”的特性,为后世高扬“流丽”之美作了铺垫;[2]司马相如《上林赋》说:“君子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以“巨丽”形容皇家苑囿的广博富丽;班固《东都赋》说“凤盖涔丽,和銮玲珑”,[3]以涔丽形容凤盖之美;蔡邕《九势》说:“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4]以“肌肤之丽”表现书法艺术蕴含的生命之美。
文学上,“丽”常被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本质特征。在汉代,尤其是楚辞和赋的美学特征。司马相如说“材极富,辞极丽”;扬雄说“好沈博绝丽之文”。[5](《扬雄·答刘歆书》)其评司马相如赋曰“弘丽温雅”;论诗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皇甫士安说“文必极美,辞必极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三都赋序》)班固评《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评扬雄赋“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班固《汉书·扬雄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奏雅,不已戏乎!”[3](《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赋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论汉赋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6]王充论汉赋:“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7](《论衡·定贤》)“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具务,言眇而趣深,然而不能外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论衡·佚文》)。汉宣帝论赋:“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3](《汉书·王褒传》)崆充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的赋尽管“弘丽”,但无助于判定是非真假,“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在汉代“丽”更多地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评论汉赋用“丽雅”、“靡丽”、“弘丽”、“巨丽”、“侈丽”、“华丽”等词汇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其它著述评论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涔丽”、“华丽”、“奢丽”、“夸丽”、“涔丽”……在以“丽”构成的众多的语义场中,在它与各种不同的词素的组合关系中我们可以把握“丽”的含义,认识到“丽”作为民族审美情趣的一个具体历史范畴,具有多种丰富的规定性,闪耀出它特具的历史光泽。
我们来看“丽”与不同词素的组合在一个共同语义场中呈现的含义:
“富丽”:富,繁复众多;“神丽”:神,神秘色彩;“靡丽”:靡,涂饰意味;“夸丽”:夸,夸张中的气势;“奢丽”:奢,物的会聚堆砌;“弘丽”:弘,堂庑阔大;“丽雅”:雅,高尚,不粗俗;“崇丽”:崇,高贵;“涔丽”:涔,绵密披覆;“华丽”:华,有文采;“奇丽”:奇,出人意料,令人难测的;“巨丽”:巨,大,很大;“极丽”:极,达到最高程度;“绝丽”:绝,极,最;“辩丽”:辩,多方面言说;“侈丽”:侈,夸大。
以上各例由“靡、弘、侈、辩、巨、夸、富、神、雅、绝、涔、奢、奇”等不同语素与“丽”组合,形成了以“丽”为共同语素的语义场,汉代文艺用“丽”来描述作品、描状赋体,“丽”与其他词一起构成了一代汉文学“丽”的共同语义场。其中“富、奢、巨、辩、侈”等语素具有众多繁富之意,“奢、涔、巨、靡、辩、侈”等语素具有物的会聚堆砌、铺排之意,“极、绝、崇、夸”等语素展现了汉代这一特定时期人们饱满充沛、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了汉代文艺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繁富铺陈、饱满充沛。两汉一统四百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局面,尤其是西汉,更是一个气魄恢弘的朝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均呈现出大发展,在社会生活领域,农业的相当进步、商业手工业的较大发展、域外物品和域外文化的输入,人们的认识领域大大拓展了,在这样一个空前丰富的环境中,“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奓靡,临迴望之广场,程角牴之妙戏”,他们忙于认识、熟悉、占有、享受这个“地沃野丰、百物殷富”的世界,于是滋长了“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的怡乐之志,正是这种“耽乐是从”的心理流露出一种自足与夸诞的心理。因为夸诞,所以沉溺于更加丽靡的铺张之中。正是与这种特定时期的心理状态相适应,于是繁衍、琐碎、夸饰、炫耀的方式乃成为汉人的语言用语习惯,而对繁富靡丽的追求乃成为汉人美学情趣之所在。现实生活的极大拓展,观念世界的纷纭繁富,社会风气的侈靡奢华,产生了以“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为能事的靡丽“国华”,以繁富铺陈为特征的汉代文学的代表汉大赋。[8]
三、两汉文艺论著中“丽”的审美范畴
繁富靡丽、饱满充沛是汉代文艺最明显的特征。汉代文学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最简洁的概括便是“丽”。它描写的场面阔大、气魄宏伟、铺张扬厉、繁富众多、五彩斑斓、堂哉皇哉,透露出一股外在的涂饰美,从审美心理来说,“丽”的审美范畴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容上的琳琅满目,色彩上的富丽堂皇的视觉美,这种视觉美又是以饱满绚丽来厌足人心的。[8]
周均平先生对“丽”的审美内涵曾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丽”是一种强烈地诉诸感官的美,具有感性的鲜明性和愉悦性。作为形式美属性,有着人工创造性和主观追求性。它包含着大美:形态上气势浩荡、气概雄浑和气象万千,有空间开放感;又包含着精美:质感上要求精美绝伦、精致灵巧和精徼超妙,有错综彪炳感。大美和精美的整合圆融,正是“沉博绝丽”,美仑美奂。“丽”的审美概念基于“目观”为美的审美意识,以视觉审美对象的崇高华采为美。汉赋之“丽”突出的是事物的外在形态之美,是一种苞举天地,整合圆融,夺人心目、沁人肺腑的大美;它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让人产生精美绝伦的视觉美、色彩美、韵律美和令人震撼的崇高美。[9]因此,“丽”的审美范畴首先表现在形式上的“大美”和“精美”两个方面。
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在汉文学“丽”的共同语义场中,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汉赋“丽”的这种“大美”和“精美”的审美特性:
这种“大美”表现为“巨丽(侈丽、弘丽、靡丽、奢丽)”之美。在两汉文学作品中,作者选取大量的“壮丽”、“美丽”、“秀丽”的外在事物,以其宽阔的审美视野描写对象,来表现“巨丽”之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写天子的上林苑,对水、山、草、木、鸟、兽等分门别类地用夸饰意味很强的词对所描写的对象尽情地敷陈渲染,极尽夸饰。上林苑内的河流: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陋之口,触穹石,激堆琦,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文势纵横捭阖,摇曳多姿,音节浏亮,文辞弘丽,将“八川分流”的状况写得激越动荡,雄伟奇丽。张衡的《二京赋》主题意识更鲜明,功能也更突出,政治讽谏成分更多,语言的奢丽之风也更盛,特别是在渲染西都的豪奢时,极尽敷陈夸饰,文辞富赡,气象宏大,波澜壮阔,其夸饰的手法和程度与西汉大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汉王朝那种昂扬奋发、开拓进取、闳阔包容的气魄和雄浑博大的精神也溢于言表。
追求文辞富有色彩、流丽不滞的语言风格;崇尚夸张铺排,比喻形容,讲究结构的布置的艺术表现手法,又包含着“精美”的审美内涵。汉赋用很强的象形性、装饰性、绘色性、拟声性、表情性的形容词,为文章增色不少。司马相如说“材极富,辞极丽”,扬雄说“好沈博绝丽之文”,皇甫士安说“文必极美,辞必极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他们看到了两汉作品中作者对辞采美的自觉追求。汉赋利用白描、夸张、比喻、排比、类比、对偶等赋的创作手法,句势对称交错,韵散结合,使语辞和意象源源不断地生发铺陈开来,虽然有人评论汉大赋,“丽而失虚,颂而乏情”,但汉赋“富丽”、“沈博绝丽”的“精美”特点不能不让人佩服,这是多么绝伦的文章啊!到了东汉后期这种“精美”又表现为一种“巧丽”,东汉抒情小赋重抒写个人的情志,体制短小,语言凝炼工整,描绘更加细致,显得小巧精丽。如张衡《归田赋》只用短短200 余字,写作者自己归隐田园的愿望,短小隽永,朴素自然。
它把作者主体意识、抒情因素注入赋中,将外部世界转向个人的内心世界,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重视主体情感的抒发。“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鸽鹧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这里对草木禽鸟的语言描写生动清新具有质感色彩,音节谐和,句式整齐,表达出归隐者的闲情逸趣,给人以“巧丽”之美的感觉。
其次,“丽”的审美范畴表现在内容上的“性情之美”。两汉文艺论著主要体现在“鉴赏”的层面,“丽”的本体审美范畴重点表现在内容上的“性情之美”,即本体之美。两汉文艺论著中有“宗经辩骚”和“宗经辩赋”之争,萧华荣先生在《中国诗学思想史》认为:“宗经辩骚”和“宗经辩赋”是汉代“情礼冲突”“文质冲突”的具体表现。《诗经》精神要求“丽而有则”、“弘丽温雅”、“弘博丽雅”、“丽”而能讽。汉代是一个“主文谲谏”(《毛诗序》)的时代,“文”指文辞、文采,“主文”重要表现就是追求辞藻的绮丽华美,语言的绚丽多彩,内容、形式上都崇尚“丽”。“谲谏”,是指在表达讽谏的方式上,比较委婉,强调赋作既要文辞优美,适合颂唱,又要能给君主以讽谏,使之不离于正。扬雄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5](《法言·吾子》)他认为“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两种,而更主张要写作“丽雅”、“能讽”的“诗人之赋”。班固也云:“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闰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强调其社会道德功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赋”的本体审美特性。王充也说:“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汉宣帝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抓住赋“丽”特性肯定和褒扬了赋的本体功能。因此,我们认为,“丽”一方面要求“辩丽可喜”,侧重于艺术性审美批评,追求主体“情性”之愉悦,肯定骚赋之“丽”,进而肯定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另一方面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侧重于思想性政教功利批评,标示“礼法”,强调骚赋之“则”,进而以经之“则”去衡量屈骚赋,对之作出否定性的评价。肯定“情性”对于“丽”美表现的愉悦性作用,将审美主体之“情性”的认识和把握与审美客体“丽”美的显露和表现相联系,是汉代对于“丽”美表现认识的一大进步。[10]
再次,“丽”的审美范畴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命之美”。从我们民族发展的历程上来说,汉代处在封建社会的上升初期,以“丽”为标志的审美情趣中十分饱满地表现了汉人的一种对生活的充沛热情,一种大力开拓积极进取的意向,一种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一种未加节制的侈靡和一种过分注重外物的心理,一种整体繁富、色调斑斓辉煌和一种“焱焱炎炎,扬光飞文”的气势。[8]汉代文艺的美感是繁富之中的充沛,堆垛之中的厚重,排比之中的遒劲,这就是一种“生命之美”。
综上所述,在两汉文艺论著对“丽”的论评中,我们能看到:众多的词素与“丽”共同构成一个共同的语义场,那就是繁富铺陈、饱满充沛;在这个共同的语义场中,“丽”审美的范畴表现为形式上的“大美”和“精美”,内容上的“性情之美”和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命之美”。两汉文艺论著中,这些文学家、经学家甚或皇帝的“高见”,与先秦时期“丽”的语义场相比,我们认为它还不具备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还不能自觉地纳入全民视野,还不能将之视为人生审美高级状态,因此,“丽”在两汉时期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
[1]吕逸新.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J]. 社会科学家,2009,(1):129-132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
[4]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
[5]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9:1117.
[8]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18.
[9]周均平. 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何世剑,喻琴. 先秦两汉时期古典美学“丽”的审美范畴[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5,(4):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