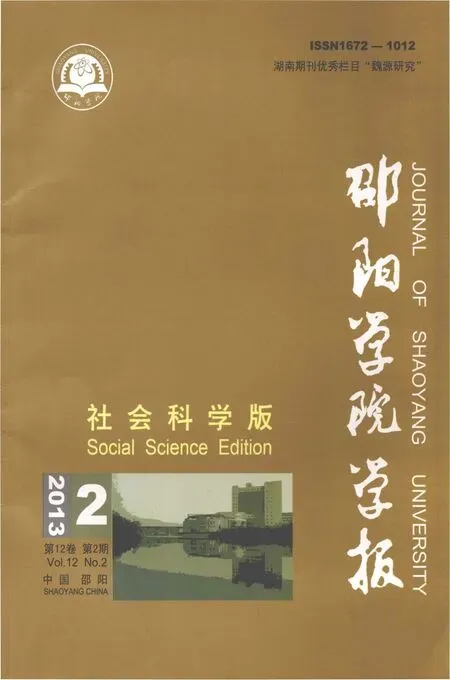两种创作情结的相互扭缠——丁玲向左转时期的创作心态分析
陈红玲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0)
丁玲一生的创作曾有过几次明显的转型。阅读丁玲在1929 年冬至1930 年底的创作文本,我们发现:丁玲的创作明显地从早期的“莎菲”天地里走出来,放弃了自我倾诉式、自我剖析式的叙述方式,运用“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表现革命与爱情的冲突,实现了创作的向“左”转。针对这一转折,冯雪峰给予高度评价:“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1]丁玲在此期间的创作,尽管她主观意识上趋同当时最流行、最先锋的革命文学思潮,在作品中注入“革命意识”这一创作新因素,创作了长篇小说《韦护》、中篇《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及数个短篇。然而,“革命意识”这一主导性的创作新因素,并没有完全挤占掉丁玲原有的个性创作因素,潜意识中仍保留着“五四”个性化创作立场。“我最后一本《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风的书,是《韦护》,出版于1930 年。这本书的作风是够写实的,但内容可是浪漫的。”[2]丁玲的这段自述充分说明,此时,她创作风格虽已改变,已经倾向于革命文学,但作品内在仍保留一贯的浪漫内容,“与其说是写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不如说是写革命为虚,写爱情幸福缠绵、相思苦恼为实。”[3]。作品中两种创作思想情结的扭缠不清,也表明处在创作转型期的丁玲创作心态具有矛盾性。
一、在显意识层面,创作转向革命文学
上世纪20 年代末到30 年代初,最流行、最先锋的文学思潮是“恋爱+革命”的左翼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丁玲的创作紧随此潮流。1930 年1 月5 日发表于《小说月刊》第2 卷1 至5 号上的《韦护》,是丁玲创作趋从“革命+恋爱”写作模式的标志。将《韦护》列入普罗小说,丁玲开始似有不服,但还是承认“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的陷阱里去了”[4]。《韦护》这篇小说是取材于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故事。但作者在创作上有了重要的突破。“这突破主要表现在它正面地、突出地写了革命,写了共产党人,写了革命的理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温情的爱情观;并着力写了具有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女知识青年丽嘉的思想转变。这实际上突破了真人真事的限制,也突破了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创作局限。”[5]宋建元的此段评论是对丁玲创作转向的肯定,特别是对作品中革命战胜爱情描写的肯定,也道出了丁玲此类小说与当时风行的“革命+恋爱”小说的相异之处。事实上,丁玲作品中恋爱和革命相冲突的主题,不同于蒋光慈之流早期小说恋爱和革命简单相加的写作模式。[6]丁玲晚年对自己的这一转折有过论断,她称之为“突破”。她认为《韦护》的题材范围有所突破,而在《田家冲》和《水》中,则是“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7]。这属于思想意识的突破。的确,1931 年随着小说《水》的发表,丁玲告别了“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标志着“新小说的诞生”。
究其原因,丁玲的向左转与当时的左联作家们的左转还是有所不同的。“鲁迅等人的向左转,是以穷尽启蒙主义作为其思想前提的。而在丁玲这里则可以说是以遭遇并穷尽个人主义话语的困境作为其思想前提。”[8]丁玲的向左转并不是突然的转变。二十年代末期,政治上的挫败迫使激进知识界对文学产生了新的期待:文学不但要承担反抗旧文化旧道德的使命,它还应该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作出切实具体的回答。其间,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等“五四”作家受到了强烈的否定性的攻击,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文艺思想引发了“五四”文学“向左转”的急剧变化。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丁玲在思想上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再加之,丁玲当时对自己的创作情况也很不满意,创作上也需求改变。她不愿只能够写出一些只有感伤主义者所最易于了解的感慨。但她也不喜欢胡也频转变后的小说,如《到莫斯科去》。她认为他的这种创作犯的是“左倾幼稚病”。她当时的想法是:“要末找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末写文章”。[9]虽然此时丁玲还未能把革命与文学联系起来看待,但在后来的客观创作实践上,她还是把革命与文学结合起来了。《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就是这种结合的有力佐证。“1930年丁玲创作发生了转变,这转变可以说由女性作家危机与意识形态特点合力促成。”[10]
在“革命+恋爱”小说中,作家表现的是知识分子抛弃个人主义,投奔大众集体革命的思想观念,丁玲的作品也不例外。韦护(《韦护》)为了革命而抛弃爱情;美琳(《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离开个人主义者子彬,走向革命大众;个人主义者玛丽(《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因为不革命而成为男性世界的包袱儿遭到抛弃。丁玲的这些作品又复原了她曾经颠覆和置换了的传统两性关系。在丁玲的“莎菲”时代,女性是绝对的主角,但在她的转型代表作《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中,男性成为了小说的主角。韦护、若泉、望微都是革命者,他们意志坚定,投身社会革命。为了革命事业,甘愿抛弃爱情,抛弃个人幸福。而其中的女性角色则降至次要地位。她们一味耽于爱情,政治上冷漠,生活上慵懒,只为爱情活着。在此,女性成了男性形象的反衬。早年男女对立的二元冲突模式消失,男性成为女性的引导者,女性如果不想被抛弃就必须站在男性同盟军的位置,来取得男性社会的认同,作品中的女性自我向革命理性作了妥协。至此,革命终于战胜了爱情,也标志着丁玲的创作由过去的“性别写作”转向了“革命写作”。
二、革命话语之下,潜意识地保留着“五四”个性化创作立场
丁玲是“五四”最后一个女作家,也是左翼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1924 年,丁玲为了追求进步思想从上海来到北京,结识胡也颇,并与胡同居,又开始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一时的小说。在此期间,丁玲都以“莎菲女士”的姿态面世,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直到1931 年胡也颇遇难后,丁玲创作才明显转向。如《水》反映的就是社会革命斗争。然而,与同期男作家此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丁玲“革命+恋爱”小说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显然都不如男作家。丁玲自称,“写《韦护》的时候,她的创作动机与写《在黑暗中》时一样,并不意在写英雄、写革命。”[11]可以说,此时丁玲的创作已经开始向左转,但她并没有完全放弃从‘五四’精神中继承过来的张扬自我价值的个性主义创作,而且这种精神或隐或显伴随了丁玲的一生。
丁玲的创作,从自我走向群体过程中,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使她“左联”时期的转型之作(《韦护》等),时常不自觉地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游离出来。按照丁玲创作的主观意图,她设想:莎菲式小资产阶级女性被革命者引导或批判,有的被改造成革命者,有的最终脱离革命大众,被革命抛弃,以此来完成对“革命话语”的表达;然而,作者潜意识中的反叛精神与性别意识,在写作过程中,使她越写越远离自己主观意图,导致她的作品客观上承传着“五四”个性主义的创作精神,依然保留着女性的主体意识。以革命党人瞿秋白为原型的小说《韦护》中,她在写作策略上有意做出‘革命战胜了爱情’的安排。但是,她仍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评立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丁玲的向左转,并不是与过去彻底决裂,而是在有所保留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在革命话语之下,任然潜意识地保留着“五四”个性化创作立场。
考察丁玲的“革命+恋爱”模式小说发现,它更倾向对两性爱情观的探索与揭示,作者对女主人公爱的合理性表示了同情,反而淡化了“革命文学”的革命性。探其原因就是,作者对爱情的崇尚。丁玲曾有这样的论断:“我个人是主张写爱情的。爱情对于人生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都需要爱情,从古到今,爱情一直与生活,与文学不可分开。我们中国有很美的爱情故事,有《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等。写爱情的作品,只有写美好的、高尚的感情,才得以流传下来。”[2]基于此种创作观,丁玲在向左转的代表作中都尽情地抒写爱情。因而,在小说《韦护》中,韦护赢得丽嘉的爱情并非因为其革命者的身份,而是韦护的人格魅力。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韦护与丽嘉的分手,表面看来,韦护离去是由于听从“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因为爱情妨碍了他的革命工作;事实上,“丽嘉并没有一次妨害他工作的动机。”“她不会要求他留在家里的。”因此,“他的冲突并不在丽嘉或工作,只是在他自己。”[12]在于他人性的惰力和弱点。美琳离开子彬也是如此,从作品中我们看不出美琳的离开是出于外在革命的感召,更多出于对爱情的失望。玛丽离开望微同样如此,是付出的爱情没有回报,是强烈的爱情渴望没有得到应答导致的。因此,“丁玲的这些作品与其说是‘革命+恋爱’的‘革命小说’,不如说是探索女性精神追求与命运出路的‘性别写作’”。[13]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30 年代向左转开始,丁玲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创作立场与倾向,开始由追求个性主义创作转向人民大众文学。但丁玲过渡期的转型不彻底。“这个转折,对丁玲太重要了,也太艰难了。”[14]《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三篇小说准确地勾勒出丁玲在“转变”过程中思想的矛盾性。尽管作者主观上有用“革命话语”努力把握时代,有着表现时代的强烈欲望,但由于作者潜在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的不时渗透、流露,使得创作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事实上,“此期丁玲的‘转折’,应该是从‘个性思想’的‘一项单立’到‘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共时的‘二项并立’”[15]。只是这种“并立”在作品中的表现迥异,前者是作者刻意要抒写的,表现在显性层面上,而后者是作者创作中潜意识流露出来的。这些都使得丁玲此时期作品呈现出矛盾复杂的思想内容,从中也可以窥见丁玲当时创作心态的复杂性。
[1]秦林芳.“转折”中的持守左联时期丁玲创作中的个性思想[J].文学评论,2008,(6) :120.
[2]宋建元.丁玲评传[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44-155.
[3]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1) :178.
[4]丁玲.我的创作生活[A].丁玲全集( 第7 卷) [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327-328.
[5]宋建元. 丁玲评传[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46-147.
[6]熊鹰.都市、电影和女性[J].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多彩画卷——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355.
[7]丁玲. 答〈开卷〉记者问答[A]. 丁玲全集( 第8 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
[8]贺桂梅. 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 —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195.
[9]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A]. 丁玲全集(第9 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8.
[1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0.
[11]阎浩岗.丁玲:革命年代的个性话语[A].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多彩画卷——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240.
[12]丁玲.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77.
[13]陈娇华.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5) :88.
[14]周良沛. 丁玲传[M]. 北京: 十 月 文 艺 出版社,1993:253.
[15]秦林芳.“转折”中的持守左联时期丁玲创作中的个性思想[J].文学评论,2008,(6)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