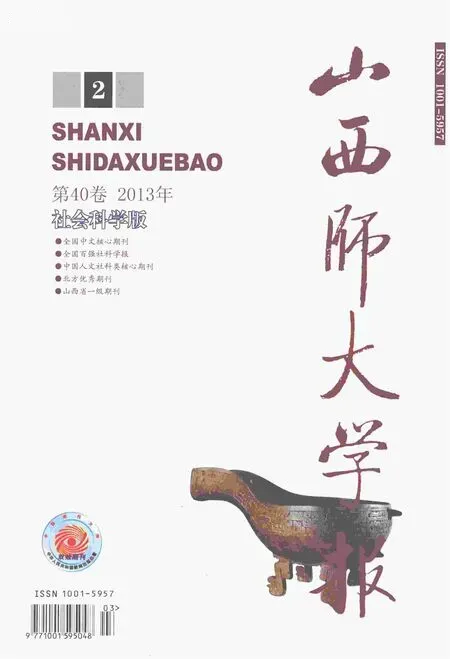船山对阳明“经权”思想的扬弃
田 丰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一
以“反经合道”来诠释“权”盖出自《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祭仲为保社稷而逐君,又不害及无辜,故公羊称之。程朱理学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说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基本倾向是将“经”诠释为不易之定理,对于人实践之中道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通过格物致知对这种“不易之定理”的学习和把握;其次是让“定理”在具体境遇中获得恰到好处的运用,此即为“权”。“权”既然是对“经”的运用,所以伊川自然认为“权”即是“经”,差别只是在于,“经”偏于体,主静,不易不变,“权”则偏于用,主动,灵活权变。人对于“经”的运用如果灵活而合于时宜,这种合宜即是“义”,因此“义”兼体用,兼“经”“权”。这就是伊川理解经权的基本结构。就此基本结构而言,朱子与伊川并无二致[1],这种以静态之“理”为核心的权衡结构有两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一般情境中的行动判断,也就是凭藉某种或几种准则定理在一般情境中应对适当,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之权”。很多时候程子朱子直接将它们称之为“经”。第二种方式是在特殊的两难困境中做出的决断,在两难复杂困境中,仅靠第一种“日常之权”并不足以完成判断。在这种境遇中,“权”之宜的问题会转化成不同定理之间孰轻孰重的判断。譬如在祭仲这里,需要权衡的是社稷与君孰轻孰重,我们可以称这种意义上的权衡为“困境之权”或曰“准则之权”。“日常之权”在程朱看来其实就是“经”,程朱在与“经”相对意义上使用的“权”是“准则之权”,“准则之权”乃是在发生冲突的道理上面寻找“上面更有一重”的道理,其本质依旧是“经”的运用。
朱子认为“盖义是活物,权是称锤。义是称星,义所以用权”[2]3269。朱子固然不会将“义”视为外在于心之物,但朱子也不会将“义”等同于心之本体,而更多地视“义”为一种合宜性的描述尺度。阳明所做的恰恰是批评朱子“义外”,并进一步去追溯人之权衡能力的本源[3]:“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则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4]205阳明的追问把对圣人境界的追寻都归本于对良知的真切体认,有了这种真切体认,才能让心成为有星之秤,良知即是此秤,亦是此秤之星,兼具认识与判断功能。也即是说,在前述“权”的两层意义之外,阳明发现了“权”的一个更加重要而根本的意义:人在具体境遇中对“良知”或“天理”的体认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认识功能,它在根本上也是一种“权”,“权”不再仅仅是由内向外的心体或天理之发用,它同时也是心通过境域中呈现的事事物物,向内在心体善恶尺度的一种回归与体认——我们将这种更源始意义上的“权”称之为“境域之权”——因为对良知的磨砺与体认必然需要对善恶是非的判断,而对善恶是非的判断按照阳明的说法,要落在“事事物物上去致良知”,又在具体境域中对事物进行权衡审度。
当阳明将这种能力落在良知上,并把“致良知”也理解为“权”之后,这里实际上发生了一个扭转,那就是“权”代替了程朱之“经”(理)而成为更源始的根基。借助于阳明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困境之权”和“日常之权”都只是一种更源始的“权”——“境域之权”的变式,而这两种同源的“权”,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本质性的。
总之,就权经关系而言,宋明儒所言之经其实皆非汉儒之经:程朱理学实以理为经,以权为经之变式;阳明心学则以心体为经(“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2]67,其实即权之本),以“日常之权”为变式。
阳明一方面将“权”理解为人心最本质性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将这种良知良能标示为绝对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将宋儒对“道”“理”祛时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如果说“理”这个概念中包含着分殊性与差异性的话,那么将“理”完全落在人心本体上之后,这种分殊性和差异性就会随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思路被敉平削弱。如果每个人的心之本体都和圣人之心体绝无二致的话,自然不必斤斤于对“圣人气象”的学习,只需在自己心上体认圣人气象,将自家精金练就。过于模仿圣人气象,反而可能造成对自家精金提纯的干扰,掺入铜铅渣滓。那么,即便不以道家思路称五经为圣人之“迹”,承认五经承载圣人之道,学者亦不必唯经是求,因为五经承载的“道”在自家心中已经具备,至于五经中涉及的文章数度、典章名物之处,反而会干扰学者对“道”的追求。
阳明据此提出的“五经皆史”[2]44,51,53意味着:经作为圣人著述,只是古今皆同的“心体”在当时境遇中的一种应对,典籍传承的每一代圣人不同的历史境遇之间具有平等性,历史境遇与当下个体的境遇也处于同一平面,人对境遇的应对与著述并不因其时间上在先就对其他著述具有绝对优先性,任何人只要能让其“心体”复归灵明,他对境遇的判断权衡就和圣人著述具有同等权利。所以前人往往批评文中子续经为僭越,而阳明则以为“拟经恐未可尽非”。这样一来,经学就丧失了其在历史中展开的对于一个民族传统的权威性与规定性。明中叶以降的“理”的去实体化趋势,以及气学的兴起,意味着对“理”的理解必须还原为生生不息的“气中之理”,形而上本体被重新置入历史性生成的道路,经史实学的回归方始再次获得其合法性。船山便是在这种思想史进程中之特立著出者。传统研究一般认为船山的思想可以总结为“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5]109。这个总结没有看到,虽然船山在其著作中总是不遗余力地批判王学,而且以重新发扬考亭横渠之学为己任,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史的演进不可能有真正的跳跃、断裂或弃绝,后人对前人的批评总是包含着对前人思路的继承与扬弃。事实上,这也是真正的思想对话之可能的条件,阳明对明代理学的巨大影响更是决定了船山并不可能像他自我认定的那样完全弃绝王学的理路。接下来笔者试图通过对船山“经权之辩”的解读去呈现其对阳明心学内在的继承性以及改造,以及这种扬弃与其向经史实学回归的内在关联。
二
船山对“经权之辩”的理解比较典型集中地体现在《读四书大全说》。在对《子罕·第九》“未可与权”一节的辨析中,他首先给出基本的论断,认为“朱子之言权,与程子亦无大差别。其云‘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与程子‘权轻重,使合义’正同。‘曲尽其宜’一‘宜’字,即义也。”接下来反对汉儒“反经合道”之论,他甚至还对《四书大全》里朱子的阐释作出批评:“朱子曲全汉人‘反经合道’之说,则终与权变、权术相乱,而于此章之旨不合。反经合道,就事上说。此由‘共学’、‘适道’进于‘立’、‘权’而言,则就心德学问言之。学问心德,岂容有反经者哉?”表面看来,这还是秉承了程朱的基本说法,以权为裁断的合宜,反对权变、权术式的理解。但仔细玩索,我们会发现,船山对“权”做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的阐释。他把“权”和“经”都分殊为“就事上说”和“学问心德”两种意义,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他是如何具体讨论这两层“经”“权”的内涵的:
于天下之事言经,则未该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经”,经疏而纬密也。于学问心德言经,则“经”字自该一切,如云“君子以经纶”,凡理其绪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则经固有权,非经疏而权密也。[6]六—738
“天下之大经”出自《中庸》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朱子章句注曰:“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船山基本上认同朱子对“经纶”和“大经”的注解,理由如下:其一,船山在其所有四书学著作中并没有对朱子此章注解提出质疑或批判;其二,“君子以经纶”出自《易经·屯卦》,而船山的《周易内传》对“经纶”的阐释——“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绪而合之”,以及上一段引文,都基本上照搬了朱子的训解;其三,船山的《四书训义》对“大经”的解释同于朱子“则人伦为之大经矣”[4]七—230。
船山的意思是说:“就事上说”,“经”指的是诸如“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大德,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它们只是一个形式规定,其内在的丰富性需要人不断地磨练去充实习得,因此单说大经不能够尽乎人情事变之曲折,在具体境域中的实践行动还需要“权”之宜,故曰经疏纬密,这里的“经”偏向抽象与静。就“学问心德”上说,“经”指的是人对境域的理解、分析、判断、权衡的综合性统一,偏向境域中的动。下面船山做了进一步阐发:
以已成之经言之,则经者天下之体也,权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经纶”之“经”言之,则非权不足以经,而经外亦无权也。经外无权,而况可反乎?在治丝曰“经”,在称物曰“权”;其为分析微密,挈持要妙,一也。特经以分厚薄、定长短,权以审轻重,为稍异耳。物之轻重既审,而后吾之厚薄长短得施焉。是又权先而经后矣。[4]六—739
作为“大经”之“经”乃是以体而言,这个意义上的经权是由内发用至外的体用关系(这种体用关系后文还会论述)。而如果在第二层意义上理解经,也就是“经纶”之“经”,船山明确指出,“经”“权”基本等同,都是人在面临事物境遇中理解、分析、权衡与判断的实践行动。其稍异处在于,权是在具体境遇中就物而审其轻重,让物的差异性呈现出来;经是在审度轻重之后获得对物的理解与权衡,从而能够合宜地对物施吾之厚薄长短。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权”“经”结构其实就是笔者在第一节中描述的“境域之权”,船山更加精微细致地对之做出了分析。而所以称其为“学问心德”,是因为这种实践行动最终是为了由外及内地让心达到“从欲不逾矩,而后即心即权,为‘可与权’也”[4]六—741,也就是以成德为目标的学问工夫。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经”的两层意义之间关系为何?第二层意义中的“权”“经”关系又是怎样的?
《孟子·告子上》里孟子、季子和公都子关于“义内”有过一段往复辩驳,这段辩驳也涉及到“权”的问题,《读四书大全说》首先对《四书大全》中潜室陈氏进行了批驳,为了明确船山所指,我们将陈氏和船山的论述都引用如下:
潜室陈氏曰:“礼敬之义在外,如叔父,如弟,如乡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义为外。然敬之所施虽在外,而所以行吾敬处却在内。如当敬叔父时则敬叔父,当敬弟时则敬弟,当敬乡人则敬乡人,所以权其事宜而为之差别者,则此理之权度,未尝不在吾心。”[7]984船山曰:“潜室以‘权度’言‘义内’,亦未尝知义也。若专在权度上见义,则权度者因物之有长短轻重而立,岂非外乎!……若非其人,则但见义由物设,如权度之因物而立,因物者固不由内矣。……庸人无集义之功而不知义,则一向将外物之至,感心以生权度而不得不授之权度者以为义。如贫人本无金谷,必借贷始有,遂以借贷而得谓之富,而不知能治生者之固有其金谷也。……固有义而固知之,则义之在吾心内者,总非外物之可比拟。权度,人为之外物也。……如说权度为义,便不知义。”[4]六—1061
这里船山实际上对陈氏有一个误解,观陈氏上下文意味,其所谓的权度应该是作动词来用,也就是吾心对事宜的权衡,度字读音应该是同“夺”。而船山则以为陈氏之权度是名词,其读音同“肚”,指的是判断事物所依凭的外在固定法则或尺度。名词意义的权度只是一个外在工具,其根源乃是来自于动词意义的权度,也就是心在具体境遇中的判断机能,如果误以前者为根本,而忘记其源头的话,就会不知自家原能治生,只会借贷金谷以为己用;或者如其后文的一个更恰切的比喻,像那些只会用算盘算账的“里胥、牙侩之流”,心中无数,所以离了算盘便茫然无措。这个误解在下面的引文会呈现得更加清楚,不过这个误解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船山认为“经”在根本上不是某种静态的常理准则,而是心体的源始判断机能,即前文所述的“理其绪而分之,比其类而合之”的能力。很显然,船山虽然原样引用了朱子的话,但他们思路有很大差别:朱子对《中庸》的注解根本上是偏向于对静态的“常理”、“定理”的强调,其对“经纶”的解读更多是处于训诂的需要,“经”的动词意义在朱子那里是不受重视的;而船山则追溯“常理”“定理”的根源,把朱子的这个训诂大加发挥,使重心落在心的源始机能上,从而让“经”获得动态意义。但他又不像阳明那样过度地强调心之灵明对定理的决定性支配,而是让静动两层意义的“经”获得循环的生成,这和他“性日生日成”、“理随势变”的基本思路也是吻合的。这种循环生成的思路在船山接下来的两小节论说中有详述,节录如下:
权之度(船山小注:音徒雒切。陈氏所云“权度”,乃如字。)之,须吾心有用权度者在,固亦非外。然权度生于心,而人心之轻轻、重重、长长、短短者,但假权度以熟,而不因权度以生也。圣人到精义入神处,也须有观物之智,取于物为则。权度近智,与义无与。然谓轻重长短茫无定则于吾心,因以权称之、以度量之而义以出,则与于外义之甚者矣。
当初者权度是何处来底?不成是天地间生成一丈尺、一称锤,能号于物曰我可以称物之轻重、量物之长短哉?人心之则,假于物以为正,先王制之,而使愚不肖相承用之,是以有权度。权度者,数也,理也;而为此合理之数者,人心之义也。故朱子谓“义如利斧劈物”,则为权度之所自出,而非权度明矣。……
若说弟重则敬弟、叔父重则敬叔父为权度,此是料量物理,智之用也,且非智之体。不与敬之本体相应。若说权度者物之所取平者也,吾心之至平者谓之权度,则夫平者固无实体,特因无不平而谓之平耳。此但私欲不行边事,未到天理处。以平为义,则义亦有名而无实矣。义者以配四德之利、四时之秋,岂但平而已哉!吾固有之气,载此刚大之理,如利斧相似,严肃武毅,遇著难分别处,一直利用,更无荏苒,此方是义之实体。故以敬以方,以宜以制,而不倚于物。岂但料量以虚公,若衡鉴之无心,而因用以见功者乎![4]六—1061—1064
第一段把权度理解为人在衡量事物长短轻重时所依仗的固定尺度准则,它是人与物相交时用智制订的,究其根本,它还是来自人心中固有的对长短轻重判断权衡的能力,也即是“经纶”之“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依凭自己心体的判断力而不运用外在尺度,而要在假借尺度的运用中,获得对长短轻重的熟习。显然,船山对外在尺度与人心权衡能力这两者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借鉴了阳明对“境域之权”作为心之本体,乃是一切尺度之发源地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没有让这种倾向走向完全的主体性内转,而是保持了一个由内及外、再由外返内的回转。尺度生于人心权衡机能,生成固定之后又可以反过来帮助人获得更好的尺度运用以及情境判断。不难看出,这个结构和船山的其他重要命题如“性日生日成”“能所”“格物致知”的结构是一致的[8]552—606,都是在强调两种维度的不即不离的同时保持住两端的张力,但并不求一个固定现成的“中”,而是在一种动态的解释学循环中不断地以更丰富的方式回到本源。还需要补充的是,船山以“度”的动词意义置换名词意义,具有明显的担忧价值准则坠入现成体系的关怀指向,而非纯粹字句训诂,对此可参看其《周易稗疏·系辞下》对“其出入以度外内以知惧”的发挥,此不详引。
第二段进一步说明了尺度准则的内外问题。尺度准则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天理的具体实现形式,按照船山的天人之辨,“天之天”必须交由“人之天”才能获得展开[9]564—561,所以尺度准则不可能是天地间自然生成,号令万物莫敢不从,而是“人心之则,假于物以为正”,也就是人心中内在的尺度凭借事物获得的外化。不过,这种外在实现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凭一己之灵明为世界立法,而只有代表了天人最高统一性的先王才有此权能。相应地,这种尺度准则一旦获得外化实现,后人,尤其是一般人就必须承袭之。在这里,尺度和准则在前述的结构之上又被赋予了阳明那里所缺失的历史维度。先王之立法之所以具有不可变乱性,不仅仅是因为其仁智高于常人,代表着最广阔丰富的视域,还因为民族的历史性世界从其开端起就是由先王之礼规定的,后人可以不断地回溯源头获得日新之丰富,也可以通过某些决断打破既有之陈规,但历史性世界永远构成着个体一切思想、判断和实践的先决条件。同时,数、理这些往往被理解为外在定则的东西,在船山这里也要被置于前述的返回循环结构中重新考虑。如果说是“人心之义”凭借于外在事物构造了“合理之数”,那么这种非纯客观的数、理,是否会随着人心世道之变化而变化呢?船山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在船山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得特别明确,前人之述备矣,此不赘述。这里只需注意的是,数、理既不是纯客观意义上的永恒普遍,也不能等同于康德主观的先验普遍形式。
第三段更进一步地分析一般意义上人依凭固定尺度对事物的判断——“日常之权”与更加根本的人心权衡能力,即“境域之权”的关系。在他看来,在情境中的权衡判断,如果只是一种轻重长短的比较,譬如敬弟和敬叔父的比较,这就和“义”没有关系,而仅仅是“智”的发用,因为它依仗的是一个外在的固定标准进行近似于纯工具性的计算推理,而和这个境域中原本最重要根本的问题脱离了关联。因为敬弟和敬叔父这两者的比较不能脱离具体境遇背后的源头,脱离了本心的诚敬,外在的判断权衡就会沦落为对礼则的纯粹工具性计算与应用。这样的“日常之权”即便是没有掺杂私欲的考量,如文中所谓的“平”,其本心也是昏然的状态,“懵懵懂懂去做”。
其实阳明强调的“致良知”也包含这个意义,只不过船山出于对明亡的痛惜,对王学一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所以这里可以看出他吸收了王学的思想而不自觉,而且更多地是在王门后学的流弊意义上来批判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的批判也不能算是完全的误解。
三
船山继承了阳明以心体为“经”的思路,认为“经”更根本的意义是动词性的,是义的发用,即我们所说的“境域之权”。人心与外物交接后“义”会获得外化,生成尺度准则,先王先圣给出了这种尺度准则的最高形式,即名词意义的“经”,后人通过对它们的熟习实践,会获得对自身学问心德的提升,但前提是始终让熟习实践落在心体上,即体即用,而不是如“里胥、牙侩之流”的“义外”状态。如果说阳明重新发现了经权统一性的话,那么船山所做的便是将这个结构奠基于人与历史的诠释学循环,使得这种统一性获得真正历史性的根基。而且船山通过对“经”这个概念层次的辨析,使人看到“经”动名双重意义的统一性,可谓有理有据。相较起来,阳明良知之学未免过于追求浑融而有空疏师心之嫌。
最后本文再对“经”的动词意义略作阐发。“理其绪而分之”本质上来说是人赋予世界秩序的行动,是人最原初意义上的实践行动。世界秩序不是固定现成的客观法则,而是存在通过人不断生成的意义整体。这个意义整体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它先于个人的生存,并且决定着个人的理解结构。人被抛入天地之间,人的在世生存必定是基于对天道的理解。人对天道的理解不是凭空产生的,从生成的逻辑源头来说,它源自人心之灵明,从历史源头来说,它源自民族历史交托给个人的礼物。个人不是无世界无历史的单子个体,他依靠这份礼物成为民族历史整体中的一环,并通过“理其绪而分之”,“比其类而合之”的方式,接受承担这份礼物并将其传承下去。如果说“经”的动词意义如上分析,乃是人主动地呼应天命,将自身投入到历史性世界中去,努力让天道秩序获得显明,那么“经”的名词意义便有如下两重:人伦五常,民族经典[3]。它们分别是“经”之行动在历史中的两种结晶:德目与流传物。既为结晶,则必有“常”的特性,但不可忽略的是,这两种结晶都要求着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对其作出理解、诠释、践履与丰富,这就又回到了“经”的动词意义。“经”的双重意义便如此地统一在了一起。
可以看到,经历了阳明心学之后儒学向程朱理学乃至先秦儒家的回归,“经”“权”获得了更加本源性的理解。程朱所谓的“常”“经”,即“日常之权”和“权变”的“困境之权”并不是对立,它们的统一性植根于心体的“境域之权”。但“境域之权”,也即是作为原初实践行动的“经”不能仅仅在个体意义上理解,个体学问心德的先决条件是“道”在民族历史性世界中的自我展开与结晶,这才是“经”更加本源的意义。在此逻辑中,历史意识与经史实学的回归成了船山乃至整个明末清初思想的自然方向。
[1]田丰.从“春秋决狱”到“四书升格”[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5).
[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田丰.阳明“良知说”对儒家“经权之辩”的发展与反思[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10).
[4]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湾学生书局,1993(第二版).
[5]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62.
[6]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8.
[7]胡广纂修.四书大全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8]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曾昭旭.王船山哲学[M].台北:台北远景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