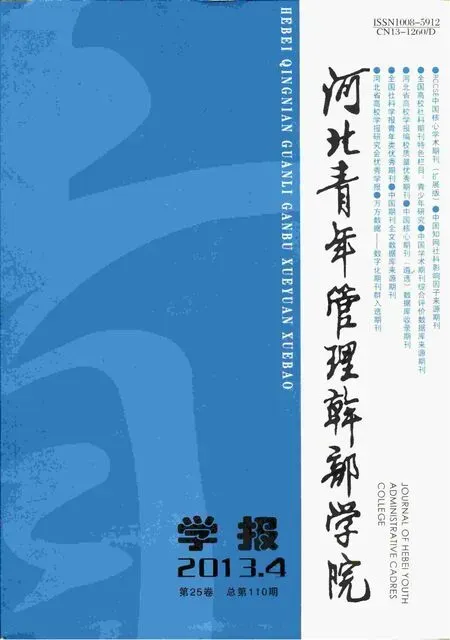《大进军》中的荒诞思想和黑色幽默
蔡玉侠 赵英俊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多克托罗的小说《大进军》自从2005年出版以来,逐渐受到了国内评论界的关注,从虚构与史实相结合的新历史主义特点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人性的彰显,再到小说对美国清教徒主义传统的扬弃等方面,都陆续有学者作了阐释。本文则试图对小说中的荒诞思想及其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进行解读,希望能借此揭示多克托罗关于战争的态度。
一
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荒诞”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bsur dus(ab-+sur dus),指一种不合理、不合逻辑的、不和谐的状况。到了20世纪,“荒诞”成为了存在主义的一个关键词。萨特和加缪等存在主义思想家认为人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内在的真理、价值和意义,人类徒劳的追寻目的和意义,但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虚无走向另一个虚无。这种令人痛苦的生存状态就是荒诞。加缪则这样来定义荒诞:“世界本身不可理喻,我们所能说的,仅此而已。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1]90他还专门用西西弗神话来阐释荒诞这一概念: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巨神西西弗冒犯了天规,被贬入地狱罚做苦役。他将一块巨石由山脚下往山上推,每当快要推到山顶时,巨石便骨碌骨碌滚下山来,他又得重新往山上推。如此周而复始,永无解脱。这种人的愿望与世界的冷漠之间的对立状态就构成了荒诞。
在《大进军》中,作家用南方士兵阿里和威尔、北方伤兵阿尔比恩·西姆斯和英国战地记者休·普莱斯这四个人物集中展示了战争的疯狂和世界的荒诞,从而引发读者对所谓“理性世界”和“正义战争”的反思。
阿里和威尔是两个穷苦出身的南方白人士兵。在这场大进军的征途中,阿里和威尔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为了活命。起初,为了跟着军队混口饭吃,他们参加了南方邦联的军队,结果一个因站岗时打盹,一个因开小差,都被军法判了死刑。后来由于南方兵源严重不足,他们被免去了死刑,却被推上了战场。然而对他们来说,战场上的血腥跟让行刑队杀了相比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他们被吓坏了,为了活命,他们换上了北军的衣服,开了小差。他们混进北军的队伍,本想等着大部队过去后在后勤部队里更好混日子,结果却稀里糊涂的睡过了头,被南军当成北方人抓了俘虏,又再次签了效力南军的协议,被派去看押北方的战俘。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战俘们在雨地里睡觉,病饿交加,气息奄奄的惨状,而他们的待遇也并不比这些战俘好到哪去。为了活命,他们在南方军队转移战俘时再次开了小差。他们再次换上了北军的衣服,假扮战俘进了战地医院。在北军占领萨凡纳之后的狂欢中,他们因贪恋声色,再次耽误了行军。为了追赶大部队,威尔在和人抢夺一头母马时中弹,最后失血过多而死。威尔死后,阿里乔装成摄影师,计划在给谢尔曼将军拍照时实施刺杀。但是在他即将下手的刹那计划破灭了,他最终被联邦军队执行了死刑。
加缪曾说,“在人的努力这点上讲,人是面对非理性的东西的。他在自身中体验到了对幸福和理性的欲望。荒诞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2]279-280在大进军途中,阿里和威尔两人千方百计想生存下来。他们一直希望能获得上帝的指引,想弄清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他们的安排。起初,他们以为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指引。“咱们活着全靠咱们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就从一方转到另一方的法子,这表明咱们已经有了上天赐给咱们的某些东西。我感觉到了上天的这种意愿,很好,我很遗憾你没有感觉到。”[3]54然而,威尔却为了争夺一匹母马,稀里糊涂的以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最终也没有盼来上帝的指引。威尔死后,阿里认为上帝交给他的伟大任务就是去刺杀谢尔曼将军。但是这个所谓的“上帝交给的伟大计划”在他即将下手的那一刻也破灭了,他最终被联邦军队执行了死刑。就像是《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一直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戈多一样,阿里和威尔至死也没能找出上帝对他们的伟大安排,即他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这是对上帝安排的极大讽刺,更是对“理性世界”的极大讽刺。在存活的愿望与死去的现实之间,找寻上帝指引的期盼与找寻未果的结局之间构成了两对反讽,而其中的张力恰恰说明了战争的残酷和世界的荒诞。
北方士兵阿尔比恩·西姆斯的经历也是对这个荒诞、疯狂世界的另一个批判。在哥伦比亚沦陷后的城市大火中,一颗钉子嵌入了阿尔比恩·西姆斯的头颅。他因而失去了记忆,忘记了过去,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你刚才叫我什么?
阿尔比恩。那是你的名字。
那是我的名字?
是的。
我的名字是什么?
阿尔比恩·西姆斯。你已经忘了吗?
是的。我已经忘了。我已经忘了什么?
你昨天知道你的名字。
这是昨天吗?
不是。
我已经忘掉了昨天。我的头受伤了。这个伤是什么伤?
你的头。你刚才说你的头受伤了。
是那么回事。我记不住了。我说一个词可我记不住它。我说我记不住什么了?
一个词。
是的。
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头受了伤。总是现在①原译文把“It’s al ways now.”译成“现在总是这样”。作者对此做了改动,译为“总是现在”。。那就是受伤的东西。你刚才说我是谁?阿尔比恩·西姆斯。
不,我不记得了。没有任何记忆。总是现在。
你在哭吗?
是的。
因为总是现在。刚才我说了什么?
总是现在。
是的。
阿尔比恩泪流满面,握着面前的把手,点着头。然后,他自己前前后后的摇摆着。总是现在,他说道。总是现在[3]232。
在有关西姆斯遭遇的这部分当中,作家没有采用小说前面所使用的有限视角下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也没有使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让当事人直抒胸臆,而是用类似于《等待戈多》中的一种机械的、毫无意义的、简单重复的对话形式再现出来,用引人发笑的对话代替了直白的陈述,以荒诞的形式来反映人物的荒诞感受。在这场冷漠的战争中,深陷其中的人们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时间停滞在了现在、此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人拼命的想弄清自己是谁,想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场战争中的意义。但是对于这个像机器一样冷漠的战争来说,人只是它随意操纵的一个工具。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说,“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的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诞感。”[1]79最终,西姆斯忍受不了这种被剥夺了意义和希望的生活,把钉子戳进头颅,以自杀作为对这个荒诞世界和这场残酷战争的无声控诉。
除了从亲历战争的南北双方士兵的角度对世界的荒诞和战争的疯狂进行揭示外,英国战地记者休·普赖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对这场战争的体验则让读者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了战争的荒诞。“什么战争打起来能比一场国内战争更为痛苦,具有更大的激情,更为惨烈呢?没有一场国家间的战争能够与它相比。北方和南方的将军们彼此相知——他们曾经一起在西点军校学习,或者曾经在墨西哥战争中肩并肩的服役……他们的战争是如此非个人化的杀戮性的战争,它使得以前进行的任何战争都变得优雅奇妙。”[3]182休·普赖斯把国内战争和国家间的战争相对比,把这场现代战争和历史上的战争相对比,指出这场战争同胞相残的本质及其史无前例的惨烈程度。骨肉相残的本质与惨烈超前的程度构成了一种反讽,也使得这场战争的荒谬异常突出。而当他坐在树上俯瞰下面的战斗时,他对于现代世界的人们所谓的“正义战争”和“理性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既不是作为冒险的战争,也不是为了严肃事业的战争,这是最纯粹的战争,一种无心的巨大怒火与任何事业、理想或道德原则毫无关系。就好像上帝已经作出了判决,他把这些没头脑军队的无聊纷争作为对人类傲慢自大的回答。”[3]251
在关于战争的疯狂和缺乏理性上,阿里和休·普赖斯具有完全一致的认识:“您能在这雨中听见我说的话吗,上帝?我正在和这个小伙子站在这儿,他认为在战争中的军队是个有理性的东西。他认为一个军人不仅仅是穿着军装的东西。他认为我们过着一种理性的生活,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而您和我都知道,那根本不是您为我们这些罪人设计的。”[3]54战争就是赤裸裸的杀戮。所有“战争是浪漫的冒险”,是“严肃崇高的事业”的说法都在这种赤裸裸的杀戮前消失殆尽。战争是残酷的,是疯狂的和非理性的,所谓战争的意义不过是这个失去理性的世界人为强加上去的一些借口而已。战争是这个世界荒诞性的终极表现形式。
二
为了表现世界的荒诞和战争的缺乏理性,小说中多处使用了黑色幽默的写作手法。黑色幽默是后现代荒诞派作家经常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他们将“或邪恶的,或天真的,或愚蠢可笑的人物置于一个怪诞如梦魇般的世界中,让他们上演一出像尤奈斯库所说的‘具有悲剧性质的闹剧’,其中的事件通常都是既滑稽,又恐怖,又怪诞”[4]2。
在《大进军》中,作家就多处采用了黑色幽默这种滑稽之中现荒诞的手法。例如在描述南方战俘营中战俘们的非人惨状时,作家就采用了一种语气轻松的幽默。“犯人们没有小屋为他们遮风避雨,他们从地上睡觉的水淋淋的小坑中站起身来。随着冷冰冰的太阳投下的最初的光线,所有人都起来了,在地上呆着,蜷着身子打哆嗦,或者像跳舞一样跳来跳去地活动着取暖。”[3]55战俘们“跳来跳去的取暖”被形容成“像跳舞一样”,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戛然而止,猛然意识到他们处境的悲惨,笑声中又隐隐感到心酸。
在处理阿里和威尔这两个小丑似的人物时,作家也多处采取了黑色幽默的手法。例如他们为了逃避战俘营中非人的待遇,打算在押运战俘转移时开小差。“阿里身后跟着威尔,向后面走去,好像要去为那些正在装人的车厢加强警卫。威尔注意到阿里看上去多么认真,他步枪在手,眼睛警觉地注意着每一个战俘逃跑的企图。就带着这样的神情,他们来到了最后一节车厢,在这时,当附近的军官下了马,正在商量面前的地图的时候,阿里和威尔偷偷绕过最后一节车厢,隐蔽到车站后面。”[3]55-56战俘们瘦骨伶仃,“他们当中很少有几个还有精神和力气问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在米伦的战俘营”[3]55,有些甚至虚弱的“再也不能走路了,要由他们的伙伴背着上车”[3]55,阿里和威尔却还做出一副煞有介事的认真警戒姿态,二者构成了一对怪诞的反讽,成功地实现了同一个场景中悲惨和滑稽的并存,战争的荒诞就通过这样一种心酸的幽默彰显了出来。紧接着,为了混进北方军队中,阿里准备装扮成南方战俘营中的北方士兵。
“阿里扒下身上湿淋淋的邦联军的军服,把它打了一个结,像个球状,扔进厕坑。他好像给威尔做示范似的,赤裸着身子在泥水里滚了滚,并且把成把的泥水倒到自己的头发里。然后他自己穿上一件他从一具尸体上扒下来的破衣裳。然后他跳来跳去,一边绕圈跑着一边高兴地吆喝、喊叫着。
你这是干什么?威尔问道。
我冷啊,你这个该死的傻瓜!阿里喊道。”[3]P55
阿里和威尔这两个小丑似的人物为了生存,不顾严寒,在泥水里打滚,又因为冷的受不了而上蹿下跳,大呼小叫的场景不禁让人哈哈大笑。他们为了活命,想出种种可笑的办法开溜却最终难逃一死的命运也让人在笑声中醒悟战争的残酷无情。
在小说《大进军》中,多克托罗创作了大批的人物,其中包括像阿里和威尔、休·普莱斯和阿尔比恩·西姆斯等一批小人物。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说,战争就是赤裸裸的杀戮,所谓的“正义”和“崇高”都不过是人们为战争找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战争无视人的一切诉求,完全漠视生命和践踏生命。人的一切努力和理性诉求在战争面前都变得徒劳、可笑。世界是荒诞的,战争是疯狂的,这就是多克托罗借这些小人物之口对这场战争所做的反思。
在美国历史上,南北双方对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大进军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南北双方都竭力标榜自己为战争的正义之师。在大多数的北方人看来,大进军是一场旨在防止国家分裂,维护联邦统一,以及把黑奴从奴隶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而在南方,这场大进军则是北方对南方的野蛮入侵。它践踏南方土地,涂炭南方生灵,尤其是摧毁了南方古老的文明与传统。因此,对于南方而言,大进军则是南方人民保卫家园,捍卫南方传统的正义之战。但在小说《大进军》中,多克托罗通过刻画各色人物,尤其是像阿里和威尔、休·普莱斯和阿尔比恩·西姆斯等一批小人物,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诞。对于这些像棋子一样任人摆布的普通人来说,战争就是赤裸裸的杀戮,所谓的“正义”和“崇高”都不过是权力阶级为战争找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战争无视人的一切诉求,完全漠视生命和践踏生命。人的一切努力和理性诉求在战争面前都变得徒劳、可笑。世界是荒诞的,战争是疯狂的,这是多克托罗借这些小人物之口对这场战争所做的反思之一。
[1] [法]阿尔贝特·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I[M].丁世中,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 [法]阿尔贝特·加缪.荒诞的墙 [M]//柳鸣九,译.柳鸣九.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3] [美]E.L.多克托罗.大进军[M].邹海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 [美]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