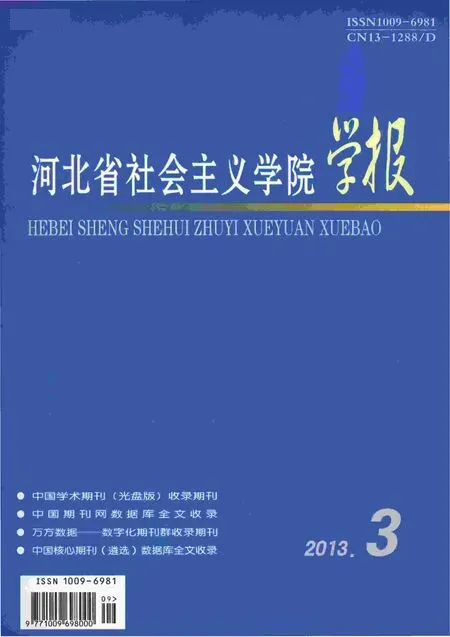意象、意境、境界:艺术审美的三个层次——李锦云《表演心理教程》读后
艾尚连 段其云
(1.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2.精英集团品牌推广部,河北石家庄050035)
由河北传媒学院院长李锦云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表演心理教程》(以下简称《教程》)[1],是一部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关表演艺术教育与教学方面的力作。它不仅涉及表演艺术及心理学的诸多内容,而且处处闪耀着学术创新的真知灼见。
一
《教程》有关艺术审美层次说的观点及其论述,是该书将传统的美学理论范畴与审美实践相结合,创新性解读审美心理过程与特点的一个范例。
《教程》以舞蹈审美为中心,明确提出舞蹈审美可分为三个层次:观众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总是从观看演员的技艺、技巧乃至形体相貌开始,“这可以说开始进人舞蹈审美的第一个层次”;然后“是感受到了舞蹈的意境,这可以说是进入了舞蹈审美的第二个层次”;“最后,观众也跟着浮想联翩,心驰神往,被引入一个美妙的境界,这是进入了舞蹈审美的第三个层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说的第二、第三个层次还分别蕴含了“意境”、“境界”的美学范畴。第一个层次表面看似无蕴含,但实际上是通过讲演员的演艺技巧等隐含了舞蹈形象的塑造及其意象的营构问题。这样,舞蹈审美的三层次,实际对应了意象、意境和境界三个美学范畴,体现了舞蹈艺术审美层深推进和次递提升的认知过程。
二
观点的提出,当然要有学理的支持。对此,《教程》不落俗套,而是独出机杼地援引了佛教大德青原惟信的一段参禅悟道的话作为学理依据,从而将审美三层次说与佛教禅宗的美学思想打通,既见理据,又显情趣,凭空增添了《教程》的信美度和耐读性。
青原禅师的话是这样说的:“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几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那么,如何理解这段充满禅意的话并将其与舞蹈观赏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呢?《教程》的回答是:“这段感悟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审美的几个阶段,我们把它引用到对舞蹈的审美里。”也就是说,这段话既适用于舞蹈审美,也适用于其他艺术样式的审美,带有普遍性的意义。所谓“指出了人们审美的几个阶段”,其实正契合了以上提出的审美三层次说。
第一个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山和水本来是大自然的造化之物,属客观存在的物象,尽管也有山清水秀之美,终因缺失审美情感难入艺术领域。但青原的这句话,劈头便着一“见”字:“见”山“见”水。则此山此水,便经人的带有倾向的选择,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如此一来,它们便不再纯属于自然之物了。正如歌德所说:“艺术家一旦把握住一个自然对象,那么自然对象就不再属于自然了。艺术家在把握住对象的那一顷刻中就是在创造对象,因为他从对象中取得了具有意蕴、显出特征、引人入胜的东西,使对象具有了更多的美的价值。”[2]“创造对象”,即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它来自“自然对象”,而又高出“自然对象”,因为它贯注了人的情感意绪。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在李白眼里“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在辛弃疾眼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诗人通过同山的情感交流,心灵对话,描摹出情满青山的文学艺术形象。这是诗人摄取客观物象入诗,融入主观情感的创造,具有高于自然的形而上的品格。但它又是来自自然,是直观感相的描写,可视可见。如《庄子·养生主》所写的庖丁,起初操刀,“所见无非牛者”,尚处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阶段。这应属审美的第一个层次——意象美。
第二个阶段:“几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这是说人在参禅后,“亲见知识”,静息虑念,心注一境,则佛性禅意,笼络百态,山水发生了变异,草木也带上了佛性,自然物象已超越了视听感官可以感知的形象,进入主观的精神层面,实现了物我贯通、情景交融,以及“万事造化,中得心源”的合而为一的化境。这应当是意境形成的机制。如同宗白华先生所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物,代山川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3]于此可见,意境比之意象,内涵更加宏阔高远,更加富有生机活力,更加引人联想不断,思达天倪。关于二者的关系,袁行霈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漂浮天上的云。”[4]水珠一旦聚而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站在云际俯瞰,“一览众山小”,“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至于那聚合成云的水珠,更是渺然若失了。如同庖丁解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是审美的第二个层次——意境美。
第三个阶段:“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里的“休歇”二字,是指禅宗大乘顿悟的前提条件。据禅宗史记载,怀海禅师曾对弟子们说:“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如此则“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也”。[5]顿悟登佛,获得大觉悟大智慧,个体精神获得自由“处处自在”,进入与宇宙自然合而为一、和谐相处、通达无碍的境界。而禅宗的这种精神境界,是以对大自然的悟解佛性真谛获得的。如云“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山水成为佛性禅意的载体,进入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而今所见山水不再是具体的一山一水,而是“悟出来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是精神化了的一种整体感受,是对自然的超越。也如庖丁解牛,“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牛虽然还是牛,但已不在庖丁的视听感官之内,而进入其心神感触、会合境界中了。这是审美的第三个层次——境界美。
宗白华先生谈到“禅境的表现”时指出:“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6]宗先生所说的艺术内涵“可以有三个层次”,与我们经对禅师青原惟信的话分析后所得出的审美三层次说,是神理相同的。《教程》以此作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可谓理证俱坚,信而有征。
三
以上我们通过青原禅师的妙悟,阐释了审美三层次说的内涵。由此不难发现,禅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活动是一脉相通的。审美三层次说既合禅意,也反映了人们审美的一般规律。对舞蹈来说,如《教程》所说:“舞蹈表演乃是内心诗的呈现艺术。”或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典型意义上看,舞蹈表演均立体地呈现出审美的三个层次。
舞蹈审美的第一个层次:意象美。《教程》指出了这样一个常见的现象,即观众在观赏舞蹈时,往往首先注意的是演员的技艺、技巧乃至形体相貌等。其实,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隐藏着艺术形象的塑造问题。因为“舞蹈是和技术相结合的艺术”,它通过人体的动作这一特殊的艺术手段和丰富细腻的舞蹈语言来反映生活,表达情感,创造出生动、具体、鲜明的舞蹈形象,让人觉得真实可感,接受认可。同时,舞蹈表演又具有情感再现的特征,演员必须将一定的思想情感贯注到形象之中,使其深蕴主观情感和意绪,并最终把这种精神、情感、思想传递给观众,这就是所谓的艺术感染力量。这种感染力量正契合了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激起了观众情感上的浪花,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观众的美感体验。从舞蹈形象的塑造、情感再现到最终与观众产生审美情感的共鸣,使舞蹈审美呈现出意象美的层次。
舞蹈审美的第二个层次:意境美。《教程》讲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观众开始密切注视舞台上舞蹈艺术家的各种动作发出的信息和表达的感情,从反复出现、不断更替、相互连接的各种形态中看到人物、事件、情感的发展和变化,感受到了舞蹈的意境。这实际是在生动形象地讲解舞蹈意境的生成和呈现问题。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各种动作,发出信息,传达感情,从而塑造出舞蹈形象。这些形象“反复出现、不断更替、相互连接”,在进行合目的性的排列、组合与交融,形成意象群,观众通过联想甚或幻想,从中看到了心仪的人物、动人的故事和饱满的情感,将舞蹈审美推向第二个层次——意境美。可见意境是由意象融合而成,它深融意象而超越了意象之和。
舞蹈审美的第三个层次:境界美。王国维论诗词,首倡境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7]这对诗词评论欣赏会一新耳目,开一新境。但艺术的最高境界,内涵要丰富、宏阔得多。《教程》在揭示舞蹈艺术境界的内涵时,就生动地指出:“最后随着舞蹈的情绪或情节层层展开、步步深入,观众也跟着浮想联翩,心驰神往,被引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最终观众的理性分析与感性体验结合,对舞蹈进行总体观照。领悟到形体之中的神韵,解得个中真味,这是进入舞蹈审美的第三个层次。”这段话开头由浅入深,娓娓道来,讲观众被舞蹈演出“引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至于如何美妙,就此打住,以给观众留有想像的余地。但接下来一句,却有奇峰突起之感,说“最终观众的理性分析与感性体验结合,对舞蹈进行总体的观照”,这就颇具哲理的高度和色彩了。怎样进行总体关照?按照儒家“志于道,游于艺”的观点,道是艺的中枢,艺是道的具象,艺无论怎样“超以象外”,变化万端,最终都要“得其环中”,并不离道而去。“这是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艺’以深度和灵魂”。[8]这段话从“道”的宏观与“艺”的微观讲透了二者的血肉联系。“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人皆有感性体验,这是进行哲学理性分析的基础。《教程》还深刻地指出:舞蹈是人的艺术,舞蹈形象便是一种人的体质力量的舞蹈化,往往具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生命力量。中国哲学是就这“生命本身”与“生命力量”体悟道的节奏,而道又是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如此,舞蹈艺术则可以直达宇宙和心灵的深境。通过这一总体观照,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悟到形体之中的神韵,解得个中真味。这里用“神韵”和“真味”来形容舞蹈的曼妙之姿与精气神,可谓曲尽其妙,抓住了艺术审美的真正义谛。古人讲“立象以尽意”,形具而神生,无神韵则无生命可言,哪里又有气韵生动之艺术的诞生。至于讲到“真味”,更有“余味曲包”之感。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舞蹈要有“真味”,就要达到精诚之至,做到内在真诚,神动于外。“贵真”,是对包括舞蹈在内的所有艺术的最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上面提到的舞蹈可以创造引人入胜的美妙境界。这境界到底如何?《教程》为我们画出了一幅动人的图景:“演员创造出角色,还要赋予角色以灵魂,让角色的灵魂直接进入观众的内心,使观众得到心灵的涤荡,精神的升华,获得审美超越阶段的愉悦,实现类似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的境界。”这是人之审美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仿佛一下进入天堂,实现了奇迹,尽善尽美,岂不令人叹为观止”。
[1]李锦云主编.表演心理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李洋.写生作品化[J].中国国家美术.2001,(1).
[3][6][8]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68 -77.
[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8.
[5]《五灯会元》(卷三)苏渊雷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133 -134.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