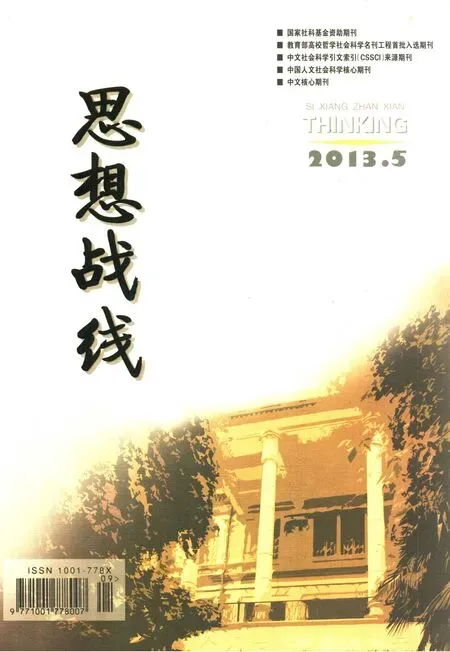乡村建设与文化转型:欧洲人类学“本土化”的借鉴与启示
刘 珩
一、导 言
欧洲人类学的本土化是指人类学向着自身的起源地——欧洲社会,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归”,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转向和实践。乡村建设与“本土化”的西方人类学初看起来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话题,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学术群体、不同的学术旨趣和知识范式,并且也分别针对特定的社会及现实问题。但是,二者在特定的区域甚至“边缘地带”①中国乡村建设学派以“村落”为其研究的区域,以村治作为其研究的路径和主体,他们所主张的“农村主位”的研究范式,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界多少有点“边缘”。贺雪峰将其表述为“在学术知识生产和行政话语支配的应用性政策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一块被人为遗漏的学术空间”。参见吴 毅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判》,《开放时代》2005 年第4 期。而以欧洲人类学为代表的“本土”学派,最初也以南欧的农村或者山地的半游牧族群为其研究的区域,相对于以西方为本位的其他社会科学,也处于边缘的地位。所进行的研究,以及获得的地方性的民族志经验,已经生成了一套显著而且有效的社会文化批评范式和习语。这种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语境中所获得的地方性民族志经验,不但值得珍视,而且也能引起反思和共鸣,同时也构成将二者并置 (juxtaposition)起来加以比较的框架。
一般而言,欧洲人类学的本土化,是为了从这一学科独特的视角,全面反思既有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官僚体制等概念,辨析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试图在欧洲边缘重建“多元”和“异质”的后民族—国家的人类学知识范式。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与建构普遍性的理论范式和比较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是这些地区的人类学亚学科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可能是蓬勃发展的动力。以农村为研究路径和主体的中国乡村建设学派,在这一意义上与欧洲人类学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中国乡村学派主张的“着意于问题透视以理解社会”的“问题主位”的观点,②吴 毅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判》,《开放时代》2005 年第4 期。对于我们理解欧洲人类学最初介入自身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是有所助益的。可以说,人类学重返欧洲,是带着一种“问题主位”,而非“学术关怀”意识的,它的切入点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为何一个在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层面都被界定为整体的欧洲社会,仍然会有所谓“冷欧洲”、“热欧洲”,抑或“快欧洲”、“慢欧洲”的分别?③Talal Asad,“Provocations of European Ethn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9,No.4,1997.人类最基本的血缘、亲属、地缘等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否已经被工业文明、公民社会扫荡干净?人的自我意识、情感、身份在看似日益规范的各种制度和结构之内又是如何表述、展演或投射的?这其中又包括什么样的修辞策略和实践方式?具有这种问题主位意识的人类学,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就是一门“参与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而非“应用的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①刘 珩:《民族志、小说、社会诗学: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 年第2 期。
其次,中国乡村建设学派“农村本位”、“中国本位”的主张其实含有较为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一点正如费孝通所言,越是知道自己传统、熟悉自身认知的经验来源的群体,越发能够对其文化产生“自知之明”的文化自觉意识,越是能够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方向。②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1 期。欧洲人类学“本土化”之后所产生的“地方性民族志经验”,多少也具有“文化自觉意识”。人类学回到其起源地,开始关注自身社会和文化,与其将这一回归看作是对现代性的研究,倒不如将其看作是一次带有“文化自觉”意味的、向自身传统的追溯,以便回答西方文化到底是什么?以乡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同样应该珍惜和重视自身的传统,以一种更加注重人的感受和实践方式的文化自觉意识,来回答自身的现代性问题。
第三,欧洲人类学同中国乡村建设学派一样,同样面临如何“解构现代性”的问题。温铁军在强调“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的时候,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在中国是无法复制的,西方的现代化对中国是伪问题。③温铁军:《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开放时代》2005 年第6 期。欧洲人类学同样致力于解构西方的现代性,试图在学科内部对自身的殖民主义经历加以反思与批判;试图考察历经工业化革命、城市化进程等多种形式的现代社会转型之后的欧洲,为何某些传统的“乡土观念”连同社会组织被保留下来,依然在指导欧洲村民的行为和言语实践方式;试图在所谓的西方官僚机制的理性中,去寻找其自身与传统的血缘宗亲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最终如福柯一样解构人的现代性和主体性。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乡村建设学派所批判的“某些照搬西方之词来对应中国之物”的学术研究,其实是对欧洲人类学“解构现代性”的学术旨趣缺乏了解的反映。赵旭东对此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简单搬用西方的社会和文化理论来关照自身的文化语境,在理论预设上无疑存在着一个西方认识论上的陷阱,只有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才能真正具有一种文化的自觉意识,并发出必要的文化自信出来。④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载《多样性:人文与生态——第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文集》(未出版),新疆阿拉尔,2012 年,第55 页。西方人类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社会和文化陷阱,如果我们对这一学术路向缺乏认识,可能会掉入这些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所以这种认识,从某种程度而言,类似于人类学的“观他而知我”,西方的现代性被解构之后,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与传统千丝万缕的社会文化形态,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建构出以诸如‘封建社会’和‘市民社会’之类的传统和现代表述来呈现的‘中国经验’”。⑤吴 毅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判》,《开放时代》2005 年第4 期。同样,在欧洲人类学的研究中,西方并不等同于现代。
由此,二者对现代性的解构以及有关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考察与阐释,将我们引入了“文化转型”这一未来理论生成的场域中。笔者以为,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再造的问题。这与中国乡村建设学派从“村治”转向“乡村治理”,从而“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⑥吴 毅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判》,《开放时代》2005 年第4 期。的学术主张是一致的。并且,部分学者以“地方性知识和中国乡土社会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的主张”,⑦吴 毅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判》,《开放时代》2005 年第4 期。同样是对传统的再造这一问题的关切和重视,尽管以“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为切入点的研究路径还值得商榷。之所以将乡村建设学派“农村主位”、 “问题主位”的学术主张作为考察文化转型的重要参照系,还基于如下两点考虑:第一,国内文化哲学派有关文化转型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论调中,包含着过于浓重的进化论色彩,他们所笼统谈论的价值体系的递嬗与建构,只停留在模糊的“意识形态”层面,而对于生活在这些价值体系中的群体或个体的社会、话语实践以及能动性(agency)基本上视而不见,对于中国以农村为主位的文化整体性变迁的考察而言,这些“形而上”⑧比如,吴理财认为,要研究农村的“真问题”就应该反对将中国农村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或“形而上”)进行讨论。参见吴理财《中国农村研究:主体意识与具体进路》,《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的讨论几乎没有可操作、可比较、可经验的价值;第二,对于以社会转型或变迁的研究为其合法性问题意识基础的西方社会学而言,他们过于宏观的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具体而微的中国村落研究,是一个需要仔细厘清的问题。此外,中国村落的组织形式能否对应西方“社会”这一概念,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所以,以一种农村本位的问题意识出发,有必要以文化转型代替社会转型,使之成为考察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概念。这种更为复杂、更为具体并且掺杂了太多人的情感、身份、自我意识等因素的文化形态或者“社会配置”(social dispositions)①布迪厄认为,“我们将个人或群体的能动性或实践情景考虑在内,社会制度或者文化模式就变成了一个包括某种习惯性状态、某种性情倾向、某种趋势、某种习性或是某种爱好等许多方面在内的一种‘配置’,即‘惯习’”。参见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82.的转变,对于习惯于微观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而言,自然拥有相应的话语权。
当然,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对于中国的乡村建设和文化转型的研究,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欧洲人类学为例,人类学家对南欧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与邻近城镇的人员、资金、观念和货物的流通、家庭和亲属体系、残存的庇护制度、社会分层以及“荣誉与耻辱”并存的地中海式的思维方式,都进行了历时性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式的考察和论述,这对于我们理解也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的状况有所助益,并且应该可以建立起比较的模式和体系。
其次,欧洲人类学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以来,有过一段相当曲折的经历,至今仍然不断地经受着学科内外的反思与批判。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南欧地区的人类学的著作,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间或提到居住在城镇中的商人和地主,偶尔会论及农民与城市之关系,但总也少得可怜。②John Davis,People of the Mediterranean: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6,p.19.这显然是批判部分学者的研究,缺乏将不同的社区、农村与城镇、农民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加以比较的意识和体系。此外,乡村社区与民族—国家之间联系的研究缺乏也饱受质疑。不过,批判较多的,还是集中在农村社区调查缺乏历史的延续性,也就是缺乏历史的关照或语境。不论上述的批判在中国的乡村建设学派的研究中是否同样存在,同样都值得我们的警醒和关注。
此外,欧洲人类学研究所经历的两个历史时期,以及正在发生的转向,对于中国乡村未来的研究面向和可能性,也颇有借鉴的意义。欧洲人类学最初在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框架内对南欧地区的农民社会 (peasant society)进行研究,传统社会以及农民的价值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欧洲人类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地方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等方面。行为理论和符号学理论作为与功能主义相对的研究范式,为人类学家考察农村社区建立在人际交往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历程(social process)开辟了新的路径。社会展演、社会戏剧以及社会诗学(social poetics)等象征体系的理论范式被用来分析社会参与者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方式和策略,并进而解读隐藏其后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如今,从研究农民社会开始的欧洲人类学,已经呈现出后民族—国家的多元主义和差异性等特点,这表明,人类学在珍视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在尝试不断超越民族—国家这一理论框架和阐释语境,从而将乡村和村民置于一种“全球性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之中加以考察。
中国乡村研究和建设不管具有怎样的地方性经验(中国经验)、本位观点、问题意识和社会学想象力,它终归还是以现代性为导向,是在社会和文化转型这一问题意识基础上来展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和中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得以发生的理据,同样是文化转型应该以什么样的现代性为指向这一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将二者并置起来加以比较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探索过程,可以作为中国乡村研究和建设的参照系,它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折射出我们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的“现代性困境”,同时也可能使我们得以绕开各种“现代性陷阱”。
二、实践场域中的价值体系
欧洲人类学最初是以南欧地区农民社会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上,一种被称作“荣誉与耻辱并存” (coexistence of honour and shame)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长期以来一直主导这一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之所以要以某种价值观念或者思维模式来概括某一地区的精神面貌或者文化模式,主要还是想从社会形态层面对南欧地区农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加以整体性的把握,以便与其他欧洲地区的“理性观念”相区别,从而在欧洲内部再现“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同时也为人类学的研究谋求合法性地位。然而,一旦某一群人或某一区域被冠以某种思维或文化模式,并且遵循某种通常被称之为“传统”的价值原则,文化也就丧失了其原本应该有的张力和变通性,变成了某种与社会制度同质的给定性实在,可以完全独立于日常生活这一实践语境之外。此外,为了突出这种价值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学者们无疑会一再表明这群人从来都按照传统的观念来思考和行动,亘古不变。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坎贝尔 (J. K. Campbell)在希腊伊庇鲁斯考察山地社区的“社会空间”概念时认为,荣誉与耻辱观念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社区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共享一定的价值观念,包括在家庭和亲属中如何正确行事,以及如何展示与性别相关的道德观念来守护家庭的荣誉。正是这种在力量、财富以及荣誉上的相互竞争,才使得对立的家庭以及相关的群体以一种一贯和规范的方式联系在一起。①J. K. Campbell,Honour,Family and Patronage:A Study of Institution and Moral Values in a Greek Mountain Comm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9.戴维斯 (John Davis)也认为荣誉更具有地方性(地方作为传统观念延续和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空间,通常以褊狭、封闭的形象出现,因此也具有“传统”与落后的寓意),地方性的荣誉观念甚至等同于防御的观念。戴维斯认为,集体的荣誉是吸引所有成员的引力,它吸引充满离心力的个体来捍卫群体共同的利益。农耕社会的各核心家庭也总是各自分散、相互独立,然而集体的荣誉观念将会消解这些分歧,并往往演变成具有侵略性的观念——它将凝聚足够的忠诚、召集足够的力量并造成侵害和破坏。②John Davis,People of the Mediterranean: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6,p.100.上述两位人类学家在论述农耕,或山地社区的民众始终谨守某种价值准则的同时,其实也暗示了这些观念落后甚至野蛮的一面。传统的社会因此就变成了,以某种价值体系和思维心性加以简单限定的“静止”和“蒙昧”的社会形态,它总是与现代相对立,并且也必须借助后者才能呈现自身。南欧传统的农民社会,只有转变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才能向着现代的欧洲社会转型,才能够加入欧洲这一共同体。
中国学界则普遍采用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所谓的“小传统”的观念,来分析农民社会或者地方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由于对这一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缺乏应有的谨慎和批判,总是衍生出士绅文化与乡民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俗文化等简单对立的分类体系和相应的快捷分析模式。乡民文化、民间文化和俗文化往往被视作“乡土中国”的表象,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障碍。此外,由于对大小传统的关系缺乏深入的辨析,被当做整体来表述的所谓“中国传统”,也总是停留在模糊的意识形态层面,而缺乏可细致操作的理论范式和实践经验,并进而遮蔽了我们对自身传统的认识。因此,小传统无一例外都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小传统的价值体系首先必须由大传统来规范、消解和吸纳,然后才有朝向现代(西方)转化的可能性。
事实上,何为现代、何为传统,远不如为什么以及如何将现代与传统加以分类重要。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只能说明,处于某一特定社会的人们,以何种方式、何种分类体系理解传统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借用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的观点,所有分类体系的实质,是要将无序和失范之物(matter out of place)加以分类、界定甚至净化,从而重回一种常态的实践方式。在以民族国家以及相关的知识范式为理论预设的学者眼中,传统多少意味着无序和失范,因此是需要加以改造的对象。这一传统与现代的分类体系,将传统社会内含的现代性刻意遮蔽,同时也高扬现代社会 (西方社会)的“祛魅”和“理性”,而遮蔽其与传统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现代性的反思,应该从西方 (先进)与中国 (落后)这一二元对立模式的两极同时进行,即重新反思,这一二元结构对立之下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传统性。国内已经有学者对传统中国等同于乡土中国的观点加以批判,并指出城镇以及城乡关系在认识及阐发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性。③陈映芳:《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开放时代》2007 年第6 期。也有学者考察了“法治”与“礼治”的二元论观点,指出明清时期的“礼治”社会中,诉讼数量的增多已经为现代司法制度的介入做了准备。④梁治平:《从“礼治”到“法治”》,《开放时代》1999 年第1 期。当然,对传统中国“现代性”的考察,应该避免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对中国的乡村进行新一轮的剪裁和过滤,从而使之符合现代性规范。这种考察的积极意义在于,任何有关“传统”与“现代”的描述,都是一种可供人们把握和言说的分类体系和知识范式,它更关心的是这一二元结构是如何被建构、被阐释的,而不会将这种分类和表述看做一种给定性的社会事实,反而是社会事实,是如何被这一二元分类体系所遮蔽和扭曲的。
此外,我们只要对某种价值观念的社会参与者的话语和社会实践稍加考察,便会发现,这种看似铁板一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屡屡被“侵蚀”的痕迹。戴维斯对荣誉的认识显然过于绝对,他一方面强调荣誉自成一格,荣誉的分层模式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似乎荣誉是一个独立的俗世的和道德的评价体系。但同时他又强调了荣誉与物质和财富的关系,因为后者连同一个社区内的等级和地位显然是变动的,这就使得他对荣誉的认识多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荣誉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体系。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荣誉感得以展现的语境及其功能,也就是反思人类学经常强调的现实的社会交往语境,这些迸发荣誉感的瞬间和零散的时刻,显然难以用“绝对”和“体系”来衡量和假设。所以,剥离开是什么样的主体在与价值体系互动这一前提来讨论价值观念的转变,从根本上而言毫无意义。价值体系不是某种独立于人们话语和社会实践语境之外的“给定性实在”,而是以日常生活这一“竞技领域” (arena)为背景的建构之物。考察某些观念在实践语境中被建构出来的过程,远比分析这些观念的“实质”重要得多。
由此可见,与某种价值观念相对应的社会形态或者文化模式的建构过程,其实是一个将其同实践语境以及实践的主体相分离的过程,目的是要通过分类体系,来建构出一个可以不受其他因素干扰、自给自足的社会实体。这样的判断,符合实证人类学或社会学通过将他者的文化具体化(reification)、类型化,并进而把握其实质的认识论立场。对这种“社会中心主义”及其相应的社会转型理论加以解构的两条途径分别是:首先,考察“传统”与“现代”这一二元结构或知识范式,是通过何种分类体系和理论预设加以建构的,从而关注“传统”社会被发现和再造的过程;其次,重新关注和审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促使人类学采取了一种另类的视角。按照科恩(Anthony Cohen)的观点,这种另类的视角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他认为,与其演绎式地从社会和文化出发去认识个体,为什么不归纳式地,或至少是经验式地通过个体去认识社会呢?与其将个体看作被各种制度或体系剥离了自我的社会成员,为什么不将社会制度看作内并(incorporation)入个体世界的一种形式呢?①Anthony Cohn,Self Consciousness:An Alternative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London:Routledge,1994,p.99.同样,社会学领域近来也强调一种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②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1 期。也有学者主张用“后社会学”的知识范式,对传统社会学完全独立于人们的话语系统之外的“社会实在”的观点予以反思和批判。③谢立忠:《后社会学:探索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1 期。
这些研究视角无疑都表明,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有关“人”的科学,无法脱离且必须勇于面对生产知识的主体及现实语境。价值体系因此也不再是独立于社会参与者的支配性原则或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社会参与者可以利用的符号资本。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在大多数社会现实中,往往只是一种话语形式或者修辞体系,它的范围、言说和展现要依照社会参与者日常的生活情景和言语实践,因此绝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指涉对象的空洞的价值体系。
三、传统与现代: 内与外的分类体系
从根本上而言,内与外的分类是一种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本能或思维定势。道格拉斯认为,当一个观察者的感官面对外部事物的刺激的时候,总会选择性地接收那些我们感兴趣的,而我们的兴趣又受到一种具有倾向性的模式的支配,这种模式有时被称作先验图式。④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p.45.可见,我们的先验图式作为一套分类和过滤的体系,总会在第一时间,将那些我们认为无序和失范的事物界定为不洁、肮脏、外来或者危险而加以拒斥,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既定的认知模式的混乱和对立。现代性作为一种外来之物,有时候可能也会引起既定认知模式的混乱,个体或群体因此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必须梳理这些纷繁芜杂的经验,并将其纳入到一个有序的经验体 (unity of experience,道格拉斯语)之中。内与外的分类体系,其实就是社会参与者所特有的实践精神和能动意识的体现,相应的传统与现代也被纳入到这一经验体之中,成为由社会参与者来运作的一套内与外的分类体系。
马维强对山西平遥双口村集体化时代政治身份以及日常生活的调查表明,固着于乡村日常生活实践的传统,有着惊人的对于外来事物的整合、吸收甚至超越的能力。尽管村庄传统的社会分层被急剧地阶级改造运动所颠覆,但是新生的阶级关系,仍然处于乡村传统的地缘和人情关系的依附地位,乡村传统而非阶级关系,在村民的相互交往中仍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⑤马维强:《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开放时代》2011 年第8 期。双口村民的传统,事实上就是一个有序的经验体,村庄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总是在积极地梳理、改造和消解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下移,所可能引发的认知模式和经验感受的混乱。从某种程度而言,村庄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这一文化体系,相对于外来、危险等事物和观念而存在。在社会和文化剧烈震荡的时期,它的功能,似乎不再局限于调节社区的各种组织和人际关系,而在于帮助社区的大多数个体,应对任何对既定的思维范式的挑战,帮助他们,积极主动地将这些无序和危险的东西要么拒斥在基本的分类体系之外,要么将其辩证地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内。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某种无序和失范,对于社区既有的价值观念形成对立和挑战,而社区固有的文化分类机制因此被激发出来,以帮助个体设计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此外,在外来的现代性的冲击和挤压之下,内部的传统观念以及地方性知识,往往是朝着正统和保守这一方向来整合和强化自身的经验体。这一整合和表述内部经验的过程,就是传统复兴或再造的过程。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对于希腊乡村正统宗教观念的复振,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他说,乡村神职人员的恪守职责和奉献精神以及英雄主义——部分可以理解成传统——与官方教堂的乌烟瘴气形成鲜明对比,传统在现代的语境中渐渐复活了。同样,在希腊克里特高地,以相互间的牲畜盗窃而闻名的牧羊人的传统也在复活,相互盗窃、桀骜不驯作为对现代法律的蔑视,在这群高地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希腊精神的象征,那就是高傲、独立以及蔑视权力。①Michael Herzfeld,“Cultura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Regimentation of Identity”,In Ulf Hedefoft & Mette Hjort (eds.),The Postnatonal Self:Belonging and Identity,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p.204 ~205.
近年来,国内乡村传统的复兴,同样也是在现代语境中对自身内部经验体重新界定、整合并加以社会展演的过程。这一内部经验体多少类似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它总是相对于一种外力而存在,这一外力就是现代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下移和改造,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力量在互动过程中,此消彼长,通常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共谋关系。吴重庆的《孙村的路》一文表明,民间权威作为这一文化网络自身运作的结果,在国家权力下移和挤压的过程中,反而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一局面显然来自这样一个悖论,即国家经济体制下的基层政权的极大膨胀,在大大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盘剥与获利能力的同时,反而大大降低了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治理能力。此外,民间或者宗教型权威的获得,是以纯正的道德品质为必要条件的,这显然已经与唯利是图的政治型权威形成强烈的对照,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在这种不同的诉求和价值取向的互动关系中来运作的。②吴重庆:《孙村的路—— “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开放时代》2000 年第11 期。这种不同的诉求和价值取向显然就是由乡土社会参与者来运作的一套内与外的分类体系,传统在高尚、自豪、蔑视权力这一内部经验体中得以全面的复苏。
这一套内与外、传统与现代的分类体系的运作,事实上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展演 (social performance)来完成的,同时也是地方性的话语和知识得以生成的重要场域。此处的社会展演,与特纳所谓的“社会戏剧” (social drama)有着显著的差别,前者更为关注人们日常话语和行为中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强调社会参与者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展演,后者则注重在充满“仪式性”和“戏剧性”的行为和事件中去寻求意义。中国乡村建设的“现代化”过程,往往与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发的民众的抗争性行为,因其具有的“群体性”和“戏剧性”特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某种程度而言,广大的乡村民众,正是在这些激烈的社会变迁中获得了最初的现代性的启蒙。比如有的学者关注城郊失地农民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上发生的现代转向,③叶继红:《城郊失地农民的集中居住与移民文化适应》,《思想战线》2010 年第2 期。有的则关注环境诉讼案中农民在如何提供证据这一环节所处的不利地位,④司开玲:《农民环境抗争中的“审判性真理”与证据展示》,《开放时代》2011 年第8 期。然而正是打官司这一过程,完成了农民最初的现代法治观念教育。此外,农民抗争的群体性事件,因其“戏剧性”被一些学者称作表演式抗争(一种新的政治景观),因为它完全满足了包括“舞台” (即抗争发生的街道、高楼、桥梁等公共场所)、表演主角、观众等所有戏剧要素。⑤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开放时代》2011 年第2 期。虽然表演式抗争的个体或群体,以达成某种利益诉求为目的,但是走上街道的“表演者”,在目睹警察、医疗、消防等救援和协调力量的到场,以及随后所参与的调解和处置过程,本身也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权力运作机制的体认。乡民在这种仪式性的表演过程中,强化了对民族—国家的体验以及认同,而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以及合法性也正是源自这些不断被违犯、矫正与妥协的仪式性空间,民众与国家形成了一种悖论式 (paradoxical)的共谋关系。
尽管戏剧式的表演强化了乡民现代性的经验,但却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社会展演。因为除了有声有色的社会戏剧和仪式过程,我们还应该经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言语和社会实践,以便考察他们在平凡和世俗的语境中是如何体验传统与现代,如何生产和延续地方性知识以及如何形成有序的经验体。赫茨菲尔德有关希腊克里特乡村手工艺人的身份建构、技艺的传承以及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论述,为我们考察中国乡村“现代性”建设过程中,乡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社会展演过程有所裨益。
首先,克里特乡村手工艺人的处境和地位,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十分微妙。赫茨菲尔德认为,手工艺制造在希腊通常与民族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并且被尊为希腊古典技艺和品格的宝库。如此一来,乡村手工艺人就成为希腊整个国家的一个缩影,因为前者也正背负着西方文明遗产和起源的沉重包袱。手工艺人们知道,他们同传统的关系就像一柄双刃剑,在提升他们地位的同时,也将其边缘化了,从而无法享受最为渴盼的现代性的成果。①Michael Herzfeld,The Body Impolitic:Artisans and Artifice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5.显然,这种边缘身份习得的过程,肯定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密不可分,他们在最不经意的社会和言语实践中,接受了这一等级体系的灌输,其中包括表示他们职业和身份的语言 (所谓的生产术语或行话)、工作的装束、技艺的传承方式 (主要是通过沉默以及无声的领会),以及通过身体来进行的自我以及社会知识的双重复制等等。
此外,如果我们以沉默和观察,作为希腊乡村艺人日常生产生活中知识的生产方式,并将其与言语进行比较,便会明了,乡村手工艺人用身体在复制何种与传统与现代有关的知识体系。通过沉默与言语的比较,我们大概能区分出两种知识的习得途径,一种是沉默的观察与触摸(touch),而另一种是用言语抽象地归纳出经验。前者更多地同身体、感官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更多地同智力、推理联系在一起。前者是一种凡俗智慧的知识生产方式,而后者则更像是一种玄学智慧②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认为,认知的过程应该是“凭凡俗的智慧感觉到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理智不能超越或取代感官,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参见[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143 ~158 页。的生产方式。在笛卡尔的二分法中,二者是被割裂开的。然而对于手工艺人而言,话语使得他的身体的感知变得麻木和迟钝,他们如同刀锋一样敏锐的头脑会被过多的言语所懈怠和麻痹。他们相信自己的感觉,以及作为艺人的天资,这种敏锐的视觉和触觉,激发起他学习知识的灵感,语言此时是苍白无力的。然而,由于现代性的遮蔽和扭曲,手工艺人们的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被贴上粗鄙、笨拙、落后的标签,他们当然清楚现代性运作的这一套话语体系,从而只能在内部保持着,他们自认为的包括沉默、男子气概(masculinity)在内的种种美德,固守着这一高尚的传统,周旋在现代性的边缘。他们的沉默,如同他们所掌握的物质技艺一样,同样是应对当下现代性困境的一种高超的技艺,只可惜这种技艺的展演方式于太过于平凡和日常,缺乏戏剧性和仪式性的因素,往往被学者们所忽视。
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的传统在与西方现代性的互动关系和分类体系中得以复苏和延续,西方的现代性构成了传统的展演的重要语境,甚至是传统复振的催化剂。然而西方的现代性,又是如何相对于乡土社会的传统而加以想象和建构的,却又是我们在探讨乡村社会和文化转型时,必须首先加以厘清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构西方的现代性。
四、西方现代性的解构
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构这种所谓的西方现代理性。道格拉斯分析和比较原始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仪式以及象征性行为,旨在说明,现代人也在象征性行为的不同领域进行仪式的操演。对于布须曼人以及其他原始文化而言,象征性行为的领域只有一个。他们通过分离、整理和归置的方式,创造出的这一整体,并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而是整个宇宙,所有的经验受到这一整体的规范而秩序井然。我们同布须曼人一样出于对危险的恐惧,都在对肮脏加以规避,并证明规避的正当性。我们的行为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所不同的是,我们不会将某一语境中的一套象征体系带入到下一个语境之中,因此我们的经验是支离破碎的。我们的仪式创造出了一个一个众多而零散的“次级世界(sub-worlds)”,彼此毫无关联。然而他们的仪式创造出的是一个单一并且连贯 (至少在象征意义上)的世界。③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pp.85 ~86.道格拉斯据此认为,坚持人类经验的统一性或一致性,是将“原始”和“现代”加以比较的基础。否则,只能像布留尔一样,得出一种脱离社会语境和社会制度的机械的原始思维模式,更糟的是,为了证明原始和现代两种思维模式的根本对立,布留尔将原始文化说得更加神秘莫测,而将西方文明夸大得更加现代理性。①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p.96.
由此可见,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就是要说明传统(原始)和现代之间的联系。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斯特森 (Marilyn Strathern),通过对一个叫做埃姆顿 (Elmdon)村庄村民的身份意识和认同问题的研究,旨在说明这个距伦敦仅50 英里的村庄,在历经英国工业化革命、城市化进程等多种形式的现代社会转型之后,某些传统的“乡土观念”连同社会组织被保留下来,依然在指导村民的行为和言语实践方式。根据斯特森的观察,在有关村庄的观念中,几乎不同类型的村民,②斯特森区分了Elmdon 的五种家庭。第一种是核心家庭(core families),因为有四个家族总是被认为是真正的Elmdon 人。第二种是“其他长期居住的家庭”(other established families)。第三种是“老移民家庭”(old immigrant families),指1914 年之前移入该村的家庭。第四种是新移民家庭,指“一战”以后移入的家庭,主要为农场工人,小商店主或是牧师。第五种则是乘通勤车往返的人。参见Marilyn Strathern,Kinship at the Core:An Anthropology of Elmdon a Village in North-west Essex in the Nineteen-six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5 ~28.都会以自己的家族在村庄中的历史作为一条纵向的追溯线索,同时又横向地梳理血亲和姻亲的亲属关系,从而确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组成的亲属关系,就会成为有关村庄的主要观念,村民们似乎都嵌置在一个亲属关系的网络中,从而形成整体的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③Marilyn Strathern,Kinship at the Core:An Anthropology of Elmdon a Village in North-west Essex in the Nineteen-six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斯特森认为,这种村庄性(village-ness)观念的普遍共识,不仅仅只是关于村庄生活的本质和属性,在更大层面上与英国的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对埃姆顿村民“村庄”观念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揭示现代英国文化和阶级中,以等级、地位以及经济关系为标记的种种观念的起源。④Marilyn Strathern,Kinship at the Core:An Anthropology of Elmdon a Village in North-west Essex in the Nineteen-six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reface.
此外,一直被当作现代理性化身的西方官僚机制,同样受到人类学的考察和批判。在西方学界中,韦伯是最早关注西方官僚机制的伦理精神的学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具体阐释了西方官僚机制的理性,并将其认定为某种教义 (新教)冲动的结果,似乎西方的官僚机制,在韦伯那里已经变成了某种自足的超验体,可以超越一切俗世的生活而存在,并成为西方宗教精神的代表。然而随着人类学对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政治实践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将这一“理性”的精神实体,还原到了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中,并指出,官僚体系与民众生活经验和日常实践彼此依存的事实。
受到道格拉斯肮脏与洁净分类体系研究的启示,赫茨菲尔德在《冷漠的社会生成——探索西方官僚体制的象征性根源》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的分类体系 (内与外、种族、血统、世系、民族精神),进一步而言种族之优与劣、血统的纯正与混杂、世系的尊贵与卑贱、民族精神的高尚与低俗,全都来自民间的宇宙观念,只不过民间和官方的象征体系,具有多重的意义和无限解释的可能性。为了说明官僚体系运作,完全建立在民间的一整套分类体系和相应的宇宙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他接着指出,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冷漠是文化问题,具体而言,是建立在内与外对立基础之上的民间分类体系和宇宙观念的延续。这种冷漠又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和血的象征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种族、国民身份的内外有别等多种文化因素相关。所以,冷漠是社会产生的,而其直接根源则是建立在“我者”与“他者”之区别的亲属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我”与“他”的选择体系。⑤Herzfeld,Michael,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Exploring the Symbolic Roots of Western Bureaucra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72.
简而言之,乡村社会亲属和血缘的内外有别的分类体系的扩展和蔓延,造成了今天西方社会官僚体系的格局和运作机制,如果我们忽略官方和民间分类体系的同中心性,就会产生出一套官与民、大传统与小传统之类的简单化分类体系,一旦将其用于分析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果是相当有害的。其实,宗教的、父系的、血缘的等等传统社会经验及其象征意义,构成现代民族主义、国民身份以及官僚机制的基础。根据福柯的观点,民族国家要做的,就是要保守这一官僚机制运作和知识生产的秘密。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广大的乡民对于这一权力运作的秘密和民族国家起源的知识懵懂无知,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普通民众也在发掘国家、民族以及官僚机制中宗族、父系、血缘以及庇护的象征意义,并在实践中将地方性的社区“变成”国家的一个缩微版,并屡屡对国家层面看似僵硬刻板的法律和政策进行违犯。由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实已经认识到自身与地方性知识的种种象征意义和隐喻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这些伎俩的存在,并以此来获得民众的忠诚和认同意识。另一方面,民众自然也认识到官僚机构中的人与自己并无不同,因此对于官僚机构的敷衍塞责、相互推诿普遍持有理解和默许的态度。正是在这一充满血缘、宗亲等非理性的象征层面上,普通大众开始了对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想象之旅,而现代社会、民族—国家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地方性社会的象征性层面,以获取知识和权力运作的秘密,二者因此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共谋关系。国内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乡村日常生活中权力和政治运作的方式,提出乡村政治就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的观点。①郭巍青:《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和政治——以下塘村修祠为例》,《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对乡村政治生态及其运作方式的考察,看作对现代性的解构的一种尝试,本身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上述西方和国内学者的观点无疑都在表明,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加以解构,其目的在于以一种反理性的方式向着个体的社会实践和能动性回归,从而考察地方性知识和传统在吸纳、适应以及整合现代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这种特定的且主体性鲜明的地方性实践,有时也被称作差异实践,它是一种相对于现代理性而言的实践方式。
五、差异实践
差异的话语和实践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difference)是发展人类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这一概念认为在当今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学研究将十分有助于阐明,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社会和经济差异方面所存在的话语关系,从而可以以差异的话语和实践为基础,来寻求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计划。②[美] 赫茨菲尔德:《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刘 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年,第191 页。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初衷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根据温铁军的观点,尽管中国的产业资本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抱有走西方现代化这一条路的幻想,必须解构“现代化”,重视农村、农业、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发展过程中必将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事实,重新走上乡村建设的发展道路。③温铁军:《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开放时代》2005 年第6 期。
事实上,重视地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差异及其实践和运作的逻辑的观点,并非是发展人类学或者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新发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就注意到了同乡会在城市经济一体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④[美]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321 页。这大约也可以称为,中国城市经济中乡村社会和文化极富地方特色的差异实践,而它又是这种现代经济体系的有益补充。有中国学者受到施坚雅有关城乡关系论述的启发,认为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的城乡关系,他们认为,传统的宗族和地缘,对于传统国家的市场发育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体现出了一种以乡村为主体的城乡关系,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是相反的。⑤吕新雨:《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载费孝通《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第92 页。黄宗智则在考察中国小农与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所发生的“流通关系”之后,认为中国现代农业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来理解,也不能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理解,它是一系列既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也非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⑥黄宗智:《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开放时代》2012 年第3 期。人类学家自然对于这些与现代经济理性相抵触的种种差异性话语和实践更感兴趣,他们专注于研究与发展理念“格格不入”的地方习俗和文化的“异质性”特点,以及这些异质性的观念是如何在实践中应对现代以及发展的话语和理念的。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白思德 (Theodore C Bestor)通过对日本东京鱼市 (tsukiji)家庭商行(family firm)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考察,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这种与现代理性经济格格不入,并且带有浓重地方习俗烙印的“差异实践”。从17 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建立在亲属、同乡、学徒、帮工等机制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鱼市中仍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正是依靠这些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商行,所建构起来的带有地方性和极强的亲属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网络,东京鱼市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市场。根据白思德的统计,东京鱼市在2001 年就创下了47 亿美元的海产品交易额,平均每天的海产品交易量就达到230 万千克。作者因此感叹道,东京鱼市绝妙地配合着日本饮食文化的细腻精致,而且还是国家文化身份的象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市场驱动了全球的渔业,从缅因州潜水采摘海胆的人到泰国的虾养殖者,从印度洋上的日本拖网捕鱼者到亚德里亚海的克罗地亚金枪鱼捕捞者,都因为这一市场而联系在一起。⑦Theodore C. Bestor,Tsukiji: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reface.
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差异性实践也体现在乡村的生活中,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关注和重视。应该说,目前的乡村建设是在民族国家这一框架内考察抑或促成、指导、安排乡村的经济发展、村民自治,并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可以说这一努力是从民族国家拯救乡村。但是这些需要拯救的群体恐怕早已卷入了全球的资本运作这一洪流中并且已经独立地获得了某种身份或者阶级意识。潘毅有关打工妹群体的研究表明, “打工”不仅仅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老板”,而且也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全面庇护,打工妹这一阶级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工程交汇处出现的新主体。①潘 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事实上,中国乡村的这种新型的有关阶级(阶层)以及身份认同的实践方式,在一种全球性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中获得了意义。乡民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不但嵌置在民族国家的话语和意识形态之中,而且也嵌置于一套,以西方为主导地位、继殖民主义的军事结构之后的另一种道德的、伦理的以及审美的殖民体系之中,②Denis Byrne,“Archaeologic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ntimacy: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erzfeld”,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Vol.11,No.2,2011.而后者对于新阶级和身份意识的获得至关重要。此外,这一套全球性文化价值体系,也在改造着民族国家话语的表述方式,官方的政治话语和表述也越来越规范化和国际化,并且借助大众传媒,对乡村的“全球化”视野和“世界公民”的身份进行了最初的教育和启蒙。显然,这种有别于民族国家语境之下的差异性实践,对于潘毅论述的打工妹群体阶级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
对于人类学而言,半个多世纪以前,人类学家们还在为地方性社会与民族国家之关系的建立而煞费苦心,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的文化、商品、信息、人员的流通如一股洪流,一下子将我们卷进了一个异质杂陈、没有界限、充满变量的后国家时代。我们被迫面对拥有各种身份的群体,他们通过移民、经商以及进城打工等流通的方式,在重构自身的身份认同甚至阶级意识。对于中国乡村建设学派而言,他们的困境与半个世纪之前的人类学困境如出一辙。当下的乡村建设理论考虑,更多的可能还是民族国家观念如何塑造了某一群体的类型化和实质化的身份,然而面对乡村文化的日益多元性、差异性、流动性等特点,我们将面对的是,一群已经发生“政治位移”③[法] 马克·阿贝莱斯:《人类学的新视野》,黄缇莹译,《民族研究》2012 年第4 期。的群体,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差异性实践。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全球性的变动、流通以及身份困境为导向。
六、余 论
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并持续至今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经历了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面的转型及其实践之后,又回到了文化转型这一维度。文化转型,成为我们反思传统与现代之分类体系及其运作方式的重要场域。道理很简单,如果对传统与现代的概念及关系都缺乏基本的辨析和厘清,任何所谓的价值体系、文化模式、思维心性的断裂式,或者进化论式的转型的观点,都将是脱离社会参与者及其实践语境的空谈。当下的乡村建设派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有学者已经指出,所谓“乡土中国”是基于西方现代性对自身的一种二元建构,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导向对自身经验的过滤和剪裁。然而,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学界对广大乡村中参与这一“转型”时期的主体(广大的村民)仍然关注不够,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语、社会实践以及诗性的社会展演策略,④刘 珩:《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民族研究》2012 年第4 期。缺乏可操作、可经验、可比较以及可反思的分析和研究手段,因此学者们在自己的表述和话语体系中,多多少少、下意识地还带有拯救落后,启迪蒙昧的救世主心态。
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正好在两个层面,对于我们当下乡村建设的理论实践具有启示作用。其一,西方人类学对自身现代性的解构表明,乡村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在隐喻层面和象征意义上与现代社会及民族国家的同构性,从乡村发现、想象和建构民族—国家因此不但是一种理论抱负,而且还是一种“观他而知我”的人类学谦虚、包容的研究路径。这表明,地方性知识应该也必须构成我们经验的反思的基础和前提。其二,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本身表明,对地方性知识的珍视,以“农村主位”为导向的乡村建设,因此更没有理由不珍视乡村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才能够对这一传统进行知识谱系的梳理,重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不至于沦为西学的一种补充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人类学的本土化和中国的乡村建设虽然都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但这一处境反而更利于对主流加以反思和批判。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