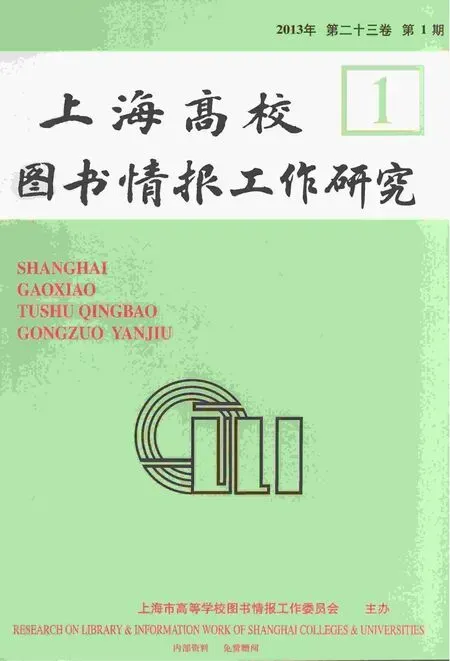《中国印刷史(增订版)》平议*
蒋鹏翔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长沙 410004)
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是当代学者研究印刷术源流演变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自1989年面世以来,钱存训、杨成凯等专家都曾撰写书评盛赞其学术价值,然书中观点、体例亦有可议之处。笔者研读该书,得札记若干,又多见前贤持论与之有异者,今择其要,整理成文,以识管见,并求教于方家(本文所论皆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印行之《中国印刷史(增订版)》为据,下简称《印刷史》)。
一
《印刷史》编撰历时四十年,字数过百万,是相关领域中难得一见的巨制,立论突过前人之处不胜枚举,其特点最著者有三。
其一,材料充实。全书一百一十万字,十之八九皆为史料。之所以能成此空前丰富的材料汇编,主要得益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张先生供职北京图书馆长达四十年,得以利用公余时间翻阅馆藏三百五十五部宋本原书及明抄《永乐大典》残本二百余册,退休后又遍访江南馆藏,并应邀登临宁波天一阁,参与挑选善本达五十日。如此丰富的目验古籍的经历,在近现代文献工作者中极为难得。
其二,视野开阔。《印刷史》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传统的古籍印本,纸币、报纸、版画、茶盐钞引、印契等“小众化”的印刷品也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无疑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印刷术演变、推广的历程。对域外印刷事业的关注尤为本书特色,作者不仅在考论本国印刷史时,分期对其境外之传播加以介绍,更设专章讨论中国印刷术对亚、非、欧诸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如此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之前的同类研究成果中实不多见。
其三,富于实践实证意识。古人修史,长于文献层面的梳理考辨,而对实践层面的技术、工匠等问题则较少关心,故《〈印刷史〉自序》称“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是印本书之直接生产者,为旧社会所不齿。本书多方搜罗其生活事迹,兼及妇女、和尚、监生之刻字”,更以“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为题独立一章。这种技术史中的“平民关怀”是修史理念的一大进步。除尊重工人的态度外,该书还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尽量完整地抄录有关古代印刷术的技术数据,工序如第154页记录蝴蝶装古籍修补装订、辅助的各十三步工序,第236页记录包背装的十九步工序,第381页记录线装的二十一步工序;物料如第236页对元代《秘书监志》所载裱褙书籍的“打面糊物料”功效的介绍,第385页记录明代司礼监行造纸二十八色和乙字库造纸十一色的详目,凡此种种,皆足广闻见而切实用。一是主动取今之民间风俗、实物材料与印刷史文献相参证,如第141页介绍南宋雕印历日时称“这种简明小历,很像至今仍在吾乡流行的《春牛图》……过去由丐头向乡间印卖,近年图上的耕牛,已改为拖拉机了”,第384页考证明代墨工时引用作者在故宫所见四十五家明代墨锭上的工匠名。此类例证都体现了该书对实证、实践层面的材料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对于一部优秀的专门技术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二
《印刷史》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余年,地域涉及亚、非、欧三大洲,对象包括雕版、活字、金属版、蜡版、泥版、石印、铅印。以个人之力进行如此宏大的全面研究,所论不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下面举几个例子。
1 蔡伦造纸说
《印刷史》将后汉宦官蔡伦认定为植物纤维制纸方法的发明者。此说成立的前提是否定蔡伦之前存在用植物纤维制作的纸张实物,故作者称“过去报上大肆宣传的所谓‘两汉灞桥纸’,后经科学鉴定是废麻絮,不是纸。其他所谓西汉纸也无确证。”(第7页,“两汉”当作“西汉”),所谓“科学鉴定”的细节语焉不详,事实也并非如此。
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实物样本曾经六次研究鉴定①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7页。,采用显微分析、光谱分析、对比化验等多种技术手段,最终均确认灞桥纸是以麻纤维为原料,经切、蒸、捣等造纸工序制成的,其物理结构和技术指标都符合手工纸要求,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并发布了灞桥纸麻纤维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及其分析化验结果(原料、厚度、定量、紧度、白度、纤维平均长宽等信息),故“废麻絮”之说不成立。
《印刷史》又提出“即使在同一处发掘出来的古物,也不一定都是同时的”(第4页),以此质疑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纸张年代。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但关于出土文物年代的判定自有一套周密的评估指标,否则任何出土文物都能以莫须有的可能性否定其所属年代的结论了。以灞桥纸为例,“(出土现场)只见一处墓葬遗迹,周围没有其他建筑遗址或墓葬,没有发现盗墓迹象,而出土器物组合又与已知其他西汉初墓葬器物组合相符,对灞桥文物逐件鉴定后没有发现晚于西汉武帝者”②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57页。,故将灞桥纸的年代断为汉武帝时的结论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
除灞桥纸外,《中国造纸史》第64至65页还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十三种西汉古纸的出土情况。如此丰富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西汉古纸确有实证,利用植物纤维造纸并非始自蔡伦。
2 雕版印刷发明于唐贞观十年(636)说
《印刷史》主张雕版印刷发明于唐贞观十年,论据有二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9-11页。。一为明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有唐太宗“以(长孙皇)后此书(《女则》)足垂后世,令梓行之”的记载,一为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按徐忆农《雕版印刷始于贞观说质疑》(载《江苏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2期)已详细论证了《弘简录》“令梓行之”之说系邵经邦杜撰,曹之《〈云仙杂记〉真伪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及其与郭伟玲合撰的《〈云仙散录〉作伪小考》(载《图书情报知识》2011年第6期)则证明《云仙散录》是宋人依托的伪书,故其所载玄奘印普贤像事同样不足凭信,因知《印刷史》中列举的论据,今人已有不同评价。
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论据不可靠,并不意味着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必然晚于唐贞观时期。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系唐武周朝刻本(可能刻于702年)④参见潘吉星《论韩国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科学通报》1997年第10期;邱瑞中《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武周朝刻本补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4期。,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内唐墓所出《梵文陀罗尼经》则被学界认为应该是7世纪唐初印本⑤参见潘吉星《1974年西安发现的唐初梵文陀罗尼印本研究》,《广东印刷》2000年第6期、2001年第1期。,都与贞观时期比较接近,可见《印刷史》的相关结论仍可能是正确的,但论证时应以这些较为可靠的实物材料为据,不能将观点建立在伪书或后人讹传的基础上。
3 宋体字的来源
第365页:这类(明刻本的)肤郭方体字,当时称“宋体”,或称“宋板字”或称“宋字样”,又称“匠体字”。其实它与真正宋版字毫无相同之处。笔者曾翻阅了现存宋版书近四百种,从未发现此类呆板不灵的方块字,所以应改称为“明体字”或“明朝字”,比较名副其实。
按一种新字体的形成,必然由之前的某种旧字体演变而来,不可能凭空诞生,且与过去的字体毫无联系,明刻本中的硬体字也是如此。取之与宋本欧体字相较,不难看出前者是后者标准化、模式化的结果。尽管明刻硬体字的结构更为方整,笔划趋于平直,二者在间架体态、用笔细节上的延续性仍然表现得十分清楚。
其实明刻本中的硬体字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雕版技术的成熟,硬体字的个性化成分、书写笔意都在不断削弱,笔划结构规范化、统一化的趋势则日益明显。从提高雕刻效率和准确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时代越晚的明刻本硬体字,其字体越方正,与宋本字体之间的差异也越大,但无论如何,硬体字源于宋本欧体字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更不能说“它与真正宋版字毫无相同之处”。
三
上文讨论的是《印刷史》中的具体观点,而作为一部今人编撰的专门技术史,其体例有无改进的余地,日后如再加修订是否应在整体上有所调整,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五点:
1 客观科学的态度
(1)编撰技术史,首先应在引用、解读史料时保持冷静客观的心态,杜绝情绪化的主观评价,如《印刷史》第509页“可笑者前清遗老在民国以后的写作或印本中,还在避宣统溥仪的讳,以示忠诚”,第709页“十多年前国内报刊大力宣扬所谓‘西汉坝桥纸’对海内外产生不良影响”,“可笑”、“不良影响”之类的用词都有欠斟酌。
(2)立论言必有征,减少无确凿依据的猜测。第11页“唐太宗时又有叶子格(纸牌)……此种玩具,不会在请客吃酒时临时自己赶制,需要量大,疑当时即有印刷品”,第379页“笔者怀疑南宋小报赚钱,日出一纸,又京城有专卖报纸的小贩,应该是印本,不过不用活字耳”,第663页“金朝刻经和尚自称为‘雕经僧’、‘雕字僧’或‘雕造僧’……又有作僧善定学者,应是初学雕字之徒工和尚。”前两条观点都是纯粹的猜测,第三条中仅凭一个“学”字就将其定为初学雕字之人,却未考虑古人撰述为表谦逊也往往题某某学的惯例(如《仪礼正义》卷端题“绩溪胡培翚学”),这样的结论自然也是不甚可靠的。
2 对术语、概念应作明晰精确的界定
(1)研究印刷史必然会涉及相当数量的专用术语,对之作明晰精确的界定,既有利于提高论证的严密性,也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印刷史》中对部分术语的处理值得商榷。
第116页介绍宋版书字体时,列举了颜体、欧体、柳体、苏体、瘦金体、手写体、古体、简体、方体、长体、扁体、圆活体、细瘦体等字体。首先这些字体在逻辑上分属不同层面,细瘦体与柳体、瘦金体有重合的部分,古体、简体是从文字规范的角度判定的,颜、欧、柳、苏、瘦金又以书法风格区分,所以这十三种字体不应并列。其次,术语命名考虑不周,所谓“古体”是刻书者为追求古雅韵味故意用楷体刻篆籀字形造成的怪字(明人许宗鲁亦擅此道),宋朝的楷书字体早已完全成熟规范,此时再刻意用楷体模仿篆籀,不过是藉之骇俗的小众化偏好,故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异体”。“简体”字是民间为提高刻版效率,遵从约定俗成的习惯简化一些字形笔划而成,这种简化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也未经统一推广,故称“俗体”更为恰当。“圆活体”是作者根据《天禄琳琅书目》卷一“周易”条所述自行定义的,其引文称“字画圆活,刻手精整”,而核诸原书,此句实作“字法圆活,刻手精整”⑥(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圆活云云,不过是指书法风格而已,不应自拟出“圆活体”这样的新名词。
第232页:(元)世祖又用许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版及江西诸郡书版,立兴文署以掌之。故元初中秘之藏亦富。其书版经元代重印,宋版即成为元版矣。
按一书若在宋代刻版,元代刷印,应称“宋刻元印”或“宋版元印”,并非如《印刷史》所言“宋版即成为元版”。
第683页:朝鲜造木活字,有《康熙字典》体、钱谦益《初学集》体、笔书体、印书体等。
按钱谦益《初学集》体、笔书体、印书体都属于印刷史中较为生僻的字体术语,作者却未作解释。
(2)论述中涉及具体概念时应保持上下文的一致性,不能暗换概念。
第576页:(有人认为)断版裂版只是版刻中的现象。其实活字版中并非没有这种断裂痕,如乾隆末年活字本《京畿金石考》卷上十四页“赵孟頫撰”四字均裂开,“赵”字几乎已分为走、肖两字,其余三字亦断裂分离颇远。
按断版裂版是指版片出现较长的连续裂痕(穿过数行甚至整块版片),《京畿金石考》四字裂开都是单个字型分别发生断裂的情况,其裂痕并未连成一线,与断版裂版是两回事,所以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活字本也有断版裂版的现象。
第624页:活字本多为非卖品,如家谱印成,编上字号,不许外姓阅览,多为十部左右,为各房子孙珍藏而已。
按家谱多为活字本且一般不对外发售,并不能由此得出“活字本多为非卖品”的结论。明代著名活字印刷出版家华燧、安国“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⑦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61页。,“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⑧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62页。,所谓“订正以行”、“以广其传”当然都含卖书的意思。到了清乾隆朝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更专门制作用于对外发售的竹纸印本,可知活字本多非卖品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3 合理地安排、利用材料
(1)《印刷史》以材料富赡见长,但过度堆积材料,不加拣择也是该书的缺点之一。各章介绍印刷物料时常分笔、墨、纸、砚四节,其中笔、砚二物与印刷无直接关系,不过是写样时所用工具而已。相较而言,版片(包括其木料)、刻印工具(用于雕刻版片的刀具、在版片上涂墨的排刷、压印纸张的棕刷)与印刷的关系倒是密切得多,却不见介绍。具体材料方面,第101页“(宋人)尤喜评诗,故诗话莫盛于宋。……以严羽《沧浪诗话》较有名”是文学批评史中的常识,与印刷无关;第326页罗列二十七种明代哲学著作的书名作者,而无其刊印细节,要了解此类信息,翻翻书目即可,不必在《印刷史》中赘述。其余各章多如此。
还有部分内容应该直接删除。第13页引《正统道藏》之“济饥辟谷仙方”论十六国后赵印书说,出注云“此方被说得如此神奇,又据说‘用之有验’,值得有关方面研究,故介绍原文于下”,然后抄录“仙方”全文。按方中所说的糯米混杂粮成团蒸食之,三百日不饥,完全是道家妄语,不值得转录。第533页介绍毕升活字时,引用电影《毕升》的情节并辩证其不合情理之处,此类讨论当然也不应出现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
(2)引用材料前,应正确地认识其性质、体例,不能草率评价。
第282页:《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著作四千六百三十三种,亦很不全,如藩王宗室诸作,大部分遗漏。
按历代史志书目都要经过修订删汰,向来不以求全为尚,与今天所说的古籍总目是两回事,不应以“不全”责之。
第511页:南京黄虞稷有《千顷堂书目》,较《明史·艺文志》详博,但多存虚目,非实有藏本。
按黄虞稷所以编撰《千顷堂书目》,是为了保存有明一代著述之全貌,而非私家藏书目录(尽管它是在《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编成的),故杭世骏跋云“俞邰徵修《明史》,为此书以备《艺文志》采用”⑨(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97页。,张均衡跋云“意欲成明一代艺文志”⑩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第793页。,因而其“多存虚目,非实有藏本”实属应有之义。
(3)对材料的解读应符合原作者的本意,不能为支撑观点牵强述之。
第314页:明谢肇淛以为“闵优于凌,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五杂俎》卷十三)。其实两家所印均优美,似难分高下。
按谢肇淛批评的是凌刻校勘未精,并非指其套印效果不如闵刻,《印刷史》用二家所印均优美的事实来辩驳其说,是对谢氏原话的误解。
第507页:胡克家翻刻宋尤袤本《文选》,就是请许氏影写的。胡氏自吹说:“雕造精致,勘对严审,虽尤氏真本殆不是过。”但是形式主义的摹仿,充其量只能惟妙惟肖,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按胡刻《文选》模仿宋本面貌,字作欧体,笔划圆厚,间架布局饶有古意,虽不如尤刻原本之方正工整,笔势挺秀,要不失为清刻中赏心悦目者;其校勘用功颇深,改正尤刻本明显的错误多达七百余处⑪据胡刻《文选》影印本的《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7年版。,故胡氏评语确属实情,“自吹”一词对古人有失尊重。且摹刻旧本,当然以惟妙惟肖为尚,用形式主义来批评此种行为,文不对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要求更与摹刻风马牛不相及,不知作者为何有此议论。
4 进一步深入研究印刷史中的技术问题
《印刷史》的篇幅安排不尽合理,一方面保留了过多无关主题的冗余材料,另一方面对书中述及的部分印刷技术问题却未能深入探讨其细节及可行性,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憾。
第579页介绍清人吕抚自制活字泥版印书的方法,称其有两个特点:一、调制泥土用刻好的印版挤印,造成单字,不经火烧,阴干待燥就能使之坚于梨枣;二、挤印成泥字的阴文字模后,将字模印在泥片上,成为阳文,再用泥片印刷。
按此法有两个疑点:一、泥土仅靠掺入秫米、棉花的调制方法而不经火烧,不可能达到“坚于梨枣”的效果,吕抚如何使制成的泥字字模具有并保持足够的硬度;二、将制成的阴文字模压在泥片上,使泥片对应笔划的部分向外凸出,成为适于刷印的阳文印版,这种用字模压印的方法如何使泥片上无字之处平整下陷,保证其在印本中较好地呈现为空白。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此活字泥版印书法的可行性,系工序中的关键环节,但《印刷史》未作解释。
第601页:(活字印)谱中印错之字多用墨等盖去,再用红字木印或黑字印于其上或四周,而原字仍隐约可见。……家谱一般印数自七八部至十数部,或二三十部,也有多至四五十部甚至一百部的。
第617页:活字本印错之字常用木等盖去,另以木戳印改正之字于旁,或墨印,或朱印,或印于另纸贴上,以资补救。
按活字本校改错讹,只需将对应的错字抽换成正确的活字即可,比雕版改字要快捷得多,批量印刷更应如此。如果采用《印刷史》所述之法,则每一部印成的活字本都要重复进行这种处理,版面既不美观,效率尤为低下,远不如直接抽换活字后再进行刷印来得方便,故此法只适用于校正活字试印本时。活字排成后,先印成一部或少量试印本,校勘该本,发现错字即用墨等盖去,然后在天头或四周加印正字(或印于另纸),提醒排字者注意。校勘完毕后,由工匠将试印本中标出的错字逐一抽换,排成校正后的字版,再批量刷印定本。第605页介绍铜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时,根据谕旨,得出六十部《古今图书集成》在雍正元年(1723)已全部刷好,然后校改错误、折配装订,故直到雍正三年才正式完成的结论,同样犯了颠倒工序的错误。六十部上万卷的活字印本,不可能一开始就全部印好,再逐部校改重复出现的错误,所以也必然是先印成试印本,加以校正,然后抽换活字字模,使最终排好的字版形成相对正确的面貌,之后才能大量刷印,否则浪费的工时、人力都是不可想象的。
5 遵守现代学术规范
《印刷史》成书于1989年,其增订本刊行于2006年,这一阶段出版的著作理应严格遵守现代学术规范,遗憾的是,该书还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1)注文规范
书中引用史料,有相当一部分完全不注出处(各章述历代史实多如此),又有不少材料仅注书名,其卷数、版本都付之阙如,如第181页述金人破宋京城时索取释、道经版事,注出自《三朝北盟会编》,按《三朝北盟会编》煌煌二百五十卷,不注卷数,如何查核。还有一些材料加脚注称“据旧笔记”(第135页注二)、“据旧稿,忘所引书,本书凡有”、“引号者均有根据”(第388页),手稿为求便捷当然可以这样表述,但作为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此类注文就显得不够严谨了。
(2)书名著录规范
《印刷史》是以古籍为主题的技术史,著录古籍书名时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其中有误判书名者,第254页“万历《野获编》”当作《万历野获编》,第271页“黄帝《内经素问》”当作《黄帝内经素问》;有标点不确者,第273页“《宋、元资治通鉴》”书名号中不应加顿号,第293页“元《张伯颜本李善文选注》”当作“元张伯颜本李善注《文选》”;有过度简称者,第299页“宋《毛晃韵》”实指宋毛晃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663页“邢凖编《玉篇》”实指邢凖编《新修絫音引证群籍玉篇》。还有部分书名著录前后不一,如第624页“华氏会通馆铜版《宋诸臣奏议》”,其配图题《会通馆印正本诸臣奏议》,第628页“《校正音释诗经》”,其配图题《会通馆校正音释诗经》(皆当从后者)。
根据著录惯例,古籍书名应以正文首页首行题名为定,其他位置记录的书名均不足凭,《印刷史》这一点做得不够规范。
(3)正文引文之区分
现代学术著作引用他人文字超过十四个字就必须明确标识并加注出处,《印刷史》中却经常出现引文正文混杂且不作说明的情况。
第118页:(宋本《妙法莲华经》)元人跋语称:“自圣教东流,卷帙之简要者无出此本之奇也!”
第127页:所见宋本《妙法莲华经》……元人至正己亥题称吴郡章某得此,自圣教东流,卷帙之简要者无出书之奇也。
按第127页再次引用元人跋语时就未用双引号标识,而是稍加改动,混入正文,且“书”前又脱一“此”字。还有部分章节完全不作说明,径将各种材料的原文略加连贯,便置于正文中(第382页记明代制笔,第383页记明代造墨皆如此),以致文白夹杂,辞气不畅,此类表达也需修正。
(4)表述的严谨性
表述严谨是技术史编撰者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印刷史》在叙述部分史实时,所加案语缺少斟酌,故其论断间有疏失。
第37页:(五代刊印监本《五经》)从此古代以来传写舛谬的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
按自东汉蔡邕等人写成熹平石经起,经书就已有了统一的标准本,五代只是开始以官方名义雕印《五经》而已。
第89页:周昙《咏史诗》宋本之最佳者。
按此条见作者所编宋本别集书目,贸然称《咏史诗》为宋本最佳者,佳处何在则无一字解释,令人不解。第99页:宋人最重要之小说《太平广记》五百卷,幸而尚存。
按《太平广记》系类书,非小说。
此外像“八股文本身毫无价值,随生随灭”(第480页)、“(清人诗歌)多属无病呻吟,陈词滥调、千篇一律……(弘历以外)其他诗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地位”(第481页)之类的观点有失武断,都不应出现在《印刷史》中。至于“清人少独创精神,反映在印刷上,除盛行明代的方体字外,又流行一种影宋本”(第507页),这样牵强的解释,就更应加以修改了。
四
《印刷史》一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前贤已在书评中做过较好的总结。笔者个人认为,该书最大的成功,是其对印刷史材料搜辑、整合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内容丰富翔实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任何一部同类著作。在此基础上作者尽力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中国本土的印刷史材料、传统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尽管不及《印刷史》完备深入),但印刷术在海外诸国的传播影响、印刷过程中具体的工序物料等问题在张秀民先生之前却较少得到系统的关注和研究,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领域的拓展甚至比单纯材料的搜辑更有意义。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印刷史》本身并不完美,无论是其具体观点还是全书体例,都不乏应改进的地方。一部更好的印刷史应该怎么写?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以下几点是不能不努力去做的:
承继《印刷史》的丰富史料和广阔视野,编撰时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减少过于情绪化的批评。对书中涉及的术语、概念作准确明晰的界定,并在各处的引用、解释中保持一致。紧扣印刷史的主题,删减无关的材料。引用材料时要明了其体例,据之立论时不能违背原作者的本意。对《印刷史》中涉及而未能详考的技术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依据现代学术规范,对全书重加审订:详注出处、规范书名、区分正文引文并改正表述中不够严谨的地方。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印刷史》才能成为一部较为成熟完善的学术成果。
张秀民先生的大作为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但学术探索是永无止境、不断前行的过程,希望本文能为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增订本)[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2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