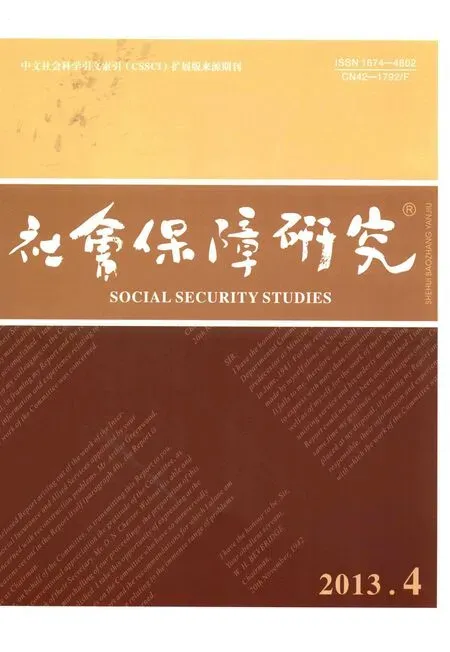国外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商业参与*——兼论公共物品供给
孙嘉尉 顾 海
(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与医疗保障政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93)
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及商业保险机构(商保机构)在补充医疗保障项目、参与基本医疗保险运营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号)明确提出了“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承办方式,《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发〔2012〕57号)也列入了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和委托商保机构经办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等内容。这些无疑是对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在促进完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积极作用的肯定。目前,医疗保障体系的商保参与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试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物品,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国民健康利益、减轻疾病负担等功能还有待完善,而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在其中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发挥。
一、发达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及商保机构在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作用
(一)瑞士——基本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营
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国土面积4.1万平方公里,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公园的美誉。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607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3073美元,是世界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1996年,为了改善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和可承受性,以及更好地控制成本,瑞士通过了《医疗保险法》,全体居民被强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同时,从这一年开始,瑞士对全国医疗系统进行重整,实施了商业化运作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由相当数量的、相互竞争且非营利的商保机构,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服务,成为瑞士全民医疗保险的突出特征。
瑞士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通常以个人为单位,其家属必须另外购买单独的保单,才可以享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不论投保者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如何,所有的商保机构都不得拒绝其参保。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一般并不按照收入的某特定比例收取,而是根据参保者的年龄、性别及所在州等指标确定,[1]因此缴费标准在各州和各人群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如2011年,各州26岁以上的成人,其基本医疗保险平均年缴费水平,最低为3326瑞士法郎(CHF),最高则达到5810CHF。这对于一般的瑞士公民而言并不算高(2010年瑞士就业者的月平均工资为5979CHF),但对于低收入群体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会对社会低收入的个体和家庭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补贴,以帮助他们支付医疗保险的保费。此外,州政府和市级政府还会为符合相关要求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自付费用补贴,以帮助他们解决患病负担。
商保机构在规定的范围内自行确定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例如,它们可以设定较低的保费和较高的起付线标准,作为较高的保费和较低的起付线标准的替代方案,供人们自由选择。起付线和替代保险计划(如管理式医疗保健计划)只允许在三个年龄层次之间加以区别,分别是18岁及以下的儿童、19-25岁之间的年轻人和25岁以上的成人。由于不同商保机构的参保者特征存在差异,从而患病风险和预期医疗开支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和减少商保机构的风险选择,瑞士引入了风险平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医保基金的重新分配。瑞士公共卫生局负责对商保机构的监管,并通过制定相关标准,以批准和控制这些商保机构的保费额度。
在保障项目上,瑞士联邦政府只制定了最低标准的、覆盖范围较广的基本医疗福利包,内容包括大部分的全科医生、专科医生服务和药品处方,部分物理疗法、精神疾病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服务等;选择性疫苗接种和选择性一般健康检查的费用、某些特定群体的早期病种诊断,以及某些形式的辅助性药物等,也是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除此之外,联邦政府允许各州在该福利包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情况对基本医疗福利包的内容进行增加和调整,因此,各地的医疗保障政策同样存在差异。当然,基本医疗福利包以外的医疗服务,会收取患者额外的费用,如果患者不希望全部自付,就需要事先参加其他自愿型的商业健康保险来获得帮助。许多居民购买了自愿型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从而得以免费或部分免费地享受未被基本医疗福利包所覆盖的医疗服务、免费选择诊治医生,或者改善住院时的住宿条件(如单人或双人间)等。自愿型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份额较小,共承担了大概9%的医疗总费用。
在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管控下,营利性的商保机构,对其提供的自愿型医疗福利包及其保费,实行多样化经营,并可以根据个体的病史拒绝其参保。与此相异的是,商保机构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时,必须秉着非营利的原则进行经营。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商保机构一般会有一个非营利的支部,专门提供强制性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并另设其他营利性的支部,以提供自愿型健康保险服务。
瑞士的以商保机构为载体的基本医疗保险运行方式,强化了承保机构之间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提高了它们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并维护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其体系仍不十分成熟,在控制费用、提高运行效率和对商保机构的有效监管等方面,仍然需要改进,但这种方式无疑为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荷兰于2006年将其原有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也转向了这种以商保机构为经营载体的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并根据自身条件,在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集中度、风险平衡机制和医保报销政策等方面,形成了与瑞士有所差别的医保制度。[2]二者都较好地利用了市场竞争的优势,降低了行政执行成本,在有效减少政府财政预算的同时,使政府回到监管职责上来,从而更加明确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虽然也实行医疗保险市场化模式,但并不强制参保,从而难以保障居民健康权益的有效和公平获得;与瑞士和荷兰相比,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略显不足。
(二)澳大利亚——公共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并重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东临太平洋、西临印度洋,由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等岛屿组成,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达。2011年GDP为14869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6371美元。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起步较晚,以1973年颁布《健康保险法》(Health Insurance Act 1973)为标志;但经过10多年的努力,1984年,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便正式确立,并成为澳大利亚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Medicare以税收为基础,主要来源于一般性税收。个人应纳税收入的1.5%则被作为专门的税款(该税款对部分低收入群体减免),成为Medicare的固定筹资渠道。Medicare参照医疗福利计划(Medical Benefits Schedule,MBS)和药物福利计划(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dule,PBS),对大部分的医疗服务和处方药,实施免费或部分免费的提供,并为以公共医疗保险参保者身份住院的患者提供完全免费的住院服务。通常情况下,Medicare会支付目录内门诊项目指导价格①医生对于诊疗费用的多少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收取比指导价格稍高的费用。的85%(主要针对专科医生服务)到100%(主要针对全科医生服务),以及目录内住院项目指导价格的75%。澳大利亚实行医药分开,患者持医生开具的处方到药店自行购药。在PBS内的处方药,一般患者需要支付数额为35.4澳元(AUS)的共付费用,而对于持有特许卡的患者(一般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低收入者和老年人),则仅支付5.8AUS即可;一些特殊处方药的共付费用还要再低一些。
尽管澳大利亚的医疗保障水平较高,但人们过度依赖公共医疗部门,影响了医保基金运行和医疗资源分配的效果。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尝试鼓励人们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使其能够较为廉价地使用私人医疗资源,从而缓解公共医疗资源和公共财政的压力。1997年,澳大利亚政府执行了两项政策:一是对参加商业健康保险者提供部分的保费返还,一般居民为30%,65-69岁的老人为35%,70岁以上的老人则为40%;二是对没有参加商业住院保险的、年收入较高的个人和家庭(目前对于个人和家庭的高收入标准分别为达到80000AUS和160000AUS),额外征收应纳税收入的1%作为处罚。2000年7月,终生医疗保险(Lifetime Health Cover)政策生效,它为在30岁之前就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保者,提供一个相对低廉的保费,且不考虑其实际健康状况;而初次参加时超过30岁的个体,将会受到惩罚——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为延迟参加的年份,每年缴纳额外的2%的保费。[3]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奖惩双管齐下,推动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商业健康保险由个体自由选择。商保机构的不同内容的保险单,在保费上允许差异化,但其同一保险单,则要求在参保者的保费额度相同。因此,澳大利亚也引入了风险平衡机制,用以帮助控制各商保基金的运营稳定性。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帮助参保者免费或部分免费地在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中选择私人服务、自主安排就诊时间;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商业健康保险获得尚未被Medicare所覆盖、或尚未纳入公共医疗服务系统的辅助性医疗服务(如物理疗法、牙科、眼科、足病科等),以及其他补充医学服务等。
澳大利亚卫生与老龄事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负责制定商业健康保险的相关政策,部长必须为任何的保费增长进行批准核实。同时,独立的法定管理当局——商业健康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Council)负责对该行业的管理。商保机构可以是非营利性的,也可以是营利性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前者居多。不同于瑞士的分散于各州且激烈竞争的商保市场格局,澳大利亚的商保机构大多在国家层面进行经营,且市场集中度较高[4]。
截至2011年6月,澳大利亚有44.3%的人口拥有商业住院保险,52.5%的人口拥有一般性的健康保险(含辅助医疗服务项目)。[5]商业健康保险同Medicare一起,较好地满足了国民的健康需求。但当前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比较突出的是,医保服务项目的重复覆盖和重复补偿。[6]因此,将商业健康保险定位于Medicare的替代保险,从而允许居民二选一,还是将其定位于Medicare的补充保险,仅允许其经营Medicare覆盖范围以外的内容,仍然存在争议。同样对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给予重视的德国,源于其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便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难题。它允许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体,自由选择退出法定医疗保险、加入商业健康保险;并且,如果想要再次回到法定医疗保险,还必须满足一些特定条件。而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的澳大利亚,则需要在借鉴德国做法的同时,较好地协调税收与Medicare及商保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较为高效地利用公共和私人医疗资源、提高医保基金运作效率的目的。
(三)日本——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保机构的补充角色
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北部,是一个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大岛及3900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尽管自然资源贫乏、人口拥挤,但其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2011年GDP为58665亿美元,人均GDP达到45870美元。日本的社会福利制度,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日臻完善,并形成了独特的亚洲福利模式。就医疗保险制度而言,日本于1961年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体系,成为世界上继德国、英国和挪威之后,第四个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7]因医疗体制健全、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较高,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国际上也获得了高度评价。[8]
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了根据职域和地域确定参保对象的多种类型。包括针对大企业雇员、中小企业雇员、企业日工的健康保险,针对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船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等特殊职业人群的专门健康保险,以及由市町村政府管理的囊括了农民、无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参保群体的国民健康保险。其中,以职域为主的医疗保险主要由雇员和单位共同缴费,雇员的家人也被要求加入该医疗保险;而以地域为主的国民健康保险,则由参保者个人和国家财政共同承担保费。[9]此外,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日本逐渐建立起了老年医疗保健制度,该部分的医保基金独立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其使用要求在政策上逐步细化,[10]医保报销待遇相对更为优厚,且得到了更多的国家财政支持。由于细碎化的分类和管理,日本当前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囊括了3500多个承保机构,且由于有特定的覆盖人群,参保者无权选择承保机构,各机构之间一般因此并不存在竞争。不过,尽管所属的医保基金不同、医保缴费存在差异,但所有的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均包含相同的法定医疗服务包,[11]从而保证了不同人群在享受医疗福利时的公平性。
日本的国家法定医疗服务包覆盖了门诊服务、住院服务、精神健康服务、获得批准的处方药和大部分牙科服务,许多预防保健性服务也向40岁及以上的人群公开提供,包括筛查、健康教育和咨询等。一般地,患者在使用福利包内的医疗服务时,都会被要求支付30%的共付费用,针对一些特殊年龄人群,则会适当降低该比例。如6岁以下的儿童和70-74岁的老人,其共付比为20%;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仅负担10%的共付费用;而收入水平较高的、70岁以上的老人,却难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其共付比仍然是30%。[16]一些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会为其雇员的基本医疗保险,提供一个较低的共付比例。当然,针对这一较高共付率而制定的自付封顶政策,较好地解决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市场化或商业化元素,在日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中,较多地运用于门诊和住院等部门,[12]在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作用较小,主要表现在大型企业对其雇员的健康保险基金的独立运营管理。经批准设立的针对大型企业雇员的健康保险,以“组合会”为管理机构,组成成员为代表企业主和劳动者双方利益的议员;由组合会议员选出的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为该组合的执行机构。[13]掌管健康保险的大型企业的医疗保险部门,同其他健康保险组合一样,接受厚生劳动省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保险补贴和组织监管等。另外,在补充医疗保险方面,虽然大部分日本成年人都拥有商业健康保险,但其在医疗总费用中的份额很少,作用较难显现。尽管各健康保险的细碎化增加了行政成本,但日本政府在基金整合中,似乎并没有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的意向;而逐年增加的医保基金压力,政府则主要求助于支付制度改革。[14]因此,日本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尚未成为其医疗保险事业发展中的有力支持。[15]
其实,诸如日本这样的以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为从属的方式,较为多见。它既存在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如瑞典;也存在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尚待完善的国家,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前者源于发达的国民医疗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从而使得商业健康保险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而后者则源于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但受限于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或政府管制,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虽然广阔、但较难开拓。可见,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或从属地位,既可能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壮大和完善的原因,也可能是其结果。
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同样处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地位,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总费用中所占比重较小。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需求多样化的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将有潜力发挥其市场经营优势,从而为提高医保基金运作效率、加大补偿力度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医保制度做出贡献。
二、基本医疗保险的商业参与——政府与市场的共同选择
从上述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运作特点来看,不论商业健康保险及商保机构在其中占据主体地位还是补充地位,都不同程度地显现了市场对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实际证明了市场部门参与(准)公共物品供给的可行性及可观性。
传统观点通常将政府视为公共物品的最佳供给者。尤其是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因其涉及公民权利、需要较好地保障公平性,[16]往往被认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一项社会性公共服务,似乎理应由政府供给。然而,市场在供给公共物品时产生的“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总能依靠政府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方面,受到可得信息和财政约束的影响,政府只能够供给部分公共物品;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组织的特性,使得其在供给公共物品时常常显得低效。[17]同时,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一些市场部门已经有能力帮助政府分担公共物品的部分供给,此时政府如若还坚持全权包揽,则将无益于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非此即彼的排斥态势渐渐消除,两者可以通过相互合作、相互补充,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缺陷,在包括公共物品供给在内的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共同发挥作用。[18]
就基本医疗保险而言,人口老龄化、需求多元化、医疗费用日益攀升,以及人们对于健康和医疗公平的关注等,使得主体单一的社会性保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配合政府有效应对这些新的挑战。例如,医疗保险通过商业健康保险及商保机构进行筹资,可以增加或替代原有基金的筹资途径;医疗保险系统的运行能力可以借助于商保机构的管理优势而获得提升;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还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特定的政策目标,如增强个人的健康责任意识等。因此,政府有必要在保障对象、保障范围和保障路径等领域,有效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的功能,利用其在筹资、设计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化、多样化和市场化优势,实现医疗保险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国外商业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供给的启示
医疗保险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本身的复杂性,也有可能对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19]在引入商业元素时,政府需要谨慎考虑其潜在角色,由此带来的公共部门、商业部门和参保者之间的新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商业参与方式下的整体效果等问题。在我国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明确两者如何衔接和各自应当承担的职能,显得尤为重要。
在机构衔接方面,商保机构通过经办的方式参与我国新农合基金的管理、通过承办的方式负责大病保险的运营等,能够在不降低居民受益标准的基础上,较好地提高基金使用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并有助于政府实行管办分离,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能。这是我国政府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所做出的合理选择,也是进一步保障居民健康权益的重要举措。当然,当前的商保机构参与方式,还不能够帮助各医保基金很好地解决医疗费用上涨等关键问题,各地因社会经济水平不同,从而对商保机构的激励程度也有所差异。在条件适当的时候,政府可以尝试让商保机构参与更多的医保基金管理工作,在政府、商保机构、医疗机构和参保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互动中,实现医疗保险体系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在职能分工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着重履行其监管职能。首先,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有必要对商保机构介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的方式,进行考察和论证,以宏观的、系统的视角把握各相关主体在新规则下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寻求提升管理质量、避免利益冲突的最佳途径,进而形成一般性制度,指导和约束各相关者的行为,使其在合理的框架内追求自身利益;其次,作为市场活动的监督者,政府有必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利用先进技术、配备专业人员,对该制度下各相关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并及时反馈,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损害患者利益和影响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效率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政府还应当提供相关渠道,及时公开医保有关信息,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反馈。一系列的监督措施,将最终形成医疗保险体系各利益相关者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网络格局,有效防止市场参与主体的不合理操作及政府自身权力的过度扩张;再次,作为市场经济的维护者,政府有必要考虑市场中的非理性因素,防止市场失灵的发生。一方面,在当前情况下,基本医疗保险的商业参与是需要竞争的,但该竞争必须适度,过多的经办机构或承保机构反而会增加管理成本,形成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商保机构在经办和承办中无权剔除任何参保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商保机构将面对参保集体的所有风险,对于商保机构而言,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政府应当与商保机构共同承担该风险,制定合理的分担标准,并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适当激励商保机构,以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参与的可持续性。最后,基本医疗保险毕竟属于社会性保险,不能将其当做谋利的工具,所以,作为公共物品的保护者,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管理办法,严格保证该基金的账户独立和专款专用、保证广大参保者的利益不受侵犯。
总之,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现代政府理念和公共物品供给的新形式,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商业参与,是该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必然选择。随着政府向监管职能的逐渐归位,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保机构将在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中担当更多的角色,它们将同政府一起,成为满足参保者多层次需求、促进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提高和维护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及公平性的重要力量。
[1][2]van de Ven.W.P.M.M.and Schut.F.T."Universal Mandatory Health Insurance with Managed Competition in the Netherlands:A Model for the USA?".Health Affairs,2008,27(3):771 -781.
[3]Butler.J.R.G."Policy Change an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Did the Cheapest Policy do the Trick?",Australian Health Review,2002,25(6):33 -41.
[4]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Council(PHIAC)."Operations of the Private Health Insurers:Annual Report 2006-07",PHIAC,Canberra,2007.
[5][11]Thomson.S.,Osborn.R.,Squires.D.and Reed.S.J."International Profiles of Health Care Systems,2011",New York:The Commonwealth Fund,2011.
[6]Paolucci.F.,Butler.J.R.G.and van de Ven.W.P.M.M."Subsidizing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in Australia:Why,How,and How to Proceed?",Australian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Health(ACERH)Working Paper,2008,No.2.
[7]吴显华:《国内外农村医疗保障的政府规制比较分析》,载《医学与哲学》,2008(1)。
[8]张再生、陈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国际比较》,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9]Bennett.S.,Creese.A.and Monasch.R.“Health Insurance Schemes for People outside Formal Sector Employment”,WHO ARA Paper,1998,No 16.
[10]任静、程念、汪早立:《日本医疗保险制度概况及对我国新农合制度的启示》,载《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2(3)。
[12]刘晓莉、冯泽永、方明金等:《日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11)。
[13]Imai.Y."Health Care Reform in Japan",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2002,No.321.
[14]赵永生:《劳者有其保——日本职域医疗保险的发展与改革》,载《中国医疗保险》,2009(3)。
[15] Ikegami.N.and Campbell.J.C."Japan's Health Care System:Containing Costs And Attempting Reform",Health Affairs,2004(3):26 -36.
[16]Henke.K -D.and Schrey?gg.J."Towards Sustainable Health Care Systems:Strategies in Health Insurance Schemes in France,Germany,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a Comparative Study",Diskussionspapiere//Technische Universit t Berlin,Fakult t Wirtschaft und Management,No.2004/9.
[17]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8][美]查尔斯·沃尔夫著,马洪、孙尚清主编:《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33~42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19]刘祖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载《江海学刊》,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