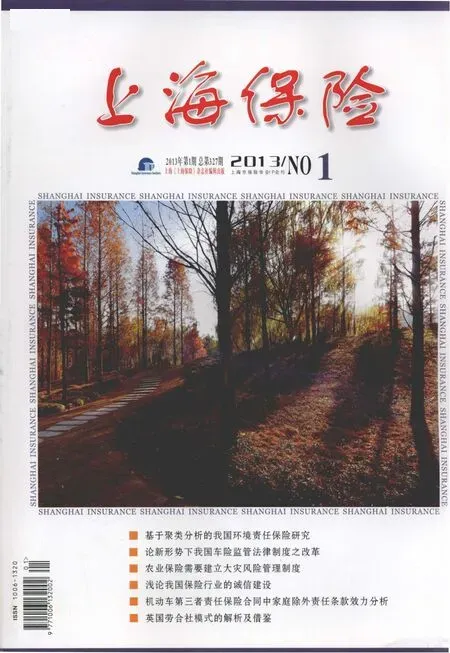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效力分析
吴峻雪 涂 君
一、案件内容
张某就其轿车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险,保险期限自2010年12月11日至2011年12月10日。其中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机动车商业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附加投保不计免赔率)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商业险保险单正面的“明示告知”一栏第一条载明:“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对应的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五条第(一)项载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保管的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原审查明,投保单上的名字不是投保人张某所签,保险公司也没有对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
2011年5月23日11时40分许,张某驾驶其轿车在其自家楼下由南向北倒车时,碰撞到行走至此的儿子小张,造成小张当天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在倒车时未确保安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张不负事故责任。在派出所主持下,张某与其妻陈某达成损害赔偿协议,约定由张某向陈某赔偿71.0667万元(其中医药费107元、死亡赔偿金63.67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丧葬费 2万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500元和衣服损失300元)。陈某于2011年6月15日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张某赔偿款。张某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以受害者小张系张某之子为由仅同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张某遂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0407万元,在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50万元。后一审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付张某保险赔偿金61.0407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遂提出上诉。保险公司认为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故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
二、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基本含义
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是指保险人在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中规定,被保险人驾车造成其家庭成员人身伤害的,保险人对其家庭成员的伤害不负赔偿责任。在不同时期,许多国家的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载入这一条款,但对其态度和效力认定有不同看法。上述案例中当事人的争议主要也集中于家庭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
我国目前各大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中一般设计有“家庭除外责任条款”。例如《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第六条规定:“保险车辆造成下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都不负责赔偿……(二)私有、个人承包车辆的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员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太平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第六条规定:“保险车辆造成下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员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所有或代管的财产。”等等。但是,从立法情况看,我国《保险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有明文的确认。由于立法和司法界未明确表态,保险业又普遍坚持这一条款,对于家庭责任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将结合美国保险法理论的相关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审判,对上述案例进行评析,并对三责险中家庭除外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分析。
三、美国保险法中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法律效力问题
在保险业发达的美国,许多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均有“家庭除外责任条款”,但法院对“家庭除外责任条款”的基本态度是:该条款违反了“公共政策”,应当将这一条款作为无效条款对待,除非保险人有非常强势的相反证据证明该拒赔不违反公共政策。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通过“Bishop案”“Lewis案”等案件,美国保险法学界目前持以下观点:“家庭除外责任条款”违背了公共政策,通常情况下应当从保险合同中删除,保险公司对保险人造成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害应予赔付。这一观点已经写入了美国保险法教科书。
美国法院对“家庭除外责任条款”进行规制并确认为无效的主要理由表现为:
1.“家庭除外责任条款”不同于其他除外责任条款,其目的在于防止“道德危险”,即防止家庭成员互相之间为获取高额赔款合谋欺诈保险人;而其他除外责任条款的目的则在于合理地控制风险,如“未取得驾照驾车免责”的除外责任条款是为了合理限制没有驾驶资格而驾车的风险。
2.被保险人与其家庭成员合谋欺诈保险人的情形只是少数情形,很少有人愿意通过撞伤自己亲人的方式获得保险赔付,因此,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已经超越了保险人意欲解决的问题,在法庭看来,“合谋和欺诈仅仅是例外,而不是原则”。如果没有非常强势的相反正当理由,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即违反了公共政策。
3.对受害人因车祸受到的伤害进行补偿是一项公共政策,这项公共政策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色彩,如果不对受害人进行补偿,明显有悖于社会正义。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已经为驾驶机动车颁布强制性金融责任法案的司法管辖区,都会认定机动车责任保险保单中的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无效。不过,已经颁布强制性金融责任法案的司法管辖区,也有些仅仅在机动车责任保险的强制性最低保障范围内,宣告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无效。另外,也有少部分司法管辖区,尽管已经颁布了机动车金融责任法,但是仍支持汽车保险保单中的家庭除外责任条款有效。
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在我国法律语境下的效力分析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指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的保险。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则将家庭成员从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范围中排除。认为这一免责条款有效的主要理由是:家庭成员之间侵权责任是否存疑、侵权人因保险而获利、条款无效将诱发道德风险等,针对上述观点,笔者分述如下。
(一)侵权责任与保险责任的区别与联系
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有一定联系,但又相互区别。其联系在于:①侵权责任可能引发保险责任。②侵权责任与保险责任均具有对受害人损失的补偿作用。但并不能因为以上联系就认为保险责任的范围和性质等同于侵权责任。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①并非被保险人所有的侵权责任都能引发保险责任,如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毁,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承保范围。②功能上的差异。侵权责任具备补偿功能与惩罚功能(威慑功能),即通过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补偿而对加害人进行惩罚,也因此具有预防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社会功能。保险责任的功能最主要体现为对受害人进行补偿。这是第三者责任险最基本的功能,是一项“公共政策”。它并非狭隘地仅仅为个案服务,而是集社会之力,对受损方的利益进行弥补。保险责任并不具有惩罚加害人的功能,相反,在被保险人支付对价的前提下,由保险人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可以减轻侵权人(被保险人)的责任负担。在我国台湾地区,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保险与汽车责任保险系各自独立的制度,并不挂钩。汽车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为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提供保险给付,被保险人有无侵权责任在所不问(加害人应负侵权责任时,保险给付有减轻其责任的作用)。综合言之,侵权责任在于强调人的行为自由、自主性及自己责任原则。保险责任则在于分散危险,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安全。
(二)家庭成员之间的侵权、赔偿责任与保险责任的关系
1.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
有观点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无侵权。这一观点起源于家庭隐私权。隐私权的实质是对专属于个人之私生活领域加以保障,避免他人、公众、社会侵扰之权利。世人常以其作为主张法律不介入家庭冲突的理由,从而主张家庭冲突的自我调节。美国法院1965年Griswoldv.Connecticut一案以“婚姻隐私理论”(Doctrine of Marital Privacy)为由,回避审理夫妻之间的对抗方式及在家庭内部所发生的冲突。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即为司法所管辖,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地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承认。如英美法等国家把虐待作为对配偶权的违法侵权行为而负赔偿责任。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看,家庭成员侵权案件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家庭法的权限包括决定是否判决离异,以及在何种前提下导致婚姻他方获得婚姻补偿的权利。例如,NWANKWO v.KIMBERLY NWANKWO案为夫妻之间关于儿童监护权提起的诉讼。如果违反了一般法律义务,如配偶一方对另一方造成了身体伤害等,当然也应适用侵权法。Isabelle S.SCHWARTZ v.Morris SCHWARTZ的案件中有同样的详细论述,身份并不能使得行为人具有免于起诉的权利。从上述立法和司法实践可知,在法理上家庭成员之间并非不存在侵权,而是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相比,冲突需要达到较高的程度方可纳入法律调节范围。
案例中,张某由于过失剥夺了儿子小张的生命权,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使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关系受法律调节而不能仅由家庭伦理进行调节,张某理应对其致小张死亡的后果承担法律上的侵权责任。
2.家庭成员之间侵权赔偿与保险责任承担
有观点认为,家庭成员之间虽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但由于家庭财产混同,侵权人若赔偿,也是只将钱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赔偿义务无法实际履行。如果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侵权人将因此获利,故保险责任不存在。还有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家庭)虽然实际上因交通事故遭受了损失,但由于该损失并不是因为被保险人承担了法律上的赔偿责任引起的,因此并不属于商业三责险的保险责任。
首先,上述观点混淆了应不应赔偿与能不能即时赔偿的概念。案例中,家庭成员侵权造成的损失实际存在且能够计算出损失额,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及赔偿额度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侵权并无二异。即便当前无法实际履行,也不排除将来得以实际履行的可能性。如夫妻因此离婚,财产分割后,小张之母可以向张某主张赔偿;又如若小张未死亡,只是受重伤,则在其成年后,可以以自己名义向张某提起赔偿之诉。其次,上述观点未理清侵权与获利之间的关系。在侵权行为法上诚有“侵权人不得从侵权中获利”之说,但张某并未因侵权而获利。张某实际对外支付了医药费、护理费,产生了误工费等损失,对小张的财产性损失已作出实际弥补;而张某因丧子产生的感情上的伤痛,这种人身精神上的损害是无法进行经济衡量的,故并不存在张某因过失侵权行为获得额外的利益之说。再次,上述观点对责任保险承保对象也存有误解。责任保险实际承保的是第三者因被保险人的行为造成的损失,而非被保险人自身的损失,承保损失的范围则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范围。即便案例中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处于同一个家庭,财产具有同一性,也不能就此认为保险赔偿的对象是被保险人的损失。如上文所述,保险责任功能主要体现为对受害人的补偿,并不具有惩罚加害人的功能。张某投保就是为了分散驾车风险,不能因其侵权行为未受惩罚或惩罚减轻而否定其与保险人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
(三)家庭成员道德风险不应通过保险合同进行防控
在类似案例中,保险人拒赔援引概率最高的理由就是家庭责任免除条款可以防控道德风险。从保险公司利益角度看,制定家庭责任免责条款可以保护保险人免受欺诈,亦可使保险人免于同一家庭成员合谋对其进行的诉讼。然而,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出,以牺牲家庭成员人身安全谋求保险金利益的方式成本过高,即便保险合同取消家庭责任免除条款,绝大多数投保人也不会故意采用这种方式谋取保险金。当然,道德风险在现实社会并非不存在,但正如美国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对Lewis by Lewis v.West American Insurance(ky.1996)一案判决所认为的那样,家庭除外责任条款与公共政策相违背,不符合责任保险最重要的正义——补偿受害人原则。两者相权,该条款无效。
同时,家庭责任引发的道德风险,作为小概率事件,在车辆三责险“大数法则”下可以忽略不计。上文Lewis案的法官指出:“自从Bishop案发生以来,我们从未看到,当事人也从未提供过任何证据,以此证明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增加了合谋索赔。”保险人以防范小概率的道德风险为目的,却将其余并不存在道德风险的家庭责任排除于车辆三责险保险责任之外,缺少法律及社会意义上的正当性。笔者认为,保险欺诈的道德风险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刑事侦查及诉讼手段确认和排除。通过国家公权力来治理道德风险,较之保险人制定合同条款来规制,将更为有效和直接。家庭责任道德风险一旦查实,保险公司若已作出保险赔付,有权向实施欺诈的被保险人及其他获利者追偿并要求赔偿损失。
综上,通过保险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家庭除外责任条款应当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格式保险合同中废除,以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
五、结语
保险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明进步的保障和标志。通过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而对偶然损失进行分散,保险具有损失分摊、偶然损失的偿付、风险转移和赔偿的特点。正是由于保险这些特点,才使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如可赔偿损失、减少担心和恐惧、投资基金、损失预防和增强信用等。同时,保险的社会成本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营费用的支出、欺诈性索赔与夸大性索赔,这些应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牺牲。对于保险人而言,所谓的防范道德风险和防止欺诈合谋的家庭除外责任条款也应作为在保险业发展时保险人所应付出的“必要牺牲”。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是保险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作为“损失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保险就是投保人“将风险转移给了职业的风险承担者”,“以确定的小额损失替代了发生不确定巨额损失的可能性”,从而转移社会风险。因而保险的根本职能是经济补偿,其目的就是要把被保险人的损失风险转移给保险人。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保险人应当以诚实信用为准则来参与市场竞争与市场开拓,凭借其优质的保险产品和后期服务来占领市场。同时在交强险连年处于亏损状态以及保险业向外资企业全面开放的情况下,保险人更加应当以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牢固树立诚信理念,完善服务标准,规范服务程序,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促进保险市场健康、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