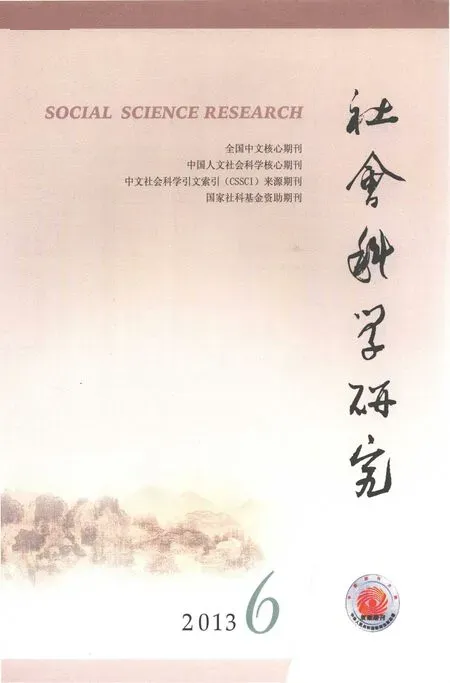史料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周维东 邱 月
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文协”》)带给读者的感受中,史料梳理与辨析应该是最强烈,也最有特色的一点。在该书《序》言中,温儒敏先生特别在文章末尾,不惜篇幅强调了史料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足可见该书在史料学研究方面的“典范”意义。文学史既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科学。在现代文学史这样一个公认早已经走向成熟的学科中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段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抗战文学研究已经持续多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关于“文协”的许多基本史实,学人们其实并不完全清楚。不少通行的说法,只能说是学界的“公误”,其中个别的还是一望而知的低级“公误”,足见学界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个学科的史学性质。从《“文协”》引申开去,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很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这对经常有人抱怨“每一块石头都被摸了不止一遍”的学科来说,真是有警醒之处。
与此同时,在重视史料日渐得到共识的今天,“史料学”研究的一些失范之处,也应受到学界重视。当下史料学研究的“失范”之处,在我们看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史料而史料,为考证而考证,史料研究变得过于琐屑。有些问题不能说不重要,但如果单纯为这些问题而考证,至少意义不大。在网络和报纸传媒文化的影响下,部分考证和史料研究甚至走向了低俗化、猎奇化。与作家思想变迁、创作背景等关系不大的婚姻生活,甚至在当时就说不清楚,也不值得说清楚的作家私生活传闻等,也变成了不少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考辨”对象。第二,史料研究方式不够规范,本该客观严谨的考证,变成个人臆断或猜想,考、证、辩、论等不同手段与研究方法,往往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界限模糊。第三,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有意择取史料,以便形成“新论”、“新解”。这样的情况常常还有麻痹性,对某些史实不了解的人,常常还为其所骗。史料学“水深”,即使一生钻研史料考证的人,也不敢说对每一个领域都处处内行,这给了“史料学”研究弄虚作假的机会。以上提到的种种失范表现,有些是不知学术规范,有些是不愿刨根问底,有些则是急功近利。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虽然涌现了大量的史料学成果,但真正对中国现代文学已有结论产生冲击的并不多。甚至,让我们感到信服的作品也不多,很多作品只是充当了当今学术GDP生产的一份子而已。正因为此,《“文协”》这部“典范之作”的意义,就更值得评说。
其“典范”意义的第一个方面,是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说到问题意识,其实是个可大可小的范畴。纠正一个错误是问题意识,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也是问题意识。但从问题的意义而言,后者显然更加重要。说到底,“问题意识”是个眼光问题,小问题大视野,“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是史料学研究的至高境界。说到这,可能需要我们明确的一个观念,其实并没有纯粹的史料学研究,也没有纯粹的史论研究,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研究。所以,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必然不拘泥于考证,对研究对象有全面的把握。王晓明教授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一文,将目光锁定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却对整个五四文学传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之所以要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入手,是因为它们是其“重识”的节点,打蛇打七寸,抓住了问题的节点,大的问题迎刃而解。段著将目光锁定在“文协”,虽然如其导论所说,主要是关于“文协”有诸多史料不实之处,但纵观全书,其真正用意还在于“文协”是整个“抗战文学”研究的“节点”。如同《新青年》同人在五四文学中的作用,“文协”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纽结点:抗战文学的基本格局随“文协”的确立而确立;抗战文学的诸多文学活动、思潮、论争与“文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把文协的史实澄清了,抗战文学研究如同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部作品有没有“问题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有没有对一个领域产生启示作用,即作品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二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否与庸常看法拉开距离,言他人未言之事。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很多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学著作,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盘散沙,看时觉得新鲜,过后收获甚微。《“文协”》并不是这样,它的主要章节都牢牢抓住了抗战文学中的问题。譬如,关于“‘文协’历届常务理事考论”、“老舍在‘文协’中领导地位之建立”,看似是一些琐碎的人事关系,其实是关于抗战文学格局确立的问题,尤其是“左”、“右”文人博弈平衡的问题,是抗战文学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再如“‘有关’与‘无关’之外”,涉及到“文协”作为抗战文学的领导机关,其行使这个功能时运作的细节;“通俗文艺运动与‘民族形式’之争”,是抗战文学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论争;“战地文艺的拓展与推进”、“‘抗战文艺’的历史呈现”,是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文学传统秩序与文艺方向”则谈到抗战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的问题。通过一点一滴,为抗战文学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面目。在大视野的指导下,难能可贵的是,段著对很多微观问题有独到的看法,如其对“抗战无关论”的分析;对“民族形式”论争的看法,言他人所未言,十分具有启示意义。在这些细节上,研究者没有敏锐的视野和扎实的考证功力,都很难实现。其实,学术研究最难的一点,莫过于将敏锐的视野和扎实的考证结合起来,这是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老问题,但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多。
《“文协”》“典范”意义的第二方面,是打破既有文学史观念的藩篱,探析到历史的幽微。在这方面,该书有两个明显的特色值得重视。第一个方面是作者自己将文学史回归到社会史,通俗地讲,就是让文学史回归生活。所谓将“文学史回归生活”,就是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想象历史,将历史人物作观念化的解读。段著很多方面的创新,都来自于这种认识历史的方法。譬如在探究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的历史过程时,作者就注意到了中国社会中一个普遍现象——派系斗争。在很多历史书中,“文协”的成立理所当然,老舍成为“文协”领导者也是“当然中的当然”。然而设身处地来看,在左有“左联”旧人,右有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文协”中,老舍其实很难说一开始就具备了领导者的条件。只有回到当时的生活中,这个问题才好解释:正是在“左”、“右”对峙当中,大家普遍接受的老舍才能成功“逆袭”。再譬如,关于“民族形式”论争——几乎是文学史上最费解的论争,费解的地方在于:论争的各方众说纷纭,很多时候并没有形成焦点,但却吸引了大量人参与进来;向林冰关于“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说法如此幼稚,提出者作何考虑?这种争论放在具体生活当中,其实也不难理解,“民族形式”既是一个有待争议的概念,又是一个未来文艺走向的抓手,身在抗战文学中的人岂有不争论的理由。再者,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运动蔚然成风,通俗读物编刊社通过这种争论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合情合理。其实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的文坛依然可见,换位思考一下,其义自见。将文学史回归到社会史,就史料学研究的意义而言,一是要求拓展史料考察的范围,再是改变对待历史的眼光。
再一个方面,便是作者考察了文学史场域中的幽微之处,譬如“寿郭”、“骂战”等。“寿郭”与“骂战”与文学史的关系,如果不觉察二者意味深长之处,似乎并不明显。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照实理解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又显得费解。譬如“寿郭”,在国难之际做寿并不值得夸耀,况且频频为之、大张旗鼓。再譬如“骂战”,若论“与抗战无关论”有何不妥之处,实在也说不上来:在持久战争的对峙消耗中,让人永远斗志昂扬,太过苛刻;况且若回顾整个抗战文学,与抗战无关的文学比比皆是,为何揪住梁实秋不放呢?问题的玄妙之处,便在于这些事情“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幽微之处。很多历史的真相并不在表面,而是暗流涌动,只有从表面事件的裂隙入手,深入辨识这些幽微之处,才能对历史的复杂性有真正的理解,对历史中人的处境有“理解之同情”。这些往往为过分“实沉”的史料学研究所忽视的幽微之处,通常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文协”》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典范”意义,当然不止这两点。其实书中体现的“典范”之处还有很多,譬如史料的发掘、收集、考证、整理、证伪等等,都有值得言说的地方,当下史料学研究的很多问题也出在这些方面。但就著作的创造性而言,这两点可以说是此前的著述普遍重视不够,或者说表现不够突出的地方,因而也是最值得当下研究者重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