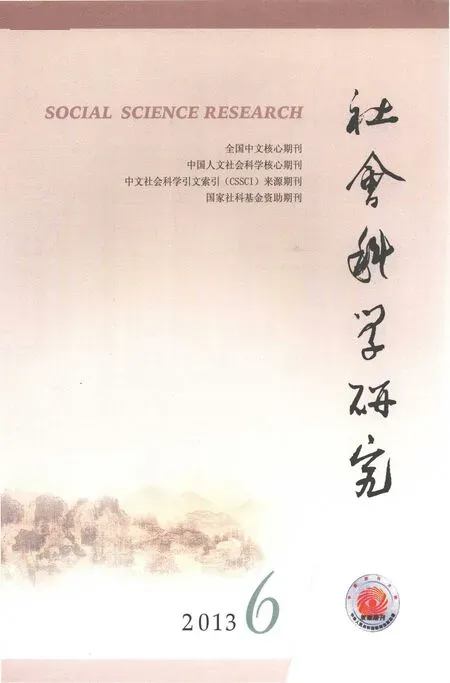中国传统美学之生命意识与“本真”诉求
李天道 侯李游美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美”是通过当下的“人”,即现代存在论所谓的“此在”,从当下存在的“人”的生存中显现、生成的,所以,“美”是“与天地共生”、因“人”而彰、发生构成于纯粹的原初域“道”的,其自身的缘在构成态表征为“自然而然”,由此,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所谓“美”,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缘在构成域。这种审美域,生成于一个自在自为、自由自化、“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1〕,是审美者通过回复到本心本性,通过内在超越、反观自身来体会、体悟与通达的,是“此在”之去蔽与揭蔽流的生动呈现。这种去蔽与揭蔽也就是“此在”于敞亮中的不断构成流。就审美活动而言,即是审美者经由任情适性、自由自得、直观感悟,直觉体悟,以达成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即心即佛,进而达成的顿悟“人”生真谛的“本真”生命域的审美流程。审美活动中,只有达成这种生命域,即审美域,审美者才能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海德格尔说得好,唯有“此在”是存在在此显现的可能途径。“只要此在存在,在此在中就有某种它所能是、所将是的东西亏欠着。”〔2〕“亏欠着”的、“所能是、所将是的东西”,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必须靠体悟。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推崇任情适性、自由自得审美域的实质就是强调对“此在”的体悟。这种体悟的进程是,通过“由己”、“返身”、“归朴”,“还原”到“自我”,即“此在”,在去蔽与揭蔽流中不断超越“非本真”存在者,并且在其构成中体悟到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非本真”存在者。这种“本真”审美域的本质在于“自我”“本真”生存,以充分地显现生存的意义与存在中的生成流态势。应该说,“本真”生命域,即“本真”审美域不仅是一个生存的过程,而且总是从其“本真”生存中领会、显现着“自我”存在。它“原发于本心本性”。其意义的生成不是外在的给予,而是通过各种活动方式促使内在“本心本性”的显现,具有一种内向性和自明性。因此,这种本来具有的内在的“心性”显现于外的过程又被称之为一种自我呈现或内在超越。由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诉求就是“身心合一”、“情景合一”、“意象合一”、“心物合一”,就是“人”与存在、“人”与道的相融合一,也就是“本真”生命域与审美域的达成。所以,只有从存在论美学和“人”与存在交相化合的“本真”审美域构成论切入,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才可能揭示其深层内核。
一、本真生存与本己自由
就当今现象学存在论的视域来看,有关“人”的意义与审美价值的追问,其实质上应该是一种涉及到“本真”性的问题,是来自个体生命内在精神向度上对自我的“本真”性的追问,而不是一个“人”追问他“人”的价值,也不是对“人”的总体价值的追问。因此,只有从有生命的个体的“人”的存在特性出发,才能完成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的确,“人”是宇宙自然间晓知自身存在着的生物,这种“晓知”,是通过体悟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此在”的体悟,也就是对“人”的生存与生命呈现态势的体认、考察与感悟,特别是对“人”的生命在时间性中的呈现流程,即“人”自身的生存态势的体认与研究才能进一步追问“人”及其生命的意义。 “此在”是“人”,但“人”不一定就是“此在”。人要成为“此在”,首先必须有体悟与感知自身存在的能力。由于“此在”具有可能性,被可能如何生存所规定,所以“此在”可能选择自身、获得自身,也可能失去自身。因为“此在”可能是它自身,所以也可能不是它自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失去自身的“此在”与获得自身的“此在”都是“此在”。同时,他又把前者,即失去自身、没有立足自身生存的称为“非本真生存”,把后者,即获得自身,立足于自身的生存称为“本真生存”。 “此在”在根本上属于“人”自身。“此在”,即“人”的生命意义在于他的存在,但“人”的生命存在不是预设的,而是从存在中去获取生命的意义。作为生命的存在,“人”存在着,并且清楚地知道自身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生存着。“人”的意识是自觉的,动物则是不自觉的。动物和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身同自身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身的生命活动。“人”与自身的生命活动超越动物性的直接同一,“人”使自身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身意志的和自已意识的对象。“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人”可以使自身生存活动的目的以一种可能性内存于自我意识中,以观念的形式构筑他尚未进行的活动及其结果,并由此引导自身不断超出自身物种规定的活动尺度,由此,可以说,“人”自身的生存态与价值意义域是可以自由选择、不断超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努力发现自我生存的现状,通过“祛魅”、“去蔽”,克服自我的限制,达到超我的自在自为境域。自我意识是把“人”自发的生存态势变成自觉的体验和认识,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缘由与价值。只有自觉到自我在做什么,做的意义何在,以及如此做的效果,自我才真正成为自身,也才能发现由此带来的充实的精神快乐,获得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发现与觉醒是一种自我性的体验,而恰恰是这种自我性引起了自觉,进而超越“沉沦”,真正面对自身,回归到本己,作为最本己的自身,自身领会自身,筹划自身,掌握自身本身的自由。自身面对,自身承担,属于“本真”的自身。在现象学存在论,这种发现与觉醒就是“去蔽”。存在者的存在流程与生命活动态势,是通过“此在”的显现来表征的。可以说,“此在”即“人”生命活动流程的动态呈现。如此,“此在”,即“人”的生命活动与生存态势同样也表征着“此在”是“在世中展开其生存的”。所谓“在世中展开其生存”就是人在生存流程中呈现其生命意义。“此在”“在世中展开其生存”,换言之,即“此在在真理中”。这是人生的真相。但是,因为作为“此在”,即“人”又是以被抛、遮蔽、筹划、沉沦于“在世”的方式存在着。哪里有“遮蔽”,哪里就有“去蔽”,所以,“此在”,即“人”生存态势的真相是“遮蔽”与“去蔽”的合一、“非本真”与“本真”的合一。所以,“人”“本真”的生命呈现流程与生存态势,既是“此在”处于“去蔽”态势,同时也是“此在”处于“遮蔽”态势,即“本真”与“非本真”、“去蔽”与“遮蔽”合二为一的态势。在“此在” “去蔽”、“敞亮”之时,也就是“此在”处于“遮蔽”之时,“去蔽”和“遮蔽”合一、相依相存。由此,“此在在真理中”也就是“此在”在“不真”中,而“此在”在“揭蔽”中,也就是“此在”在“遮蔽”之中。〔4〕“此在”,即“人”具有“去蔽”、敞亮和“遮蔽”的双重属性。这样,“人”的生成态势则是通过“此在”的呈现与展现来“去蔽”与敞亮,那么“此在”的呈现与展现态势同样也表征着“此在在真理中”与“此在在遮蔽之中”。
存在者显现自身就是存在者处于一种“去蔽”与“澄明”态势,即无蔽态势,也就是让存在然其所然、存其所存。存在者只有在“去蔽”、敞亮、澄明之域,才能显示自身,成其所是,是其所是。而存其所存,自然而然,就是自由,因此“去蔽”、敞亮、澄明之境就是自由之境域。所以,海德格尔指出:“向着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自由便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5〕所谓“让存在者存在”,海德格尔解释说:“作为这种让存在,它向存在者本身展开自身,并把一切行为置入敞开域中。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 (aussetzend),是绽出的 (ek-sistent)。着眼于真理的本质。”〔6〕可见,“让存在”是自身的展开,是自明的。由此,不难看出,被“遮蔽”的生存活动态势就是“非本真”生存态。所谓“非本真”不是指不真实,而是存在者处于一种“遮蔽”状态。但这种“遮蔽”同样是属于存在者的一种生命活动态势。并且它为揭蔽、去蔽,乃至无蔽的生命活动态势呈现着其所固有的、原初的、最基本的东西。〔7〕如此,承认“本真”与“非本真”、“去蔽”与“遮蔽”的合一态势,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其所是、然其所然、如其所如、自其所自。这自然是由“此在”的生命的自由活动与生存的自在展现态势来呈现的。而存在者生存的自在展现态势自然既是存在者处于“揭蔽”、“去蔽”与“无蔽”生存态势,同时又是存在者处于“遮蔽”生存态势。前者为“本真”生存态,后者则为“非本真”生存态。
“人”之所以可以通过“去蔽”、澄明以领悟自身、选择自身、获得自身,也可以失去自身,因为“人”本身是一种可能性,既可能处于“去蔽”态势,同时也可能处于“遮蔽态势”,可能是“本真”的生存,也可能是非“本真”的生存,从而遮蔽存在的意义,失去自我。海德格尔认为,“人”之所以能够于“本真”生存中得以成为能够领会存在意义的存在者,是因为“人”就是“此在”本身。“此在”乃是一种时间性结构。而时间性结构本身就分为“本真”生存性结构与日常沉沦于世的“非本真”变式。因此,要领会存在意义的“本真”域,就必须揭示“此在”“非本真”生存的时间性结构。由于被抛性的作用,“人”的存在始终处于一种本质性的不安之中。可以说,正由于“人”自由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在其“实际此在”中必然是以一种自由能动的方式沉溺并局限于他外部的现成“世界”之中并因此而不自由。这种本质性的沉溺态势在海德格尔就是“此在”的沉沦。“人”沉沦于现成“世界”中,从而既遮蔽了自由的本质,也遗忘了“本真”生存的态势,进而始终为此种遮蔽和遗忘所攫获。沉沦于世,日常操劳的“此在”不是“人”自身,而是“常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个体的“人”融入现成“世界”的整体共相之中,从而失去个性的“人”是“常人”。应该说,“常人”就是“平均化”了的生存主宰者。“平均化”使每个“人”互为尺度,从而遮蔽了“本真”生存。所谓“平均化”,就是“常人”采取一种物态化的,或者说是物质层面上的态度来对自身存在的体认。存在的生命活力与创新性、趋新性、自在自由性,在这里被省略为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具有物质形态的事物。在这样的态势,“人”们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价值评判标准,以审视、衡量、想象自身的未来。这种思想完全阻遏了生存的可能性之时,个“人”的社会活动由此而被限定在肤浅的、表层的经验层面。当“人”日以继夜、周而复始地生活于这单调、同一的生存模式,其本身显然已经被异化为经验的工具。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人”的“沉沦”。“常人”没日没夜地想望于将来的事物,从而使自身蓬蓬勃勃的生气散于外在的物质追求,进而失去自我。对这些事物的判断为“常人”看法所主导,缺乏对他“人”或事物本身深入的真正的理解,生命的意义、存在的真谛与真相被遮蔽着。当然,尽管处于这样的一种生存现状,也是由“此在”的时间性所决定的,因此,“人”自身是可以自由选择其生存的样态的。作为个体,“人”都生存在特定的生活世界。能不能看穿“人”世间一些被遮蔽的真相,关键在于以哪一种感觉和认知模式来对生活环境进行观察与审视,进而展开自身的思考和判断,由此而逼显出“真相”,绽出“本真”,以及那些未被“常人”语言系统所意指的“人”或物。这样,日常操劳所处的无休止的“非本真”生存就可能被阻止而“到了尽头”,而显现出来的则是只属于“人”自身的时间性。这种仅仅属于作为个体的“人”,即“此在”的时间性,应该就是“本真”性生存态势。从这样的现象学生存论视域出发,作为个体的“此在”,即“人”所直接面临的,也即是真正的“他人”和事物本身。这样,“人”的生命意义及其存在的意义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
“此在”,即“人”必须从预成的“在世”中剥离出来,去除尘世杂念,超越各种各样的世事杂务,解脱一切庸俗低级的情感羁绊,成为个体性的人,在“非本真”态势中来审视“无意义”生存的自身,才能彰显“本真”的生存态,进而领会“本真”存在的意义。要实现这一点,就要从“常人”中逼出“本真”的独立“人”格,彰显“本真”的“此在”。“本真”“此在”是断了世俗因缘的“本真”个体。这里,“本真”“此在”主要是指从“常人”,即一般“人”中抽离出来的、断了世俗因缘的、超然挺拔、卓尔不群、我行我素的“人”自身。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人”对自身自由的关切体现为生存理想与生命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人”被抛在世中,与“常人”为伍,陷入生存困境。“常人”的存在为“非本真”的“此在”,是被摆置了的、异化了的、千人一面、缺乏独特个性的“人”。现成“世界”中,技术的控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低俗生活以及虚伪矫情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人”生命质量的低下与生存的困境。因此,作为孤独无援、单独个体的“本真”“此在”,必须从“常人”中超越出来,否则无以获得其“本真”性,而只是苟且于日常事务、没有生活质量和生命诉求的一种“非本真”的“我能”,不涉及到可能性、选择性和具体能做什么、生命价值等存在论问题。对此,海德格尔指出:“那个自己并不是‘我’之最富代表性的规定,具有奠基性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接着,他又强调指出,只有在我们中才找到自己。他认为,“在‘我们’这个层次上,也有本真本己性与非本真本己性之分。非本真本己的‘我们’是‘常人’,本真本己的真正的‘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像一个人一样维护着自己的存在。”〔8〕要作为“本真”的“此在”,要确认自我,维护自身的存在,就必须要有创新精神,通过自由的生命体验,穿透这个“人”世间的幻相而直达生命的“本真”。“本真”和“非本真”是合一的,是绝对不能够分割而存在的两种生存“态势”。“本真”的存在是超常规的,从“非本真”角度看,是有别于理性思维的、非理性的。因此,决不能让一些固有思维模式和“观念”成为自我存在的规则,从而束缚自我,遮蔽“本真”“此在”。“此在”历史性地被抛于“本真”与“非本真”态势相依相存、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关照之中。因此,应该说,海德格尔所指的“本真”还是取决于“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一体两面、合二为一,取决于共同性与个别性、实体性与虚体性、关系性与独立性、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相互关涉之中。“此在”,即“人”在在世中操劳,在日常事务中钻营,在“常人”中蝇营狗苟,从“彼”处领会他的“此”,“彼”“此”双方、人我之间,对象性地存在并彼此赋予生存的意义。在这种“忘我”中,人我之间、物我之间、“彼”“此”双方都迷失与遮蔽了自身的本性:“此在”向“非本真”倾斜,进而沉沦为“常人”;“物”则沦陷为必须被“常人”赋予意义的对象;而日常在世与一般现成的“生活世界”则只能表征为“非本真”样态。从发展的视域讲,“本真”境域并不是没有对象,就好比是信奉神灵的“人”赤诚地面对邻“人”,“本真”“此在”面对“本真”对象,“此在”同样是从“本真”的“物”或“他者”、“彼者”的“本真”态势中感觉,进而领悟、了悟到“人”自身之“本真”意义的。依顺天道、随任自然、存其所存、然其所然,以成就“物我”、“彼此”双方之本真本性。按照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也不难发现,“本真”和“非本真”的“此在”生存态势本身就是无中介的同一。海德格尔强调“本真”与“非本真”的合一性、生成性、构成性与同一性,但这种合一性、同构性、生成性绝对不是直接、单调的同一,而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对立、相反相成中相互牵制、相互彰显,是现象学生存论意义上的相反者相成、相对者相依。海德格尔强调指出,“此在”的实际生存态势中本身就包含有封闭和遮蔽。就其完整的现象学存在论视域来看,所谓“此在在真理中”同样意味着“此在不在真理中”。〔9〕“此在在真理中”与“此在不在真理中”是相对相应的。所谓“本真”和“非本真”,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上更多地是对“真理”与“非真理”这一必然、本然事件的描述。“真理”与“非真理”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相依相存的。当然,存在之真理,生命之意义生成的场所无疑仍然是“此在”,因此,“真理”和“非真理”的发生结构、生命价值与“此在”的“本真”和“非本真”生命活动、生成态势原本就是“一”,是同一事件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感应、相互存在的生动呈现与表征。“本真”“此在”在“天命”赋予之下“去蔽”与“揭蔽”,从而使“本真”呈现的同时,由于“此在”的抛入性、有限性、边缘性、封闭性而又“遮蔽”“本真”,从而成为“非本真”。但极端的“非本真”的日常生活处境中又蕴藉着进一步“揭蔽”与“去蔽”的可能,包含着“本真”的敞亮。可以说,海德格尔在对“本真”生存态势发生结构的描述中,其“本真”观念中又呈现出一种生成性、构成性意义。“真理”即“无蔽”,其本身就意味着对某种“遮蔽”态势的“揭蔽”与“去蔽”。“此在”被抛于现成“世界”中,从而承受“揭蔽”的天命,进而不断地被抛于“本真”与“非本真”之间。从根本上看,“此在”无法单独持守“本真”态势,这也是“此在”最根本的有限性。如果“本真”“此在”的确存在,那必然是“此在”通过自由选择的结果。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人”只有被卷入“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去蔽”与“遮蔽”的存在态势中,才真正成为其所是的东西,而固其所然,然其所是,以成就其有限的本质。“此在”只能永远处于追求“本真”生存的途中,直面“沉沦”以承受这种被抛的不甘的命运,这也才是顺应自然,才是存其所存、道其所道、生其所生、是其所是,才是处于“本真”生存态势的“此在”。
这样的“本真”“此在”突出地呈现出一种个体性、自由性。这种个体性、自由性也就是中国传统美学所推崇的最自由、最充沛、真力弥满,洒脱自在、澄清俗务、本性逍遥、此心安宁审美域所显现的特性。这种特性的体现是“本真”生存、直面“本真”他“人”和事物本身、领会存在之意义的前提。而“本真”“此在”的自觉领悟与自由选择一定要陷入“非本真”层面,“本真”与“非本真”的合一性、生成性与构成性规定了“人”,即“此在”现实的可能性,“此在”要想看到一切而不受操纵,要想还原原初,还原“人”最原初的生存,即“本真”生存态势,真正成就“自身”,具有自由选择其生存态势的能力,就必须唤醒被遮蔽于心灵深处的那些与普遍性生命价值相关的欲望、冲动与诉求,由此而具备不被生活世界各种因缘关联或因果必然性所控制的绝对的否定性、超越性、自由性和创造性。当然,就另一方面来看,“本真”与“非本真”的一体两面性,同样决定了“人”,即“此在”,必然依“天命”而行事,由此,“人”,即“此在”的最原初、最根本的被抛性、个体性、有限性、边缘性和可能性得到彰显。应该说,这之中,被抛性、可能性是最具有海德格尔特色的思想。“本真”和“非本真”生存态势的相依相存、相互归属、相反相成、相对相应,自由选择其生存样态与生命流程则只是“人”生的一种可能性存在。正由于这样,因此“人”只是不断被逼回到“人”世生活中。应该说,“本真”与“非本真”存在的一体两面性决定了“人”,即“此在”,只能在不断被遮蔽与去蔽、揭蔽中存在与生存。
在现象学存在论看来,“本真”生存是本其所本、然其所然的生存,是自身为自身存在的原因和根据,所以它是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的,“本真”生存是自然而然的生存,是有因无因、有为无为、有得无得、有有无有、有性无性,独化自生,所生所在完全由己,不假外力,是敞亮本心,任其自然。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他者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在儒家美学,这就是“为仁由己”、“求仁得仁”。在道家美学,则为道法自然,自然无为,内缘己心,外参群意,目击道存,取法自然。
显然,现象学存在论的“本真”论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意识与“本真”诉求是一致的。受儒道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本真”审美域的达成过程是自得自明,内缘己心,外参群意,投身大化,身其所身,化其所化,敞亮之“己心”与万千生命交相融汇,随氤氲婉转之生气流连,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随着物象与灵心的相交互织,最终达成宇宙大千、天人心物一体贯融之域。故而中国传统美学认为,“人”心能视通万里,神游古今,视其所视,游其所游,发其所发,到其所到,而无所不至;最灵之心能体道、合道,以化自身清净之心永葆最灵之心;心之所在,有如诚者自成,道者自道,在者自在。审美者在审美活动中任情随意,让自然万物撞击自身心灵,心游目想,目其所目,想其所想,寓目入咏,即事游神,以达成与还原“本真”审美域。
二、“由己”“自明”与自我生存
儒家美学认为,“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是“由己”,是生命原初域的一种自明,没有预先的规定性,是“人”生命的自由卷舒,是自为的。如儒家美学所提出的“为仁由己”中所谓的“由己”就是依靠自身。“仁”审美域达成中的这种自由自为、自明自成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自明性,能赋予个体生命新的内涵。“仁”审美域达成中所呈现出来的自为态、自明态,既成就了个体生命向整体生命的超越,也成就了“人”于日常沉沦与“在世”中向“本真”生存的超拔。正是这样,个体生命本然、决然、“块然”①郭象《庄子·齐物论》注云:“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50页。、“掘然”②郭象《庄子·大宗师》注云:“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251页。地自其所自、因其所因、由其所由、道其所道、然其所然。作为“人”,“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一体相存的。“人”的意识之中,自然性的生存意识、生命冲动与社会意识,“非本真”性的沉沦与“本真”存在,即审美生存等意识共同存有,而后者更是抉择“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人”必然在对时间不断流动的深切体验中进行着自身的抉择。而“人”之为“人”的所谓“本真”生存态,就在这种自由抉择中铸就。“人”要成就从“沉沦”于日常世俗世界的“非本真”生存到“本真”生存的态势,要“本真”的、审美的“生存”,成就生命的觉悟,则必须超拔于“在世”。处于“本真”生存态的“人”在“常人”中孤独地行走,在与理性社会、世俗功利、其他个体“人”群、“常人”的“共在”中坚守本身的自由,保持自身精神的独立。“人”在世界之中“非本真”的生存是没有美学意义的。追求“本真”生存态的“人”必须放弃一切预设,只是身在其中,“由己”独立特行、去蔽“自明”,不让闲言壅塞视听,摆脱“常人”的制约。同时,不断地颠覆自我、超越自我,使自身永远处于流动之中,回到“本真”的自身,在生存的意义、依据、目标缺失的条件下“人”依然要到“场”。显然,这样的“人”已超拔了“常人”的特性,向着另一个精神自我,即“本真”生存态超越,自由自在,澄明透脱。依赖“常人”,被其所支配,根据作为“他者”的“常人”旨意去抉择自身的生存态,被“他者”所支配,从而丧失了自我的“本真”生存态,让“人”无法正视“本真”的自己,领悟自身。因此,要成就从“非本真”生存态超拔出来,走向或者回复到原初的、“本真”的、“切己”的审美生存是极为困难的。这也使得“人”的生存态总是在遮蔽与彰显、浑噩与清醒中游移,在沉沦与超越中滑动不定。习惯能铸就第二天性,促使“本真”被遮蔽,隐而不露。实际上,“本真”与“非本真”是相互彰显,互为一体的,“人”只有通过“非本真”的视域来看被“遮蔽”而“异化”的自身,才能通过“去蔽”与“揭蔽”来彰显“本真”的生命流程与生存态,进而体悟“本真”存在以及生命的意义,所以,只有在“日常”的生存态势与特定的心灵相交,独立的、个体的自我与“常人”合一,“本真”生存的超越性与日常的“沉沦”性相融中,才能够揭示出日常生存之“非本真”的“人”生态势,进而才可能把“人”带进到自我的生存体验之中,成就“本真”的审美生存态。
受古代生命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具有极为浓厚的崇尚生命的色彩,注重生命与人生,重视对“人”的追问,推崇并追求“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真”存在之审美域。如在“人”生价值论方面,荀子曾经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也为天下贵。”〔10〕《礼记·礼运》也指出: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11〕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强调:“天地人,万物之本也。”〔12〕“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13〕他们都认为“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本”,“人”与天地自然同体,作为天地之“心”之“本”的“人”可以融入宇宙自然,与天地万物相交同构,参与天地的化生化育,所以在天地万物中为最可宝贵的。同时,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人”与“道”的关系是相依相存,须臾不可离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4〕;“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5〕;“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16〕;“修身则道立”〔17〕。“道”不是远离人的异己性彼在,“道”与人是一体的,“道”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之生命意义就在于“行道”,因此,人应该时时、事事“弘道”、“体道”,以“道”为己任,与“道”合一是“人”天赋的使命。所以《中庸》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18〕“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9〕。“道”之意义的绽出是通过“人”之“性”的自明而实现的。“道”之意义的彰显源出于“人”的天性,因此“人”、“道”不离,否则,“道”将“非道”。因此,“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受此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与“道”合一、天人一体审美域,即“本真”生存审美域的构成与达成是“物”有所触,“心”有所向,“心”与“物”交、“情”与“景”融、“人”与“天”合、“人”与“道”合。同时,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妙契万有、神交众美的“本真”生存审美域的达成能够使人心定神闲、心气平和、处心有道、意得心定、内心充实、陶冶情操、纯洁情感、感化性灵、净化灵魂;通过“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活动,可以促使人“厚德载物”,宽容谦让,心胸像大地那样,厚实宽广,承载万物,生长万物,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从“本真”的境域体悟自我生命价值。应该说,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这种对人的重视与强调,从而促使其显现出鲜明突出的尚“生”贵“生”的生命意识。宇宙天地的审美意义就在于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生气盎然、氤氲变化、生生不已,对人的生命价值,儒家认为人贵于物,道家主张天人一体。对于不同生命,儒家主张凡圣一如,释家认为众生平等,道家则认为物无贵贱。对于生命所持情感,儒家主张兼爱万物,道家主张泛爱万众,都充满泛爱生命的仁爱精神。由此,也促使其对审美活动、审美价值、审美意义的探寻和讨论总是落实到人与人生的层面。就其具体体现来看,则中国传统美学一直在追求如何通过“本真”审美域达成审美活动以实现一种和合完美的人生自由境域,如何通过“尽心”、“尽性”、“克己”、“由己”、“返朴归真”而“知天”、“合天”。美与不美取决于“人”,即“此在”。就此意义来看,所谓“人”,即“此在”,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气流淌的天人一体化生成域,即人与当下的自然万物一体交融、息息相关的生命域。所谓“真体内充”、“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20〕的生命体与生命域。中国传统美学强调“厚积薄发”,强调创作者、审美者内在的生命意识与对生命意义感悟的修为。所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21〕;认为“中充实”是进入生命域,即“本真”审美域的前提。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本真”审美域的达成与实现就是一种“尽心尽性”、“反身而诚”,即人的自我生命、本心本性得到自由敞亮的境域。也正由于此,所以中国传统美学极为重视人的本心本性的澄明与绽出,强调“诚者自成”、“为仁由己”。
就纯粹美学来看,“人”的生命意义及其审美价值是一种个体价值,具有一种自明性和自我性,“人”的生命意义及其审美价值,只能通过“人”自身的体认得以确立,而不能依靠他者。因为他者是滑动的、变动不居的。在这一问题上,虽然儒道两家在观念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确认“人”的生命意义,重“生”贵“生”。儒家学者主张“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22〕这里所谓的“天”,应该就是“道”。“天”即“道”,是自然而然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3〕大道流烨,育养万物,上天下地,日月周行,生气氤氲,四季轮转,万物滋生,所有一切都天然自然,本然悠然,静穆无言。即如戴震所指出的:“性之欲,自然之符;性之德,归于必然。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变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24〕这里所谓的 “自然”“必然”,就是指的“道”体的本然与必然。对于“尽心知性”而“知天”之说,朱熹解释说:“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25〕这里所谓的“理”,即“道”。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天”之“道”原本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不可见于形象、无可琢磨,同时,又是形而下的、具象的,可见可视的,可以穷致,故通过“格物致知”能够上达“天人合一”之域。在儒家学者看来,生死休咎功名富贵皆得之于“天”。这个“天”也就是“道”,就是“天命”。“天命”自然必然。孟子说:“莫非命也。”〔26〕由其自然而曰命,由其必然而曰天命。
应该说,所谓“尽心”就是孟子所说的“求其放心”,即不必去执着于“心”。“尽心知性”就是去除私蔽,自然如实地显现出自身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呈现本心本性,也即扫除私心,诚者自成,呈现诚心诚性。这种本心本性的澄明,即如池塘春水,涟漪初歇,石头落地,游子归家,“本真”审美域呈现。这种“本真”审美域的达成与还原也就是所谓的味其味、美其美、真其真,言其言,只有天下那些能尽其心者知之。宇宙间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自然,其生命意义是天之所赋的,故曰“天命之谓性”〔27〕。“人”的生命意义、本心本性为“天”的赋予,为“天道”之必然,所以说“尽心存性”能“知天”。朱熹说:“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28〕“理”在“人”的本心本性,在内“不外”。本心本性即“仁心”“仁性”。儒家学者强调“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审美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就是本心本性的还原。这种“仁”审美域的达成与还原是自然而然、油然而生,倏然而至,廓然而尽的。因此,赵岐解释孟子的话说:“尽心竭性,所以承天。夭寿祸福,秉心不违。立命之道,唯是为珍。”〔29〕“尽心知性”是“天”命如此,自然而然的。而戴震则进一步解释说:“尽其心,即伏羲之‘通德类情’黄帝尧舜之‘通变神化’。”又说:“圣人事天,犹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寿穷达智愚贤不肖,而圣人尽其心以存之养之。存之养之,即所以修身使天下皆归于善。天之命虽有不齐,至是而皆齐之,故为立命知性,知天穷理也。”〔30〕无论是“通德类情”还是“通变神化”都是“圣人事天”,自然本然的事,是存其所存,养其所养。可见,“存心养性”,“尽心知性”就是本心本性的自然澄明、本然敞亮,就是去蔽,求之在我。对此,朱熹解释说:“在我者,谓仁义礼智,凡性之所有者。有命,则不可必得。在外者,谓富贵利达,凡外物皆是。”〔31〕以“在我者”对比于“在外者”。“在外者”既非在我,求之何益,因此,先向内做工夫则不必求而自然可见,此即所谓“反身”。“反身”就是自明、就是自我敞亮。立命在我,本自具足,万物皆备,“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2〕。求之于内,形之于外;得之于心,推己及人,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矣”。
宋明时期的新儒家学者也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原初域为“理”。“理”是形上与形下的统一,是抽象与具象共存,是理性与感性合为一体。就形上意义看,“理”无所不在,“理”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并且,“理”就是“善”的,“人”生成于“理”,“理”即“善”,即“人”之“本性”。就社会人生而言,“理”即“善”,“善”即“礼”,即为“人”与“人”之间所应该遵守的规范和准则。“人”在与万物、与社会生活、与他者、与自身等各种各样、繁富复杂、纷扰交错的关系中生存,极容易迷失自身,使“善”的“本性”被遮蔽,由此而失“礼”,偏离了“天理”,从而混迹于“常人”之中,迷失于人世间,所以“人”应该修身养性,去蔽揭蔽,以归返于“善”,也即原初生成域“理”,因此,“人”应该收敛私心欲望的膨胀,敞亮“理”所赋予的“本性”,“存天理,灭人欲”〔33〕,“天理”生成“人”的“本性”。“人”后天的“气质之性”遮蔽了“天理”“本性”,从而形成人欲。与人欲相对,“天理”是纯粹的“善”。放纵人欲,就必然遮蔽“天理”;要敞亮“天理”,就必须去蔽人欲,促使“天理”、“本性”澄明,以达成“仁”之境域,即还原到原初“天理”“本性”一体、“天人一体”之境域。
在宋明新儒家学者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生成于“理”,“理”即“道”。就“理”即“道”的意义而言,天人相类,“物我一体”。通过“理”而天人一致,进而天人相应,天人相通。整个宇宙,犹如一个生命体,人与万物都是这个大生命体的一分子。依照天然“本性”,本其所本,天人既是一体,又各有其分,体其所体,分其所分,依此而形成宇宙间整体的和谐与秩序。人的天性灵明能觉,其原因就在于能够去蔽与揭蔽,使本心本性澄明与敞亮,维护生气通贯畅达,以保持大化氤氲,生命运行。投身、跃入、参与、进入这宇宙大生命的一体流行,赞助这大生命的有序运转,德其所德、序其所序、明其所明,然其所然,就是“天人一体”之域的生动呈现。所谓“为仁由己”,能否达成“仁”之域,不依靠他者,完全是由“人”自身决定的。同时,程朱理学认为,个人本心本性上达成“仁”之域,也即达成“天人一体”之域。但程朱理学主张人绝不止于个人本心本性上达成“仁”之域,还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追求天下一体同仁。“为仁由己”的“天人一体”之域与“必也圣乎”的“天人一体”之域,是相同的、一致的。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实际上前者也内在地蕴藉着后者。换言之,“物我一体”的审美诉求必然内在地包含着使自身外在化的倾向,不然就不是程朱理学所谓的“仁”与“圣域”。“天人一体”、“物我一体”,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万物本身 (即原初)就是一体相关的体认基础上。在程朱理学看来,“天人一体”的自然属性,是永恒不变,不会泯灭,不会消失的。其生动呈现便是圣人的“一体之仁”。因此,就美学意义看,“一体之仁”也是一种审美诉求。所以,程朱理学的“天人一体”之域乃是“物我一体”的审美追求,是“物我一体”的审美效果的体现。这种“一体”,也可称为“内圣外王”。
道家学者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由原初“道”域生成,人与万物的原初为有机的统一体,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应该还原至原初本性,返朴归真,与“道”为一。在审美域的达成上,道家主张“自然无为”、“道法自然”。所谓“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34〕。 “道”的原初态,即“本真”审美特性,是“自然无为”的。人在审美活动中,即“本真”审美域达成中,只有保持“自然无为”的“本真”态势,清净寡欲,复归于朴,从而才能实现“天人一体”,达成“本真”审美域。显然,道家学者所重视的是人自身的“归朴”、“返真”,即自身生命的本然态势。“天人并生”、“天人一体”的审美观点,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共同构成宇宙世界,其审美价值都在于自身独特的个性及存在价值得到确认。人在宇宙天地间最为神奇,最为完美〔35〕。人由于得到促使天地万物生生不已之“秀”气的滋养而“最灵”,所以“美”必须因人而“彰”。但“人”又必须还原到原初的本心本性,从而才能与“道”合一,以达成“本真”的审美域。
的确,儒道两家都贵“生”重“生”。如果说儒道两家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相关解释有助于“人”们多方位地认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审美价值,那么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尚”生、“贵”生精神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体认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意识与审美诉求。在“人”的生命意义与审美价值的看法上,儒道两家应该是一致的。应该说,正是儒道两家学者这种以人为本的美学思想,强调“求之于内”,要求从人自身出发,以人自身的心灵本性去体认自然万物的生命意识,从而才能还原到人本心本性,以达成“本真”审美域的观点,才构成中国传统的纯粹美学思想的精髓。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9.
〔2〕〔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269,254.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5-8月)〔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4〕〔5〕〔6〕〔7〕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A〕.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23,222,223,227.
〔8〕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靳西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59-360.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64.
〔11〕孔颖达.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1550.
〔12〕〔13〕苏舆.春秋繁露义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168,465-466.
〔14〕〔23〕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78,123.
〔15〕〔16〕〔17〕〔18〕〔19〕〔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28,30,17,18,17.
〔20〕司空图撰.二十四诗品〔A〕.何文焕辑.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97.38.
〔21〕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A〕.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22〕〔25〕〔26〕〔28〕〔29〕〔31〕〔32〕朱熹.四书集注·孟子〔M〕,南京: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2005.18,18,18,18,18,18,18.
〔24〕〔30〕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张岱年主编.见戴震全书 (六)〔Z〕.合肥:黄山书社,1995.147.
〔3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111,118.
〔3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
〔35〕周敦颐.通书·诚上第一〔A〕.宋元学案〔C〕.北京:中华书局,1986.49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