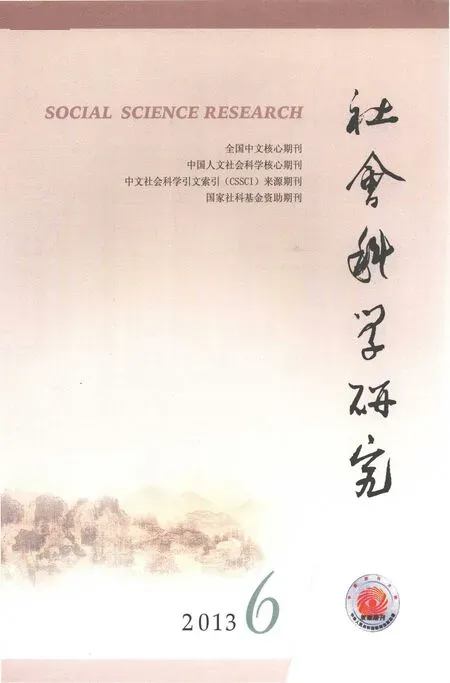“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王东杰
中国现代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初。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它自始就处在国际学术的影响下。西方语言和语言学的影子一直在中国语言学中若隐若现——或是参照的基准,或是比较的对象。在民国时期,引起中国语言学家浓厚兴致的一个问题是,在人类语言进化史上,汉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①本文使用的“汉语”一词,在民国文献中对应的术语为“中国语言”。严格来说,二者所指虽同,语义却有很大差异,值得做深入分析。另外,即使是汉语,也存在众多方言,按照西人标准看,甚至可以视为不同的“语言”。不过,这些问题都并非本文关注重心所在。此处采用这一概念,仅为表述方便起见。这个问题本由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提出,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答案,但大多数并不令中国人满意,因此,中国语言学家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答。这场讨论并不只是语言学的“内部”事务,实与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理想息息相关。
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曾说,“‘纯粹’语言学”研究所持的“语法学家的态度”,和实践中的“言说者的态度迥然不同,后者力图通过言辞用以行事的能力在世界中完成各种行为,并影响这个世界”。〔1〕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注意到,“语法学家”对语言的分析也是一种“言说”,同样是“行事”的工具。他们常常借助于此,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达成自己的目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界对汉语进化地位的讨论,既是中外语言学家之间的专业对话,又构成了他们各自与外部世界对话的一部分。从字面上看,汉语进化地位的问题至少指涉了三个层面:一是对汉语性质的认知,二是对人类语言整体图景的把握,三是对语言进化序列的勾勒,并为汉语定位。第三个层次是问题的核心:由于不同的语言学家所持进化标准不同,他们在前两个层次的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答案。至于语言进化标准的选择,并不是完全由语言学理论决定的,而是语言学理论和各种文化、政治考量互动的结果。
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语言学文本(“专业”的和“不专业”的)进行分析,探索这些观念背后的文化与政治立场。①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对一些语言学家的看法做了介绍,见77-81页。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52-258页)更加关注19世纪的语言学是怎样“成为国际关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 (265页),与本文取径相似,不过,她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意味,内容上也主要着眼于西方语言学界对汉语的认知。本文主要是一个历史学研究,更关注的是中国本土语言学家对西人理论的回应。实际上,刘禾的观点,有不少都和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语言学家对西方语言学的批评相仿。本文特别关注的是:中国语言学家的语言学观点如何被各种文化与政治考量影响?他们欲图通过语言学的学术话语营造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又寄托了他们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和政治理想?
一、19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形态分类法及其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7、18世纪以来,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和殖民进程的开展,西人接触到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作为这种接触的一个直接后果,西方语言学者试图按照不同的标准,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类型,比如,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缪勒 (Friedrich Müller)就以种族为依据对语言分类。不过,语言和种族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这一分类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一种更为流行的分类方法是“形态分类法”或称“类型分类法”,主要根据语言的语法特点,包括词的构造、语法意义的表达方式等对人类语言进行分类。
较早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的,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把人类语言分为两种,一是“分析性语言” (langues analytiques),一是“词序可变语言” (langues transpositives)。“前一种语言类似某些现代欧洲语言,词形变化较少,主要靠据说跟思想的自然顺序一样的词序表示语法关系;另一种类似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词形变化丰富,因此词序可以较自由地变化,而不影响句子的语法关系。”这两者之间具有历史承续关系。换言之,“分析性语言”是“词序可变语言”发展的结果。〔2〕之后,又有语言学家将语言分为“综合语”(synthetical language)与“分析语” (analytical language)两类。②笔者查阅诸了多种中外文献,都没有谈到“综合语”和“分析语”的划分是什么时候、由哪位语言学家提出来的(相反,对于下文提到的“三分法”,一般论述都很详细。可知二者的影响力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很明显,这一划分和“百科全书派”划分的“分析性语言”和“词序可变语言”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在综合语中,语词中表示语法关系的形态部分与表示语意的语根部分密不可分;在分析语中,二者可“任意分离独立”,主要靠语序和虚词等表示语法关系。欧洲语言皆属综合语,“惟近代变迁之倾向,已渐趋于分析语矣”。〔3〕
19世纪以后,比这种“二分法”影响更大的是“三分法”。先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把语言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合体语四类;之后,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奥·施莱赫尔 (August Schleicher)将合体语并入黏着语,保留了孤立语和屈折语,分为三类。③有关论述,参考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129、200页。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有不同的称呼,如孤立语又名“词根语”、“无形态语”,黏着语或称“关节语”、“胶着语”、“接合语”,屈折语 (亦有人写为“曲折语”)或称“诘诎语”、“诎诘语”、“变形语”等。下文征引史料,不再一一说明。这种“三分法”提出后,长期为世界各国语言学家普遍采用,也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家重点针对的一种分类方法 (详后)。这里可以用丹麦语言学家裴特生 (H.Pedersen)的一段话,对三分法略做解释:“孤立语一般引汉语为例:所有的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任何曲折变化。凡是印欧语系利用曲折变化来表示的关系,如果在汉语里必须表明而不能完全省略的话,就利用独立的单字。印欧语必不可少的曲折变化 (如属格、复数、动词的时式等),在汉语里也是同样利用单字来处理。”黏着语以土耳其语为范例,“利用大量的词尾来表示词的关系,不过词 (干)和词 (尾)的连接是很清楚的,这两部分的界限不会发生混淆。”屈折语的“词和词尾混成一个不能分解的整体,词的内部变化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关系”,其典型是原始印欧语。〔4〕
这几种类型之间存在着历时性的进化关系。洪堡一方面提出,“对于任何语言,哪怕是最野蛮的部落的,也不应该予以歧视,或贬低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有“完备的”和“不完备的”之分,屈折语是最完备的语言,孤立语是最不完备的语言。苏联学者拉·绍尔指出:在洪堡那里,“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被理解为“人类精神为解决同一任务 (即创造‘形成思维的武器’)所经历的阶段顺序”,因而把“语言类型上的不同”看做“语言的发展史”。施莱赫尔则说,这三类语言“构成三个发展阶段”,只有屈折语“才完全跨越了那三个发展阶段”。施氏受进化论影响甚大,强调语系犹如物种,有分化,有竞争。有学者指出,在他那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取代了洪堡特的追求完美的进化论”。①参考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按,此处的“洪堡特”,今通译“洪堡”),199、208页;威廉·汤姆逊 (Vilhelm Thomsen)《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99-101页;拉·绍尔《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说史梗概》,收威廉·汤姆逊同书,143页;罗宾斯 (R.H.Robins)《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98页。随着施氏三分法理论的传播,他的语言进化三段论也被广泛接受。
语言分类法的提出和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主导的殖民进程的展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殖民进程为语言分类法提供了物质、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分类法本身也是殖民进程的学术表现。在这里,世界各民族语言所处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体相当:殖民者的语言属于最先进的类型,被殖民者的语言则被归入落后之列。不过,其中也有一个最引人瞩目的例外,那就是梵语,它和诸多欧洲语言一起,被归入印欧语系,且古梵语还被视为这一语系的祖先。因此,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对梵语多很推崇。这和印度当时所处的殖民地境遇截然相反。但19世纪晚期,德国“新语法学派”发现梵语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古老,有些语法现象甚至晚于希腊语。这使得本来不赞同这一学派的德国语言学家古尔替乌斯 (Georg Curtius)非常高兴:“梵语曾经是这门新兴学科的神启,且曾为许多人盲目地信从过,现在却要把它搁在一边了;传统上所说的ex oriente lux(从东方升起的曙光)现在却要代之以in oriente tenebroe(东方的黑暗)了。”〔5〕此言一语道破了西人心事: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梵语,目标都只有一个:证实西方文明的先进。如果能够把梵语踢出先进之列,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梵语好歹与欧洲语言沾亲带故,汉语却与之毫无瓜葛。因此,在这些理论中,汉语一直被视为“东方黑暗”的最直接证据。其时不少西人认为,汉语没有语法。洪堡虽承认汉语有语法,仍把它作为孤立语的典型,归入人类语言中落后的部分。他提出:从“创造‘形成思维的武器’”的角度看,“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洪堡这个论断影响很大,黑格尔在此基础上提出:“拼音文字是理性反思的产物,是将词分析为要素的结果;象形—会意文字如汉字,则源于对事物的感性印象,与理性的分析行为无关。”〔6〕19世纪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一看法,多认为汉语受到“语言结构上的局限”,难以表达“科学观念”。〔7〕
洪堡认为汉语不利于思维的开展,主要因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词汇没有形态上的屈折变化。但问题是,欧洲不少语言也呈现出向单音节发展的趋势,英语尤为典型。如果这一发展就代表进步的话,汉语立刻会从“最落后”的语言变为“最进步”的语言,这显然是其时大多数西人不能接受的。为此,施莱赫尔提出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语言的生命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史前时期,这是语言形式的发展期,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再到屈折语的进化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随着文字的发明,语言为文字所束缚,遂进入第二个时期,趋于反向发展,这是语言的衰败期。〔8〕现代欧洲语言处于第二个时期,单音节化代表了“退化”的趋势;而汉语则根本就仍处在第一个时期的孤立语阶段。显然,施氏虽不能不面对语言变化的客观实际,但通过理论技巧,他把看来非常近似的两个语言现象区隔为遥遥相对的两端,汉语依然陷入最原始的阶段。此说提出后,很快被广泛接受。19世纪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 (Whitney)竭力强调英语的“单音节”趋势,“与原始语言的单音节性相比” (主要指汉语)实是“天壤之别”,就是一例。①事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258页。
实际上,西人对中国语言的认知也经过一个变化。17世纪欧洲人初次接触到较多的中国知识,对汉语极为推崇,还爆发过一场中国语言是否人类“原初语言”(即建造“巴别塔”之前通用的全球语言)的讨论。②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46-150页。该书还论述了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批评,不过,其征引的内容多集中在汉字方面,171-175页。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事业的开展和中国形象在18世纪的迅速恶化,“原初语言”也沦落为“原始语言”。美国来华传教士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 Nevius)186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注意到:“现在有些作家根据汉语的单音节形式和它缺少曲折变化的特点而将其视为是世界上最原始、最简单的一种语言。”对此,他并不赞同:“就汉语当前所使用的形式而言,它即使算不上是最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结构最细致、表达最精妙的语言之一。”但他仍认为,汉语是原始语言的说法“可能并非谬论”。〔9〕
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评论,在19世纪下半期传入了中国。1882年,《万国公报》刊登了沈毓桂笔述的一篇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一观念:“梵言变换多端,华言虽有变换,然不多于印度。是中国人之语言犹近于古初孩童语言之式也;若梵言则不然,于古初语言已多更变。试即梵文细审之,观其随时更变之活字、死字、虚字、实字、助语,语字真有千变万化,故知其语言去古已远也。”该文指出,西人研究语言,最重“折节”(即“屈折”):“折节察不清楚,不能识其语言之归属。是以无论何国,凡欲察方言者,必于分折节之语言中细心审察也。折节愈多,语意之变换亦愈多,其去古初之语言亦愈远。惟语言中有一折节者,可谓与上古相近。”准此,汉语虽“较上古变者已多”,但“较西国之言去上古式绝远犹觉少耳。故讲方言家欲知上古之人之语言如何,不能不于中国语言文字多多致意。”〔10〕即是说,汉语处在人类语言进化的初级阶段,在语言史上具有一种“标本”意义。
不过,从整体看,在清末,介绍“纯语言学”知识的文献并不多,有关文本似乎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相对于确定汉语的进化地位,国人更关注的是怎样使汉字更加简便易学。〔11〕汉字繁难的观念和汉语原始论一样,也是西人影响的结果,但对中国人来说,前者似乎更为急迫。③西人也有类似认知。1902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呼吁中国进行语文改革。但他特别强调,这只是要“增新字、变文体”,并非要用外语代替汉语。至“他日者新籍流行,有可循习,必仍用其旧有之语言。盖中国之所乏者,不在语言而在文化也。”其实,华文适应力极强,“不独可应格致之用,无论何种专门,亦可藉以传达”,故“华文之所欠阙者,不在不足而在难通”。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 (1902年3月4日),14A-16B页。其时引起中国人关注的语言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统一国语方面,对汉语的发展地位并未留意;至于人类语言的分类,更可说是毫不上心。〔12〕
清末最杰出的语言学家章太炎那一时期发表的大量著作,也几乎没有提到相关知识。这些著作中,与此问题最接近的当是1908年发表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此文为批驳吴稚晖等人的“废汉文,用万国新语”论而作,但通篇都集中在音韵、词汇方面,并未涉及语法,也就不可能谈到形态分类法了。当然,吴稚晖等人的立论,本未涉及此一问题;章太炎的这种回应也是很正常的。这就意味着,双方都没有把形态分类法作为必要的知识背景加以考虑。这当然并不一定就表明他们对此说不了解,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有零星介绍,有关系统分类法的知识在清末并未引发中国人的足够关注。
二、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对汉语进化水平的再定位:胡以鲁的观点
这一状况在民国以后略有改变。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中国学者对形态分类法的系统介绍和回应,首见于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胡以鲁,字仰曾,浙江宁波人。清末留学生,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政法,后进入东京大学博言科学习语言学;1913年被聘为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会员,1914年至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1915年逝世。《国语学草创》被认为是第一部利用理论语言学框架写成的“汉语概论”,1913年初次印行,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除了学习过政法和语言学外,胡以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知识背景是在东京时,跟从章太炎学习国学,这使他兼具对西方理论的熟知和对中国文化特色(“国粹”)的敏感。因此,他在《国语学草创》中虽然广泛运用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却并没有把汉语强行套入其中,相反,他试图强调,汉语有其特殊性,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并不表明汉语落后,而代表了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为此,他对汉语原始论予以了严厉的批驳。
胡以鲁的阐释不是从广泛流行的三分法开始的,而是采用了“综合语—分析语”的二分法。他强调,语言之用在“明瞭表彰”思想,所取手段则应尽可能“单纯”。在综合语中,不同词性主要通过语词自身的形态变化表现,“一一分立,不相通用”;语词顺序反而不重要,可以随意排布。分析语则不然,“表示二段以上之思想,各以其相当语词为之,无错杂纠综之弊”;词语的语法关系靠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显示,而“位置之配赋又自由自在,不失独立”,更合乎人的思维习惯,有利于表达复杂观念。也就是说,除了表达手段更简便,分析语也标志着人的思维水平的提升:“语言趋于分析,思想分化之要求也。”对词汇的“职掌”与“意义”的“分析愈精”,就愈能表达“精密”的思想。这就是人类语言从综合语走向分析语的主因。欧洲近代语言渐趋分析语,就是显证。惟真正的分析语要到中国、安南、暹罗、缅甸去找,而汉语尤为其中之“纯之纯者”。①本节除特别说明者外,均出自胡以鲁《国语学草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69-82页。
结论很明显:如果分析语代表了综合语演进的方向,汉语无疑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同样,如果分析语是“思想分化”的结果,那么,与洪堡、黑格尔的认知恰恰相反,汉语实际上是思想更为“精密”阶段的产物。
这个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胡以鲁选取的理论依据。他并没有回避三分法,相反,他指出,二分法和三分法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孤立语属于分析语,黏着语 (胡以鲁称为“抱体语”)和屈折语属于综合语。那么,胡以鲁为何要采用二分法,而非更有影响的三分法作为立论框架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二分法的分类更为简洁,也更易展示汉语的先进性。
不过,胡以鲁并没有回避三分法对汉语的责难。他提出,施莱赫尔 (胡译为“胥拉海”)等“动辄以吾国语形式之缺乏,贬之为初等”,其实,他们所谓“形式”,主要就是“屈折的形式(Flexional formal elements)”,而不包括其他“形式”。这决定了他们“不能不以综合语为高等”。但这也就无法解释欧洲语言的演变趋向,除非以之为“退化”,然而这和一般认为的社会文化的进化论又不一致,遂使此派学者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境地。其实,按照形态分类法的逻辑,“吾辈转不得不谓纯粹分析语无屈折之形式,如吾国语者,为高等而进化者矣”。
胡以鲁分析了西方语言中的形式变化因素——“人称、时、位、性、数、法、气”等,认为它们并非思想的内在要求,而是因为在“词句关系上各语词欲明示其职用”,然又“不能活用”,故不得不“求之于形式”的结果。故这些屈折只能表明语言的笨拙:“若以句为单位,其成分之语词,固不须更用形式辨别也。”而后者正代表了汉语的长处。汉语能“化单纯之音响为特定之意义”,“思虑”和“语言”直接对应,怎么想就怎么说,“以心传心”,简洁准确。汉语通过词序的排布,已能使各个成分“克尽厥职,无不足之感”,自然无需屈折变化这类“蛇足”。故其缺乏形式上的屈折,并非落后的表现。
不仅于此,胡以鲁对三分法本身就很有意见;这可从他对汉语为“孤立语”说,甚至“孤立语”这一概念本身的否定中看出。
胡以鲁开列了一串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的名单,特别摘出他们对汉语的评论:施莱格尔(Schlegel,胡译为“胥立盖而”)、葆朴 (Bopp,胡译为“抱浦”)、麦克斯·缪勒 (Max Müller,胡译为“麦斯牟勒”)皆以汉语为孤立语,并因此把它放在语言发展的“初步”阶段;葆朴“谓吾国语无文法,且无机如矿物然”;缪勒说汉语为“家族的组织语”;施莱格尔甚至谓汉语乃“止于太古状态而未尝发展者”。
胡以鲁对此做了一一批驳:所谓汉语“无机”说,乃就“语词”而论。孤立地看一个语词,它自然是“无机”的,但在此意义上,所有语言皆可说是“无机”,岂独汉语为然?更重要的是,讨论语言,决不能仅“以语词为根据”:“语词生存于句中,惟在句中方为有机之关系,而亦不得不有机者也。”因此,“孤立语”一名在学理上已根本不能成立:“语词之于语句,犹元素分子之于有机化合体,不成其为孤立也。”汉语语词本身虽是“孤立”的,然在句中则成为“化合体”的一部分。故“苟家族组织国家组织等比喻语而有当也,吾辈毋宁谓吾国语为有联邦组织耳。虽不如屈折语灭却其存在之一部而屈服于他,谓为孤立则非。”这样,三分法的体系也就自然坍塌。据此,胡以鲁断言:这些观点“不惟不知吾国语,且不知当世之有语言学矣”。
这还是在学理上的驳斥。很快,胡以鲁就把战场转移到了文化心态领域:“若必以易于屈折而失独立者为高等,即北美土人语为最高;印度日耳曼语固亦曾为高等者,不幸而形消式灭,渐退化于初等者也。”这对西人的“自夸之情”无疑是个严重打击;为此,德国语言学家加贝伦兹(G.von de Gabelenz,胡译为“迦伯林”)提出了一种循环论。他设想在印欧语系成为综合语之前,曾有一分析语阶段;因此,分析语并非必然高级,也可能比综合语更低。胡指责此说不仅是为了挽回印欧语言的面子,也是要打击汉语:“氏以是为论据,谓吾国语之现在乃便宜之结果,在螺旋中适值孤立语”,并非最先进的表现。胡则强调此说只是“想像”,从“历史事实”看,只有“屈折语”向“孤立语”的进步,而不存在什么“螺旋”;从人的“心理”看,“语言之发展”必以“精神活动之简易”为“原则”。汉语“简单”而非“初等”,盖“简单”正是先进的表征。
洪堡 (胡译为“亨抱而的”)等人则部分认可中国文明的价值,因而把汉语归入“有形式”一类中。不过,其仍有一基本“假定”,即“以形式为精密文明思想唯一发表具”,因而“迷惘于形式之中,不知形式之外亦有特长”,仍是印欧语系“国民之先入僻见”。这使他们“不得不贬无形式者为劣等”;而在有“形式”的语言中,又“以语词之连结配置”者为高级,以贬低汉语地位。胡以鲁批评他们:“立一己语族之规则为格,欲以范世界之语言,是之谓不知务;不求诸语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见其文明,逆推而外铄,混思想语言为一事,是之谓不知本。”这实际不只适合于洪堡,也是他对于前述诸人的总批判。
20世纪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 (Jens O.H.Jespersen)的“语言进化论”是胡以鲁较为满意的一个学说,以为“最为得其平”。因其“以不用形式之末迹而寓意于词句相维之间者为进步”,这就意味着汉语是一种“发达”的语言。不过,他仍认为,叶氏对汉语未作“根本之研究,仍未足以言吾国语也”。
总的来说,胡以鲁的论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理上的,主要是解构形态三分法和语言进化三段论;一个是心态上的,主要是揭露这些语言学观点背后的西方中心论。而正是后一点,又进一步提示出,我们也应对他本人的心态做一分析。这一点,在下面这段忿忿不平的话中展示得最为直接:“贬吾国语为初等,诿为未尝发达者,不惟不知吾国语言史,且蔑视吾国文明史者也。”就是说,他之所以竭力为汉语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这不仅是个语言问题,也是和更根本的文化认同联在一起的。
不过,胡以鲁主要的意图恐怕还不是向西方语言学发起进攻,他的行为毋宁是“防守性”的。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清末的一个重要思想成就,就是将“齐物”观念引入社会政治理论,强调各个民族和文化是平等的。章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欲以己之‘娴’改变东方之‘陋’,实际上引来流血战争”,皆是缺乏平等精神所致。①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155-162页,引文在160页。胡以鲁显然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他强调:“一切国语皆有机制,皆有精神。”因此,他强调汉语的先进,主要是欲反抗西人的“自夸”,以维护“吾国文明”之尊严,其所指是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非把西人的等级观念简单地颠倒过来,把西洋语言贬低为落后语言了事。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强调:“甚矣,研究外国语而欲知其语言精神之难也”。要了解中国语言之真相,“则支那语国民之责任,不能望于他族也”。而这样做又不止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汉语是世界语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不得吾国语之真相,语言分类亦殆无望”。
胡以鲁对汉语的描述,带有很强的政治学色彩。他对麦克斯·缪勒把汉语的组织形式比做“家族”一语,尤为反感,再三置辩。这里的原因,应从其时流行的社会思潮中去寻找。1904年,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出版,提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且认为中国正处在从“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时期。此说一出,迅速风靡。章太炎为批驳此说,专门著文,指出《社会通诠》所谓“宗法社会”与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不合。〔13〕缪勒使用的“家族”比喻,与严译“宗法社会”的概念虽不等同,但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此。胡以鲁深受章太炎影响,当然极力反对。
与此同时,胡以鲁试图把汉语放在“国家”(对应于严译的“军国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定位:
比喻的言之,有实质之语词,单独国也;复合词,政合国;形式复合词,则隶有附庸之国也;介节词,自由市;而语助节词,从属国也。从属国而外,其他皆有自由意志之实质,以自由意志联合而为句,句犹一大联邦也。发表完全思想,即运用国际主体之时,则以联邦总体之句为之,而内政上依然独立,自有意志,即不失其实质意义也。自由市虽不具国家性质之实质,仍不失其自由。惟附庸国之独立意志大半为主国所左右,而从属国则国际主体之体面上一附属品耳。然是不过欲明吾国语在句上之关系而已,非如麦克斯牟拉氏之论发达上组织也。……即无国家组织之国语,非吾辈所敢知也,然则以一切国语皆为有国家组织者,比吾国语于联邦组织可乎。
胡以鲁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联邦思潮盛行之时,其主要目标就是维护民间自治、自主和自由,反对中央集权——采用胡以鲁的术语来说,所谓中央集权,即是“灭却其存在之一部而屈服于他”,正像屈折语。从《国语学草创》对汉语的定位看,胡显然是联邦制度的赞赏者。问题是,他为何要用政治术语描述语言?仅仅是因为缪勒使用了一个政治术语评价汉语,而胡要反驳之,故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或者是因为他曾学习过政法和语言两个学科,对它们的术语都很熟悉?答案显然不这么简单。他对汉语的特色有一简洁的总结:“自由自在,吾辈所谓之为国语特色者也。”这正可与“联邦组织”一词互相发明。如前所述,对于胡以鲁来说,语言并不仅是语言本身,它也代表了“文明”;这番论述进一步表明,语言还关系到“政治文明”,和国家乃至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连在一起。汉语以“自由自在”为特色,也意味着中国文明和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体”,具有“自由意志之实质”。用刘禾的话说,语言的背后,有一个“主权”身份在。〔14〕
三、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对汉语进化水平的再定位: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
《国语学草创》为中国学者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一个论述典范。此后的著作,从议题到论证方式,基本都不出此书范围:一、语言的形态三分法是否成立?二、汉语是孤立语吗?三、语言进化的标准是什么?四、汉语在语言进化史上处于何种地位?五、形态三分法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多数学者异口同声,认为这些学说暴露了西人自尊自大的文化偏见;而汉语在人类语言中,即使不能说是最进步的,也处于先进之列。
对三分法的介绍,当然是有关著作的必备内容。重要的是,大多数论者都对此说持批评态度。薛祥绥1919年在“保守派”刊物《国故》上发表文章说,三分法只能说是言语的“运用”法,不能说是言语的分类法:“盖以三者亦可互通,非必判然不合也。”英语就同时兼具三种类型的特征,汉语亦然:其“一字一义,多为单音,藉所安而别其职,如‘鸣钟’之与‘钟鸣’,同一‘钟’也,所安有先后,而宾主之职斯别。”可说是孤立语;而“亦有合二字始足一义者”,单字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双字的如“夫渠”、“巴且”、“覼缕”、“赑屃”等。这可说是诘诎语。汉文中又有大量形声字,有“根”(即通常所谓“声符”)有“系”(通常所谓“形符”),“分析之亦皆成字”,类似于“关节语”。〔15〕据此,三分法实未稳妥。
在新派人士眼里,薛文很可能被视为语言文字混为一谈的典型,正是“不入流”的表现。不过,新派语言学家与之结论相同者比比皆是。曾留学美国,又在北京大学、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教授过普通语言学的沈步洲在1931年出版的《言语学概论》中指出,施莱赫尔提出三分法时,“言语研究之历程,远不逮今日,而所谓关节、诎诘者,皆无确断之性能,奚足以包举一切?”洪堡早就说,梵语与华语分处“语言构造之两极”,其他各种语言皆在二者之间,关节语包含范围尤广,可见三分本就“不足”。即使“视为科学初创时仓卒之误,取其说而置之高阁,亦未尝不可”。〔16〕杨树达也说:三分法实不能“统括今日世界所有之言语”,很多语言也并不全合分类标准,“如中国文有介词,即有关节语之性质,而土耳其语中之语尾亦有与语根融合而类似屈折语者”,故三分法不可过于当真。〔17〕
其实,中国学者真正在乎的未必是三分法在学理上是否成立,他们很多人讨论这一问题,盖别有关怀在——即汉语是否“孤立语”?薛祥绥就是一个典型。他先后论证汉语具有孤立语、诘诎语和关节语的特征,最后归结为:“观此,则目中国语为孤立语者,其陋可知也。”〔18〕这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与薛祥绥把汉字、汉语打作一气不同,在新派语言学家那里,证明汉语不是孤立语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强调二者的差异性。1922年,黎锦熙指出,西洋学者常以汉语为单音语而贬之为落后,实则汉字虽是单音字,汉语“实在乃双音语”。〔19〕不久,刘复也说,三分法实不能概括中国语。“中国的文字诚然是单音的,但语言并不全是单音。”〔20〕20年代初在巴黎研究语言学的李思纯则称,三分法在各种分类法中“最为允当”,汉语确系孤立语 (李译为“单立体语”)。不过,他又立刻注明:所谓“单立”,只是就其“成文之语”而言;至于口语,则要复杂很多:“时有分体,缀系首尾,幻化无恒,决非离立。”而近世语汇又“大率两音连缀而成”,绝非“单音只字”。〔21〕与黎、刘所见略同。当然,严格说,单音语和孤立语并非同一概念,一个是从音节构成上说,一个是从语法形态上说,惟二者又密不可分,相互决定,往往被视为一体。〔22〕
胡以鲁提出应从语句而非语词的角度理解语言性质,这一思路被沈步洲继承了:“夫依形态以分类,当以句为本,不当以字为本。”〔23〕张公辉也说:“中国语的语词在外表上虽然孤立,而在语句中,却是有机体的结合,决非各个孤立的;语词的意义在全句的总意义上自然显现。”因此,即使“没有时间、数目、性别、位格、人称等的形态变化”,亦“决不至于含混不明”。汉语语词并非没有词性差别,只是并不通过屈折表现,而是通过具体“措辞”和语序表现的。〔24〕因此,对汉语性质的判断,就不能以西洋为准,而应从汉语自身的特征出发。
高名凯的意见则略有不同: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孤立语,20世纪则有一批学者如瑞典的高本汉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认为汉语“有许多附加成分,甚至于有屈折”,故“不是孤立语”。高名凯则以为,把汉语视为“完全孤立语”固然不对,高本汉的新说也“太趋于极端”。其实,“中国语虽有一部分的屈折成分,虽有一部分的粘着成分,但终不失其为一种孤立语,只是不能说是绝对的孤立语而已”。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说中国语是无机的,是没有语法的”。〔25〕
这些学者之所以关注汉语的性质,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潜藏着语言进化三段论的阴影。如果汉语不是孤立语,也就不是原始语言。张世禄对此说得很清楚:“汉语名为孤立语,而实际上语词在语句中,正是有机的结合,绝非各个孤立的。语词的品性和意义在全句的总意义上自然显现;没有时间、数目、性别、位格、人称等等的差别,决不致于含糊相混。”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孤立、接合、变形三段进化说,也就不攻自破了”。〔26〕高名凯虽然认可汉语大体仍是孤立语,但其最后一句话表明,他试图把形态三分法和进化三段论拆分开来。这就意味着,他对那些否定汉语是孤立语的中国学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实际上,否定汉语是孤立语的人,暗中都承认孤立语是原始语言,这也正是他们要把汉语从“孤立语”中拯救出来的主因。倘若他们像高名凯一样,并不认为孤立语是原始的、“无机的”,倒也可以坦然接受汉语属于孤立语了。
在三分法受到质疑的同时,二分法被不少人采用——这也是由胡以鲁开启的。张世禄提出:“中国语是否为单节语”,在文法学上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在综合语和分析语的分别。中国语为分析语的代表,这是语言学界所公认的。”〔27〕二分法较之三分法更适合汉语,这不光是怎样认识汉语性质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汉语的地位。浦江清就曾对朱自清说,汉语“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28〕曾在德国学过语言学的傅斯年也说,汉语“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 (Syntax)求接近逻辑的要求”。它“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29〕傅斯年所说的,显然就是“分析语”。
刘复把西人关于语言进化的学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语言形态为依据,把形式上的“复杂”或“简单”视为语言“完备”或“幼稚”的标志;第二阶段则以是否“适应环境”、是否“经济”作为标准。标准不同,同一语言的历史地位也就大不一样:按照第一种观点,“英语是最退化的”;按照第二种观点,英语却是“最进化的”。但刘复也指出,英语的进化论对于汉语未必适用。因西方学界虽有人提出汉语是“最进步”的语言,但“一般的语言学者”都认为,汉语的简单正表明其维持着原始状态,仍是“最幼稚的”语言,“它必须将来先进到了变化繁复的地位,然后才能慢慢的由繁趋简,走上英语可走的进化路”。〔30〕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中讨论到这个问题,沿袭了刘复的说法,并把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前期进化说”和“后期进化说”。①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9页。按,何九盈教授说《高等国文法》论言语类别等章“多采自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16页)。然至少此部分而言,从学说的介绍、例证的选取,乃至术语的使用,都明显袭自刘复的演说。而实际上,“前期进化说”并不只有“进化”,也包含了“退化”过程;“后期进化论”才真可说是“进化”。
刘复以自己没有研究为由,对汉语的进化地位问题未做表态。不过,下面一段话仍透露出他的态度:
也有人大胆的说,中国语言是全无文法的。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文法中有变化,就把变化占据了文法的全体,以为没有变化,就是没有文法。这种不通的说话,是我们根本不能承认的。他们有了这种偏见,就以为语言的变化,愈简单就愈幼稚,愈复杂就愈完备,结果是对于古语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等备极推崇,而于近世的语言,反视为退化。这种尊古抑今的调调儿,何异于老顽固们的“人心不古,世道沦亡”的论调呢?〔31〕
这当然并不等于赞同汉语即是最先进的语言,然而,一旦采用“简单”作为进化标准,汉语无疑更占先手。
有学者也为汉语建立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高本汉曾根据汉藏语系中缅甸语、藏语的现象推论:中国古语系双音缀,有语尾变化,不过早已演进为“一种最先进的与极省略的语言的代表,其单纯与平衡的现象,较之英语尤为深进”。〔32〕此说在中国学者中影响很大。①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高本汉的观点。如前所述,高名凯就持批评态度。前引傅斯年的判断,就是受到高本汉的启发;张世禄也据此断言,语言的演变“正是由变形语进向于孤立语,事实上正是和三段进化论所假定的步骤适得其反”。〔33〕更有人提出,语言是由屈折语进化到黏着语,再到孤立语的。1944年湖南印刷的一本小册子说,周秦以上,汉语为多音节,有倒装句,“盖亦注重语根语尾之变化,而语词排列先后无甚关系”——这是综合语的特征。由此推知,“今日之分析语,必上承关节语,而更上则为综合语”;此乃“语法进化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也”。故现代文的“欧化”语法实“乖语言进化之序”。②彭泽陶:《中国语文嬗变论》,23页B-24页A、25页A。版权页显示,此书由湘云印刷局印刷,1944年6月初版,发售者通信处为“湖南桥头市省立第一中学转彭葛怀”。这本小册子不是正式出版物,作者应是一位语言学的业余爱好者。这里提出的倒装的“进化三段论”大约是综合了不少专业读物和个人研究心得而成。
既然“简单”就是进化,则汉语即使是“孤立语”也没有多大妨碍了。岑麒祥说:“中国语在世界语言林中,自语词形式方面而言,乃孤立语之标本;自语词构造方面而言,亦为分析语之极则。则其在语言学上之地位,已概可想见。”盖无论是孤立语还是分析语,都是世界上“最纯净、最简洁”,故也是“最进化”的语言。〔34〕张公辉也说:汉语“淘汰了多音节语的成分,而演进为单纯化的单音节语;洗刷了屈折语的成分,而演进为纯粹的孤立语;摒弃了综合语的成分,而演进为纯粹的分析语,已经是世界上最进步的语言”。〔35〕在这里,“纯粹的孤立语”一变而为进步的象征。沈步洲则引叶斯柏森为据:叶氏认为今语优于古语,“是单节语宜优于诎诘语,中语宜优于外国语”。〔36〕其实,叶氏原意本是说,同一语系的语言存在从繁到简的进化关系,沈步洲却把它用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之间了。但这一误解也正表明,语言以“简化”为进步,已成为中国语言学家的一个共识。
清末民初,曾颇有人提出废除汉文采用世界语 (Esperanto)的呼声。然而,随着汉语被视为最进步的语言,不少人开始设想其变为“世界语”的可能。30年代,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来华,盛称洋泾浜英语不“太受文法拘牵”,可成未来之世界语。“某记者告以华文实际上即不讲文法。萧氏曰: ‘然则,华文将来或可为世界语耳。’”曹聚仁对此非常不满:“世间岂有不讲文法的语言文字吗?”〔37〕“某记者”的表述确实有误,但他看到的正是汉语文法简单的特征。张世禄也注意到世界语与汉语的亲近性:“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觉得繁难,学习世界语,便很容易;这是因为世界语具有他的优长以外,还适合着中国语里自然的文法组织。”〔38〕张公辉干脆认为:汉语在“本质”上,比Esperanto“进步了数千年之久”,乃是“世界共通语的基础”。〔39〕
与此相应,屈折语的形态变化沦为落后的表现。华超说:“性的阴阳、位的宾主、数的多少、气的虚实、主动和被动,都可藉语词在句中的关系定的。吾国语本来不以多变算作能事,平实使用起来,亦不觉他不便,则简单正是分析语的特长。”〔40〕沈步洲也说,法语、德语、拉丁语对性的区分时或“任意颠倒,漫无标准,徒滋纷扰”,殊属“无谓”;汉语“本不以多变为能,而平时使用殊不觉其窘苦”,两者相较,高下立辨。〔41〕景昌极直称西文之语尾变化是“不必要”的“恶习”。〔42〕这基本都是重复胡以鲁的话。陈寅恪则从历史角度解析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当日固无比较语言学之知识,且其所拟定之规律,亦非通筹全局及有统系之学说。罗马又全部因袭翻译之,其立义定名,以传统承用之故,颇有讹误可笑者。如西欧近世语言之文法,其动词完全时间式,而有不完全之义。不完全时间式,转有完全之义,是其一例也。〔43〕
屈光参差对弱视来说是公认的危险因素。所谓屈光参差,是指双眼在一条或两条子午线上的屈光力存在差异,人群中双眼屈光力完全相等者较少见,多数表现有一定差异。我国2011年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发布的弱视诊断专家共识中指出双眼远视性球镜度数相差1.50 D或柱镜度数相差1.00 D为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危险因素[6]。屈光参差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有研究表明其和遗传机制有关,胎儿包括出生前的胚眼发育以及出生后双眼正视化进程差异等眼球发育平衡的因素如受到影响,将导致屈光参差的发生[7]。双眼轴增长速度不同,前房深度不同,角膜曲率不一致等均会造成屈光参差[8]。
陈寅恪并不是要论证汉语的先进性;但他指出印欧语言的形态变化只是承袭传统而来,并无深刻义理,且有不通之处,无疑有助于屈折语地位的动摇。
揭示西方语言学家的文化偏见,也是这些著作的重头戏。沈步洲特别留意到有关学者所运用的术语:施莱格尔把语言分为“无机的”和“有机的”,洪堡、波特认为语言有“正格”、“过正格”和“偏正格”的区别,司奈嚇、缪勒用社会组织的形态来区分语言形态:“营家族生活之人种斯用孤立语;游牧人种乃用关节语;知有国家之人民乃用诎诘语。”这些表述无关学理,而有“抑扬之意”,“适足以彰其愚陋耳”。〔44〕王古鲁则说,“以一己之语族自诩为高等的偏见”,就好比“在人种学上占有势力之主张以亚利安民族为世界民族中最优者的僻说”一样,都是“亚利安民族”的“自夸心理”的表现。〔45〕张世禄则在1933年一篇专论汉语世界地位的文章中,特别揭露施莱赫尔的“言语退化论”不过是对其理论中自相矛盾之处的弥缝,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46〕
值得注意的是,张世禄这篇文章的开头就点出了文化偏见的存在:“古代文化发达的民族,往往对于国外的异族,具有一种轻视的心理。”这本应抛弃,“不料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和二十世纪东亚的某种民族还是沿着太古的遗俗,或且变本加厉,由轻视而引起仇视,由相轻而至于相杀”。其影响所及,“不特世界的和平没有实现的希望,各处文化的交流也受了无形的阻碍,终究没有完全沟通的一天”。学者“参杂了民族相轻的心理,就完全失去客观的态度,把自己民族的偏见作为前提,不惜将科学的事实勉强来‘削足适履’;这样学术界还有光明的一天吗?”三分法就是这种偏见的产物。西人对屈折语何以高等,“始终未曾有明确的解释”,不过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而已,甚至“不惜将全世界的语言归于退化的过程中”。〔47〕“二十世纪东亚的某种民族”几个字,一下把此文立意彰显了出来:张世禄是借着对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批判,来批判日本日益昭著的侵略野心;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则是寄托对世界和平与文化交流的期望。
显然,192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家虽不像胡以鲁一样使用了很多政治学术语,整个论述看来也具有更强的“专业”特征,但文化认同和政治理念仍在暗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四、余论
英国语言学家简·爱切生 (Jean Aitchison)说:“一旦我们把宗教的和哲学的偏见剥去,那么我们发现没有证据可说语言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另外,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看,也没有证据可以说语言是在朝某一个方向移动——有些语言其实正在向相反方向移动。”〔48〕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进化论却是各个学科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理论是付出了绝大代价换得的教训,故服膺之诚笃,有时且超过西人。如前所述,19世纪西方语言学对语言发展的描述实际非常复杂,甚至有人称之为语言“退化论”;而20世纪中国学者对语言的线性进化观倒更加执著。他们都相信语言是进步的,不少人且像刘复一样,嘲笑19世纪语言学家乃是“尊古抑今”的“老顽固”。因此,本文讨论的主题,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历史观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在进化论视野下,中国文化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中国学者怎样面对这一挑战?本文的事例表明,尽管近人对西方充满了欣羡之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心也大打折扣,但并不甘于西人指派的“落后”地位,而是利用各种可能,证明中国文明并非停滞不前,乃是不断进步的。诸多历史学家试图从“社会史”、“文明史”、“国民史”、“世界史”的视角发现中国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表现。〔49〕在语言学领域,形势似乎乐观很多,故学者的目标也更进一层,他们要证明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甚至借此修改19世纪定下的语言进化标准。①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界,与本文所述观点相反的意见一直存在。其中,瞿秋白的态度最为鲜明。不过,他否认汉语是一种进步的语言,主要是为了汉字拼音化服务。但此问题牵涉过广,此处难以详论。一些相关讨论,参考王东杰《解放汉语:白话文运动引发的语文论争与汉字拼音化论证策略的调整》,《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学者的独立成果。在批判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的同时,另一些西方语言学家却颇为中国学者倚重。其中,20世纪丹麦学者叶斯柏森因为提出“语言进化论”而最受重视,被人反复称引。另一个受到青睐的是高本汉。日本语言学家安藤正次也是一个思想资源。王古鲁就明说,他的《言语学通论》“纯以”安藤的《言语学概论》 “为根据”。〔50〕1931年,安藤的《言语学大纲》一书中译本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整体看,其影响力远不能和西洋语言学家相比。此外,在论述分析语的进步性时,英语也是人人必提的佐证 (意图当然不在英语本身)。
除了论著外,译文也是中国学者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渠道。1929年,《学衡》刊登了张荫麟翻译的美国学者德效骞 (Homer H.Dubs)的文章《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此文意在反驳德国哲学家赫克曼 (Heinrich Hackmann)的“汉语无屈折变化,无法胜任高级智力文明”的观点。德氏宣称,语尾的屈折变化与能否表达精密思想之间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他同时也援引了语言进化论,提出:“语言之发展,既为字尾变化之简单化,而非繁复化,则谓中国语实较欧洲之语言为进步,而非其反,似亦言之成理,因中国语无字尾变化也。”①德效骞:《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张荫麟译,《学衡》第69期 (1925年5月),5-7页 (篇页)。又载《辽宁教育月刊》第1卷第4期,77-90页。可知张对此文的重视。
汉语进步论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一般认为,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是中国语法学建立的标志;但几乎自《马氏文通》出版开始,就不断被人批评为削足适履,把西方文法强套在中国语文之上。即使一些主张西化的人士,对此也颇多非议。陈独秀就说:中文“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 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54〕从汉语自身的独特性出发研究汉语,成为不少语言学家的自觉追求 (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这当然并不一定就要证明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但二者在反对以西律中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胡以鲁强调每种语言皆有自己的“精神”,就把这两个问题贯穿在了一起。张世禄也明确宣称:“我要凭语序来研究中国的文法,便是要适合中国语文的特殊性的。”〔55〕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研究“中国语文的特殊性”,并不等于他们把汉语视为一种独立于“世界语言”之外的语言;恰恰相反,他们是把汉语放在“世界”之中定位的。进一步,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论题成为一个“问题”的历史前提,就是“世界”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如前所述,这是西方近代殖民活动的直接结果。换言之,西人在武器和商品之外,也通过“知识”上的分类、描述、论证、定位等工作,对世界的版图加以重新划分和组织。中国学者的工作无疑是对这一过程的回应,但这回应不是机械的,同时也是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与改造,以描绘另一幅世界地图。
因此,尽管除了少数几位,本文提到的大部分语言学家都带有很强的专业色彩,所做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内部;但他们的关怀绝不限于此。事实上,激发了中国语言学家的讨论兴致的,与其说是“汉语在语言进化史上的地位”这一问题本身,毋宁是它所指向的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用胡以鲁的话说,这关系到汉语是否能作为一个“国际主体”而存在。
但应该注意的是,当中国学者强调汉语是最为先进的语言时,并不等于他们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实际上,有学者在论证汉语的先进性时,表述中一度流露出暧昧和迟疑的神色。华超说:“究竟就实用而论,什么言语是最适当?这问题很不容易回答。”从言语变迁的趋势看,诘诎语“往往”渐变为关节语或分析语,“则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然而把这种意思告诉诘诎语族的人民,则他们一定要大反对。”紧接着,他就批评缪勒、施莱赫尔等“对于吾国的言语,没有下切实的研究,断语怎样能真切?”〔56〕沈步洲则根本像是照抄华文:
究竟就实用言之,何者为最适,于斯实未易置答。考言语嬗变之历史,每见有诎诘语渐趋而入于单节语或关节语,如英语是也;单节语或关节语变为诎诘语者,则未之前闻。倘认嬗变为进步,似单节、关节为较善。又人类之思想,初涉大凡,后及细微,是其趋向乃由综合以至分析,似乎偏重分析如单节语者,应较适于文明国家之用。为持此论以质诎诘语族,必群焉非之,即吾国人习用单节语,亦未敢遽执理论之后盾以自豪也。言语肇者如辉特尼(即本文前所谓“惠特尼”——引者注),公然目吾国语为单简;德国学者如司奈嚇、波普等亦云然。成见主其中,知识又肤浅,不能为矫正成见之资,所言自多误会。……持论所据既泛,其断语自不值一顾。且就理论言之,单节语是否幼稚,殊难遽定。〔57〕
细味这两篇文章可知,他们在这里对于分析语是否就是“最文明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并没有下明确判断。从全文来看,这点犹豫几乎是一闪而过,他们在其他地方仍一口咬定分析语就是最进步的语言。但也正因如此,使这点犹豫之色分外惹眼,透露出作者心态中极复杂迂曲的一面。
造成这种心态的一个原因,大概和20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界盛行的“反求诸己”的自省风气有关。面对近代中国的危机,一批读书人非常注重从中国自身寻找失败原因,对“天朝上国”心态复活的危险异常警惕。1921年,周作人就曾调侃道:“今日阅《教育杂志》的国语号,看到几件妙的事情。一位讲言语学的,以为‘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分析语的中国当然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但是同语族的西藏、安南、缅甸又怎样呢?……就实际上说,这缺少前置词 (除了‘自’、‘于’两三个字)的中国语,即使最文明,也未免太简单了一点吧。”〔58〕这位“讲言语学的”,就是华超。其实周作人反对的,未必就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但他显然担心有人从中读出“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的结论,阻碍中国的“文明化”进程。
张世禄则试图从学理上把语言的优劣性和文化的优劣性区分开来:
在普通的眼光看来,文化较优的民族所用的语言,自然比文化较劣的民族所用的,内容来得丰富,词句来得完备。但是语言优劣的问题,应该取决于这种工具自身的适用与否,应该以这种工具性质上的差异为标准,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来评判它的高下。因为语言虽然是社会习惯的一种,而和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社会的制度不能同样的看待;语言是不能随着民族的意志可以自由加以改革的,语言习惯的养成,往往出于民族的不自觉。……语言演变的原动力是介于自然和人为之间,民族文化的高下和语言本身的优劣是两件事。说我们所用的国语,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我们的民族固然不必因此而自馁;说我们所用的国语,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自豪。〔59〕
这和周作人的担心是一样的。不过,如前所述,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开文化认同和日益紧张的政治格局的压迫。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知识人对文化平等的追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与胡以鲁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精神”相应,华超、沈步洲等也都采用了“换位思考”的办法:如果把分析语作为最文明的语言,使用屈折语的人们会同意吗?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犹豫起来。显然,汉语被贬低为原始语言所带给中国人的屈辱感,促使长期受到“絜矩之道”训练的中国学者以更平等的心态处理问题。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沈步洲对斯泰因塔尔 (Steinthal)、洪堡等因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而把汉语“强纳”进“风马牛不相及”的印欧语系,同时又把与汉语甚为密切的缅甸语排除在外的做法并不领情,以为其“根本之见已误”,此不过“迁就”而已,“自欺欺人,莫此为甚”。〔60〕这再次表明,沈步洲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汉语在西方语言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而是揭示语言分类背后的文化“成见”。张世禄对世界语和汉语关系的分析,则提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论点:由西人发明的世界语同时暗合汉语的特性,表明它“并没有泯灭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优点”,这同时“可以促进世人的反省:要实现世界的和平,决不能泯灭了中国的优点”。〔61〕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中国应以一个平等身份参与到世界和平事业中,而这个事业不应“泯灭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优点”。这样,中国学者的汉语先进论,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版本,而是他们对一个不平等世界的抗议。
自然,中国在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心态时而失衡,也难以像西人一样真正地把世界尽收眼底 (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还只是汉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关怀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族主义”四个字——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概念,那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章太炎。章在清末批评吴稚晖用“万国新语”代替汉语的主张,实质是想“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而“欲中国为远西藩地”。他指出:“大地富媪博厚”,绝“非白人所独有”。以语言论,汉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皆在学术上有独特贡献,不亚于欧洲语文。就世界各大语言看,“纽之繁莫如印度,韵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国者,执天均以比其音,虽有少缺,而较他方为完备矣。”〔62〕章太炎这里判断语言发达与否的依据,主要是根据音韵,而非语法;不过,把梵、汉并提,仍和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后者来说,梵语不但是欧洲语言的近亲,且是印欧语系的祖先;汉语则根本属于另一语系,实不能混为一谈。
那一时期,章氏连续写了六七篇与印度有关的文章,将它们合而观之,或可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意思。他为什么会密切关注印度?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这两大古国在近代遭遇相似,同病相怜;但更重要的是,他提到的是中国和印度,想到的却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63〕中印两国是作为与“帝国主义群盗”支配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秩序的提倡者出现的;而这个新世界形成的前提,则是两大被奴役的文明古国各自赢得民族的 “独立”,“返为自主国”。〔64〕正是这个政治理想,才为我们解读章太炎的语言论提供了一条主线。①如果我们将此言和前引德人古尔替乌斯的话对比一下,章说的政治意义会更加鲜明。
“返为自主国”这五个字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语言学界围绕汉语进步性问题的争论。1920年代以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似乎越来越“专业化”。但由本文可知,即使在汉语是否孤立语、有无语尾变化等一些看来非常“语言学”的论题之后,也有一条大路通往更广阔和复杂的论域:强调汉语并非孤立语,不仅是要证实汉语的进步性,也是要拒绝西人为汉语指派的地位,按照汉语自己的面貌描写汉语,以谋求“真正中国文法”的“成立”。②引文出自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52页。这其实就是要在语言学领域内使中国“返为自主国”。换言之,对于汉语在国际学术格局中自主性的关注,赋予这些“专业”语言学家们的文化讨论以浓厚的政治意义。
因此,不管是在学理还是象征层面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的研究都和那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汉语进步论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来自同一个政治进程,即近代西方的全球殖民过程;但和19世纪西方语言学不同的是,它们也是对这个进程的自觉反抗。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抗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颠倒,而是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向往。
这种反抗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或出于中国传统对现代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毕竟,这里讨论的课题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外,它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倒装。③正是这些特征使其与最近20多年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旨趣存在着共鸣,除了刘禾的例子外,何伟亚 (James L.Hevia)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史学家那里发现了相同的现象,见氏著《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69页。这提示我们采用一个更综合和复杂的视角:在近代中国,古今中外都可以成为思考资源。中国人不但利用它们营造自己的形象,也致力于推进一个崭新的世界理想。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Wacquant).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6-187.
〔2〕罗宾斯 (R.H.Robins).简明语言学史〔M〕.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8.
〔3〕〔34〕岑麒祥.中国语在语言学上之地位〔J〕.统一评论,创刊号 (1937年):14,14、15.
〔4〕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M〕.钱晋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91-92.
〔5〕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126.
〔6〕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60-61.
〔7〕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M〕.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7.
〔8〕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206,207;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M〕.199.
〔9〕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M〕.崔丽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167-168.
〔10〕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J〕.古吴居士 (沈毓桂)笔译.万国公报,第708卷 (1882年9月30日):58B-59A.
〔11〕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J〕.中山大学学报,2009,(1).
〔12〕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J〕.近代史研究,2010,(5).
〔13〕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6.
〔14〕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M〕.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265.
〔15〕〔18〕薛祥绥.中国言语文字说略〔J〕.国故,第4期 (1919年):1B,1B.
〔16〕〔23〕〔36〕〔41〕〔44〕〔52〕〔57〕〔60〕沈步洲.言语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38-39,42,51,40,42,50,39,43.
〔17〕杨树达.高等国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
〔19〕黎锦熙.国语学大概〔J〕.晨报副镌 (1922年12月31日):2.
〔20〕〔30〕〔31〕刘复.语言的进化〔J〕.晨报副镌 (1926年12月13日):29,29-31,30.
〔21〕李思纯.语言学方法论·译余小言〔J〕.改造,第4卷第7期 (1922年):28.
〔22〕张世禄.中国语言与文学〔J〕.学识,第1卷第1期 (1947年):21,22.
〔24〕张公辉.中国语的优点及其评价〔J〕.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2期 (1945年):49.
〔25〕高名凯.中国语的特性〔J〕.国文月刊,第41期 (1946年):2,7-8.
〔26〕〔33〕〔46〕〔47〕〔59〕张世禄.汉语在世界上之地位〔A〕.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12,110,110,103 -104、111,104.
〔27〕〔55〕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A〕.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C〕.汪馥泉编.上海:学术社,1940.59-60,63.
〔28〕朱自清日记 (1932年10月3日)〔A〕.朱自清全集:第9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63.
〔29〕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A〕.傅斯年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252-253.
〔32〕高本汉.中国语言学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8,9.
〔35〕〔39〕张公辉.论中国语将成为国际语〔J〕.国讯,第374期 (1944年):20,20.
〔37〕曹聚仁.谈屑·“洋泾浜”与“世界语”〔A〕.笔端〔M〕.北京:三联书店,2010.265-266.
〔38〕〔61〕张世禄.世界语和中国语〔J〕.语文,第2卷第2期 (1937年):46,46.
〔40〕〔56〕华超.什么叫做言语学?〔J〕.教育杂志,第13卷第6期 (1921年6月20日):7,7.
〔42〕景昌极.中国语文法新探要略〔J〕.东方与西方,第1卷第1期 (1947年):13.
〔43〕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A〕.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50.
〔45〕〔50〕王古鲁.言语学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89,1(卷前页).
〔48〕简·爱切生.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M〕.徐家祯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290.
〔49〕王东杰.“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末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J〕.近代史研究,2012,(3):28-47.
〔51〕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A〕.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154.
〔53〕张世禄.言语学简述〔J〕.新中华,第2卷第19期 (1934年):123.
〔54〕陈独秀.答胡适之 (1916年10月)〔A〕.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635.
〔58〕周作人.国语〔A〕.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354.
〔62〕太炎.规新世纪 (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J〕.民报,第24号 (1908年10月10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6.3772,3773,3774.
〔63〕章太炎.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序〔A〕.章太炎全集: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60.
〔64〕章太炎.印度独立方法〔A〕.章太炎全集:第4册〔M〕.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