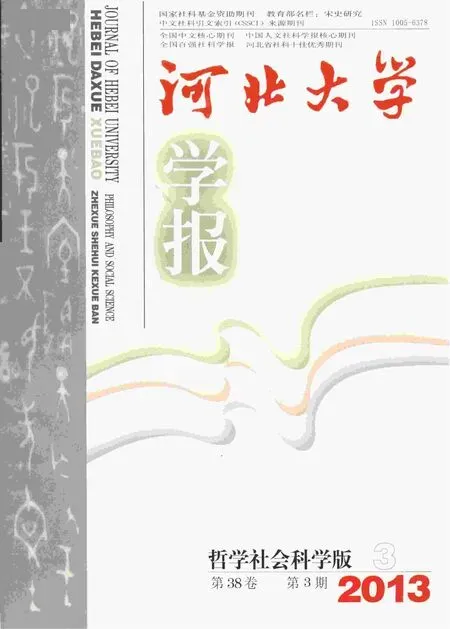民国时期的妇女社会工作
吕红平
(河北大学 人口研究所,河北 保定 071002)
从我国妇女运动史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这一时期继承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下“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格局;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刺激下,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新思潮开始涌入,带来了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新认识以及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也促进了人们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缓解和应对妇女的不利处境及其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念与方法,开始运用于妇女社会救助和社会支持的活动中。
一、民国时期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
我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就曾达到过一个小高潮[1]。但真正形而上的探讨,以及从宏观的社会运动转为对妇女的专业支持和帮助,则是民国时期才开始的。
民国十二年(1923年),梅生主编、新文化书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中,把当时的妇女问题归纳为“教育问题、生活问题、参政问题、生育制度问题、社交问题、两性问题和家庭问题”[2]。季陶(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撰文认为,当时的中国女子地位,在法律上无独立人格,在政治上是被统治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道德上完全“适用特种的道德法”,为男性的奴隶[3]。冯乘在《妇女问题概论》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和婚姻等方面剖析了的妇女不利地位:“……至于恋爱婚姻问题,因为广行父母代订婚姻的结果,简直还说不上;参政问题,不待言更远了;经济问题,仍然和历史上的一样,毫无变动,毫无解决之希望。”[4]与此同时,遗留的缠足、妾婢制度、娼妓制度以及工厂里的女工问题、贫困人口中的妇女群体,加上战乱频仍导致的女性流民问题,使得当时的妇女问题错综复杂:一方面封建父权制影响深远,非妇女解放运动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另一方面,时局动荡,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在《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一书中,谈社英将民国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分为三个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并认为“原妇女运动每次发展与消沉,多随革命运动而升降”;自戊戌变法以来,妇女运动就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5]。我国近代社会“西学东渐”的路径有两条:一是来自西方宗教组织的传教活动,二是留学海外归来的知识精英的传播。前者在客观上推动了“民主、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先进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后者则将这些理念打造成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武器。在当时社会精英们的视野里,要拯救衰败的中国,就必须进行社会改良;中国妇女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大受害者,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因此,解放妇女是变革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妇女为什么受压迫、为什么要解放妇女以及如何才能解放妇女的问题,罗家伦在《妇女解放》[6]一文中作出了颇具代表性的综合阐述。首先,对于妇女为什么受压迫的问题,罗家伦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压制主义”,另一个是“引诱主义”。有意思的是,按照他的理解,这两方面实际上一个是结构主义的权力压迫,即封建专制主义纲常的束缚;一个是建构主义的文化塑造,即以正面的价值观,比如“名节”去引导。关于为什么要解放妇女的问题,罗家伦认为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支持:一是伦理方面,不解放妇女与人道主义相冲突;二是心理方面,男子不能压制女子;三是生物方面,男女实在没有不平等的理由;四是社会方面,妇女不解放是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五是政治方面,妇女解放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六是经济方面,妇女解放有利于经济发展。至于如何解放妇女的问题,罗家伦重点强调了两点:一个是教育,去除蒙昧,提升妇女素质;一个是就业,使妇女参与到经济和社会中来。实际上这两条路径恰恰是改善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关键: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也仍然不过时。正是这些新的思潮,引发了社会对妇女生存处境和解放的新思考,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妇女工作向近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化转型。
二、妇女社会工作的发端:教会的活动与社会工作的引入
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发展历程相一致,最早针对中国妇女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是和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服务活动分不开的。教会组织在功能上至少有两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妇女社会工作具有突出贡献:一是对妇女开展了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包括妇女救济、教育、家庭和就业等多方面,为国内开展妇女社会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和方法;二是“孵化”和刺激了民间妇女组织的产生和发育,为妇女社会工作的广泛开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以基督教为首的教会组织的社会服务活动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慈善事业,包括救济、赈灾、建立福利收容机构等;二是教育和社会改良,尤其是兴办平民教育和移风易俗;三是兴办社会服务工作机构,包括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的专业机构;四是妇女社会工作。教会开展的妇女社会工作,除了传教和社会救济之外,重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建设机构,帮扶妇女儿童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建立起大量分支机构,并逐渐孵化出专门帮助和扶持妇女儿童的组织,以维护妇女的平等权益。教会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设“社会服务部”,建“妇孺教养院”,收容教育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基督教节制会增设了相应的机构,重点帮扶“妓女”群体。美国富轲慕慈夫人领导下的万国节制会还设置了“女工保护部”[7]342,北平女青年会还曾为外地来北平求学的女学生设置“女子寄住宿舍”和“学生俱乐部宿舍”[8]132。教会还创办了一大批以帮助和扶持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庭为宗旨的医院和慈善救助机构,如创办了专门的“女医院”,建设了妇婴医院。这些医院在正常营业之余,还兼行社会救助职责,比如宽仁女医院、仁济女医院等。这些工作实际上都已经引入了当时西方国家刚刚兴起的社会工作方法,并且几乎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同步发展。
(二)兴办女学,提高妇女素质
徐宗泽编著的圣教杂志丛刊之一《妇女问题》认为:“女子有求真爱美之司,无异于男性,故亦应当培植之,使之发育;换言之,即女子不可无教育是也。”[9]这一观点表明了基督教对男女平等和妇女教育的态度。在兴办教育方面,基督教教会组织在中国本土投入颇多,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兴建体制内的学校,自1831年到1920年,就建设各级小学、中学、大学及专科学校7382所,吸纳学生近30万人[10],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以及后来建立的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另一个层面是兴办各种社区教育,包括成人识字班、成人夜校、各种短期技术培训班和主题教育班等。女学方面也是如此,除兴办各种正规女子学校之外,还在城乡开展各种短期的女子识字班和女子技能培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下属的智育部,1924年10月就开始为北平一切不得入学校的妇女开设英文、国文、手工、缝纫、编物、弹琴、打字、唱歌、算术、注音字母、家政、中西烹饪等各种培训班[8]132。类似的还有在城乡社区开展的知识讲座和电影观摩等多元化的社区教育活动,比如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在1924年4月开展的卫生运动大会上,东北城、北城、磁器口、灯市口、西北城五个地方服务团组织了近30场包括妇幼保健知识在内的专业卫生及疾病预防演讲,向广大妇女宣传和普及卫生与疾病预防知识[8]126。如果说前者是基督教教会对正规教育的贡献,那么后者则带有那个时期社会工作在社区开展的典型特征,这也包括传教士在农村开展的妇女教育工作。
(三)移风易俗,打破束缚妇女的枷锁
基督教教会开始在中国传教后,力主变革中国社会的传统陋习,开展了大量针对赌博和吸毒等不良风气的矫正和服务活动。在诸多关于妇女的社会陋习中,“缠足”是尤其被教会反对并纳入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左芙蓉在其著作中曾谈到:“缠足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陋习,曾经给中国妇女造成严重的摧残,近代最早出现的反缠足宣传和戒缠足会,多由教会和传教士发起。”[8]117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刊物上发表的反缠足言论和教会发起的反缠足(天足)运动,对破除妇女作为满足男性变态审美和权力奴役的“牺牲品”的不公正社会性别格局,打破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移风易俗范围内的社会改良活动,还包括针对特殊妇女群体,比如婢女、娼妓的帮扶和社会支持活动[8]133。
三、妇女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与政府介入
(一)本土民间组织的妇女工作
这一时期,在西方教会组织的影响和推动下,除教会组织之外,一些非教会背景的本土民间组织也开始开展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妇女工作。这些组织既有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有由商业精英和社会活动家发起承办的以妇女儿童救济和教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本土民间组织,如天津的长芦育婴堂、广仁堂等[11]。本土自发建立的民间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以帮助和救济贫民、同业或同乡为主要宗旨的普济院、同乡会、共济会等慈善或互助组织,以及以救济贞节烈女为主要职能的保节堂、贞节堂、崇节堂等妇女组织[12];二是自西方引入的具有现代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以救助为主(包括战时临时救济以及对妇女儿童的救济和帮助)的民间组织,如国际救济会、华洋义赈会、救乞会等。无论是传统还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当时都已经开始了由纯粹的救助性质到教养的转变。以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为例,1932年的报告书中就记载了下面的内容“……本年度共办新旧案171件……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本会内个案中选定妇女五人交由协和医院职业治疗部卜女士办公室开始教做女工……本年一月其中一人选充工头担任管理及教导女工之责任,并迁至本会办公室继续工作,于是妇女工厂始正式成立。嗣后人数渐增……”[13]这种帮助方式的变化说明,已经从传统的救济发展到专业的“助人自助”,带有了现代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的特征。
(二)政府介入与妇女社会工作的体制化
民国初期,政府除了在法律上对“不幸妇女”有救济规定之外,对妇女的救助主要从属于救灾工作。1928年,内政部颁布救济院管理规则,主张将贞节堂及济良所等设施与其他救济设施合并,成立新的管理规范的救济机构。随后,各地也都开始了机构改组。如长沙将原有的养济院、保节堂等合并为湖南省立救济院。另外,湖南45个县市也先后将原有的救济设施合并,成立新的救济设施。就全国而言,改组后的救助机构迅速发展到各类救济院、所466个,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专门救助不幸妇女的机构,如妇女救济院、慈幼院等。据1930年统计,共收容教养不幸妇女52464人[7]174。这一时期的妇女救助工作虽然仍以传统的收容方式为主,但也出现了向现代福利制度转变的苗头。
1940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公布《社会部组织法》,同年11月取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另在行政院内设立社会部,并将内政部民政司管辖的社会福利业务划归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社会部遂由党务系统转到政府系统。社会部的设立反映出两个转向:一是政府开始将社会福利事业纳入行政管理体制中来,顺应了现代社会管理的要求,因为社会福利事业是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尝试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并纳入社会福利体制。杨光辉在1949年《社会建设》第一卷第九期《实验救济应有之认识》一文中从社会救济角度总结概括了这一变化:“社会救济,将由社会救济趋于社会保险,更由社会保险进而采取社会安全制度。在方法上,已由个人慈善事业转为政府举办,由习惯的办法到社会立法,由自觉的施舍,到社会个案工作。”[14]
这一时期,妇女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保障已经开始纳入立法,尤其是开始把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及儿童的社会工作系统纳入到了社会行政管理和社会福利的体制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48年7月1日出版的《社会建设》第一卷第三期对重庆实验救济院的介绍 :“实验救济院,根据社会救济法第一章各条所规定的从事实验:(一)贫穷救济;(二)灾难救济;(三)矫正救济。他们根据这三种规定,分设安老所、育幼所、习艺所、残疾教养所、施医所、助产所,均各按照性别性能予以救济,另设习艺工厂、习艺农场,分别予以习艺……”在其具体工作中,该文还用到了“辅导”“谈话”“个案记录”等社会工作专业术语,并且能够挖掘其中的“助人自助”理念和“社会功能重建”目标。该文最后提出,“多方尝试,必要由事业化达到专业化,由专业化达到计划化”[15]。重庆实验救济院的工作表明,无论从系统还是从专业角度而言,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体制都已经初现端倪。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351-356.
[2]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C].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
[3]季陶.中国女子的地位[M]//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66
[4]冯乘.妇女问题概论[M]//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55
[5]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南京:妇女共鸣社,1936:2.
[6]罗家伦.妇女解放[M]//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1-23.
[7]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
[8]徐宗泽.妇女问题[M].上海:徐汇圣教杂志社,1926.
[9]同人.本刊宣言[J].中华基督会教育季刊,1923(1):1.
[10]左芙蓉.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M].成都:巴蜀书社,2009:132
[11]任云兰.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京津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J].天津社会科学,2006(5):141-144.
[12]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2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90.
[13]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报告书[Z].1932:61.
[14]杨光辉.实验救济应有之认识[J].社会建设,1949,1(9):23-27.
[15]杨光辉.重庆实验救济院工作概况[J].社会建设,1949,1(3):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