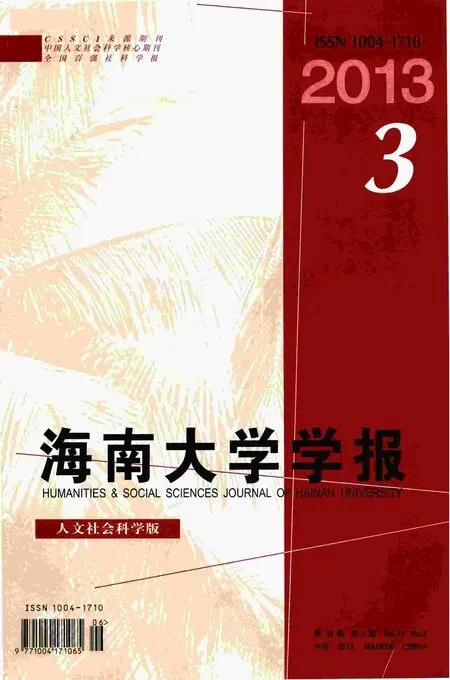樗下的彷徨——庄子“逍遥义”散论①
朱 赢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浩荡两千年,庄子的“逍遥义”遍入各家思想,但各家似乎都无法独善自得。故窃以为,在理解庄子“逍遥义”时,不应简单地执门派之见作解。
《逍遥游》中只出现一次“逍遥”,说的是樗下的彷徨者。尽管这种“逍遥义”实际属于“天分”,因而未必由人为凭一力、一念所能求得,但求不可求之“逍遥”,恰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意”在其中。庄子或许并不打算把“逍遥义”展开,或许一旦展开,“逍遥”注定失其本义。那么,不妨带着《逍遥游》中瞽、聋者的视听去造访——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忘言几处以期得意几分。
由此之故,笔者不得不暂且摆脱学院派的论说界定之书写,尝试于阅读的冥想之中去看、去听——愿心领而神会之也。
一
不可声张。
道不可说,道说不可。可与不可之间,说与不说之间,彷徨着一只无厚的“形影”——形影,不过是个牵强的指代。或许,其“形”已幻化了灵魂,甚至仅仅只留有某种意念;而“影”更未尝可见。逍遥者自称是游于“无”的,他游于传说中的“无何有之乡”。但偏偏,那么多人从“无”中“看清”了、又“听懂”了他:逍遥,真的可以说清道明吗?
倏、忽二帝见中央之帝“浑沌”无七窍,便为他日通一窍,结果七日之后浑沌就死了。[1]68
焉知言说“逍遥”不会使逍遥本身招致通窍绝命?所以声张不可,并非声者不可声、张者不可张,而是可声、可张之外的不可。声是由于听到了能听到的,张是由于看到了能看到的,但谁又能保证,在“形影”所在的无何有之乡,想象者非瞽非聋?
或许并没有什么费解的天机:“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1]6无非是樗木下的形单影只,他说逍遥就是无为——奈何,世世代代,尔等都在为无为的逍遥而煞费苦心!
二
没有天眼与天听,要如何到达“无何有”的异乡呢?庄子或者是能还乡的,但庄学后人恐怕多属“外来”——有谁真的“逍遥”了?
惟有立于“此在”。
逍遥并不向天分之外展开;人,仍须尽人事。彷徨于逍遥之下,欲得其意,或许正需带着瞽、聋的视听去造访;听不见的听见,看不见的看见。
三
庄子没有圣人的衣冠,因而多半读者对其有景仰却不必有敬畏。历代庄学观点差异之大,在诸子学术中绝然鲜见。清代陆树芝感慨:“博采者是非杂陈,妄庸者任臆猜混……说经者多而经亡,祸有甚于秦火者,况以洸洋自恣之文而復为瞽说所蒙”[2]4。此等愤世嫉俗的言语到底显露了现实困境:凡者何以为超凡者立?立者可能做到虚己而及人吗?陆树芝对庄子有“雪”之妙喻:“且夫庄子,雪人也;其文,雪文也”,可万一俗口一开就玷污了雪的质洁呢?
还有另一种情形:不是庄子被玷污了,而是庄子引起了玷污。早先荀子就批评庄子“敝于天而不知人”[3],后世执儒家意志以隔庄子者实不在少数。尤其越到晚近,现世的危机越逼人,批判也就表现得越为自觉。甲午战争那一年,王先谦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作序,竟写下“彼庄子者,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寥阔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乌足及天下”这样的微词。庄子似乎是有毒的:“晋演为玄学,无解于胡羯之氛;唐尊为真经,无救于安史之祸。徒以药世主淫侈,淡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4]1无怪乎到了郭沫若,干脆就赤条条地揭了庄学的老底:“抗又无法去抗,顺又昧不过良心,只好闭着眼睛一切不管,芒乎昧乎,恍兮惚兮,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游戏人间。这本来是悲愤的极端,然而却也成为了油滑的开始”[5]208。“油滑”之说不应为过。自从世间有了“逍遥”这一剂丹方,仿佛任何形式的落跑、推脱都得了至上的加冕。仅仅“无为”二字,连圣贤的身体力行都化解了,况乎芸芸众生。可有大仁能成全忍辱负重?可有大义值得忍辱负重?倘若曾经是残暴的现实催生了无为,那么终于,“无为”的逃匿竟也做了残暴的帮凶。
逍遥,难道只是一剂美妙的麻醉品?一饮尽之而自以为废,是否就此得道了?即便保持沉默,中国的书生们到底绕不开庄子:心有向往者,总不免面对现实的拷问;心有戒备者,又难保日后不会向虚静中求解脱。“无为”如此难至,却又难以不至,浩荡两千年,庄子的“恩惠”实在太普遍了——普遍到无论是“求”还是“反”,都无法独善自得,“若即者”与“若离者”却在喋喋不休的纷争中敞开彼此的困惑。
陆树芝渴望是庄子的知音:“庄叟如可作也,倘亦曰‘我有文字,人梦讝之;我有苦心,云雾蒙之;得一畸士,从而雪之’乎?”[2]5拨云撩雾,他“雪”庄子之用心实乃为孔子之道。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执此类观点的学者。韩愈就曾疑庄子本是儒家,而明末的觉浪道盛更提出“庄子托孤”说,认为庄子“实儒者之宗门,犹教外之别传也”[6]。该说法由方以智申发,并著成《药地炮庄》一书。觉浪乃一高僧,怎就从虚静中看出了庄子的“儒性”?入清后,遗民方以智随觉浪理佛灯,却也不肯随无为而求一己之逍遥?连郭沫若也疑庄子本是“颜氏之儒”,并说庄子在不少地方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儒家”本色[5]194。原来《庄子》中的儒道之争是可以作“趋同”解的,曾经所谓的是非判断在某种眼光下如同庸人自扰。
以“有为”作“无为”的归宿,油滑的危机自是被肃清了;只不过,那彷徨的形影果然就此真“象”大白?一旦有了征圣的冠冕,是否玷污的风险从此不再?
四
谁的声张?
说庄子之要归于老子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提到了庄子,司马迁认为《庄子》“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而《庄子》中诋讠此孔门的内容,是在“明老子之术”[7]。
说“子夏出田子方,子方出庄子,庄子乃为孔颜滴髓”[8]的方以智,终在《药地炮庄》末尾透露了玄机:“和尚以庄子为托孤,实是和尚托孤于庄子,而庄子又因得托孤于和尚也。”[9]
后来也有人说:“庄子另是一种学问,与老子同而异,与孔子异而同。今人把庄子与老子看做一样,与孔子看做二样,此大过也。”[10]7
道学、玄学、佛学、儒学、易学、理学……次第爬上庄子的形影。并非庄子不“有为”,并非庄子不“无为”;但,“有为”便是“儒”,“无为”便是“道”——非此即彼,乃真知儒、道乎?也并非,庄子入不得百家视野,但,百家视野焉得拘庄子于私意?
谁在声张?知者不外自知。逍遥者自在彷徨。
五
逍遥——快活。这样的组合几乎成为常识。然而从“逍遥——自得”发展到“自得——其乐”,其实历经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宋代林希逸解“逍遥游”:“游者,心有天游也;逍遥,言优游自在也。《论语》之门人形容夫子只一‘乐’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台》曰:‘乐只君子。’亦止一‘乐’字。此之所谓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11]
但庄子不曾说过,逍遥就是快乐的。他只是说:
“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1]6
“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1]58
“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1]118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1]223
可见:
(1)逍遥系乎“无”:无为,无事。
(2)逍遥关乎“自得”:寝卧,心意。
(3)逍遥顺乎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4)逍遥超脱世俗:尘垢之外。
至少在表面上,“逍遥”与“彷徨”并列,描述某种状态,而并不带有指实的判断性。当然,诸如“尘垢之外”、“心意自得”的陈述会令读者产生某种比附现实的高下之分,但这未必是庄子所想。一个无为、自得的人,何苦为现实中的比较级而沾染尘埃。“无为”高于“有为”?这是向往无为的有为者说的。逍遥之所以显得更高明,大约是读者在难以企及的想象中明显感到了自身的不高明。
因而,“逍遥——快活”只能作为一种立足于现实的假设。逍遥可自得,自得便有乐——顺理成章,却不过来自推演;并且这种推演可能已经消解了“无为”的超然。须知庄子尚有“至乐无乐”[1]142一说。
逍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说文解字》:“逍遥,犹翱翔也”,“臣铉等案:‘《诗》只用消摇。此二字《字林》所加。’”[12]84。《说文解字》中:消,尽也,从水[12]562;段玉裁注为“未尽而将尽也”[13]。摇,动也,从手[12]606。《礼记》中记录了孔子死前的“消摇”:在去逝前7 天的清晨,孔子“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14]
将尽未尽的余音。哪怕是分寸间的距离也会招致忧郁。“逍遥”轻乎重乎?现实摸不到它的分量。
六
“大而无用”是惠子对庄子的断言。或许《逍遥游》通篇都在回应。在开宗明义的首篇,庄子并不急于揭示逍遥的奥秘:“逍遥”一词,仅仅在篇尾出现了一次,并且丝毫无关得道的门径;反而是关于“大——小”、“无用——有用”的论述贯彻了通篇。
《逍遥游》中出现了大量的比较级:如“鹏”这一对象,与之形成显著对比的是蜩、鸠、鴳。因而在这一组比较中,如果将“鹏”设为“甲”,将“蜩、鸠、鴳”设为“乙”,那么直观来看,无疑甲大而乙小;或者像许多读者得出的结论那样:甲高级而乙低级。以上结论似乎不至惹出什么大纰漏;无论是阅读常识还是经验常识都能支持这种判断的合理性。何况庄子似也有意为之,故而先让蜩、鸠笑鹏: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1]2
而后就顺水推舟地以另一组对比化解蜩、鸠的笑话:
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1]2
“二虫”之喻即便不带有嘲讽意味,也已明示了大、小之指。马其昶注“之二虫”:“‘之’,‘是也’,斥蜩、鸠。”[1]2将“二虫”作“蜩、鸠”解是后世较为认可的,文义中所指的显然应是“鹏大虫小”。但正是这直观中“甲大于乙”的陈述,却曾经被申发为“甲等于乙”、或者至少是“甲不大于乙”的解释。魏晋时期郭象的注本认为“二虫”应指“鹏、蜩”:
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2]15
在郭象看来,鹏与蜩、鸠虽然在“体征”上有大小差异,但从“适性”说来,它们的逍遥却属同质。因而他将“蜩、鸠笑鹏”一事解释为“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15]5。于现实而言,这是一支绝佳的安慰剂:只要各安其分,即便小鸟只能飞上枝头,却也势同大鹏“扶摇而上九万里”。然而有一些潜台词却不得不防:大鹏不自贵于小鸟,可等同为小鸟自贵如大鹏?小鸟无羡于天池,是否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前提:小鸟就是小鸟,它不可能飞到天池一游;而只要做到“安于不能”,“不能”的小鸟便与“能”的大鹏有了一样的境界——即郭象所认为的“逍遥之大意”:
夫小大虽异,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5]6
既然如此,为什么蜩、鸠还要以冷语笑鹏?为什么——先将大与小同流,再将小与大同列之后,逍遥之“大”不过是将“大鹏”拉入了“小虫”的行列?
之二虫?又何知!
当然,走在郭象反面的注本绝不在少数。就是因为“逍遥”——那庄子不曾点破的迷津,竟能散发出各种南辕北辙、但又合乎情理的解释。莫非,庄子“逍遥义”所敞开的空间恰如北冥、南冥的鲲、鹏之化?
宋末的罗勉道认为,《逍遥游》的奥秘就在一个“化”字:
篇首言鲲化而为鹏则能高飞远徙,引喻下文人化而为圣为神为至则能逍遥游。初出一化字,乍读未觉其有意,细看始知此字不闲。[16]110
与郭象试图以消除差异而达到逍遥的观点不同,罗勉道在“化”中肯定了大小差异;因而,蜩、鸠与鹏是绝不可能“逍遥一也”的;并且于“逍遥”之中,尚有优劣之分:
第一段言鲲、鹏、蜩、鸠、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飞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为逍遥游有优劣。[16]118
罗勉道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作的排序值得推敲:他认为至人、神人、至人者都是“化之大者”,但“三等亦自有深浅”:至人最高,神人次之,而圣人的逍遥在三者中为最低等。对“至人、神人、圣人”三者注解,罗勉道显然是顺着孟子“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7]而推演的:
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测之谓神,至者神之极。[16]116
理学的痕迹昭然若揭,况乎罗勉道还孜孜期以“逍遥”而教世人求道:
夫天之所赋,各有定分,岂可强同蜩、鸠、斥鴳于鲲、鹏哉。而人则无智、愚、贤、不肖,皆可以阶大道,然亦有自视若蜩、鸠、斥鴳者焉。故于篇终晓之曰:人虽如呺然难举之瓠、拥肿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资质用之,随事而化,岂夫其为逍遥游哉![16]119
这究竟与郭象有点殊途同归的意思了。郭象说蜩、鸠、斥鴳和鲲、鹏是可以“一样”的,罗勉道则声称小化、大化间不可强扭的差异;但最终,罗勉道认为人“皆可以阶大道”,好似郭象认为无论大小都可能达到逍遥。当然,“阶大道”的罗勉道绝不会将大鹏与二虫“齐”;相反的,他教人不要“自视若蜩、鸠、斥鴳”,其意指对“逍遥游”应抱有鲲鹏之志。看似顺理成章,只是有一点:庄子所举瓠、樗无用,是因大、因超常而不为“常识”所用。罗勉道在说“人虽如呺然难举之瓠、拥肿卷曲之樗”之时,难道确定了这些人都是因“超越常识”而无用于世的?
“化之小者”弗如“化之大者”;那么“人皆可以阶”的“大道”,乃“化之小”还是“化之大”?
罗勉道说鲲、鹏之化是“质之大者,化益大也”[16]110。这“大”的奥义到了明清之际愈发显山露水。明代高僧释德清:“逍遥者,广大自在之意。”[18]明代陆西星:“夫人必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故《内篇》首之以《逍遥游》。游,谓心与天游也。逍遥者,汗漫自适之义。夫人之心体,本自广大,但以意见自小,横生障碍。此篇极意形容出箇致广大的道理”[19]。明代吴默的《逍遥游总论》:“此篇以‘大’为纲。”[20]
及至清初的林云铭,对“大”之旨意的阐发可谓无所不至。林氏以为《逍遥游》“是惟大者方能游也,通篇以‘大’字作眼”[10]9,因而,他在注解时亦是通篇以“大”观之。林云铭颇有其细腻处,对行文的“话音”重视有加。如蜩、鸠笑鹏一事,他格外点出“笑”字:“笑人倒是此辈,若鹏必不轻易笑人”;又“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一句,他格外点出“而已矣”三字:“‘而已矣’者,言其无他能,亦无他愿也”。大者大矣,小者小矣,界限分明之后便是森严的等级。然而林云铭不再像前人欲化解小者之悲,却随时透露出对“小”的嘲讽与鄙夷。“人惟求其大而已”,为此,他不惜弃置“不轻易笑人”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袒露出“高贵”的眼色:“至如鹏之适,而斥鴳之笑也,诚不异于二虫所云,此无他,大小之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10]2
林云铭或许是晓畅真相的,他的二十六则《庄子杂说》实在有独到的精彩处。又或者,于现实之中,他遭遇过太多“以小笑大”、不知深浅的荒谬,因而恨不得在解《逍遥游》时把“二虫”的可悲一吐为快——只可惜他这一说,恐怕会招来“大”之奥义的反讽:以大笑小者,究竟是由于知“大”还是知“小”?
何为逍遥?何以逍遥?《逍遥游》中的众生们:鲲、鹏;蜩、鸠、鴳;列子、尧、许由;神人、圣人、至人……游乎逍遥者其谁?
若从郭象之“适性”,则万物皆可逍遥。
若从罗勉道之“化”,且任其逍遥也,惟有优劣之分。
若从林云铭之“大”,则鹏能逍遥,神人、圣人、至人可逍遥,而蜩、鸠之类与得道无缘也。
……
还有诸多不胜枚举的“逍遥门径”。
有意思的是,《逍遥游》中的起始形象“鲲、鹏”恰恰引发了极大的“逍遥”争议。与郭象年代颇近的支遁是魏晋时期另一位极重要的解庄者,他的《逍遥义》解逍遥之旨为“明至人之心”。支遁认为:惟有“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至人是逍遥的;而鹏是“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后人以为“鹏因大而累”者亦不在少数,如宋代王雱认为“道”是“无方”、“无物”的,而鲲、鹏与蜩、鸠都是“有物有方”——“有物有方,则造物之所制,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岂得谓之逍遥乎?”[21]鹏作为一个“大”形象无疑,却“彷徨”于“逍遥”、“不逍遥”之间——亦是亦非,此乃一例。
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形象——列子。他明明能御风,看起来十分轻巧快活,庄子的原话描述是“泠然善也”;但即便认为万物皆可逍遥的注解者,也不会将列子注为上乘。只因为文中的“有所待”三字透露了取向:“御风”必等风来,无风便不能成行,何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所以王先谦就直说“列子亦不足羡”,又说“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4]5。庄学之中,执此观点者众多;以“所待”之有无而判别“逍遥”,几乎成为破“表象”而识“本真”的法眼——列子可说是“似是而非”的例证。
若“亦是亦非”者常见,“似是而非”者常有,则“逍遥”之奥义难道只系于众知无疑的“至人、神人、圣人”?他们是逍遥的大义吗?庄子好像没这么说过。
《逍遥游》中只出现一次“逍遥”,说的是樗下的彷徨者。
七
不妨重读庄子的“大”寓言。
怎么读是大问题。林云铭的“杂说”得其妙处:
庄子学问是和盘打筭法,其议论亦用和盘打筭法,读者须知有和盘打筭法。
庄子学问有进一步法,其议论亦每用进一步法,读者须知有进一步法。
《庄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类于儒书,或有类于禅教,合三氏之长者,方许读此书。
《庄子》为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禅解,究竟牵强无当,不如还以庄子解之[10]10。
还以庄子而解《庄子》——重哉!何以“还”——重中之重!
可弃乎一己之知,以防二虫之害?
既是“和盘打筭”,那么分而治之显然有折损的风险;若勉强为求解而分治,则仍需把握“进一步法”而前后贯通。
自开头“北冥有鱼”至“此大小之辩也”部分,出现的对象大部分非“人”,大概是出于“客观”需要而以免推己及“人”的混淆。而在观“客观”时,却仍有一个隐形陈述者在说话——客观之观,“他”一开始就声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大”是无疑的,但究竟如何“大”,却是“不知”。之后陈述的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是引《齐谐》记载令世俗想象“大”的尺度,实际仍是以“大之知”而彰“大之不知”。紧接着,这个陈述者提出了一个极大的怀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人从下往上看天,与大鹏从上往下看天,是不是一样看不到尽头——真是“大”不可测的真相。随之“他”又举出一个十分浅显的例子说明大、小殊异:在小洼地里倒一杯水,只能载小草以为舟,放一个杯子上去就载不动了;而载动大鹏却需要厚实的风力——不仅是说鹏大,更昭示了天之大。正当此时,蜩、鸠却不知天高地厚地笑说“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二虫一发笑,陈述者便感慨:“之二虫,又何知!”并且,此“二虫”是真不知——不知何为大,只缘不知一己之小,否则它们应该不会如此发笑。
直至上述内容,庄子所述还是清楚明白的:大就是大,小就是小;若进一步推演,则庄子可能还在隐射:大未能知,小不自知。然而随后的,当陈述者真正把“小知不及大知”说出来后,情形反而稍显混杂了——亦是亦非?似是而非?陈述者由“小年不及大年”说起。他举出了看不见夜晚的“朝菌”,不知春秋的寒蝉;它们只是小年。又举出了楚之南以两千岁为一年的冥灵树,以及上古以八千年为一春的大椿树;它们才是大年。这是一组稍显复杂的寓言:若从相对而言,则能活一个季节的“寒蝉”较只能活一个白天的“朝菌”,显然已是“大年”;而以五百年为春的冥灵树较之以八千年为春的大椿,无疑又太过渺小。但陈述者在此处却不急于显示“相对”,而是确切地从属了世俗的“人”的常识:人是得享朝暮白昼、春夏秋冬的,所以无朝暮、无春秋的生物相对“人”的时间只能属“小”。然而人能不能属“大”呢?这里没有亦是亦非。春夏秋冬,不过人间的定义,而五百年为春、八千年为春,早已在人定的限度之外了。于是陈述者所举的彭祖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人间“年七百岁”的寿长足以为“大”吗?尽管众人都因不及彭祖的年岁而悲。陈述者没有发话。“大”有大的限度,知“大”者当知此度。所以他只接着陈述了汤与棘的对话:大鹏飞上九万里,仍然被鴳嘲笑。鴳声称自己腾跃而上、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也是“飞之至”。陈述者说:“此大小之辩也”。
辩乃辩矣,但人间之语未必定夺天分。
自“故夫知效一官”至“窅然丧其天下焉”部分,虽承接“大小之辩”,却终究变得错综复杂。一干人等相继出场,孰为大、孰为小?一连串的亦是亦非、似是而非。若非大知,安能详辩?
“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于世俗之中,不正是有用之才;但陈述者认为,这不过如同鴳雀的“飞之至”。此段行文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蜩、鸠、鴳“笑”鹏之后,首次出现了人间之“笑”。不过这个发笑的人——宋荣子,看起来倒应该比被笑者更高明;他不把个人荣辱系乎世俗眼光,难道不是达到了某种境界?然而陈述者却再次话锋一转,将其否定了。
暂且停顿。庄子究竟想说明什么?即便是俗知为小,那些德行合乎尺规而有用于世的人,那些心性豁达而辩乎荣辱的人,难道就彻底被隔绝于“高明”之下?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庄子否定了他们的“高明”?
“列子御风”透露了取向——陈述者说:“犹有所待者也。”诸多庄学家从“待”中解开“逍遥”的奥义。“无所待”较“有所待”为高,在此处似不需质疑。但惟独行文至此,才格外显出主题的进入:前面不都在说大知小知、大小之辩么,此刻才真的开始“逍遥游”吧?在世俗“小知”上,善守德行、辩乎荣辱显然并不低下;不过在“逍遥”的层面上,他们就犹如鴳雀。当然,若有个狡猾的读者反问到:那些对“逍遥”无所待的人呢?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祈求得到逍遥,那么德行、荣辱在现实中是否仍位列其“大”?
“逍遥”是不会作答的。或者“他”会说:逍遥岂在“待”中!“无”是可以“待”的吗?“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有待的世俗与他们可有干系?
至人、神人、圣人是《逍遥游》中的“无”解之谜。有人说他们是一人的三种属性,也有人为他们“论资排辈”;更纷杂的还有对号入座:后文中出现的尧、许由难有定分,藐姑射神人、四子亦高下不明。既然庄子有心考验后人的“知”性,那么不如暂且将推理悬置。回到原文之中,“至人、神人、圣人”虽关乎“逍遥游”的主题性陈述,整个段落却并不脱离“大小之辩”:陈述者在此段开头评说“知行一乡、德合一君”者有如鴳雀,那么在段末出现的“至人、神人、圣人”应属“大”流,此为其一。又,此段提出“无所待”之重旨,而段末出现“无己、无功、无名”,可见“至人、神人、圣人”的“无”应与“无所待”相关,此其二。一旦将此二条线索“和盘打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多少能得出些“大知无待”的意味。林云铭解此语为“无待于己之所有”、“无待于功之所及”、“无待于名之所归”[10]5。己、功、名都是世俗的声张,待己、待功、待名都是世俗所求,于“大知”者又有何用!
“用”在此一大部分中也是逐渐显露出来的;如同题旨“逍遥”一样,“用”亦被大、小牵引着——逍遥与用,看似一对截然不合的反义词,此时却在盘中纠缠为“大小之辩”的漩涡。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说“予无所用天下为”——谁更高明?藐姑射的神人如此超凡,是否就代表了至上的逍遥?
陈述者只自顾陈述,此外他不露任何评说。“小知”愈发地力不从心了——谁为大,谁更逍遥?庄子没有明示。
然而有一种通往“大”的可能性倒是向世俗展开了。肩吾听说藐姑射神人的故事,不肯相信。连叔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连叔的高明处在于:小知也能自觉于“小”的限度。
自惠子与庄子的对话开始,直至结尾,亦是亦非、似是而非都随“陈述者”的身影退场了。他已经完成了大小之辩?只等庄子把最后的“逍遥”说出来了。
惠子说大瓠无用,庄子向他指出如何可用。惠子说自己的大樗树不中绳墨规矩,不得受用,又说庄子的话大而无用;庄子便以“逍遥”作答——全文中仅有的“逍遥”: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1]6
此句中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1)患其无用的“患”,非真的无用,而是“子”患其无用。惠子说樗木不为人所用,即不材,是因为不合绳墨也不合规矩。然而绳墨、规矩无非是俗世的价值标准,故“不材”只是于俗世价值的不材;而患不材,自是局限在“俗知”之中。
(2)“无何有”与“彷徨”、“逍遥”的关系:“无何有之乡”在“俗知”之外,是“无用之用”的去处,又成为彷徨、逍遥的归宿。因而,逍遥即便在《庄子》中作“无为”解,也未必是真的“不用”;不过是其“所用”在“无用”,而此一“无用”的判断又是出自“俗知”的。
(3)“安所困苦哉”的“困苦”:对俗知而言,无用有困苦,此乃惠子的“患”。对俗世而言,“用”亦有困苦,此乃庄子说的“夭斤斧”。庄子在此显露的困苦岂独止于惠子一人。
还有一个“玄机”可能暗藏了庄子的“用”心。
惠子说自己把无用的大瓠打碎了,因为它实在太大:用来盛水,其坚固度不足以支持水的重量;切开做成瓢,又没有水缸容得下它。庄子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惠子是“拙于用大”:宋国有人善为不龟手之药,他们的家族世代从事漂丝于水的工作;这药虽然保护他们的手不开裂,但他们从事的工作只能赚到数金。后来有人以百金买走了他们的药方,用在吴国“冬与越人水战”中;那人因大败越人而得到了封地。就是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庄子就指出了大瓠的用处:“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乍听之下,这实在是个很“逍遥”的“大用”,与树“大樗”于无何有之乡几乎异曲同工。然而有一个“机关”不得不道破。庄子在此作了一个十分隐晦的转换:大瓠用来“盛水”、做成“水瓢”,或“以为大樽”,是其使用性质发生了改变。所以文中“大瓠”的“用小”、“用大”是基于“器具”本身的——是“用来做成什么”。而“不龟手之药”的情况实则不同:这药的使用性质就是不让手开裂,未曾有改变;但庄子却说用于“水中漂丝”则小,用于“冬日水战”则大——是“用来去做什么”。当然,庄子说这话仍是以世俗标准——“财富”作衡量的:用于漂丝,世代只得数金;卖给知用者,则得百金;知用者得其用,终得封地。
瓠的“用大”是落回到“大”自身的,而药的“用大”却是用于战争。况且不龟手药并没有“大而无用”的尴尬,庄子引此例说明“用大”,实在不可等闲视之。或者虚静、无为也有其限度?是否——大而无用于世者以“用于无”为上;有用于世者又当以“用于世俗之大”为上?
八
有一些重要但纷争的问题在上文中跳过了——尧、许由、藐姑射神人和四子。看见的、听见的论述很多,却不外乎持一种见地将他们对号入座,再根据各自对“至人、神人、圣人”的理解作出排名。
《逍遥游》读到这里,实在也应自知了;对那些世俗之外的不凡者,要如何用凡语评说?当然,如果力强为之,非要作出点区分,那么仍有两种人值得关切:一种是与现实有关的,另一种则“游乎四海之外”。
《逍遥游》中有两个角色尤其动人。
第一个是尧。不是因为他肯把天下让与他人,而是他手握天下却不力争。尧绝不是鴳雀一般的见识,《逍遥游》中写他是到过神山藐姑射的。他到了那里,见到四子,“窅然丧其天下焉”。这就是先王之道的限度:天下没有谁比他更大,然而他却能知守于“一己”。其实,尧大可以动用独尊的权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有一则故事:太公望封于齐时,将两个声称“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的贤人诛杀了。他们自足于耕作,无争于世俗名利,为什么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其实,哪怕只是若有所失的感受,也会让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感到不安。太公望说“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23]但尧却不是这样。他恐怕只能做个望神山而兴叹的王者——他是知的,也到了那里,却并不走入藐姑射的神境。窅然失天下,尧能不能不失?
还有一个是庄子。他当然也不是鴳雀;并且,他可能是惟一洞察了一切的那个无用之人:他知道世俗的知,世俗的用,世俗的有限与困苦,也分明觉察了世俗之外的一切奥秘。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1]97。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知无”者,却也不像藐姑射的入化之人。为什么,逍遥的结局只是在无何有之乡种下无用的樗木?樗下的彷徨者,可曾声张了什么?
九
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但,只能言尽于此了。其实,他早已把什么都说了出来,只是那样的说却指向了“不知”。
从来,以自知为大者,都在以小知害大知。大知是“知无”的——以无为知,无能养知。惟知能此,则以“小知”存“大”,“小”才不至落入“大小之辩”的天分。
“声张”亦止步于此了。逍遥只在樗下,彷徨者自白于天地而不求俗知。
[1]庄子.庄子[M]∥钱穆.庄子纂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陆树芝.庄子雪[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荀子.荀子[M].安继民,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67.
[4]王先谦.庄子集释[M]∥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
[5]郭沫若.庄子的批判[M]∥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觉浪道盛.庄子提正[M]∥方勇.庄学史略.成都:巴蜀书社,2008:492.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01.
[8]方以智.一贯问答[M]∥方勇.庄学史略.成都:巴蜀书社,2008:431.
[9]方以智.药地炮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468.
[10]林云铭.庄子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1]林希逸.庄子虞斋口义校注:卷1[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12]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973.
[14]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77.
[15]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M]∥续修四库全书:956 册·子部·道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孟子.孟子[M]∥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52.
[18]释德清.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19]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
[20]吴默.庄子解[M]∥郭良翰.南华经荟解:逍遥游文.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23.
[21]王雱.南华真经新传[M]∥叶蓓卿.庄学逍遥义演变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61.
[22]王先谦.庄子集解:内篇·逍遥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
[23]张觉.韩非子校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