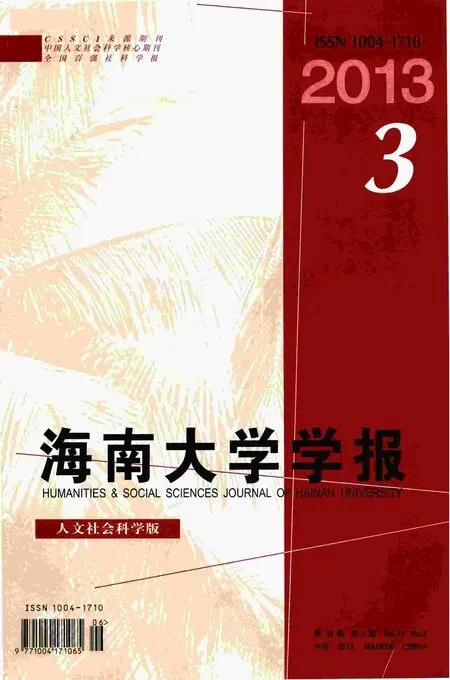治气与教化:《五帝本纪》读解
柯小刚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史记·五帝本纪》开篇第一句话中的“成而聪明”,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的开篇写做“成而登天”。小小一个词的区别蕴含的意义并不小。孔子编《书》断自尧舜,此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尽皆芟夷,至于《汉书·艺文志》中冠以黄帝之名的书,则多神仙方术一类。而太史公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篇首,述黄帝之德,记黄帝之行,不言“登天”,只说“聪明”,是否为孔子删《书》之遗意?《书》断尧舜,《史》自黄帝,取舍不同而其义则一也。何以见得?不妨细读文本。
一、阴阳:天地生物
《五帝本纪》先谓黄帝“生而神灵”:神灵者,非谓“超自然”,而是能感通自然。其次“弱而能言”:“能言”是人之为人的文明出发点。“幼而徇齐”:“徇齐”如《史记集解》所谓“徇,疾;齐,速也”,相当于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之义(《论语·学而》)。“幼而徇齐”是敏于事,“弱而能言”是善于言而慎于言。接着“长而敦敏”:敦厚往往不能敏捷,敏捷往往不易敦厚;能把敦厚与敏捷这两个矛盾的方面结合在一起,所以黄帝能化五方、合和众善。终于“成而聪明”:回照起初的“生而神灵”。“生而神灵”即《中庸》“天命之谓性”。“生而神灵”之性必须通过人之言行发明出来,是为“弱而能言、幼而徇齐”,也就是“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成而聪明”是最终成就人之为人的聪明,亦即成大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聪者耳听天命,明者眼观天象,天道之成人而人道之齐天也。《尚书》开篇赞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亦此义也。太史公书史,犹远绪圣人削删之遗意也。
所谓五帝:帝者,谛也,谛听天命之谓。聪明就是能听能见:能听天意,能听民意;能看天象,能观民风。太史公对于上古先王德性的描写,不是渲染他有多少超自然的能力,而是写他如何能听能看。天子虽受天命而代天牧民,但“天难谌、命靡常”,除了随时谛听天命,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主权契约”。
聪明,是把知识和理性从一开始就是放在核心的位置。但这里的知识是指什么呢?“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这里的核心是“治五气,蓺五种”。这是承自神农氏的传统,而神农氏又从伏羲氏而来。三皇五帝一以贯之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原本含义很简单,就是有白天有黑夜,就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昼夜寒暑往来,于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与农作关系最密切,所以“治五气,蓺五种”成为神农、黄帝、后稷、公刘的主线。于是,接下来黄帝做过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命太挠作甲子,即沿用至今的天干地支记年、月、日、时,所谓八字。《尚书·尧典》任命羲和敬授民时,日出日落,四时稼穑,其义一以贯之,构成中华文明的主脉。黄帝处在中华文明主脉的节点。这条脉发源于三皇五帝,中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下逮秦汉唐宋历朝历代,一直到现代中国。这条脉的核心就是阴阳之道。所谓生而神灵、成而聪明,聪明在起初是指明天象、历法,也就是知阴阳之理。知阴阳就是知道。
黄帝最重要的武功除了统一炎黄,就是擒杀蚩尤。为什么杀蚩尤?根据孔安国的说法,九黎君号蚩尤,隐约可与《国语·楚语》所载“九黎乱德”相关,直到尧舜时代的羲和、四岳连成一条线索。这是“师”的巫觋布魅之线,与“君”的聪明理性构成竞争。“师”把知识做了神话的、垄断的处理,把知识弄成神秘的巫术①此为“天师”。后来有儒家“人师”与“君”结合,才形成中国成熟的政教体系。而同时,“天师”的知识也通过史官制度的完善,乃至后世道教建制的发展,成为被驯服的布魅知识。。黄帝杀蚩尤,颛顼平九黎,尧舜流四岳、共工,可能都是这一斗争的表现。可以说它是一条启蒙之路,但这是一种正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启蒙。片面的启蒙是西方近现代的那场启蒙,那场启蒙为了解决那个时代的“神人杂扰”问题导致了天人隔绝。而“黄帝—颛顼—尧舜”启蒙运动的结果,却是使“绝地天通”成为“天人合一”的前提。中国从黄帝尧舜开始,到周公制礼作乐、直至孔子行教,这个漫长的启蒙过程是知识的、理性的,但同时并不是祛魅的。绝地天通并没有导致天人分离,而天人合一并没有导致神人杂扰,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反之,则有“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智者过之,则神人杂扰;愚者不及,则天人分离。《荷马史诗》和基督教是神人杂扰的战争,现代性是政教分离的俗世,而中国则是“干称父,坤称母,予兹渺焉,乃混然中处”的世界。在这里,“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仕进有先后,命途有穷通,但君子小人之间、在野在朝之间、学与仕之间,一气贯之,没有阶级斗争,根源于天人相通。
所以,华夏先王统治的合法性不在于能行超自然的神迹:那些恰恰是蚩尤、九黎、四岳这些人神巫觋所干的事。华夏政治文明特别浩大、正直的开端在于它是理性的、清明的,同时是虔敬的、德性的。《五帝本纪》载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②可参《礼记·经解》:“善书教者,疏通知远而不诬。”:这是一种清明的理性,而不是科学的、偏执的理性。所谓科学的、偏执的理性,就是神人隔绝,完全取消神性的维度,是政教分离,是祛魅,是整个世界不再有神性,不再有魅力。读《五帝本纪》可联系到孔子的“丘之祷久矣”:那是一种保有山河大地之神性的聪明。人与天地是可以感而遂通的,但是他不会因通神而贼物(贼物即害物,神迹多属此类),因通神而乱人事。他不会玩弄神通,用超自然的手段来玩弄大众。也不会把自然视为表象,致力于寻找表象背后永恒的真实。无论宗教还是哲学,在黄帝的聪明和孔子的中庸智慧面前,都显得太过偏执。
黄帝承伏羲神农,治五气,蓺五种,学在阴阳。而无论老西学、新西学,容易耽恋的是超越阴阳时辰的净土。自古中学化西,关节在此。西游记第91-92 回,说唐僧师徒四众在西方天竺国遇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之难,而终于在年月日时四值功曹使者的指点和角、斗、奎、井四木禽星的帮助下降服妖魔,说的就是用一阴一阳的时辰之道来驯服超时间的不变净土幻象。三大王原是“三个犀牛之精,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1],可比之西方哲人欲以几何学截断阴阳之变,超诸尘世之上。考三大王命名之意,乃在超越阴阳寒暑之变,脱离俗世尘垢,贪恋佛国香火,适成魔障。唐僧须经此劫,破此魔障,乃见真性。三大王居东北艮方,逃离时亦走艮方。艮,止也,高也。三大王偏在艮方,正是其偏执不变、贪恋高洁之意。故三大王爱吃敬佛香油,假扮佛像窃取供养,又有洁癖,常爱香汤凈浴,皆其偏性之情也(红楼梦中妙玉差似之)。欲超越时间,寒暑不侵,远离尘世,正是西学魔障之大者。唐之西游取经者已过此关,今之西游问学者何如?
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读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时,往往面临一个困难,就是所谓physis(自然)与nomos(礼法)之间的鸿沟问题。一直到西方现代哲学形成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乃至政治上形成不可动摇的教条:政教分离。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虚无化、犬儒化、价值相对化,乃至低俗化,同时又激起原教旨主义极端保守派的恐怖主义反动。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回过头来读《五帝本纪》,看看颛顼能给人什么启发。
“治气以教化”:“治气”治的是阴阳、四时、五行之气,这是属于nature、属于physis 的;而“教化”是教化人,是拿文化、价值、伦理道德、社会理想,拿正义、美德来教化人民,属于culture、nomos、value 的。在颛顼“治气以教化”里的“以”如何解:这个“以”通“而”,其义正如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亦如《春秋公羊传》开篇“元年春,王正月”的一气流行。在那里,从天时到人事,乃至草木昆虫,都是一以贯之的。何谓“王”?“王”字三横一竖,是贯穿天地、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治气以教化”就是王道,而不是人为地把physis 与nomos、政与教、事实与价值割裂开,使整个现代世界陷入一种深重的危机之中。这是在今天所谓发达的现代社会读古史的现实意义。
“依鬼神以制义”:《史记正义》云“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2]这一解说可以矫正现代汉语中对神和鬼的一些认识。关于鬼神有很多说法,比如《礼记》中提到,人死之后,精气发越于上谓之神,形骸归之于地谓之鬼,所以,神者伸也,鬼者归也。在祭祀传统中,既有在家庙中敬神主,也有于郊野里扫墓。庙祭是敬神,扫墓则是敬鬼。所以,《中庸》感慨“鬼神之义大矣哉!”颛顼“依鬼神以制义”要点在“义”字上。帝喾“明鬼神而敬事之”,其所“明”者也是鬼神之义。这个“义”是人文之义,是把鬼神纳入到人文教化的框架之中。鬼神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政治文明传统中,从一开始就有比较协调的处理方式(如荷尔德林所说“你如何开始,就将如何保持”),即“明鬼神以制义”的方式。孔子一方面“不语怪力乱神”,一方面又“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这一精神的典范。
对于孔子的“祭如在”和“丘之祷久矣”来说,对于颛顼和帝喾的“依鬼神以制义”来说,托马斯·阿奎那和安瑟尔谟的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简直如同儿戏。但是反过来,从西方神学立场出发,他们会觉得从孔子开始,乃至从颛顼、帝喾开始,甚至从伏羲开始,就在装模作样地神道设教或骗人。西方文化非常自诩的一点就是:它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祛魅的科学,它信仰的虔敬达到了“正因为不理解所以才相信”的极端程度。它的理性是彻底的理性,它的信仰是极端的信仰。所以,它的理性和信仰互相打了几千年,缺乏一个统一的和中庸的东西。它自诩自己的理性和信仰都比别人的强。是不是这样呢?否。不虔敬的理性谓工具理性,不理性的信仰谓意见。西方现代性的世界难道不就是一个工具理性加大众意见的世界?理性何存?虔敬何在?《中庸》云“不诚无物”,《易传》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生气就是和气。文明的生气就氤氲在貌似相反的东西之间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二、五行:圣人行教
“尧命羲和”一章取自《尚书·尧典》,其中已有《周礼》雏形。周礼依天象“辨方正位”,羲和已据“日永”、“夜中”、“星鸟”、“星火”来定四时、正四方。周礼“体国经野”,羲和已察四方四时,其民如何:“其民析”、“其民因”、“其民夷易”、“其民燠”;又察风土物候,鸟兽如何:“鸟兽字微”、“鸟兽希革”、“鸟兽毛毨”、“鸟兽氄毛”。从尧到周公,“设官分职”作为政治安排,无不与天地四时、风土人情、节气物候息息相关。王道不只是对人事的安排,而且是对天地之间的人事安排。所以,《春秋》开篇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对人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对何谓政治的不同理解。
从“慎徽五典”(史记作“慎和五典”)开始,古文《尚书》断开尧典舜典(今文皆属尧典)。在《五帝本纪》的记述中,舜走向政治领域的起点也在这里。五典就是《周礼》司徒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五教来化民,叫做五典。这是尧舜以来,华夏文明对政治的基本理解,即政治作为一种教化,作为一种风俗伦理的培育,也即孟子所谓善推扩之意,就是能齐自己的家,还能带动家家之父能义、家家之母能慈、家家之兄能友、家家之弟能恭、家家之子能孝。于是“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舜以孝行举于草野,而终有天下,是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之典范。所以,《五帝本纪》对舜的记述多次重复写到舜的家庭状况: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3]
舜德如何?不妨回顾一下黄帝的“生而神灵”、“成而聪明”和尧的“聪明文思安安”,把他们和舜做一个比较。“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一种解释是说“华谓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于尧”(古文《尚书》孔传),另一种解释是说舜“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史记正义》):他的瞳子是双重的,似乎暗示他有双重的明德,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无法知道在太史公的笔法里,这是不是暗示圣人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看一下有关他身世的叙述:这个家世起自黄帝之子昌意,高峰是五帝之一的颛顼,然后从穷蝉开始衰落,到舜父瞽叟嚚顽不化,降到谷底。在这七世变迁中,这个家族的命运有穷有通,有贵有贱,在天地大化流行中载浮载沉。一般人容易惑于这种浮沉变迁,为之歌哭,因之怨尤。而面对先祖的圣明贤达和父顽母嚚的现状,舜为什么可以安之若素?是不是一双重华的瞳子可以看到:在这浮沉变幻的人世中发生的穷通贵贱,原不过是一气流行?跟“重华”相对的正好是“瞽叟”。对“瞽叟”的解释,一说是瞎子,看不见;一说是眼睛没瞎,但有眼无珠,就像看不见东西似的,不能识别善恶美丑、贤良与不肖。无论哪种解释,都跟舜之为“重华”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是意味深长的,尤其当考虑到瞽叟之子、重华之弟的名字竟然叫做“象”时。“象”的产生必须是在明暗交会之地。象后来被舜封在西南地方,属坤的阴暗之域。象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的地方诸侯。出人意外的是,在后世史书中,象在西南民俗崇拜中的影响若隐若现。
对这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恶劣家庭环境,舜为什么可以安之若素,略无怨恨?他的亲生父亲、继母和弟弟每天都在设计害他,乃至要杀之而后快。他一方面是不怨恨,孝顺父母,关爱弟弟;另一方面,他又不是逆来顺受,如曾参那样愚孝。舜之孝行如流,小仗受之,大仗则走:“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有着重华之眼的圣人,他其实能看到宇宙大化之流:能看到天地一气流行,看到人世一气流行,才可以如此洒脱、如此通达,才可以既不怨恨又不完全逃避呢?这岂不就是“知道”吗?
一气流行的运化又可以具体分疏为五行或大气的五种流行态势:升曰木,降曰金,聚曰水,散曰火,升降聚散之中行曰土。在太史公对大舜生平的笔法中,似乎可以读到五行的消息。首先是“耕历山”:耕作是培育庄稼,与草木打交道。木德曰仁。舜耕历山,木气仁德流行无碍。接下来“渔雷泽”:与水打交道。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渔雷泽是跟水行之气打交道。接下来“陶河滨”:跟土打交道,土气流行无碍。可以看到,正因为舜能充分地畅通木气,所以他“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木气之化流行于民间,所以人民相亲互让,不再争夺土地③后世文王弭虞芮之争,不假狱讼,亦由木德仁教之行也。。“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水气流行无碍,故水畔之民能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窳”就是病,就是器具的空乏。土气流行无碍,所以民生器用皆不空乏。他可以看到所有气息的流行,解开气息的郁结,疏通流行的孔道,所以他对人世的命途穷通、贫富贵贱都能超然视之、安然处之,对各种争讼、各种纠结不通的东西都能纷然解之、疏而通之。
接下来“作什器于寿丘”:什器指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小器具,如菜刀、锄头、剪刀等。这些东西要经过火才能做出来。在希腊神话中,做这些器具的赫淮斯托斯也是火神。在奇门遁甲中,这类小物什对应十二天干中的“丁”。丁属火,是阴火。“作什器于寿丘”实际上就是与火打交道,以使火气流行无碍。舜作什器,以疏通畅达火气流行之人、火气流行之事。最后“就时于负夏”:“就时”即货值射利,就是甲地的某种东西物价低,他就跑到甲地买进,而乙地的这种东西物价高,他就乘着这个时机,及时跑到乙地卖出,从中盈利。“负夏”是个地方,就是到负夏这个地方来“投机倒把”,利用时机和差价“射利”。显然,这是与金打交道,是搞经济,做生意。这是商品流通,货值生利,金气流行无碍。
舜做过农民,做过渔民,又做过手工艺人(其中还特别分成两件事:作陶器和什器),最后还做过商人,刚好是五件事。根据上述的分析,可发现这五件事分别与木、水、土、火、金对应,正好是五行。可能有人觉得这种解读太穿凿,但如果考虑到司马家族的家学渊源,就不会大惊小怪。读《太史公自序》,可知道他是四岳之后,是天官家族。天官的看家本领便是阴阳、历算、易经、术数。读三家《诗》,能知晓史家学《诗》都是学《齐诗》,因为《齐诗》是阴阳家一路的,用易经象数和阴阳五行思想来解《诗经》。这个传统承自伏羲、黄帝,是华夏文明正脉,并不诡异。只是现代人囿于科学禁锢,思想封闭,少见多怪而已。
三、三才:王者建国
在上文所引关于舜的几章叙述里,已注意到太史公对大舜家世和孝行的记述多有重复,虽然每章变换角度、详略不等。以太史公继承春秋笔法之志,读者似宜尽心其中大义④在读书会上,此问题由曾维术、陈明珠提出,特此致谢。。有文献学解释倾向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它们抄自不同的文献来源。这种解释可能是对的,但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即使抄自不同文献来源,材料的排序也是值得思考的。《史记》是深思熟虑的作品,不是有待整理的资料汇编。
情况是,第一章叙述舜家族的完整世系结构,第二章概括地讲了他的父母兄弟、家庭的情况,这种写法像镜头从远拉到近,直接顺承了前面对世系的追溯。世系追溯是从时间上讲,而接下来从“舜,冀州之人也”开始转到空间的叙述。世系追溯的背景是天道,因为人生于父母,父母生于祖先,祭祀便有报本反始、敬天法祖之义,所以《孝经》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通于《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接下来讲五件事对应五个地方:“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这些地方其实都很重要。譬如寿丘是鲁东门之北,是黄帝出生的地方,离孔子出生的地方也不远。在这些涉及各种地方的空间叙述之后,又回头讲到他的家族世系,但这次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前面叙述家世,讲了家庭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尚能笃孝;接下来叙述地方,辗转东南西北做四方事业,与金木水火土五行人事打交道。这时候,他的孝行就不只是被动地承自天命的德性了,而是风行地上的修道之谓教了。
所以,在接下的来一章里,当第三次叙述舜的家庭时,就以“舜年二十以孝闻”起首,直接点出舜的立身之本:孝德。这次重述将是一个综合,同时从时间和空间角度、从天和地一起讲。而能合天地的是一个人,所以句子的起首是他的名字(一说为谥号)。“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叙述时间上的成长。接下来叙述他的家庭情况,“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随后又转到地方,叙述他在大地上行教化的效果:“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当再次叙述舜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做这些不同事业的时候,就不只是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历数他出生和工作过的地方,而是从政教的角度,讲一个潜在的王者如何走遍大地、教化人民。所以,这一段叙述的结语是一个缩小版的天下往归之象:“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只有把天道的时间流行和地道的风行教化结合在一起,才有人事的成聚、成邑、成都。这便是通天地人三才曰王、天下往归曰王的意思。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里暗含建国之意。建国肯定是时间空间俱全、天地人兼备的事业。《周礼》开篇每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某官”云云:“辨方正位”是根据天象来定的,也包含一个敬授民时的历法问题;“体国经野”是空间上的规划;“设官分职”是人事的安排。天地人通,乃有王者之建国。到这一步,似乎距离起首的“以孝闻”已经很远了。然而,如果温习《孝经·三才章》,读孔子说孝之大亦从天地人立论,就可知道,太史公笔下的舜之孝道并不是简单顺从父母之类的意思,而有着更加深远宏阔的政教维度。这个维度在一个以孝行为本的王者身上,原是与“身体发肤”之细与事亲之切一以贯之的。与常人不同的是,舜于孝道之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为了保存身体性命这个“父母之遗体”,他恰恰要躲避父母的谋害。一个在孝道之始就遭遇巨大困难的人,竟然可以最终达到孝道之大(通三才,“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以这个人成为孝行的永恒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好学君子。故孟子载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4]。
接下来“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仓廪和牛羊,一个是庄稼,一个是牲畜,是两种能让人活下去基本食物类型。然后是礼乐:絺衣是礼,琴是乐。既有粮食,又有礼乐。当然这个粢盛和牛羊也用于祭祀,也是礼乐的因素。在此之后,又叙述了一遍他的家庭状况,以及他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家庭环境中如何维持他的极为艰难的孝道。这次叙述的时候,讲了两个具体的事情:一个是登高,一个是下地。登高是“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这蕴含着什幺意思呢?你准备做天子了,或者是做普通的公卿大夫,你能上,你能下吗?一个能下的人才能上。舜能上能下。他上去了,瞽叟和象想烧死他,让他不能下来,他想办法下来了,没有死(“去,得不死”)。好,你能下,又能下到多深?“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能主动地深入洞穴,又能自如地走出洞穴。能通天地人三才,才能上下自如。
故《诗》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易》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此之谓也。
[1]吴承恩.西游记:第92 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66.
[2]张守节.《史记正义》五帝本纪篇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司马迁.史记正义·五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孟子.孟子·滕文公上[M]∥朱熹.四书单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