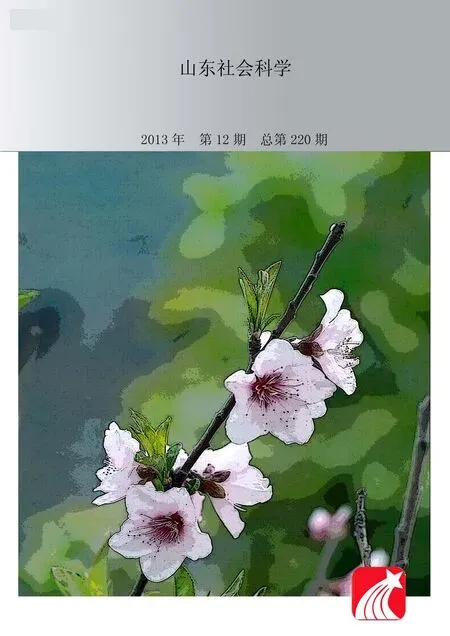儒家“持静修养”理论的深度阐释
王 晶 闫红卫
(山东政法学院 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山东 济南 250014)
静修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修养方法。以儒学为例,持静的修养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孔子的弟子颜回。郭沫若先生在《静坐》中说:“论者多以为(静坐)是从禅来,但我觉得当溯源于颜回。《庄子》上有颜回‘坐忘’之说,这怕是我国静坐的起源。”这是有道理的,而为静修提供详尽理论支撑的是儒学大师荀子。他在《荀子·解蔽篇》中提出“虚壹而静”的思想。荀子继承了《尚书·大禹谟》中的观点,认为不加修养的人心给人生带来的只有危害,因为它会始终处于内在繁塞、纷杂、不受控制的状态。为了使人役心而不为心所役,不为尘嚣扰其智,就应把主观的成见、欲念以及与目前活动无关的散乱思维排除掉,使自己虚明湛然,从而避免“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①王先谦:《解蔽篇》,载《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8页。。而排除各种干扰后的精神更容易集中、精一、安定、宁静,这就是荀子所谓的“大清明”。荀子对人心灵状态的认识以及理想的心灵境界的描述无疑为今后儒学持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之后儒家吸收了佛教的禅法,在唐朝出现了静坐这一养生方法。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在晚年就常常静坐,其《静坐诗》说:“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饮似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写其负暄静坐时达至的心灵宁静状态。此时他心无杂念,忘记了尘世的喧嚣,忘记了身边的一切,进入清静、空旷的世界,感受到安宁祥和的欣喜与幸福,这种静坐更多带有佛学禅宗的味道。后来,静修法成为宋明诸儒修身养性的普遍方法。郭沫若赞同静坐在宋明儒学修养论中的重要地位,说“静坐这项工夫在宋、明诸儒是很注重的”②郭沫若:《王阳明礼赞》,载《郭沫若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静坐法精义》中举例说:“宋之程子、朱子, 明之王阳明、陈白沙, 皆讲静坐法。”③丁福宝:《静坐法精义》,上海医学书局民国九年八月版,第5页。其实,不止以上提到的人物,周敦颐、高攀龙、梁章钜、谢良佐等也都有相关静坐修身的记录。静坐已经成为宋明诸儒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明人高攀龙为例,“五鼓拥衾,起坐,叩齿凝神,澹然自摄。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毕,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后,徐行百步,课儿童,灌花木。即入室,静意读书。午食后,散步舒啸,觉有昏气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至日昃而止。趺坐,尽线香一炷。落日衔山,出,望云物课。园丁执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灯,随意涉猎,兴尽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寝。”④高攀龙:《山居课程》,载《高子遗书》卷三,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这是宋明诸儒现实修身生活的写照。
儒学特别是宋明诸儒如此重视持静的修养方法的重要原因是希望通过静养能使“心体”显露,体会安定、宁静、澄澈、喜悦的境界,并对维持身体康健有重要作用。
一、静心呈体
通过静修的功夫进入本体世界是许多宋明儒者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陆九渊那里,他继承了二程特别是程颢的思想,理世界即是他的本体世界。陆九渊认为,此理昭昭然然于天地之间,无所隐遁。包括天地在内的万物只有克尽己私、因顺此理才能成就自己,人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一旦被私心所蒙蔽,就与理世界相隔膜,所以,让理在本心中呈现、成长,让理对人生起指引导向之功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其主要的方法当然是包括静修在内的功夫论入路。在此意义上,他明确指出:“此理在宇宙,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注]陆九渊:《与朱济道》,载《陆九渊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页。
当然,静修是陆九渊哲学宏大的修养论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内容,通过这一系列的修养功夫,人就体会到心世界与理世界的交融与汇通。从而领会到人心的纯然本善,体会到理本人心中之固有,如果能够持之以恒终身不断地修养,让心不受戕害,那么心体就会自动自为地生长而日趋向于美好、道德与智慧。他说:“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铄,但无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则当日以畅茂。圣贤之形容咏叹者,皆吾分内事。日充日明,谁得而御之。”[注]陆九渊:《与舒元宾》,载《陆九渊集》卷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通过持静等修养方法使心体呈现后,人就能进入理世界。体会到天理与人本一无间,只是人蒙于私欲与天自相隔膜了。修得此心明澈,必见此理。体会到天理是第一性的存在,是万物的根据而不以万物为根据,是最大的存在,万事万物相形之下均为小者。它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在空间上具有遍在性与普适性。陆九渊在此意义上说:“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见此理,此理无非,何缘未知今是?”[注]陆九渊:《与朱济道》,载《陆九渊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页。又说:“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所谓‘本诸身,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注]陆九渊:《与陶赞仲》,载《陆九渊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194页。学者正要穷此理,明此理。
陆九渊的这番道理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版,第270页。。只要通过持静等修养方法使心理交融,那么“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2页。,从而达纲举目张之效,其余所谓动旋中礼、事物应对、孝悌忠信之道自然呈现,这也就是所谓的易简之道。
“静坐明体”也是陈献章理学思想真正开始建基的转折点,即从静坐中体会出治心与治学端倪,他所谓“舍彼之繁”[注]陈献章:《复赵提学佥宪》,载《陈献章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145 页。,是指舍弃朱子读书穷理之途,而专求于静坐,通过非逻辑的、自我内省的方法,从静坐中体验心的本体。心体呈现之后,心灵圆成无缺,呈现出“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注]黄宗羲:《白沙学案上》,载《明儒学案》卷五,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0页。的精神状态,“如马之御衔勒也”[注]陈献章:《复赵提学佥宪》,载《陈献章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145 页。,就如套在马嘴上的衔勒驾驭马匹一般,从此获得了对自我意识的主宰力,自然也就无往而不利了。更为重要的是,自此以后,他豁然开悟,领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注]黄宗羲:《师说》,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的治学方法论,自此学风大变,“于是迅扫夙习, 或浩歌长林, 或孤啸绝岛, 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 忘形骸,捐耳目, 去心智, 久之然后有得焉, 于是自信自乐。其为道也,主静而见大,盖濂洛之学也。由斯致力, 迟迟至于二十馀年之久, 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 一真万事真, 本自圆成, 不假人力”[注]陈献章:《白沙先生墓表》,载《陈献章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883页。。所以,他十分强调静修对于证悟心体的重要性,他在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反复强调此观点:“然在学者须自量度何如,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静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尤为对症药也”[注]陈献章:《与罗一峰》,载《陈献章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157页。;“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注]陈献章:《与贺克恭黄门》,载《陈献章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133页。;“人心本来体段皆一般,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注]黄宗羲:《白沙学案上》,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4页。。
高攀龙也认为,“默然静去”之法有助于体会“无动无静之体”,“心中无丝发事, 此为立本”[注]高攀龙:《语一百八十二则》,载《高子遗书》卷一,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此是说心性显露的关键方法是通过静坐使自己不为世间万事、心中万念所系、所缚,使心绪平常自然,心体的本然清明状态自然会呈现。“无杂念虑, 即真精神。去其本无, 即吾固有。”[注]高攀龙:《语一百八十二则》,载《高子遗书》卷一,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只有这样,才会体会到心体在没有展开、发用之前是清静不容一物、无喜无悲、无动无静、廓然大公的状态。也只有在动静之中都保持心体的湛然本色,方能顺应天理、物来顺应、无事不成。如高攀龙在《静坐说》中所言:“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净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画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静以上如此,喜怒哀乐未发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须在人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真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着一毫见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静而动,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静中得力,方是动中真得力,动中得力,方是静中真得力。所谓敬者此也,所谓仁者此也,所谓诚者此也,是复性之道也。”[注]高攀龙:《静坐说》,载《高子遗书》卷三,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二程也持如此观点,《程氏外书》卷一二载,程颢“终日坐如泥塑人”, 学生问其如何修身力行, 他答道:“且去静坐”,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究其根本是他们均认为通过静修可直入本体。
二、澄莹和乐
需要注意的是入静状态既不同于普通人的日常精神状态,亦不同于睡眠状态,更不是绝对的万念俱寂,因为它还保持着某种纯一的意念活动。即如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言:“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注]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03页。因为心如其弟子陈淳所言:“是个活物,不是贴静死定在那里,常爱动。”[注]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勉强让其一念不生,反而使“坐忘”变为“坐驰”。静修中实际上是以一念代万念的意念活动。
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静修方式达到的入静状态都可以使人感受到轻松舒适,气清心定。因为在入静的状态,人不会被外事所扰。明代吴康斋先生讲述自己在静修之前往往心志散乱、神不归体,感知与判断能力低下。“夜病卧,思家务,不免有所计虑,心绪便乱,气即不清。”[注]黄宗羲:《吴康斋先生语》,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弊病。大儒王阳明也有类似的感慨,“所谓静坐事, 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 未知为己。”[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人心本应是在腔子里的,“配义与道”[注]李学勤:《公孙丑章句上》,载《孟子注疏》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物来顺应、当怒则怒、当喜则喜。但大多数人一旦遇到与切己之欲望纠缠在一起的事项,就会被外事牵制、扰攘,本心就丢弃了。所以从孟子开始就力主“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李学勤:《告子章句上》,载《孟子注疏》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而“求放心”的一个重要修养方式就是持静。人在静修之后内心则会全心贯注于应然之理,常保持一种警觉、谨慎的态度,心主于一、诸邪不入,纷纭的思绪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么内心就会体会到一种特殊的宁静。“心于是乎定,气于是乎清。”[注]黄宗羲:《吴康斋先生语》,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就会达至“月下咏诗,独步绿阴,时倚修竹,好风徐来,人境寂然,心甚平澹,无康节所谓攻心之事”[注]黄宗羲:《吴康斋先生语》,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的境界。
在静修的过程中,人不仅不为外事所胜,而且内念俱熄。因为入静之后,所有的差别都会消泯。程颢说内外消失了,他在《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中说:“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注]程颢、程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载《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1页。人的内心没有偏颇、没有偏好,所以天理常明。据此,程颐说:“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注]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9页。此时进入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没有分别的本体世界。陆九渊的学生杨简的一段记录,讲述了自己静坐悟道的奇妙体验。他说:“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学之循理斋,时首秋,入夜,斋仆以灯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尝有训曰:时复反观。某方反观,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略无缝罅。”[注]杨简:《炳讲师求训》,载《慈湖先生遗书》卷十九,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杨氏便是在这次静坐中体验到万物混然一体,感受到一切差别、界线之消失。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人与天理、大道合而为一、湛然而粹。此时人的情绪反应就会变得平和安定。
总之,当一个人纯然与天理合一,与道冥合、与无一体,外不累于物,内不惑于情,就会内心澄莹。据陆九渊的弟子詹阜民记载:“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持,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1页。这种感受,高忠宪在其《困学记》中说得最为贴切。“静坐中不贴处, 只将程、朱所示法门参求。于凡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 一一行之……偶见明道先生曰:‘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 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猛省曰, 原来如此, 实无一事也。一念缠绵, 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 顿尔落地, 又如电光一闪, 透体通明, 遂与大化融合无际, 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 腔子是其区宇, 方寸亦其本位, 神而明之, 总无方所可言也。”[注]高攀龙:《困学记》,载《高子遗书》卷三,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不但如此,当一个人纯然与天理合一,与道冥合、与无一体,外不累于物,内不惑于情,还会得到精神层面的巨大的愉悦与满足。即便是身处逆境,也会泰然自若。此时,人就会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所遇之境,均是乐土。如吴康斋生计窘迫,常常旧债未去,又添新债,但长期的涵养之功使他“晴窗亲笔砚,心下清凉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节云:‘虽贫无害日高眠’。”[注]黄宗羲:《吴康斋先生语》,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明儒学案·吴康斋先生语》又云:“夜大雨,屋漏无干处,吾意泰然。”这便是与物偕春、顺心循理的孔颜之乐,人与天地自然、天理道体浑融一体,生命气象便体现出直接、活泼、洒落、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特点。吴康斋先生自述:“南轩读《孟子》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阴清昼,熏风徐来,而山林阒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于斯可验。”[注]黄宗羲:《吴康斋先生语》,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生命于此呈现出富有生机的“鸢飞鱼跃”的景象,视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所以怡然而乐,这便是孔门之“至乐”。
三、静得其寿
持静的修养之法对于维持身体康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古代儒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清儒梁章钜更是一语中的,“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 但学道者, 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 虽学道亦为养生耳。”[注]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载《二思堂丛书》,光绪元年校刊本。
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之中,认为精、气、神是个体生命的根本内容,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为人身之“三宝”。《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精、气、神对于人生命的始基作用。《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难经·八难》曰:“气者,人之根本也”,《素问·移精变气论》也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等等。中国传统养生理论认为,精充、气足、神旺则人的生命活动旺盛、身健少病,否则,则人的生命力衰退、体弱多病。
而静修对于精、气、神的养护、调理、升华都有巨大的作用。持静的修养方式直接的功效便是使神思虚静。因为神具有易动而难静的特点,如吴康斋所言,“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摇动”[注]黄宗羲:《吴康斋先生语》,载《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常于瞬息之间驰骋于万事万物之中,心情宁静就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据于此,老子要求“致虚极,守静笃”[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十六章,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4页。,《黄帝内经》也说:“恬淡虚无,病安从来?”总的思路是通过一切方法使神气清静而摄生防病,而所有持静的修养方式都会对此有所帮助。精、气、神分言为三,合而为一,相互派生。神清则气旺,气旺则精足,人的整个生命状态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我国传统文化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很早以前学者们已经将静修与养生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以苏东坡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注重持静养生对于人身体与精神的巨大支撑作用。苏东坡一生饱受磨难与打击,在为官的40余年间,他经历过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一生志向未遂,在“乌台诗案”中还差点以谋反罪丢掉脑袋,甚至在花甲之年被流放于当时的瘴疠之地。“恨此生, 长向别离中, 添华发。”(《满江红》)宋朝此时整个社会黑暗混乱、民不聊生,而苏轼又身处相互倾轧、相互排斥的官场,“ 浮名浮利, 虚苦劳神”(〈行香子〉)。他在《初别子由》中不满地说:“南都信繁会,人事水火争”,在《满庭芳》中感慨地说:“蜗角虚名, 蝇头微利, 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 谁弱又谁强。”在这样严酷险恶的环境之中,面对如此多舛的命运,如若不是苏东坡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用诸如“静坐”一类的养生术来调养身心,使自己有所超越,宁静逍遥、随缘放旷,很难活到近70岁的古稀之年。苏轼撰有《养生说》、《问养生》、《续养生论》、《养生偈》、《论修养寄子由》、《书养生后论》等养生方面的文章,十分注重维持心神的安定对修养身心的基础性作用。他自己也经常用儒家包括道家与佛学的静修方式收敛心神,保持心灵的寂然虚空,使心灵如珠在渊,沉静虚明。如苏轼般通过持静而得以修真养性的人还有许多,据有关资料介绍,活了101岁的张学良从年轻时即常习静坐,故而长寿;南宋时期的爱国诗人陆游命终时85岁,他年轻时也不断地习静修养,直至晚年身体都十分健壮并头脑灵活。可见,保持心灵的静寂确实有强健身体之功。
不仅如此,持静的修养方式还能有效地缓解甚至消除亚健康状态,提高免疫力。这方面朱子本人深有体会, 朱熹晚年由于治学过度,时常神思衰败、气力不支、百病缠身,静坐后才觉身体健旺。他在《朱文公别集·答林井伯 》中说:“某今年顿觉衰惫,异于常时。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药更不见效,只得一两日静坐不读书,则便觉差胜。” 在他的《调息箴》里,他介绍了自己调息以致静的方式,即“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翕,如百虫蛰”。这与道家的调息修炼法很有些相似。梁章钜也深有感触地说:“余尝十日九疾, 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 只坐气薄耳。自今于喜怒哀乐上理会,即病即药,不须外求也。”[注]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载《二思堂丛书》,光绪元年校刊本。他敏锐地觉察到精神状态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身体的运行状况,所以必须通过安定情绪,“于喜怒哀乐上理会”来静神、养气、健体。曾文正公也非常善于养生,他说:“病在心肝两家血亏, 非键户静坐, 谢绝万缘,不能调摄。”[注]丁福宝:《静坐法精义》,上海医学书局民国九年八月版,第3页。只有通过“静坐”、“灭欲”诸法来维持心灵的静寂才能使整个身体气血和畅。明代文学家谢肇淛在笔记集《五杂俎》卷二中说,当时京师瘟疫横行,有善养生者采用简捷方便的静坐法提高免疫力来避免疾病:“京师住宅既偪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可见,持静修养的功效非凡。
总之,持静修养尤其静坐是儒家功夫论中的易简之学,这种修养方法被社会广泛接受,至少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以后就湮灭无闻了。静修在儒学中脱去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外衣,围绕儒者们对本体澄明的追问、对万物一体的和乐之境的追求与养生强身的目的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