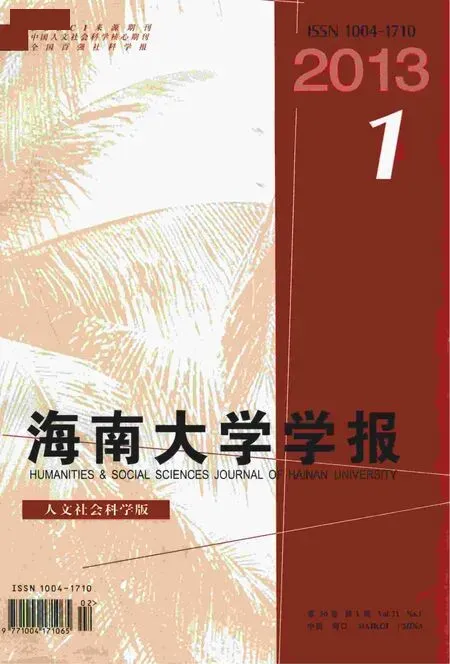历史的流向与人类的选择——奥登创作中的线性历史意识
蔡海燕
(浙江财经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历史”往往被解读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但由于这些事件与人相关,因而它们的存在就遭到了人的“理解”的侵袭[1]。当代哲学家贾尼·瓦蒂莫说:“存在在时间中延展,‘在变动,在生生灭灭’。换句话说,存在成为时间,或曰历史。”[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是人类的存在维度,人类的历史实践孕育了人类的理性和智慧,而人类的理性和智慧也塑造了人类的历史形态。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纷繁多样,渗透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体验,奥登(W.H.Auden)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对历史问题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思考。仅以1955年为例,他在这一年创作的主要诗篇——《历史的创造者》、《向克利俄致敬》、《老人的路》、《埃皮戈诺伊》、《科学的历史》等,写下的重要散文——《染匠之手》①此《染匠之手》是1955年奥登为作客BBC而准备的讲说稿,与1962年出版的散文集《染匠之手》同题。、《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等,无不关涉历史。在这些作品里,《向克利俄致敬》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对历史的礼赞。“克利俄”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女神之一,司掌时间和历史,奥登在诗篇接近尾声部分呼唤她“原谅我们的嘈杂躁动,/教会我们回忆过往”[3]613。时间以嘈杂躁动的“现在”为基点,过往已经成为了历史,却仍有回忆和学习的价值,因为它与人们观察现在和投射未来的方式息息相关。不难看出,在奥登的思想与创作中,作为承载历史的时间,是一个在“现在”这个基点上形成的“过去”和“未来”对称结构的轴线,那么历史本身也就具有了这样的线性特质。本文旨在通过对奥登最具代表性的相关诗篇的细读,结合他就有关问题所做的论述,阐释并厘清他的线性历史意识,以期挖掘诗歌文本背后的丰富内涵。
一、线性历史的矢量特质
奥登虽然深受前辈诗人叶芝的影响,但他的历史意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叶芝式的质地。叶芝在其诗作《基督重临》和著作《幻想》里探讨了人类历史的奥秘,认为历史每过2 000年就会出现一次循环。奥登则倾向于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单向延伸的线性过程,存在其中的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奥登的文学遗产委托管理人门德尔森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奥登对历史的思考是理性的、经验的。他的线性历史意识基于坚信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这样的历史意识也有充满神秘色彩的基本面目(或者说20世纪30年代偶尔出现了此类现象),那就是他认为历史可以改良,未来的社会必然比现在更为公正。”[4]229门德尔森的措辞十分谨慎,对奥登线性历史意识的“神秘色彩”做了模棱两可的时间限定。事实上,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奥登与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期”,还是之后奥登皈依基督教,这种“神秘色彩”在奥登的线性历史意识中是一以贯之的。
大家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诗坛以有关共产主义具有拯救力的诗歌为代表,而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奥登一代”诗人们。他们刚刚毕业于牛津大学,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很好的交流与合作,在文学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考量和对社会变革的期望。贝雷泰·斯特朗在考察“奥登一代”时,曾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征象:“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信仰和词语经常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的要求。‘历史’、‘行动’、‘战争’这些词语变化的用法,说明了意义在这个时代的不稳定性和极端不可测性。”[5]140作为“奥登一代”的领军人物,奥登早在1929年创作的《请求》中就迫切地希望有“神效之方”,“治疗”各种社会疾病,然后“欣然观看”“建筑的新风格,心灵的改变”[6]。随后,奥登开始使用爱德华·厄普华的“目的性历史”(purposive history)这个词及其概念。爱德华·厄普华是位旗帜鲜明的左派小说家②爱德华·厄普华比奥登年长4岁,1932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退党。,在20世纪30年代与奥登过从甚密,他的言传身教和小说作品直接影响了奥登的政治立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1932年春,他向奥登展示了新创作的短篇小说《星期天》。该小说以主人公最终决定参加共产党集会为尾声,其中穿插了很多有关历史的表述:“历史在这里,在公园,在乡镇……但历史不会一直留在这里……正如历史已经抛弃了城堡里残酷的父爱,它也会抛弃‘星期天’和办公部门的压迫。它将去往别处……一个人与其自杀或者疯掉,不若起来抗争……将与那些人为伍……”[4]308-309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人、物和环境等社会有机体所有要素作用的总和,或者说生产力;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化顺序符合了线性系统排序上的链式特征,而以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则被设想为这条线上的最终形态。包括厄普华在内的左派和左倾作家们,在历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鱼烂、经济萧条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他们看到了历史发展的线性流向,认为若不追随历史的脚步“起来抗争”的话,便只能被历史抛弃,“自杀或者疯掉”。安德鲁·桑德斯在其《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曾提及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的境况: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仿佛成了社会解放、性解放和文学解放的主要手段”,“改造社会和建立民主盛世的传播福音般的使命填补了信仰真空”[7]。奥登本身就对当时的时代症候有敏锐的把握,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请求》,他还在组诗《1929》里写到过——“时间流逝,现在情形已不同”[3]46和“消灭错误现在正当其时”[3]49。他的改变现有社会的诉求,经厄普华、布莱希特、托马斯·曼等人的影响③奥登不但与左派作家爱德华·厄普华私交甚好,还与左倾文学领域的前辈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有过直接接触,甚至为帮助托马斯·曼的女儿离开德国而与之结婚。,逐渐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了呼应,因而奥登也将社会变革视为线性历史发展的必经之途,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前的所有标准都已经瓦解的时代,与此同时,集中传播思想的技术已经完善。某种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少数人势必会自上而下地强加这种革命……”[8]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线性历史观直接影响了奥登的诗歌题材。他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一些带有历史回溯色彩的诗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写于1933年的《寓意之景》。在这首诗中,奥登将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先辈们征服自然、建设城市到启蒙思想家们呼吁民主、创建道德理想国,再到浪漫主义者们渴望逃离自身的环境、奔向遥远的彼岸,线性回溯的方式恰恰反映了奥登的线性历史意识,而他在诗篇最后提出的“我们重建城市,而非梦想海岛”[3]120,则指向了那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未来。
然而,奥登与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期”十分短暂。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尽管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但不再相信“它能够战胜法西斯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9]。他开始把改善现实沉疴的责任放在普通个人的肩上,希望通过每一个个体的心智内明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改良,而基督教信仰就成了他的最好选择。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他以基督教神学阐释人类历史,相继创作了《战争时期》组诗(1938年)、《迷宫》(1940年)、《探索》组诗(1940年)、《城市纪念馆》(1949年)和《祈祷轮唱》组诗(1949—1954年)等著名诗篇。巧合的是,基督教历史观恰恰也是一种线性历史观,指向了独特而确定的终极。早在古罗马时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曾对承载历史的时间做出精彩的分析:“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10]在这条线性时间链上,奥古斯丁把人类历史的起点定为该隐创造“地上之城”之时,而未来的终结便是“上帝之城”取代“地上之城”之时。奥古斯丁的历史阐释论证了上帝与基督教的合理性,他的写作范式和思想观念被后世的神学家们继承并发展下去,成为基督教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曾谈到了这种基督教历史观对普通人的影响:“不仅因为它的线性时间概念,还因为它的神圣天意观为人类的整个历史时间赋予了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通过救赎计划而实现。”[11]由此可见,基督教历史观虽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却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样,都为线性历设定了一个终点——在前者是“上帝之城”,在后者是“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把这种共性称为线性历史的矢量特质,因为在数学上,“矢量”通常被标示为一个带箭头的线段,箭头所指的方向即矢量的方向,那么线性历史的终极指向便如矢量上的那个箭头了。
二、线性历史与人之“选择”
奥登对线性历史的矢量认识,虽然暗含了未来拯救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的未来都要比它们的过去更完善、更公正。也就是说,进步并不是绝对的。《1929》里的一行诗句值得我们注意——“做出选择看来是一个必要的错误”[3]45。再来看看他在1956年写下的话:“生活,如我个人所经历,从根本上而言由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选择构成的集合体,有些选择是目光短浅的,有些选择则高瞻远瞩”;“时间并非在我身外循环运作,而是由独特的瞬间组成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我自身的选择决定了这些瞬间。”[12]“选择”这个词在奥登诗作里出现的频率极高:个人的“选择”构建了个人的生活,或者说历史;群体的“选择”也莫过如此,只不过范围扩大了、情况复杂了。
奥登认为历史是由人类的“选择”构成的不可逆转的集合体。既然有“选择”,那么必然有选项。这些选项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目光短浅的”,也可能是“高瞻远瞩”,但无论结果如何,“选择”必得进行:“但时间,行为的存在之维,/召唤一种错综复杂的语法 /要求不同的语气和时态,/尤其是那些祈使语气。/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道路 /但选择必得进行,无论 /它们通向何方……”(《晨曲》)[3]882奥登在这里提到了“自由”,也就是说,仅仅是拥有选择这个选项或者那个选项的自由,而不是接受或者放弃选择权的自由。
需要区分的是,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使用“选择”时的不同所指。在此之前,奥登常常把“选择”看成是人的“行动”,喜欢为“选择”加上诸如“合乎理性”、“合乎道德”之类的形容词,赋予它功利性的目的,这与他当时的政治取向性有密切关联。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奥登更多地把“选择”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的派生,是人不同于其他生命的独特属性,因而“选择”具有了必然性。《战争时期》可谓奥登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人类“选择”特性的奠基之作,组诗的开篇尤为重要。赵文书指出,这是“对《圣经》中的创世纪作了达尔文式的解释,认为世间万物在创世之初便从上帝手中各取所需,从此安分守己”[13],而惟独人类是个例外。相较于其他生命“满足于自己早熟的知识”[14]259,人类能够在时间的推移中“塑造出任何面目”,具有易变性;相较于其他生命“知道各自的职分”,人类会根据环境的细微变化而“动摇更改”,具有能动性;相较于其他生命“永远合理正当”,人类却因为“追寻真理”而“错谬连连”,具有未完成性;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有思想,能“选择”。人类的易变性、能动性、未完成性,都可以归结为“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因为不能“选择”,其他生命“第一次的努力”就得到定型,而正因为能“选择”,人类具有了改变自己的可能性。
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奥登从上帝造人的角度对人的本质属性以及“选择”特性做出了更为深入地阐释:“人的创造被描述为双重过程。首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也就是说,人是自然造物,如其他所有的造物那样遵循自然秩序的法则。其次,‘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意味着,人是承载神的形象的独一无二的造物,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因而能够创造历史。”[15]197这个双重过程构建了人的双重属性,虽然人与动植物共同生活于物质世界,但人的生活世界却完全不同于动植物的自然世界。人类凭借上帝赋予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获得了理解并操控自然秩序的力量。正是这第二种本质属性派生出了人的“选择”特性,而人类始祖所面临的第一次选择,就是选择摘食“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实。奥登曾撰文详细探讨了发生在伊甸园里的摘食禁果事件。他指出,创世故事里并没有说“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实具有独特的外观。也就是说,禁果的自然属性或许并不具备引人注目的诱惑力,人类始祖违抗上帝命令的动机完全无关他们生理上的软弱,而是意识上对禁果的附加功能的向往。因此,他总结说:“如亚当和夏娃那样想吃‘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其目的并不在于平等甚至超越,而是自主。这是一种渴望成为自身的价值源泉的努力,成为像神那样的普通人。”[15]199
奥登还注意到,当人类始祖摘食了禁果之后,他们最先遭遇的并不是惩罚的痛苦,而是“不快乐”。亚当和夏娃见彼此赤身裸体,便迅速拿无花果树叶遮身,这个细节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们听到上帝的脚步声,便躲藏了起来,并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个细节隐喻了人对背叛行为的内疚和焦虑。面对上帝的质询,亚当称夏娃给了他禁果,夏娃称蛇引诱了她,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们似乎忘记了“吃”这个动作是由他们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决定的,推搪或是借口并不能粉饰自身犯下的罪,这个细节预示了人类今后之种种争端与不幸。更为重要的是,是人类自己选择了摘食禁果,铸就了自身的“不快乐”。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始祖摘食禁果的行为,既是人类行使自由意志和进行自我选择的尝试,也暗含了人类要为自身的“不快乐”承担起责任的意味。
人类始祖的“不快乐”,一直延续到现今的“不快乐”,历史已经成为承载人类的“不快乐”的铁证。奥登写道:“历史的悲痛与我们轻快的歌声恰成对照一幕:/美好乐土从未存在;我们的星球温暖如斯 /催生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种族,却未曾证明其价值。”[14]271在奥登看来,人们“满腹疑虑”,总是“被错误束缚”[14]285。这些错误勾勒出“历史的悲痛”,也宣告了人们一系列的错误选择。在历史的线性横轴上,人们享有选择带来的自由,也必得承受错误选择招致的所有悲痛。
三、线性历史的希望机制
当人类始祖走向伊甸园的中心位置的时候,若是选择摘食“生命树”上的果实,情形会有多大的不同?是伊甸园里永生永世的快乐生活,还是不可避免地仍然要面临禁果的诱惑?无论如何,在智慧的大门被开启以后,人类似乎很难再心甘情愿地回到无知无觉的自由快乐:“太阳初升时醒来听到 /一只公鸡清晰地打鸣出它自己 /然而它的子孙们或遭阉割或被吃掉,/我很庆幸我是不快乐的……”(《向克利俄致敬》)[3]611亚当夏娃的子孙们不必像动植物那样受本能驱使生活,他们能够依靠自身的判断做出选择,能够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能够创造自身的历史。而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那最初的“不快乐”。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的堕落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点,奥登很喜欢从人与动植物的分野引出问题,比如他早期创作的这首诗歌:“树下站着堕落的夫妇:/远方被驱逐的雄鹿 /在荒凉的悬崖驻足 /凝望着海面目光沉静,/四周的灌木丛里 /驯养的动物们 /四顾二元性,/而鸟儿在人间尘世 /飞进又飞出。”(《谜语》)[3]257诗中出现的“二元性”,奥登研究专家富勒将之解释为“自由”与“必然”的二元格式,认为可以溯源到人类始祖的堕落[16]。树下那对“堕落的夫妇”四顾的“二元性”,恰恰是他们区别于动植物的双重属性,也是选择的双重意义。如果说奥登在上述诗歌里仍然是从宗教的角度谈人与动植物的分野,不足以代表他本人的态度的话,那么他在另外一些不带宗教因素的诗歌里的表达就更为明确了:“野兽,鸟类,鱼,花朵 /做季节要求它们做的,/但是人却按照他可以做的 /和必须做的安排日子。”(《短诗》)[3]885而1972年写成的短诗《进步?》,标题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进步”两个字后面加了“?”。在这首诗歌里,人们看到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的一系列演变:“无柄”(固定位置)——“能活动”——“爱说话”(不但能活动,还具有语言能力),“没有视力”——“有视力”——“心有所虑”(不但能看到外部世界,还具有思考能力),自然空间——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和历史时空。人类凭借第二种属性创造历史,但人类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在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谬。“选择”让人类有了进步的希望,却也埋下了灾祸的种子。正是在历史而非自然的层面上,“进步”的神话被打破了。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有追寻真理的可贵品质:“他爱上了真理,在结识她以前,/然后一路驰骋奔向那幻想国。”[14]264人类漫长文明史的主旋律是对“真理”和“幻想国”的想象。奥登的《战争时期》第二首很有意思:“他们哭泣又争吵:自由是如此狂乱。/当他向上攀登,前方的成熟 /如孩子面前的地平线已退后不见,/更严酷的惩罚,更大的危险,/而返回的路途由天使们把守/以抵御诗人还有那立法议员。”[14]260这里的“他们”指的是亚当和夏娃。失落的伊甸园被理解为“诗人还有那立法议员”无法挨近的世外桃源。奥登将诗人和立法议员视为人类“追寻真理”的典型,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对乌托邦的幻想,与立法议员对理想国的设想如出一辙,两者都具有在现实的基础上再构建的特性;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时代特征相吻合,毕竟那时出现了很多社会诗人、革命诗人、与政治气候唇齿相依的诗人。无论他们的努力是如何以失败告终的,他们内在的追寻品质却是指引人类不断“向上攀登”的力量源泉。他们明白,“返回的路途”已由天使们把守,因而惟一可行的道路是继续向前。
奥登后来多次区分“阿卡迪亚”和“乌托邦”、“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这两对概念。他说:“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对真实存在的堕落世界而言,显现出时间上的差异。伊甸园是一个存在于过去的世界,现存世界的各类矛盾尚未出现;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存在于未来的世界,各类矛盾将会得到解决”;“阿卡迪亚人最喜欢做的白日梦是伊甸园,而乌托邦者最常做的白日梦是新耶路撒冷”[17]。也就是说,伊甸园和阿卡迪亚是与过去紧密相关的概念,而承载新耶路撒冷和乌托邦的则是未来。在晚年的组诗《祈祷轮唱》的第五首里,奥登将“我”与“他”、阿卡迪亚人与乌托邦者、伊甸园与新耶路撒冷之间的差异戏剧化地表现了出来,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诗节以类似于“我是阿卡迪亚人,他是乌托邦者”[3]637的对比性句式展开。面对种种天南地北的分歧,“我”情不自禁地发问:“我们有没有共同分享的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却也代表了奥登一贯的思路,即阿卡迪亚人和乌托邦者都“忠于各自的小谎”。这里的“小谎”,有无法实现的美梦的含义。向后的道路既已封锁,因而阿卡迪亚人的伊甸园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谎”。而在《战争时期》第二首里,奥登将向前的道路描述为“当他向上攀登”的时候,“前方的成熟”却不停地向更前方隐退。也就是说,前方的“新耶路撒冷”始终是可望不可即,同样是“小谎”,只不过这个“小谎”存在于未来,是尚未发生的,是具有改变的可能性的。
在线性历史的时间横轴上,奥登认为人们惟一能够确信的是,只有不断地向前行走,不断地做出判断和选择,才有可能无限地接近理想蓝图。他对人类历史的这种理解,刚好可以用康德的这段话加以总结:我们作为“有限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指望在将来,只要在今世活着或者在来世活着,能不断地进步”,而“永远不能指望在今生,实际上不能指望在来生任何可想象的时候,和上帝的意志完全一致”,但是可以“指望在惟有上帝才能测量的无穷尽的生存之时间中有这种的一致”[18]。
奥登在《自然、历史和诗歌》中清楚地指出:“自然时间是自然事件存在的维度,它是重复的、不自觉的、可逆的环形时间;而历史时间是历史事件存在的维度,它是独特的、自主的、不可逆的线性时间。”[15]226对于奥登来说,历史蕴藏着毁灭与建设的双重性力量,过去是稳定的、保守的,未来是变化的、创造的。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者”,还是成为“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者”[5]207,奥登都全神贯注地将光亮投向了线性历史的未来,在对社会蓝图做出憧憬的同时,坚持对思想和行动进行以结果为导向的目的论解释。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意识,奥登才一再在诗歌中表达类似的观念:“因愚蠢言行而生的悲叹 /扭曲了我们有限的时日,/但我必须祝福,必须赞美。”(《谣曲十二首》第五首)[3]138
[1]韩震.历史观念大学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51.
[2]布罗伊尔.法意哲学家圆桌[M].叶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93.
[3]AUDEN W H.Collected Poem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1.
[4]EDWARD Mendelson.Early Auden[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1.
[5]贝雷泰·斯特朗.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M].陈祖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AUDEN W H.Selected Poems[M].London& Bostan:Faber and Faber,1979:7.
[7]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高万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27.
[8]AUDEN W H.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Vol.I,Prose,1926—1938[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38.
[9]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257.
[10]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7.
[11]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0-61.
[12]EDWARD Mendelson.Later Auden[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9:392.
[13]赵文书.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J].当代外国文学,1999(4):165-170.
[14]AUDEN W H.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M].New York:Random House,1939.
[15]AUDEN W H.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Vol.III,Prose,1949—1955[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6]JOHN Fuller.W.H.Auden:A Commentar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275.
[17]AUDEN W H.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M].London:Faber and Faber,1962:409 -410.
[18]康德.康德哲学原著选读[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49-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