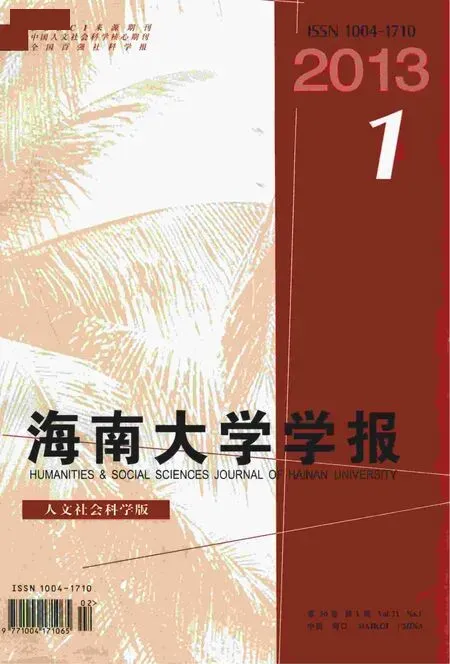《老子》中“器”的道德意蕴
莫 楠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老子》中共有十章中出现“器”字①本文《老子》引文以王弼本为准,同时参照帛书本与郭店楚简本;王弼本中第11、28、29、31、38、57、67、80章中出现“器”字,第41章王弼本作“大器晚成”,帛书本作“大器免成”,第51章王弼本作“物形之,势成之”,帛书本中作“物形之而器成之”,本文第41、51章采用帛书本文字,故计共十章中出现“器”字。,“器”的使用者和所属者是人,同时人也是“器”之一,憨山便说:“器者。人物之通称也。”[1]133老子通过“器”要论说的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器”不是在各章中孤立存在的,而是构成一个整体,一个发展过程。“器”的道德意蕴的核心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如何以道德克服异化、回归本性,重建人生价值和社会秩序。当今社会中,人们面临离德失德的困境与人际疏离等危机,“器”中的道德思想,能为人们克服困境,实现精神上的“回家”提供一条具有中国智慧的道路。
一、《老子》中的“器”
“器”字在《老子》中出现多次,分别为: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第11章)[2]26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第28章)[2]74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29章)[2]76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第31章)②据帛书本改定。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87-390页。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36章)[2]89
“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41章)③据帛书本改定。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页。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第51章)④据帛书本改定。王弼本和河上公本中,此句都作“物形之而势成之。”帛书中写作“器成之”。高明认为:“按物先有形而后成器,第28章中又有‘朴散则为器’,《周易·系辞》中有‘形乃谓之器’,韩康伯注也说:‘成形曰器。’这些例子中都是‘形’‘器’同语连用,因而应当从帛书本作‘器成之’。夫物生而后则畜,畜而后形,形成而为器。”本文采用这一观点。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9-70页。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2]149-150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第67章)[2]170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第80章)[2]190
上述这些器,分具不同含义:第11章中,“埏埴以为器”即和陶土做成器皿,这里的“器”是具体有形器皿之义。第28章的“器”并非单指具体的某一物,王弼注曰:“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2]74,“器”包含各类存在物,是物的统称即万物。第29章的“器”,河上公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3]118,可解释为物。这里将人视为“神器”,启示人们对于“器”的理解应将人考虑在内。第31、36两章中的“器”则指具体之物。第31章的“器”指兵戈或道德;第36章中的“利器”,历代有不同解释,如河上公认为指权道,韩非解释为赏罚,依据全章所说的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及第50章中同样用柔弱胜刚强之理说战争中的生死问题,应采用薛蕙的观点,指权柄军力⑤各家观点转引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9页。。第41章中的“器”是有“大”这一特性的物。第51章的“器”则指世间存在的各物。第57、80 这两章中,“器”指的也是具体的物。第57章中“利器”历来有两种解释,一说指锐利武器,一说喻权谋,参考明人王纯甫的说法:“利器,即国之利器,智慧权谋之类也”,本文采用“智巧权谋”这一解释。第80章“什佰之器”,结合下文“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舟车、甲兵都是可代替十倍百倍人工的事物,因而“什佰之器”指“十倍百倍人工之器”⑥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6页。,也就是第57章中反对的“智巧权谋”所发明出来的机械工具。第67章的“器”意为万物,陈鼓应就直接将“器长”译为“万物的首长”⑦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11页。。
从上面对“器”的分析看,字面上,“器”可归纳为两方面含义:万物或具体的某物,可解释为“物”⑧如陈鼓应和池田知久都认为“器”和“物”基本可等同。参见陈鼓应:《论道与物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哲学动态》,2005年第7 期:第55-64页;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0页。;不过,“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的文字也说明,在老子思想中,“器”与宽泛的“物”仍有区别,有其独特内涵。在笔者看来,“器”强调的是两点:一方面,强调个体特性。“朴散则为器”一句,从王弼之注可看出,“器”凸显的是分具不同特性的个体,是“道”包含的种种可能实现后的形态,就像器皿有不同造型不同用处一样。另一方面,“器”强调价值和功能。《老子》第11章就突出“器之用”,《说文解字》解释“器”:“器,皿也”[4],皿指饮食用具,“器”的本义中也有强调价值、功用之义;存在物要有自己的价值、作用才能称作“器”。当然,这里的价值、功用不是仅指对人的,而是在万物平等的前提下,所有存在物自身所有、合乎本性的价值,是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因而,真正的“器”应是保持自身本性和价值的存在物。人同样也是“器”之一,第29章中的“神器”,依河上公之注“人乃天下之神物也”,代表的即人;《辞源》也解释说:“人为万物之灵,故称人为神器”[5]。人自身,包括其所具有的智慧、力量等都应当被视为“器”。
结合各“器”前后的限定词及所在章节,可以发现“器”的蕴含非常丰富,如第28、51章中的“器”显现的是动态的变化过程,第31、36章的“器”体现老子对于人世间战争的态度,第57、80章的“器”则表明老子对人的智巧的看法,第11、29、67章中的“器”体现的是“无”的智慧。而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老子》中的“器”构成一个与“德”息息相关的发展过程。《老子》中的德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各存在物的本性,一是指人世间的道德;“器”因得“道”而有各自之“德”即独特本性;本为“神器”的人在发展中迷失自身之“德”,发生异化,也会破坏其他“器”之本性,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面对这一状况,人才认识到“德”的可贵,而道德也由此显现,人们通过人生进程与社会治理中的道德努力,重新寻回自身之“德”,终成“大器”。要言之,即“‘德’—异化—道德—回归—‘德’”这样一个过程。人与他物都是“器”,体现了万物平等的思想,但人被称作“神器”,表明其又有高明之处,能自觉自为地以道德克服异化、回归本性,正是人的“神”之所在,“器”的发展历程在人之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因而,对“器”的思考最终是对人生命的运思,生命不仅是物质生活和形体的保存,更是人生中对自我本性的体会、把握,及从中领悟到的自然、真实、圆融之境界。
二、“器”与“德”
老子哲学思想中,“道”是世界的本源,但世界的组成不能只有“道”,“道”必然要由形上的世界向形下的世界落实,显现在各存在物中,通过生活世界才能显示自身力量和价值,这就是“朴散则为器”。“道常无名、朴”⑨《老子》第32章,此句断句法历来说法不一,本文采纳陈鼓应的观点。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8页。,“朴”是“道”的状态和特点,“朴散则为器”中“朴”代表的是“道”,“朴”散为“器”即“道”散为“器”。具体来说,由“道”至“器”,要经历“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的过程,经由“道”的始生,“德”的分殊、蓄养,物质、质料的赋形,最终成为一个个具有各自特性及价值的“器”。“德”是每一“器”所得、所分享的“道”,是“道”的下落、内化,使得每个“器”作为独特的个体而存在,即各“器”的自然本性。“朴”散为“器”可说即“道”下贯成“德”,“道”要分殊到不同的“器”中,成就其“德”,才能使“道”的恍惚性化为有限性的存在。“本体的‘道’因为‘德’而成就万物,万物因为‘德’而获得‘道’的整体性与合法性。”[6]对“器”而言,守住了“德”便是与“道”合一,所以“器”在各自本性内均是自足自得的,而“德”也同时成了各“器”的相同相通之处。
“器”各有其“德”,“器”与“德”不可分离,“德”是“道”在各“器”中的显现。同时,“道”对“器”又“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⑩《老子》第51章,据帛书本改定。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9页。,让“器”保持自然本性,自我生长、发展而不加操持,“道”的这种自然无为是至大至深之德,因而说“是谓玄德”。老子思想中,“道”作为最高的概念和价值范畴,它的根本特性是“无”,没有也不能有限制,甚至不能说出,因而,“道”是“是”,却不是“什么”⑪关于“道”的这一论断,参见叶秀山先生关于“Sein”和“Dasein”的论述。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老子对人的规定也与之相类,不要求他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比如是仁爱的、正义的,因为这种规定会将人原有的种种可能变为只有或者只该有一种,不过是人为的主观预设,人在这其中是失去自由的;老子以“无名”、“不仁”等否定性说法,抹去“什么”对人的局限,只引导人该如何守住自身之“德”,因为“德”才是“器”生存的内在根据,顺应本性是最适宜的生存方式。所以老子思想中对人的根本要求是:每个人都是其自身,是其自然本性要求他所是。这样才给人无限宽广的空间。“朴”是“器”的原初状态也是最佳状态,人的原初——婴儿就是“朴”,本性纯真而未受破坏,蕴含无数生机和可能,所以老子才主张“复归于婴儿”[2]73。对婴儿的推崇,强调的正是人要珍惜和保有自身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应是人依循“德”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人能自主自由加以选择的,这种自然与自由的统一是人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这一状态的达致,不免要经历异化—复归这一过程的反复锤炼,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
三、“器”的异化
“朴”散为“器”后,人均有各自之“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2]145,能像婴儿那样保持本真是最理想的;但现实中却是本为“神器”的人迷失自身之“德”,恣意妄为,也让所有、所用之“器”成为可怕之物,导致个人和国家走向异化、陷入困境。《老子》云:“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里的“利器”指智巧权谋,多用权谋、沉溺智巧,正是个人异化的突出体现;人们背离了原本纯真素朴之“德”,靠“利器”勾心斗角、谋取私欲,而且越来越不舍和不敢收手,于是社会陷入相互倾轧中。“什佰之器”这样的机械器具同样是由于智巧才产生的,有了机械就易有机心,本性不免被污染,老子认为对其应弃之不用,故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个人异化的积聚,不仅会让国家昏乱,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国家的异化。“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2]89批评的就是国家陷溺于自身凶利之“器”即权柄军力。对外是穷兵黩武。战争是国家异化最突出的表现,老子说:“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兵戈正是参与战争,引发杀戮,才被称为“不祥之器”,它带来的是人性的扭曲与生命的破坏。对内则表现为严刑峻法。王弼注:“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2]89刑律也是国家异化的产物,有很强的破坏力,统治者不可以用其来威胁百姓,一味用严刑峻法,将统治建立在千万人本性被压制之上,注定不能长久。国家一旦发生异化,民众便更难守持自身之“德”,会不断向偏离大道的深渊滑落。
异化的根源在于何处?根本上说是由于欲望,王弼注得真切:“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2]149,人们所以用智巧等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身欲求,沉溺于欲望中才造成异化,所以说:“罪莫厚乎甚欲”⑫此句王弼本中无,帛书本中作“罪莫大于可欲”,楚简本作“罪莫厚乎甚欲”;实际上,老子重视人的合理欲望,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对过度的欲望则坚决反对,主张“圣人为腹不为目”;应该说楚简本文字更契合老子精神,故本文用楚简本文字。参见彭浩校编:《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这里的欲望指的是超出正常界限的欲望,如“五色”、“五音”等纵情声色之欲。人的欲望无法禁绝,但有合理限度,不能“甚”即过分,“如果人在满足了欲望之后还拼命地追求所欲之物,那么此时的欲望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对于欲望的欲望将是无边的。这实际上是贪欲的实质。所谓贪欲就是越过了自身界限的欲望”[7]64-65。朴散为器后,人意识到自身与他物不同,继而好奇、探索,通过不断地改造和占有他物来体现自己的力量,以期扩大能延伸到的边界,这才有了越来越大的欲望空间,这是人在追求实现自我中不可避免的探索;然而一旦超出应有界限,就可能让自己深陷在外物中,人生目标成了不断占有、享受物,手段成了目的,欲望成了贪欲,本性也被无尽的欲望所湮没,对名利展开无止境的追求。而个人的欲望还可能累积为集体性的欲望,成为社会的贪欲,全社会弥漫追名求利之风,乃至诉诸战争来满足。这些使人的“德”受到内外束缚,种种恶情恶果由此产生。
贪欲使人的本性被遮蔽,但同时也促使道德产生,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私欲与恶情之生,不特其本身为一精神现象,实亦人之超越心觉初步不能免之表现。亦唯有此初步之表现,乃有第二步之自觉的道德生活。”[8]“失道而后德”[2]93,面对贪欲酿成的恶果,人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开始精神中的超越,开辟和建立自身的道德世界。老子认为“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2]112,真正高广的道德是内敛而不外炫的,但在人的反思、悔改到再发展的历程中,却自然体现出道德的强大力量。《老子》中关于“器”的异化的文字,除了对异化后果进行批判外,也反映出人的道德自我的建立与显现。对异化的揭示首先体现出人对自身这一“器”及所用之“器”的反省,这也意味着道德自我的觉醒,因为“道德自我的特点在于具有反省性……反省性是自我区别于其他存在的内在规定之一,它从意识结构和意识活动的层面,为道德自我超越感性欲望的直接性及其单向性决定、并由此获得行为的自主性提供了可能”[9]130。反省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病病”[2]178,不是只让感性欲望驱动自身,通过自省,承认并找出自身存有的毛病,转变价值观念,从而能有下一步的调整改正,以做到“不病”[2]178。
随反省而来的是道德评判和选择。“民多利器”、“不详之器”这些“器”前的限定词,如“利”、“不详”,及后文对其引发后果的描述,如“国家滋昏”,已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自我在对智巧、兵戈等“器”进行反思后,对这些已异化之“器”的善恶评价,不再对其习以为常或贪恋其所带来的好处,判定它们违背人之本性,有作恶的力量,危及人的生存及发展,给予尖锐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在评判后,还离不开相应的选择,“在生活实践中,自我的自由品格往往通过自主的选择而得到体现”[9]133,是该继续承受还是进行改变,这种选择是个人自由的体现,也是道德自我自主性的突出表现。“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中对“不祥之器”的“不处”及后文在“不详之器”和“君子之器”中的选择,还有对“什佰人之器”的“不用”,“国之利器”的“不可以示人”,均是道德自我的选择,那些“器”已非正常自然之“器”,对它们应不再使用或让其回归正道。有了道德自我的力量,才能自觉抵御异化风险,避免在离“道”背“德”的歧途上继续滑落,并重回正道。
对“器”的道德反省、评判和选择代表的是人对自身和生活世界的思考及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反省、评判、选择标准为何?“孔德之容,唯道是从。”[2]52“道”自然是最高的根据与准则。人体悟“道”而反思现实中的祸患,认识到是由于“有身”[2]29,如前文所说,就是自私其身,只重身之欲求的满足,成为外物的奴隶。因而人需“无身”[2]29,“无身”并非不顾有形之身体,而是不能只重形体,强调自身不能为物欲左右,要意识到在有形的身背后,还有着与形上世界相通,成就人生命之常的存在——“德”,即人之自然本性,所以王弼注“无身”曰:“归之自然也”[2]29。“德”每人都有,但在失去之后才体会到“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⑬《老子》第23章,据帛书本改定。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6页。,明白“德”之可贵,真正的“器”不仅有形,还有“德”赋予的魂。在老子看来,异化是由于人“甚欲”,而欲望的合理限度应是人的自然本性,道德指引人“知足”、“知止”,即在了解本性后知晓“欲”的界限在何处,避免逾越。所以在老子思想中,“上德不德”[2]93,即真正的道德不是仁义礼法那样的强制和虚伪,为道德之名有意造作,而是出于自然本真,发自内心,是在反思本性为何之上帮助人修补现实缺失、回到自然素朴的;强调道德情感的真挚,主张道德的应然以合乎自然为准,只有自然才能保证道德给人带来自由而非新束缚。
四、“器”的复归
“器”离“道”背“德”,给个人及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作为“神器”的人却也由此开始体会自然本性的价值,道德得以出现。真正的道德是人在异化后找回本性的必需力量,是“道”的精神的体现,选择道德也就是选择回到“道”的轨道中。这既是“反者,道之动”[2]110的要求,也是人的主动选择。为何会有这种选择?道德以人的真正存在为指向,真正的人本应当达到“个体性和实体性、有限与无限的统一”[10],但由于个体陷溺于欲求中,迷失本性,其所属的实体——国家也发生异化,人在失去个体本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可归依的实体。在这一情况下,向“道”回归就成为人的必然出路,因为一方面,“道”是宇宙万有的本源,是终极实体,人皆依于“道”;另一方面,人因“道”才有各自本性,“道”让每个人都能保持其本性生存发展,所以通过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动依“道”而行,才能实现个体性与实体性的统一,使人真正成为人,这是人选择、践履道德的关键动力。每个人的“德”都是“道”的体现,返于“德”或说回到自然本性即是合于“道”,回归“道”落实在复归“德”上;同时“德”又是人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道德以人的真正存在为指向,因而道德最重要的目的和作用就是解除对人的遮蔽和束缚,帮助人寻回自身之“德”,使每个“器”都找回自然本性、存在价值。
依靠“唯道是从”的道德的力量,人能逐步摆脱异化、复归自身之“德”。对异化之“器”的论述中体现的道德反省、选择较多还是消极意义上对不道德现象的批评和抛弃,而要使人与“德”的重新统一从逻辑变为现实,在老子看来,还需更为主动的道德修养与行动。“器”中同样给予了方向指引。人最大的束缚在于执著于表面形体之有,欲有权有钱有名,概言之即有功利和利害,心智纷扰、人际争斗、国家混乱均因此而起,故要复归于“德”,具体做法上便要强调“无”,否定功利、造作的东西。一方面个人在人生进程中,应体会“无之以为用”的智慧,有虚静不争之德。老子以日常用具为例:“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得出结论:“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2]26-27。“器”真正发挥作用,是由于“无”,“有”之为“利”是以“无”为本的。就人这一“器”而言,最重要的用自然是性命的保存,性命的保存有赖本根的坚实,而“虚静是万物的本根”[11],因此“无之以为用”的“无”即是“虚灵无相之心”[1]63;在实践上就意味着要“致虚极,守静笃”[2]35,持守虚静之德而不妄动心知,用“损之又损”的功夫来“涤除玄览”,去除情欲纠结及名利诱惑。“归根曰静,是谓复命”[2]35,通过虚静回归人性本然,才有最大之“得”——长生久视,故《韩非子·解老》才说:“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12]。个人保持虚静,在与他人交往中则能贵柔处下,无以自我为中心,做到“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不敢为天下先”是谦躬居下,他人为本的品行,是“不争之德”[2]172的展现;敬重他人而不为贪欲争名夺利,自身虽有虽强,却明白有而不有才不会滞于有的道理,甘于处后守弱。这样的品德和德行能让他人从心底信任和尊重,因不以自我为先为强的“无”而有大“用”——成为众人首长。
另一方面,人生活在社会国家之中,故统治者也须去除成心欲念、虚心守静,特别是该通过“无为”这一道德原则和相应的治理方式,去除对民众的束缚,使万民能回归本性。《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2]76河上公注:“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3]118。此句很明显意在告诫统治者应破除对主宰百姓的执着,破除意念上的造作,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人的自然本真,循天地之理法不妄为,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166。统治者若能坚持这种尊重百姓本性的原则,在此之上因循百姓之“德”进行治理,将价值实现主体定于百姓之上,引导民众无知无欲,治下的万民将能发挥自为自能机能,战胜贪欲,自我化育。清静少事、绝圣弃智、以“愚”治国等,都是无为而治的具体内容,只有按“无为”原则治国才能使百姓保“德”不失、安居乐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150就是无为带来效果的很好展现。
人依靠道德摆脱内外束缚,让自己也让他“器”一步步回到本有的“德”上。真正复归于“德”的“器”,也就重回“道”的轨迹,成为“大器免成”中所说的“大器”。“大”是“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63中的“大”,表明“道”的无限性;“器”实现了向“道”的回归,就有了“道”的“大”的特性,成为“大器”。“大器”意味着“器”恢复本性,依本性自然成就自我,而不是外力强行完成,所以说“免成”。人回归自身之“德”后,也成为“大器”,此时人的生命和生活不由外在力量决定,也不受内在的成心欲念的牵绊,而是依循自己本性自然而然地生活、发展,“大器”中的“大”对于“道”来说指的是其无限性,对于人来说,是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时人的所有行为都自然合乎本性而不逾越应有界限,道德的因子已渗透到人的血液中,不用特地提倡道德来成就自我,故曰“免成”。人经历异化—回归过程后,知晓“德”之可贵,生长、化育都依本性而行,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动力在自身,能够自由地在面临的众多可能中做出选择,让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回到生命根基的同时也实现生命的目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完美、行为正当,最终落实于存在本身的完善;而存在的完善首先即在于扬弃存在的片面性、抽象性,实现其多方面的发展潜能。”[9]6-7因而,“大器”可以说是人格完美的最终实现。
五、“器”之道德意蕴的现代启示
“器”的道德意蕴是围绕“德”展开的发展历程,人从最初之“朴”各自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丰富了自身及社会,一方面也带来本性的异化,老子通过“器”告诫人们应反思本性为何,人生价值何在,以道德摆脱束缚,使生命得到解放。道德是人对自身的超越,“超越是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跳跃”[7]122,异化到回归这一过程正是人通过道德来超越自身,不断地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过程。人经历不断超越,终成“大器”,能依循本性自由全面地发展,社会也由此安定和谐。《老子》虽写在千年之前,可“器”蕴含的道德思想对当今的人们依旧十分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守住本性。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人能创造和掌握的物质之“器”日新月异,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充满彷徨、浮躁,困惑于本性为何、归宿何在,渐渐失去精神家园,于是人们才希冀能寻求到归家之路。“器”的道德内涵启示人们应守住自身之“德”,靠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和领悟自我价值,在一次次价值轮回中体会到真正本性为何,依本性而行动,和自然而然的规律融为一体,若能如此,才谈得上自由全面地发展,让生命之美完全绽放。
其次,尊重与包容他人。在当今社会,人们常以自我为中心,只以自我的标准区分善恶好坏,因而纷争不断,乃至国家间也是如此。“器”的思想让人们体悟到自身本性重要的同时,也意识到他人和我一样有着独特本性,彼此是相互平等、相互依存的。不以自我为中心、敬重谦让他人是老子大力强调的美德,“道家道德在人际的境遇里,体现出的他人优位性,包含着对他者的宽容……在满足他者需要的实践过程里实现自己需要的满足和持有”[13]。每个人都应对他人抱有尊重和包容的态度,给他人充分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境遇里才能实现自己和他人的和谐互利。
第三,学会知足知止。追求物欲是人之常情,关键是要学会知足,否则后患无穷,所以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2]125。当今社会对经济、效率的过分强调使名利成了许多人的惟一目标,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人将价值交由存折上的数字、名片上的头衔决定,自然避免不了心绪纷扰,道德堕落。更让人担忧的是,不少地方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片面追求GDP 发展,这种GDP 主义常变为对经济发展的无节制追求,为经济利益不顾其他,酿成不少恶果。贪欲不仅是个人的,还可能会演变为社会、国家的,而且会在集体的外衣下被误认为是先验道德的。因此,不仅应将个人而且也应将国家、政府作为道德制约引导的对象,重温“知足不辱,知止不殆”[2]122的思想,知足才能避免欲望膨胀,知止才能免去无谓的争夺,不让个人、国家陷入对欲望不断追逐却始终无法满足的恶性循环中;努力扭转发展思路,摆脱一味的经济决定论,让道德与经济形成合理关系与和谐生态。
[1]憨山.老子道德经解[M]∥憨山大师法汇初集:第9卷.香港:香港佛经流通处,1997.
[2]王弼,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王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6.
[5]辞源[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274.
[6]樊浩.“‘德’—‘道’”理型与形而上学的中国形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26-34.
[7]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2.
[9]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00.
[11]许建良.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6.
[12]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70.
[13]许建良.他人优位——道家道德的枢机[J].中州学刊,2008(1):16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