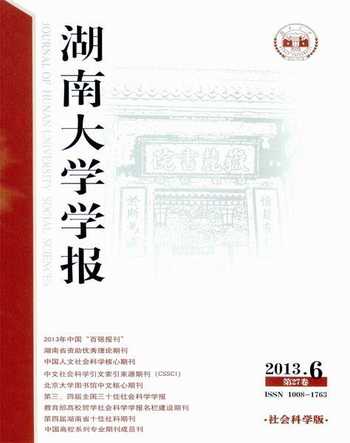揭宏举要,阐微析邃: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平议
范立舟
近代文化巨子严复曾说:“若欲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为今日之现象者,为善为恶姑具不论,而为宋之所造就者,什八九可言。”20世纪文化巨匠陈寅恪先生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代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世文化的主流,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政治伦理原则的影响更是至大至深,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风貌的形成与凝结具有无论如何估价均不为过的重大影响。不过,理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思想渊源上看,它是儒学变革之后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正是这种变革,使儒学具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和说服力,传统儒学所提供的原则才得以提升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深深植根于吾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朱汉民教授《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对玄学与理学这两个初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学术形态、思想体系进行了独出机抒的探究,揭示了两者草蛇灰线,存在着隐秘的联系,说明了中国学术思想所具有的“内在理路”体现的中国思想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志尽文畅,境玄思澹。
魏晋玄学汇通了老、庄和《周易》,打通了道家和儒学本体与实用问题上的壁垒。玄学对宋明理学发生之影响不应该为现今治中国思想史者所轻忽。20世纪30年代,任继愈曾着眼于此。他认为:“自表面观察,每误以为汉代之经学道术至魏晋而中绝,玄学之理论与发生是受印度空宗东渐之影响。揆诸实际则不然。盖中国学术自有其变迁之趋势,且此趋势诚为必然而自然,初不必有待于印度思想之输入也。略举其证,凡有四端。(一)自杨子云以下,张衡、左思、桓谭、王充诸人已发其端,原书具在,不必详征。(二)由黄老之学转入老庄之学(即由道术而入玄学),势所必然,惟多进一步而已。(三)先有宇宙论研究天地万物之构造、生成、运行,再有本体论以探究宇宙之本真,万有之大原,乃必然之序而不可倒置。(四)由具体事实而趋于理化之总汇(由粗而精),此古今中外所同。故先有《吕氏春秋》之养身,后有《淮南子》之养神。先有东汉月旦人物之风气,而后有形名之学演成理论系统,是为玄学清谈之滥觞。”①任继愈:《理学探源》,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13-314页。玄学之理论贡献,即在于着重探讨宇宙本体论之问题。“魏晋之际,玄学主要问题为体用本末有无问题,而玄学即讨论本体之学也。”②任继愈:《理学探源》,载《燕园论学集》,第316页。玄学理论之发生原与佛学无涉,但“玄学正式建立时大乘空宗之旨亦复东来。佛学玄学互相发明有如风雷之相益。中心问题则集中于本未有无之争。”③任继愈:《理学探源》,载《燕园论学集》,第315页。因此可以说,玄学也沟通了老庄和佛教般若学说往来的渠道。及至《肇论》一出,本末之辩,臻于大成。“此后学术旨趣转趋心性之探讨。心性与体用皆为宋儒所注意之中心问题。导其来源仍应远溯于魏晋之际。断无无风起浪,平地涌出之哲学系统。宋代理学发挥孔孟之学广大精微,内外兼赅,断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本,自必源远流长则能成其大。(体用本末诸名相,屡见于宋儒书中而不见于先秦两汉,习焉不察,则以宋儒所独创,实则导源于魏晋玄学)。”④任继愈:《理学探源》,载《燕园论学集》,第317页。此论提醒我们注意,在探讨理学发生的思想渊源时,断不可仅着眼于佛道二家之思想学说,玄学之为渊源,自当为当今治思想史者所关注。
《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深文隐蔚于玄学与理学“身心之学”之思想理路之间。认为魏晋名士通过“性”建构了形体享受与精神超越的依据,“性”既是身体“生之所以然”的根据,也是精神“不事而自然”的依据。任何个体只要循内在本有之性,就可以自我获得身心的全面满足。人们只要“各安其所安”,实现自己固有的本性,就可以到达身体舒畅和精神逍遥的彼岸。所以在玄学那里,“性”是与“理”或称为“道”相通的。一般而言,“性”是一切个体存在的内在本质,“理”是一切天地万物的外在法则。玄学所建构的“性理之学”,就是一种内外相通、天人同构的宇宙本体学说。而宋明理学也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身心之学”,宋儒总是强调身心一体,追求自我身心的愉悦和超脱,实现个体的精神满足,这与魏晋玄学“安心以全身”的智慧有着鲜明的思想的族类相似。宋儒将身心联系在一起加以考量,将道德修为看作是一种主体自我的精神活动,并为此寻找客观依据。宋儒一方面以人的内在之性制约情与欲,建立“定性”和“复性”的工夫论,“性”成为人的情感和欲望合理性的根本依据,冯友兰曾指出:“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⑤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性”之所以能够成为身心合理性、必然性的依据,在魏晋玄学看来人的内在之性与外在天理是同一的,宋明理学继承了内在人性与外在天理合一的性理学说,而且将此种性理学说纳入一个系统的本体论学说中去加以论证。使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天理获得了宇宙论的支持。所以从本体论思想上说,玄学对儒、道、佛学本体论的发展宋明理学本体论的创建,无疑是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轨迹。①参见方光华:《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宋儒人性层面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解,则更加显示了理学的精致。在宋儒看来,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天赋予人的本性与天道相通,从这个角度讲,人性无有不善,但为什么有恶呢?一是由于气质有偏(生理条件不同),二是由于习俗和环境的影响,后者所造就的就是人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然至善,人人同具,“气质之性”是对纯善的“天地之性”的伤害,前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而后者则是应该变化的对象。在此之前,儒家“性善”、“性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在宋儒这里,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法。“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疏,不但坚持了人性本善的儒家正统,而且使恶的来源问题获得了合理的说明。
在中国思想史上,玄学与理学代表着中国学术思想在范畴体系、逻辑结构、形上思辨等方面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两者通过诠释经典而建构思想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相通之处。新理论与新经典系统的形成总是伴随着新的知识生产与教育传播系统的诞生。在知识生产方面,儒学从孔、孟、荀之后,两汉儒学中,发展出两种类型的经典解释学,一种是社会-政治解经学,一种是语言-历史解经学。经过魏晋玄学的承前启后,宋代从解经方法、言说风格、文本写作等多方面摆脱了汉唐的正统模式,新辟出与时代相适应、贴近中下层社会的新风格。在知识生产创新的同时,儒学并非彻底与旧传统断绝,而是最终良好地实现了统合,如在经学这一专门的知识领域,旧的训诂解经方法与新的义理解经方法在更具时代性的话语中获得了整合,语言-历史解经学在新时代将社会-政治解经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层面。在教育传播方面,宋代及以后,儒学有效地进行了科举改革、书院建设、讲学革新等全方位的文化变动,使得儒学的知识生产与教育传播统合为一个能动的系统。我们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及世相流转对对儒学再建传承体系的作用,以及它们在再建过程中如何构成了传承体系的组织要素。玄学与理学构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华丽章节。在新的知识生产和教育传播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儒学内部对于再建的传承体系的核心思想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相反,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对于这种分歧,一方面应该认真揭示,以便理解再建了的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在充分认识到这种内在分歧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揭示儒学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尤其是理性精神的诉求,以便理解再建了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启示性质。毫无疑问地,玄学与理学通过诠释经典而建构思想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相通之处。这两种思想体系都非常重视对先秦经典的理论阐释,他们所建构的新思想与对传统经典的新诠释密不可分。只不过玄学重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和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理学更是推动了新一轮的经典解释学,同时创立了“四书”学。这两大学术思潮通过重新诠释经典而推动了历史性的思想创新与学术变革。而它们的相通点,又有其方法论的关联性。《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通过深入解析玄学、理学的言意之辨,玄学、理学的本末、体用之辨,来说明玄学与理学均十分重视对经典的学习与诠释,作为经典诠释的前提,是肯认义理存在于经典之中。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朱汉民教授的这本著作,对玄学与理学内在理路的把握,既弥补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足,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与优秀文化体系具有稳定的继承性,通过继承积累下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新的时代课题,它具有推陈出新的动力,和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