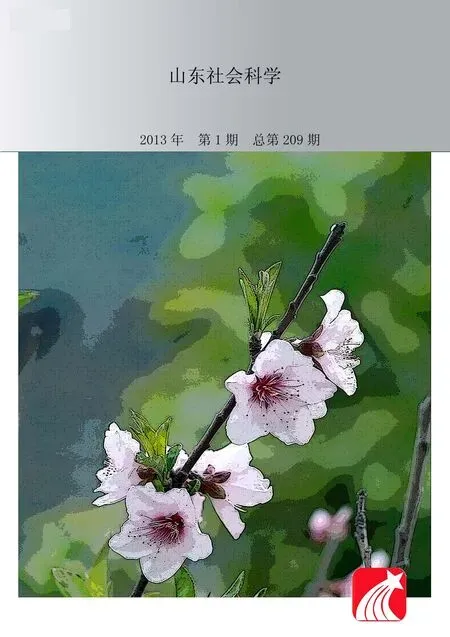“执法为民”的法权文化阐释
姜福东 傅圣敏
( 青岛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检察院,山东 青岛 266200)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央政法委近年来牵头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并突出强调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普及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中央政法委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了20 字的概括式表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该表述因其特殊的官方权威性,赢得了毋庸置疑的地位,举国上下听不到多少反思和质疑之声。“执法为民”等概括式表述,究竟是不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准确把握呢?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正如姜伟所言:“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项内容相辅相成,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科学地诠释了法治与执政、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②姜伟:《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人民检察》2008年第7 期。然而,童之伟指出,现在普遍存在着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20 字表述等同起来的认识倾向,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人们讨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时,从来只限于对20 字表述的不同理解,从未讨论过其本身是否能够准确概括和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而正是最后这个问题,才是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开展相关学习教育之前应该首先下大力气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③童之伟:《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内容构成》,《法学》2011年第1 期。笔者认同“执法为民”等表述固然具有官方权威性,但由于并未经过广泛而成熟的理性商谈过程,故对其提出反思和质疑并不违背交往行为理性的要求。仅就“执法为民”而言,理应对其展开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研究,从中探寻该表述的内在逻辑问题,以求促进社会共识之达成。在古典中国传统法文化、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文化以及西方法权文化三种不同的语境下透视,我们发现,“执法为民”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法权运行逻辑的认知差异。
一、“执法为民”:中国具体文化语境下的阐释
在古典中国法律文化语境下,当然不存在“执法为民”的说法,不过却有“执法”一词,可供我们管中窥豹。按百度词条,“执法,顾名思义是指掌管法律,手持法律做事,传布、实现法律”。这一中文表达,带有浓厚的本土资源意蕴。以笔者视域所及,“执法”二字散见于古代尤其是魏晋以前的典籍中,基本上有三层意思:一是执行法令的官职,二是执行法令,三是星宿之名。①第三层意思其实是对前两层意思的演绎,反映了古代中国法文化“天人合一”的神判色彩。如《晋书·天文志》记载:“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史记·滑稽列传》云:“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伏而饮”。三国时魏国官制中“以御史中丞督司百僚,有违法宪者,皆得纠弹。御史中丞下设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治书执法御史、侍御史(掌奏劾)、殿中侍御史(执法殿中)”。②陈致平:《中华通史》(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页。吴国官制中亦设有执法一职,为御史台属官,督查裁断百官犯案。如《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初,为左执法,迁选曹尚书,及立太子,又领少傅。”王莽篡汉时曾设执法一职。据《汉书·王莽传》言:“冯常以六管谏,莽大怒,免常官。置执法左右刺奸。”《管子·君臣下》曰:“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汉书·礼乐志》曰:“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
从上述典籍记载可知,古人所谓的“执法”,主要是指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官职(或为御史台属下,或与御史台并列,或取而代之),以及该种权能的掌握与行使。该官职与执行法令有关,主要功能是掌管狱讼,依法监督查处官员。传统中国法文化语境下的“执法”,其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该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力实施,其意不在于“为民”而在于“为君”。虽然有士大夫阶层“民贵君轻”的理论,也有帝王将相“以人为本”的实践,但中国古人的民本思维基本上在君主专制思想的框架内徘徊,甚至名为民本、实为民用,亦即把人民作为工具来利用而不是作为目的。在古汉语中,“执法”的“执”字,就是掌管之意;而“司法”的“司”字,也是掌管之意。它们基本在同一意义(掌管权力)上使用。在统治者眼里,民智未开,不过是像一些需要管理的小孩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治理模式,所以很难期待在封建统治者内心产生“民主”、“人权”的思想,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权力”二字。直至清末西学东渐,“执法”一词的意蕴才有了根本性嬗变。1877年,清朝出国留洋的官员马建忠在致信李鸿章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时,曾经谈及“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一身,权不相侵。”③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1895年,康有为在《请定立宪开国令折》中说道,“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④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两个清朝人说的是一回事——西方三权分立。马建忠所用的“执法”相当于康有为所说的“行政”(executive),“审法”则等同于康有为所说的“司法”(judicial)。显然,这是清末国人学习、翻译和移植西方分权理论的结果,无疑受到了西方近现代法权文化的影响。这里的“执法”与昔日国人所言的“执法”已是渊源有别,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文化语境下,“执法为民”被解释为“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文明执法等内容”。⑤中共中央政法委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这里的关键是,“执法”一词究竟该怎么理解?当前学术界对该词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中央政法委编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宣称,“执法为民”中的“‘执法’是在广泛的内涵和外延意义上讲的,是指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全部活动,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行为”。⑥中共中央政法委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显然,这是在最广义的层面上解释“执法”,试图将所有涉法主体的活动一网打尽。但童之伟对该种最广义的“执法”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完整体系中,“‘执法’无论怎样做扩大的解说,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其外延和内涵都无法容纳‘立法’。……强行将对‘执法’论述的范围扩大到‘立法’,试图将立法纳入‘执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出现了语文意义上的超逻辑强制现象”。⑦童之伟:《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之微观解说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 期。此外,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读本》等权威文本中,我们也发现官方对于“执法”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有的文本指出:“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授权,管理社会事务,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依法进行制裁的行政行为”。⑧中共中央政法委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该处的“执法”显然是在狭义层面上讲的,不包括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体在内。有的文本则指出:“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党的正确主张与广大人民意志的统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正确执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①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该处的“执法”显然含义又较广,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司法机关。
如此一来,“执法”以及“执法为民”就相应出现了狭义、广义、最广义三层意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以哪一个意义为准?为什么应以该意义为准?笔者认为,“执法”的广义与狭义之争,凸显了当前国人对法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三元论强调的是立法权、(狭义的)执法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二元论强调的是立法权与(广义的)执法权的二元对立;一元论所强调的,则是法与国家的同一性,借用凯尔森的名言即“国家之一切行为皆为法律行为”②[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最广义的执法权)。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眼界,站在东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视域下,就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在西方分权学说史上,同样存在着法权的三种理解。只不过,该种法权逻辑认知并不局限于对法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认知,其内涵更为丰富——涉及到童之伟所概括的法治国家法权结构中的“权力的配置与规范”和“权利的分配和实现”。
二、“执法为民”:西方法权文化视角的透视
在西方分权学说的语境下,人们基本上可以梳理出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三种法权逻辑认知。哪一种认知最为科学、最为理性,应引起国人高度重视呢?近现代分权学说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阵营:自由主义的分权学说和共和主义的分权学说。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后者的代表性人物有卢梭、马克思等。这种贴标签式的截然二分尽管不是很准确,却也基本反映了法权逻辑二元论和三元论的主流理论取向。时至今日,立法、行政(执法)、司法(审判)三元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与法治领域主流的、官方的权力分立学说;立法(法律制定)与执法(法律执行)的二元论曾经广为人们所赞同,但目前已经式微;至于法权逻辑的一元论,则是国家法律实证主义演绎到极致的结果,是片面强调国家与法律同一性的某种极端主张,已为文明国家所否弃。
(一)法权逻辑认知的三元论缘起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由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系统阐释,在美国法治实践中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提出朴素的三元论分权思想,他“假设在每一个政体之中有三种要素或者职能”亦即“议事、行政、司法”。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三权分立的理论构想。但真正把三权分立从理论自觉层面逐步落实到实践自觉层面,应归功于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洛克曾分析了国家的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认为立法权是指制定法律,从而“运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执行权是指“负责执行已经制定的、仍然有效的法律”的权力,对外权是指“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结盟以及同国外所有个人和社会交往的权力”。在洛克眼中,执行权和对外权“这两种权力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的”,“都是辅助和从属于立法权的权力”;而立法权“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中最高的权力”。④[英]洛克:《政府论》,杨思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237、241页。因此,洛克三元论分权思想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为二元论。
洛克之后,游学英伦的孟德斯鸠在谈及英格兰政治体制时说道:“每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适用万民法的执行权、适用公民法的执行权。依据第一种权力,君主或执政官制定临时或永久的法律,修改或废止已有的法律。依据第二种权力,他们媾和或宣战,派出或接受使节,维持治安,防止外敌入侵。依据第三种权力,他们惩治罪行,裁决私人争执。人们把第三种权力称作司法权,把第二种权力则简单地称作国家的行政权。”⑤[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7页。这里所谓的“适用万民法的执行权”和“适用公民法的执行权”分别用另外两个名称来替换——就是后人通常所说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二者的性质都是执行法律的权力。孟德斯鸠的三权说与洛克的三权说既有相似,也有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洛克没有明确“司法权”的概念,尽管他也探讨了法官的权力,如洛克曾指出:“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不能以临时的专断法令进行统治,而必须根据所颁布的、长期有效的法律,并由人所共知的、经过授权的法官来执行法律和决定臣民的权利。”⑥[英]洛克:《政府论》,杨思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孟德斯鸠则将“司法权”概念化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美国学者布雷恩·Z·塔玛纳哈指出:“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孟德斯鸠误读了英格兰权力分立的实际范围,他把它夸大了,……(但)这些都无关宏旨,(因为)他的权力分立构想,他给予司法作为法治之保护机制的强调,……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更直接地讲,他的思想和洛克的思想一起对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产生了重大影响。”①[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孟德斯鸠之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美国联邦党人将孟氏的三元论分权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权力制衡的理念纳入分权理念当中,大大突出了司法权的权能和权威,相对削弱了立法权力。②[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现代司法权的价值之大,司法权后来的演进和发展(以美国为代表)已经远远超乎孟德斯鸠当年的认识水平。这种三元论的分权学说大体上可以归结为自由主义的分权理论范畴。其更关心权力不被异化,不被实际掌握它的人滥用,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更重视权力之间的分配与制衡,更加彰显权力的规范化运行和科学化发展。
(二)法权逻辑认知的二元论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启蒙时代以来人民主权论的影响。按照卢梭的看法,“那些被认为是主权各个部分的权力都只不过是对最高意志的执行而已。主权仅仅是立法行为,其他的内政与外交权力只是法律的运用,是执行和贯彻公意的个别行为”。③肖君拥:《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凯尔森更是明确指出,国家的权力或职能,就是制定法律与执行法律。“实际上,通常的三分法的基础是二分法。立法职能是同行政和司法这两种职能对立的,后两种职能相互之间比对第一种职能来说显然更加密切地联系着。……如果我们讲到‘行政’,我们就一定要问执行什么。除了说要执行的就是一般规范,宪法以及立法权所创造的法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回答。然而,法律的执行也是所谓司法权的职能。……由此可见,普通的三分法归根结底是一个二分法,即立法和legis executio(立法的执行)的基本区分。后一职能再被分为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④[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可见直至凯尔森所处的20世纪,法权逻辑的二元论在西方还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分权二元论。它聚焦于人民主权的归属,而不怎么关注权力的具体运行。这种二元论更强调的是代表公意、代表最高意志的立法权,甚至将人民主权简单地等同于立法权,从而忽略了其他权力的价值,更没有注意到行政权力、司法审判权力相对独立运行的特殊价值,以及它们对立法权力的反作用力所衍生出来的附加值。诚如肖君拥所言:“人民主权理论仅仅是解决了关于国家公共权力的来源与归属问题,其他关于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及其限制、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关于尊重多数和保护少数的关系等问题,仅靠人民主权理论本身是无法给出周全答案的。”⑤肖君拥:《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其实,分权学说中的三元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人民主权理论的局限性而提出来的。
(三)法权逻辑认知的一元论并非西方法律理论的主流,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其中,早期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最具代表性。凯尔森认为:“法律正如国家一般,除人之行为的强制秩序外别无他物,与道德价值及正义更属风马牛不相及。一言以蔽之,国家只能通过法律加以理解,其既不在法之上,亦不在法之下,而恰是法律自身。法律之观念层面乃一秩序,……至于其行为层面,……则体现为合法权力。”⑥[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1页。因此他主张,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就在于“法律是权力的一种特殊秩序或组织”。⑦[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凯尔森基于其纯粹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极力排斥所有的价值对法律的渗透,让我们领略了其纯粹法学之纯而又纯的特质。但遗憾的是,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他凸显了权力对于法律的极端重要性。这在今人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片面的法权逻辑认知,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凯尔森显然受到大陆法系立法中心主义极端民主观的深刻影响。卢梭极力主张人民主权的不可再分性,坚决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思想,认为他们把主权权威(立法权)所派生出来的东西(如司法权、行政权等)视为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这只会“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⑧[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卢梭因此认为,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作为人民绝对主权之保证的直接民主制下,才能享有真正的民主。历史地来看,凯尔森对人民主权和分权的关系的认识比卢梭更为进步,但仍然存在问题。凯尔森认为:“被称作分权的原则的历史含义恰好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反对集权。……分权原则,……实质上不是民主的。相反的,符合民主观念的,却是全部权力应集中于人民,以及在不可能是直接民主而只可能是间接民主的地方,则全部权力均由一个其成员由人民所选出并在法律上对人民负责的合议机关(collegiate organ)所行使这种观念。”①[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3页。实际上,凯尔森与卢梭一样,都混淆了人民的“权利”与人民的“权力”,将人民主权与分权错误地对立起来。正如孟德斯鸠所强调的,不应将“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自由”(权利)相混淆。因为民主制“不是从其本性上就是自由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他的应对民主制弊端的“秘方”——分权,亦即“为了防止滥用权力,政府应该按照‘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构建。”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5-166页。分权的出发点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集权统治,既包括君主专制下的集权,也包括民主制下可能出现的集权。分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人权。
从理论上讲,凯尔森的前述主张似乎没有问题:分权本身并不一定是民主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全民民主,在代议制下至少是确保立法权完全在人民掌握之中。然而,事实上制度运作起来并非如此简单。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立法权应该由全体人民执掌。但是,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应该让他们的代表来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9页。而人民的权力一旦由其代表来行使,则情况立即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谁能想到,美德本身也需要极限!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制止权力”。④[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6页。于是,分权(及其制衡)便显得非常重要了。分权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它是促进民主政体健康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权利保障机制。反对君主专制、要求人民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有多大,反对各种形式的集权统治、倡导权力分立以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性就有多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执法”的内涵划分为两个层面,即作为分权层面上的执法与作为人民主权层面上的执法。从学理上辨别二者,对于正确把握和运用执法权以保障人民权利很有实际意义。
三、“执法为民”:法权逻辑的价值预设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法观在相当程度上是传统西方法学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观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具有共性,马克思主义的分权观可被视为西方共和主义分权学说的分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主流的人民主权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仅“在于是否承认人民的阶级内容和权力的经济基础”。⑤肖君拥:《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是与卢梭的直接民主思想较为接近的——他们都主张人民至上,而不是人民代表至上,最终的权力是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君主手中。这种人民主权论是用来同当时的君主主权论作斗争的。⑥周永坤:《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分权学说以致力于反对君主专制的人民主权论作为其思想政治基础,必然更为关注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而不怎么强调人民的权力具体应如何操作、运行,因此该种分权学说更注重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权,而相对忽略了其他权力。该学说甚至认为,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司法权、行政权等不过是从立法权中派生出来的。即使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权,那它们只是在“执法”——执行最高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而已,只是立法权的附庸。可见那个时代许多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对于法权逻辑规律的认知还是比较粗浅的。实际上,那是一种反对集权的共和主义分权观,一种“立法——执法”简单二分的权力观。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值得引起今人高度的重视。
法权逻辑认知的基本规律是权利与权力在法治下的对立统一。不仅资本主义国家要遵循法权逻辑的这一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违逆之,否则就要走弯路、跌跟头。我们始终坚持“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搞“权力分立”。实际上,正如童之伟所言,权力分工与权力分立并无本质区别。分工是从“社会内容”上看问题,分权是从“法律形式”上看问题,二者只有视角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亦即“在一个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和分权实际上是一回事。分权以分工为社会内容,分工以分权为其法律形式”。⑦童之伟:《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东方法学》2011年第1 期。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分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分权这种人类文明演进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同样,我们“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并不等于我们不反对集权。我们当然要坚决反对暴君式的集权统治,但同时也要高度警惕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式的专制主义。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当然不可能再沿袭前苏联的政法模式,也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于法学、法律的只言片语视为绝对的真理——那些论断实际上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我们所应秉持的,毋宁是一种进化的、进步的、现代的、反映全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法权逻辑认知与理念,并结合自己的具体境遇,努力去贯彻之、践行之。相较之下,法权逻辑的三元论最为科学和理性:其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有利于规范权力行使、防止权力腐败;有利于促进代议制民主健康发展,防止人民主权异化。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法权逻辑的自身运行规律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而不应完全被某种话语体系所禁锢。在法治国家里,权力与权利的矛盾运动,自有其特定的逻辑规律和价值预设。这就像一个系统工程,由不同的构件组合起来,其背后则是不可或缺的理念支撑。如果我们要将“执法为民”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表述,则必须始终强调:其中不得缺少民主、人权、公正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要素。
(一)必须规范权力来源的人民性,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如何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执法人员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如何教育引导全体公民知法守法,自觉通过法律渠道来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①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这里似乎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执法人员”与“全体公民”放在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层面上。“依法治国、执法为民”与“知法守法”的表达,亦然。此种说法明显有官民二元对立之嫌,并不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养成。“执法为民”应当体现出用人民主权的主体意识来规范国家权力行使的特殊意蕴。正如童之伟所言,“执法为民”四个字虽未写进宪法,但可以理解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包含的对执法机关的固有要求。②童之伟:《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之微观解说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 期。中央的初衷是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一开始并未延伸至全国其他领域。很明显,国家领导层的意图就是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来进一步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是要进一步强化权力的人民属性,绝对不是片面强化权力主体意识,这是不应被人为扭曲的。如果倡导“执法为民”反而给人们造成执法者中心主义的印象,如果践行“执法为民”反而强化了公权力的威权主义向度,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种所谓的“执法为民”。
(二)必须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的权力与权利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之间可能趋于一致,但也可能相互对立。人民主权论并不能完全解决人权保障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被权力拥有者假借“人民主权”来侵害人权。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人民主权论,还应强调人民主权论的弊端,凸显人权的极端重要性。西方许多学者看到了卢梭式人民主权论的集权主义倾向。如罗素指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让渡给国家了,这含有完全取消自由和全盘否定人权之意。③肖君拥:《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人民主权战胜了君主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然而,人民民主并不意味着通往集权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那种认为民主的降临会自动地防止集权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美国学者布雷恩·Z·塔玛纳哈甚至认为:“民主是一种愚钝且笨拙的机制,它不保证产生道德上良善的法律。它肯定是人类设计的更换政治领袖的最佳方式,但这与如何制定法律才最好这一议题没有关系。”④[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就此而言,必须以人权来制约人民主权。人权是维护民主的完整性所必需的,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行使民主的自决权。为了更大的民主之善,民主必然也必须受个人权利的限制。⑤[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35页。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人民主权的某种纠偏机制,也是正确践行“执法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执法权对私人领域的干涉力度越大、渗透力越强,维护人权的要求也就越迫切、标准也就越高。执法主体的威权主义传统越长久,相对人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就应更加强烈地受到激励。
(三)必须公正而高效地实施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从字面落实到现实,必然存在着执法者理解和适用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的权力寻租空间大得惊人,现实中滥用执法权谋取私利的现象比比皆是,防不胜防。因此,执法者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课题,应当对“执法为民”从构成要素上作适当限定。现实社会中什么力量最容易构成对人民利益的实际损害?毫无疑问是公权力,所以,“执法为民”应该有一个限制公权力的方向性限定的内涵,否则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假借“执法为民”而超越法律去害民的情形。既然是“执法为民”,就应该勇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不是“执法为民”,是不是公平正义,谁看得最清楚?当然是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真正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执法为民”,必定是一个公开化的、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质疑的过程。①参见某网友在周永坤法律博客上的评论。http://guyan.fyfz.cn/art/911671.htm#1263247来自外部的监督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职业法律人内部的制约机制尤其是遴选机制,对于实现社会公正而言更显弥足珍贵。因为不管是广义上的执法为民,还是狭义上的执法为民(行政执法意义),最终都需要精通法律的内行人来处理。法律这种职业对于业务素质和品行要求很高。因此,法治发达国家都十分强调“必须以最大注意力”来遴选法官及其他法律人,不仅关注他们的“法律知识与睿智”,而且同样关注他们“对法律的忠诚”、他们的“社会背景”、“诚实与正直”、“温和脾气与理性举止”等。②[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只有“德艺双馨“的职业法律家,才会更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
(四)必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坚持遵循规则、依法办事,坚持将法律具体解释与适用的最终发言权配属于司法审判机构。作为一个人云亦云的、模棱两可的、“相当空洞的概念”,法治甚至“可能被用来为最严重侵犯私人的和群体的尊严与自决权的行径提供正当性证明”。③Carl F.Stychin,Linda Mulcahy,Legal Methods and Systems:Text and Materials,Third Edition,London:Sweet & Maxwell Ltd,2007,p.12.然而,随着法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大家对法治还是积累起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简单地说就是三个主题词:政府受法律限制、形式合法性、法律而非人的统治。首先,法治强调“主权者、国家及其官员受法律限制”,这是“一条延续了2000年、常常被磨细但从没有彻底磨断的主线”;其次,法治必须具备“公布、面向未来以及普遍性、平等适用和确定性等品质”;第三,法治尽管“适用于在受法律支配的活动中行使职权的一切政府官员”,但其中必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即法官独立,“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们是确保其他政府官员被认为遵守法律的人”。④[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160页。这三个主题词及其阐释,是对“执法为民”的规范要求,其凸显了法治的形式标准的维度。法治当然可以有形式和实质两种不同意义的解读:一种可谓“适中的解释”,亦即遵循规则;另一种可谓“崇高的理想”,其与正义之标准合二为一。⑤Carl F.Stychin,Linda Mulcahy,Legal Methods and Systems:Text and Materials,Third Edition,London:Sweet & Maxwell Ltd,2007,p.12-13.“执法为民”也肯定要努力追求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但最低限度必须坚持法治的形式标准,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坚持遵循规则、坚持司法独立及其制度配套。诚如布雷恩·Z·塔玛纳哈所言:“分权要想实际有效,就必然要求有保护司法不受其他机构干涉的制度性安排。”⑥[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这也是法权逻辑认知三元论的基本价值预设和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