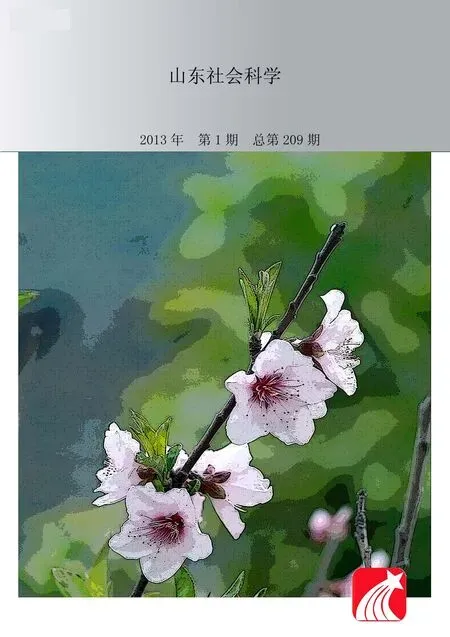哲学与政治的张力
——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
白 刚
(吉林大学 农学部公共教学中心,吉林 长春 130062)
作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①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美籍犹太裔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被公认为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国外,自20 世纪5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问世以来,她的思想就逐渐引起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和美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可以说,今日之阿伦特在世界范围内名声鹊起,“除她之外,还没有一个20 世纪的政治作家受过大家如此多和如此广泛的关注”。②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与国外的研究状况相比,国内对阿伦特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20 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而进一步的展开则是在进入21世纪后的10 多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10 余年时间里,阿伦特却成了国内政治哲学领域里的一个新“热点”,大有“超过”罗尔斯之势,以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政治哲学中的显学。本文仅就阿伦特政治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加以评述。
一、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主题。所以,如何看待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把握和理解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阿伦特早年学的是哲学,但纳粹上台后,特别是哲学家与纳粹的合作使她觉得,柏拉图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与纳粹主义有某种关联,这促使她摒弃哲学转向政治,重新反省和审视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在阿伦特看来,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是关注政治(人类事务)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隔阂始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定罪,苏格拉底之死让柏拉图对城邦生活深感绝望,同时也对苏格拉底学说的某种基础提出了质疑,这促使柏拉图从哲学回到书斋,开始了纯粹的“沉思生活”,哲学从人类事务领域“撤离”了。而正是这一“撤离”,使柏拉图用哲学“消解”了政治,导致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对世俗政治的敌视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此意义上,阿伦特与柏拉图的立场正好相反:柏拉图是为了哲学而审判政治,阿伦特则是为了政治而审判哲学。③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Edited by Dana Vill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63.
在反省和批判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基础上,阿伦特总结出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两层含义:其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哲学家对人类事务领域的态度问题。“每一种政治哲学首先要表明哲学家对于他自己也置身其中的人类事务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涉及并表明了特殊的哲学体验与我们置身人群之中的经验之间的关系”。①汉娜·阿伦特:《哲学与政治》,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对政治的看法是哲学家关于自我知识的重要部分,因为他自己就置身于人类事务领域中,他必须说明自己私人的哲学体验与生活在人群中的公共经验之间的关系。其二,哲学与政治处于一种紧张关系。“政治哲学”本身就处在政治和哲学的张力中,或者用哲学来统治政治,或者用政治来评判哲学。“政治就是这样一个场所: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在其中得以照料,绝对的哲学标准在其中得以应用”,所以“每一种政治哲学一眼就可以被看出似乎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用归源于人类事务领域的范畴来阐述其哲学体验,或是相反,宣称哲学体验的先验性,并且按此来评判所有的政治”。②汉娜·阿伦特:《哲学与政治》,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356页。在此理解的基础上,阿伦特反对像柏拉图那样用哲学“消解”政治,而是主张回到苏格拉底,通过对希腊城邦政治原型的考察,重建其关注人类“复数性”和“出生性”的“积极生活”的“行动政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阿伦特从“哲学”转向了“政治”。但到了晚年,特别是参加了艾希曼审判之后,促使她重新反省人类的“无思”状况,她又从一直关注的政治领域走向了“精神生活”,明确表示要“回到哲学去”:“我已在政治上尽了微薄之力,不再做了;从现在起,剩下的时间我要从事超越政治的事情”——“回到哲学去”。③转引自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3页。
实际上,哲学与政治并不是像有些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一定是对立的。阿伦特在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身上看到了哲学与政治和解的希望,她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政治的行动、自由的行动是需要哲学的,哲学与政治可以共存于公共领域,虽然共存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张力的消失,哲学和政治都为人自由的存在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看到,阿伦特对哲学与政治的之间关系的调和,绝不是要回到古希腊城邦制,而是“试图制订真正政治地思考的新形式和发现政治行动新的可能性”,④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从而为柏拉图创伤的继承者准备一条新的热爱整个世界、热爱此时此刻的道路。
二、关于行动的理论
可以说,关于行动的理论是阿伦特政治概念的核心。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将“积极生活”(vita activa)所包含的各种活动区分为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活动是基本的,相互不可替代,每一个都对应于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给定的一种处境,即人在世存在的基本境况:劳动的处境是生命本身,工作的处境是人造的世界,行动的处境是人的复数性,三者分别满足人不同的需要和服从不同的标准。劳动与单纯的生存本能相联系,这使它成为一种无休止的重复性活动,但它确保了个体生存和类生命的延续;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生命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外部世界,为有死者的生活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与之相比,行动并不带来外在的结果,它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为历史创造条件,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⑤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工作和行动都承担着作为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所以,它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但行动与人的诞生性境况最为紧密,行动就是“开始的能力”,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就是去创新、去开始,因而人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开始者”。
行动显示行动者本人,而劳动和工作都不显示活动者本人,且劳动和工作都需要从更高一级的活动中获得拯救,所以只有行动是其中最高的活动。人作为“劳动动物”需要“工作”把他从无休止的生命循环中拯救出来。在工作中,人是作为“技艺人”的制造者而制造出工具,工具的制造不仅减轻了劳动的痛苦,而且使劳动者获得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固的世界,但工作遵循的是手段——目的模式,在一个由手段——目的模式所决定的世界中,所有的价值都会自行贬值,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难免还要带进暴力。行动之所以不同于工作,就在于其脱离了手段——目的这一模式,因此,作为目的本身的行动就具有创造性和开端启新之功能。并且,在阿伦特看来,相对这种沉默无言的劳动和工作而言,行动往往伴随着言说,或者说,言说即行动。⑥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只有言说和行动这一以自身为目的的自我显示的活动,才能把制造者从无意义性中拯救出来,人才能获得自由。尽管劳动、工作和行动同属“积极生活”,都是人生在世必不可少的基本活动,但行动还是与其余两种活动不一样,劳动和工作是属于前政治的,而行动特别地与政治生活相关,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认可“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在阿伦特这里,投身于行动的只是自由人,广大奴隶和工匠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她的“行动创建和维护自由”大打折扣。
阿伦特建构“行动”理论的这一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20 世纪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两股独特但彼此相关的潮流——政治的“科学化”和政治浪漫主义,①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页。拯救了政治生活的存在论地位。但阿伦特过分重视“行动”的重要性,夸大了其与劳动和工作的对立性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甚至以此区分来否定和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观,体现出了她的一种“行动本体论”情结,在根本上走向了一种“行动唯我论”。因此,阿伦特反而不无讽刺地与她所反对的“正统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到了一起。②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三、关于自由问题
自由是阿伦特政治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在阿伦特看来,自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间实在,在言辞中可听,在行动中可见,在事件中可谈论、记忆并转化为故事,③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所以自由既与行动有关,又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有关。在劳动中,人完全受生命必然性制约,没有自由;在工作中,人作为制造者虽然有一定的自由,但是由于受到制作对象和制作工具等物质手段的制约,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只有在行动中,人只和人相互作用,不受任何物质因素的制约,才是完全自由的。因而阿伦特把行动看成是自由的体现,与政治生活最为相关:自由本身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政治组织中的理由,没有自由,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将是没有意义的;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而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④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这一方面表明,在阿伦特那里,自由与行动密不可分,自由与行动实际上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表明了阿伦特独特的自由观,即只有在行动中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自由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只能在行动中获得的自由才是政治的真谛。“自由是一种政治的或公有社会的现象,而行动则是真正政治的核心”。⑤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阿伦特认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⑥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但这种自由的身份却不会因为解放的行动而自然而然地到来,真正的自由是与共同体及确立共同契约的各种历史可能性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感受到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除了单纯的解放之外,还有赖于其他同样解放了的人,以及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公共的空间,没有这样的公共空间,就没有自由可言:“没有一个从政治上得到确保的公共领域,自由就没有得以显现的在世空间。”⑦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唯有存在一种公共领域,才会出现一种不仅仅是“人统治人的政治”。所以,真正的自由源于政治领域,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的世界,以便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通过词语或行动使自己加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在阿伦特这里,自由、公共领域与行动是三位一体的,人类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得自由,而自由只能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中获得,它与私人领域中的一切活动无关,只有摆脱家庭生活、生产劳动的必然性领域,进入绝对平等的公民身份的领域,政治自由才能实现。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为实现政治自由的典范。
阿伦特追求的是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实实在在的“积极的自由”,而不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消极的自由”。但阿伦特的自由观捍卫的是政治共同体里的自由,而不是个体反抗共同体的那种自由。说到底,阿伦特对自由的阐述尽管关注现实——爱这个世界,却根本上源自希腊古典时代。在阿伦特这里,政治和自由总是与城邦共存。但古希腊城邦制的政治和自由只属于“城邦之内”,而“城墙之外”实际上是既无“政治”也无“自由”,⑧参见许章润:《城墙之外无政治》,《读书》2010年第2期。所以阿伦特的自由观只是达到了形式的“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因而更多的是对现实自由的一种理论想象——一种公共政治领域的乌托邦。
四、关于公共领域问题
“公共领域”(the public realm)是通向阿伦特政治理论的钥匙。⑨Shiraz Dossa,The Public Realm and The Public Self:The political Theory of Hannah Arendt,Waterloo: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89,p.5.在阿伦特的理念中,公共领域是区别于家庭和社会而特别属于政治的,它是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借助话语和行动展示自我的“现世的空间”,有别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学艺术的领域、私人生活的空间及社会经济的领域等等。阿伦特基本上在三个层次上谈论“公共领域”概念:其一,最直接最狭义的公共领域是直接从人们的相互言说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空间,一个直接由多数的人们撑开的“之间”,它的真实性之存在于人们为着言说和行动而在一切的地方,与实际的地理空间无关;其二,在较广义上,公共领域是保证言说和行动反复出现的、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它使行动成为“一种组织化的记忆”,城邦就是这样较为稳固的政治组织形态,因而公共领域是一个显示个人独特性的舞台;其三,更广义的公共领域就是共同世界,是一切事物都要在其中显现而获得客观性的显现空间,器具、艺术、文化、传统等等都是这个共同世界的组成部分。①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11-113页。
在反省极权政治和回归古典政治的基础上,阿伦特实际上还表达出了“公共领域”的两种基本存在形态:一是公民互为主体的沟通,在此公共领域表示任何公共事务都由谈论和说服而非由权力和暴力来解决,此典型是古希腊的城邦;二是公民之间追求美德的实践,在此公共领域表示公民之间平等地相互竞争,此典型是阿伦特的“积极的生活”。②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实际上,关于公共领域,阿伦特主要从时间上、空间上指出了公共领域的一般内涵,并通过分析与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区别,建构了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在她那里,公共领域作为人的卓异性的表现场所,是人展示人自身的空间的存在,显示自身为“共同世界”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既有别于“社会”,也有别于“社群”。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人们协商一己利益或者展现血浓于水之情的地方,它是一个人们显露独特自我的场所。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显现着他是“谁”。公共环境比隐私环境更能充分显示自我。公共领域是一种“外观”,一种“井然有序的戏景”,它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公共领域“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空间,以抵御个人生活的空虚,为有死之人保留了相对的持久性”。③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公共领域是个复杂的概念,人们很难给它下一个普适性定义。我们在阿伦特的论述中,也难以找到公共领域明确清晰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规范意义上的政治范畴,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即一个公共建筑或者公共场所,而是一个能被附加许多外在属性并与具体的实体空间相区别的范畴。因此,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不如说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五、关于革命问题
在阿伦特看来,“革命”(revolution)一词原来是一个天文学范畴,指的是星体有规律的运转,而革命的原义就是“复辟”,是旧政权的恢复。但近代以来发生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却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是无知者的启蒙和受奴役者的解放。所以,创新性、开端和暴力等因素都与革命概念息息相关。因此,革命首先包含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即历史会突然开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进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但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有没有革命就要看有没有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个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革命”。④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所以,革命就是在政治世界进行的开新行动。
革命这一开新行动的核心内容是创造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没有公共自由和公共幸福的原则,革命就无从发生”,⑤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阿伦特认为人类有能力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创造真正的公共领域”。⑥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但革命要确立的这一“公共领域”,却不仅是另一个“政治秩序”,而且是另一种“社会秩序”,“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⑦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革命的主要动力乃是对自由的渴望。极权主义的施虐让阿伦特看到了与人的自由初衷完全违背的新专制压迫形式,它造就了现代政治的空前危机,这样的“革命”是坏死的革命,因为它践踏了革命的创新承诺。但阿伦特认为,要建立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政治权威,最终的希望仍然在革命。革命必须建立一个维持政治自由行动的公共空间,唯有如此,它开始的那种政治自由行动才有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革命承诺,否则,即使它的开始时刻有政治自由行动,那也只是革命“暧昧复杂”性的一部分。政治自由也许包含在革命的起始时刻中,但并不一定会在革命中得到发展,政治自由总是有待于从革命中浮现出来:“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①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阿伦特认为,革命是关于行动的个体、显现的空间、真正的权力和自由的。以此为标准,在《论革命》中,阿伦特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区别。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暴力并没有解决大众的贫困问题,反而使民众陷入了更大的恐怖之中,这种暴力革命最终葬送了个人的自由;而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暴力革命而言,他们在革命后迅速制定了一部能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出色的宪法,从而避免和压制了暴力革命的肆无忌惮的特性,保持了美国优良的革命传统。法国革命是一场导向极权主义的失败的革命,而美国革命则由于建立了自由宪政而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此为标准,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在颠覆和超越西方政治理论传统的过程中“颂扬了暴行”,②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Six Exercise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1,p.23.所以,马克思的革命理想与法国革命一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革命变成了暴力——极权主义。实际上,阿伦特误解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革命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阿伦特以理想的政治革命反对现代的社会革命的精神,带有很浓厚的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色彩。③孙磊:《革命与共和政治——论汉娜·阿伦特的共和政治思想》,载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六、关于极权主义
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阿伦特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概念概括了20 世纪出现的两种政治形式——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但“极权主义”一词有别于全能主义(totalism),更与绝对主义(absolutism)、专制主义(despotism)、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相去甚远,就是与“法西斯主义”也是有所区别的。④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极权主义在阿伦特那里特指一种以恐怖为本质、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从分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入手,阿伦特以政治现象学的方法探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探讨了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统治。在阿伦特这里,极权主义就是反犹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为扩张而扩张、资本和暴徒联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极权主义有三大本质特征:意识形态、全面恐怖和不断的群众运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最大的特色就是创造一种虚构世界,用整套的逻辑推理证明这个虚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但其“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而是改变人性”,⑤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2页。使人变成人面傀儡;极权主义的恐怖本质,不在于杀害的规模,而在于它杀害无辜,以意识形态为依据随时准备判人死刑;极权主义的“不断的群众运动”并不以某个个人或某个阶级的独占的利益为目的,而恰恰是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运动过程本身。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宣传与恐怖是相辅相成的。
在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中,阿伦特认为最根本的是“恐怖”,“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⑥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9页。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变成了全面;当谁也阻挡不了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极权主义恐怖的铁掌不留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思想能力和行动能力,在极权主义恐怖的全面统治下无一人是自由的,人人皆为多余。正是在此意义上,阿伦特称极权主义为“根本的恶”。⑦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3页。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政府形式,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⑧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它反映了“我们世纪的危机”,揭示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崩溃,极权主义统治的经验事实上已造成了西方传统的断裂。显然,阿伦特并不是要作一项关于极权主义的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要反思“我们时代的重荷”,探讨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思想和实践的渊源,由此检讨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阿伦特警示我们的是: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力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重新出现。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9页。这才是需要我们今天特别警惕的。
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中,她有意寻求极权主义的专制本质,而多少忽略了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然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智慧之光却是无法遮蔽的。她对反犹主义、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对极权主义本质的揭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的倡导,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文明的反思,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七、关于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纳粹罪行称做“根本恶”(the radical evil)。在她那里,“根本恶”有三个特征:一是不能从任何可理解的动机推出,通常的理性、思想在这里不起作用;二是根本恶无法惩罚也无法宽恕,以至于人类不能像通常对待自己的过去那样与它和解,它超出了人类事务领域和人类权力的限度;三是它让人作为人表面化了,即取消了人的不可预测性、自发性。①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04页。但参加艾希曼审判使阿伦特改变了她原先对根本恶的看法,引发了她对“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思考。②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在“根本恶”中,核心概念是“表面性”,在“平庸之恶”中,核心概念就是“无思性”。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平庸之恶中的一个典型,因为他清楚地显示了当一个人或一个文明不加思考地言说和行动时会发生什么。在她看来,艾希曼所犯滔天罪行的原因不是恶的本性,而是完全没有思想,缺乏起码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不是恶魔,也不愚蠢,只是无思之人——却又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恶的本性或许是人生来固有的,而这种远离实际和无思能比人的一切恶的本性造成更大的破坏力——这正是我们从耶路撒冷可以学到的一个教训。”③转引自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可以说,在阿伦特这里,无思比恶更可恶。
阿伦特对邪恶的重大认识转变在于,她把邪恶的难以探究归结为邪恶的平庸本质所致。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平庸之恶指的不是邪恶不凶残,而是再凶残的邪恶也是空洞的。邪恶的空洞而不是它的深奥使得哲学思想对邪恶的探究不能有所进展:“我的意思是指大恶虽然极端,但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像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④转引自徐贲:《平庸的邪恶》,《读书》2002年第8期。正是“平庸”这个词暴露了纳粹罪行的可怕深渊,暴露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本质:如此罪行竟是平庸之人犯下的。正是后来通过用“平庸”这个词描述邪恶,阿伦特拒绝把恶妖魔化,同时也拒绝了用某种历史——逻辑机制把恶神秘化。以平庸之恶来看,魔鬼撒旦不是天生的邪恶,而是堕落的天使。当然,阿伦特关注的是极权专制,她为邪恶提供的不是神学的解释,而是世俗的解释,尤其是政治道德的解释。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平庸之恶”的分析,揭示了“思考”对于维护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从而促使她晚年又从“政治”回到了“哲学”。
八、关于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是阿伦特思考政治的出发点,阿伦特从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进程中,发掘出“潜伏的历史暗流”。⑤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在阿伦特看来,有三大历史事件促进了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美洲的发现、宗教改革和望远镜的发明。但现代性的标志却不是西方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是“世界异化”,因为“现代恰恰是以把人口的某些阶层逐出世界为开端的”。⑥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通过对人类三种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现象学考察,阿伦特认为世界是人的真正的栖息地,我们的现实感、存在的意义都依靠世界,但是在现代,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控制,世界已经发生了异化,人越来越脱离了自身生存的世界,与世界疏离了,世界异化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境况和现代性的标志。阿伦特对现代性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聚焦于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世界异化。⑦塞瑞娜·潘琳:《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张云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在阿伦特看来,“世界异化”是比“人的异化”更深刻、更全面的异化,它不仅是人本身,而且是人的整个“生存境况”的全方位异化。阿伦特认为,自从柏拉图把沉思生活置于积极生活之上,将知与行相分离,把政治实践视为技术和制造开始,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体现的多样性和显现性特征就逐渐被单一性和工具性所遮蔽了。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阿伦特主要是从政治危机的角度去思考现代性。虽然现代性的危机存在于各个领域,但当计算代替了判断,生活便远离了政治,所以,阿伦特认为其中心危机就是“政治危机”。⑧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近代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世界异化和主体主义的上升,生产的私人领域迅速崛起,最终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衰落直接导致了20 世纪现代性特别是政治现代性的困境,现代政治暴露出前所未有的危机: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和大屠杀。阿伦特反思极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反思现代性,而经由对极权主义的阐释,阿伦特相当激烈地批判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成就。
关于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西方学术界为人们勾画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不同的阿伦特肖像。实际上,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她肯定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宪政主义等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现时代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和人的危机。①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回归》,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阿伦特对现代性的理解具有两面性,她一方面接受启蒙运动以来的若干现代理念,同时又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她的现代性批判并非是为回到“前现代”的古希腊城邦制,相反,阿伦特关注的是如何借鉴过去的经验,吸取过去的教训,促进当下人类政治生活的重建。现代性问题是复杂的,阿伦特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是在多维视角中进行的,重要的不在于对阿伦特进行归类,而在于我们从阿伦特那里能学到什么。若以阿伦特式的语言来说,关键在于“理解”现代性,并勇于承担起后极权时代政治世界重建的责任。
九、阿伦特论马克思
可以说,“政治观”是马克思和阿伦特相容之维的入口。②詹妮弗·林:《既需要马克思,也需要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阿伦特本人十分重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③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一书被视为她与马克思的直接“对话”,而后她又有《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讲稿问世,以致阿伦特的著作中有个“巍然耸立的马克思形象”。④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在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渊源中,可以说马克思对阿伦特的影响最大,因为:第一,马克思不能忍受沉思内省,他迫切希望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强大生产力来“改变世界”,从而明确地跟西方主流传统相决裂;第二,马克思是最明确地认识到传统之价值的人,同样,与其说阿伦特对西方思想准则持反对态度,不如说她更关心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歪曲表现;第三,唯有马克思一人使政治成为谋求更完美人生的手段,对他来说,行动的世界胜于思想的世界。虽然阿伦特本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西方政治传统的理论,马克思的哲学与其说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不如说是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⑤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但阿伦特本人却对马克思存在诸多误解,这主要体现在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革命和自由等问题的阐释上。在此,我们仅以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解为例加以说明。
马克思与阿伦特都关注劳动与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劳动的动物,将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不是理性而是劳动,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自我确证: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劳动的动物,有意识的劳动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直接体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但马克思在赞美劳动的同时,也最为充分和自觉地认识到和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还存在着“异化”,所以马克思为了“拯救劳动”,将“劳动”进行了二分:必要劳动和自由劳动,主张通过从必要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阿伦特则将“劳动”进行了三分:劳动、工作和行动,认为只有“行动”才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尽管阿伦特指出,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侧面主要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 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 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⑦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但她还是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是“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种“人类营生活动”,是一种受必然性强制的活动。而在阿伦特看来,“共同的世界是能超越这种必要、超越了自然及其代谢活动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世界”。“劳动”只是政治的“前政治”的条件,只能停留在政治的外面。⑧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存在着内在矛盾。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都坚持劳动创造人,这是完全混淆了劳动和生产。马克思以为人类的解放取决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进化,这是模糊了人造的自由领域(政治领域)和自然决定的必然领域(经济领域)间极为重要的界线,这就有可能导致以后者来代替前者。在阿伦特看来,虽然马克思从未想要与自由为敌,但他却抵挡不住必然性的诱惑,因为他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模糊了工作与劳动的界限。
阿伦特利用三分法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评,虽说是独辟蹊径的,却仍颇有争议。阿伦特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劳动观对促进她所特别关心的政治自由行动之可能性的愿望:“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阿伦特没有认识到:第一,马克思的初衷是把劳动价值论的运用范围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二,马克思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只是与这种劳动是否有助于产生剩余价值交换问题相关;第三,马克思的著作清楚地表明,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归为“异化劳动”的,这是社会生产组织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正是马克思要超越的。②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马克思其实早就认识到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导致了“劳动”由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变成了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总之,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观”是“误解”多于“理解”。
十、简短评论
近些年来,随着作为探讨最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的重新兴起,“哲学”实际上是在走向“政治哲学”,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阿伦特作为少有的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公认的难以定位的思想家,“阿伦特的思想所激起的问题远多于它所提供的答案”,③帕特里夏·约翰逊:《阿伦特》,王永生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2页。所以阿伦特的许多思想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阐发。其中,特别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阿伦特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比较问题。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有许多是直接与马克思的“对话”,这对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和理论借鉴。但在这些“对话”中也存在诸多对马克思的误解和片面理解,需要我们在“回归传统”、“解读文本”和“反思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并作出合理的解答和澄明。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进行批判和超越的两条不同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存在许多共性,可资我们今天在比较研究中借鉴,以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实际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无论是在探讨国家、社会、阶级、革命等问题,还是关注自由、正义、民主、现代性等问题,都无法也不能“绕开”马克思,阿伦特本人就是很好的证明。而美国伦理和政治哲学家乔治·G·布伦克特也指出,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④转引自吕增奎编:《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诸流派中,有些将马克思作为直接的或潜在的对手,有些将其引为同路人,有些则自称为其继承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已经成为政治哲学中堪与自由主义相对而立的另一极坐标。⑤杨学功:《中国哲学的本土意识与原创冲动》,《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借用郑昕先生评价康德的说法: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通过马克思,就会有好的政治哲学,而绕过马克思,只能是坏的政治哲学。只要是在一种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折磨人类的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马克思代表着一种世界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对关心人类状况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观是什么样的,马克思都会对他们继续提供有意义的启示。⑥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的政治哲学依然是在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作“注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是“第一哲学”,未来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在马克思的地基上继续发展。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仍然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