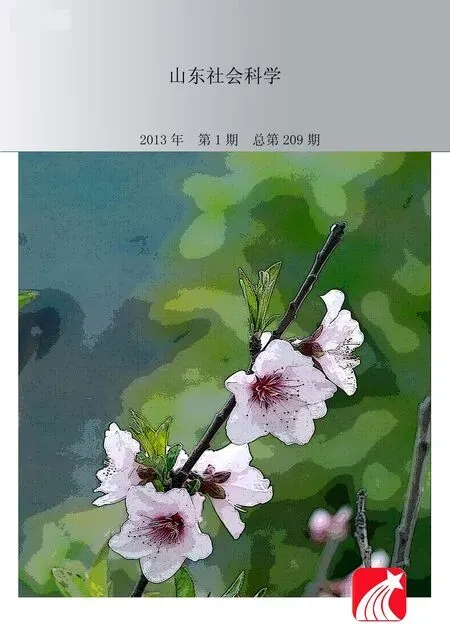“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泓 峻
(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一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如果说诗歌的突破是从“朦胧诗”开始的话,小说的真正突破,则是从1979年年底王蒙抛出他的“意识流小说”开始的。半年多之后,到1980年8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共同举办“王蒙创作讨论会”的时候,他的几部被称作“集束炸弹”的“意识流小说”的成败得失,已经成为会议讨论最为集中、最为热烈的话题。“意识流”这个概念则不仅迅速为文学界所熟知,而且越出文学界,走向电影等其他艺术领域,甚至走向日常生活。
文学界对意识流问题关注的第一个高潮大约持续了三四年时间(从1980年到1983年)。其间不仅出现了一批被称作“中国式意识流文学”的作品,而且还在作家、翻译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下,围绕“意识流文学”这一话题,展开了涉及西方文学史起源追索、主要概念内涵分析、国外代表作家作品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中国代表作家作品研究、中西方之间平行比较研究等内容的学术建构。可以这样讲,在“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坛上,“意识流文学”的出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围绕“意识流文学”的知识建构是一次以学术话语取代政治话语的尝试,它们对之后中国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的走向发生了深刻影响。
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现象之所以能够被放大,并最终扩展成为有影响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往往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某些思想倾向或文学观念,与当时正在涌动的社会潮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等等——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呼应关系。而文学思潮的生成与扩张,既得力于外在的社会潮流的促动,同时也表明了与之相关的社会潮流声势的进一步壮大。“意识流文学”在新时期之所以能够出场并迅速引起关注,在文坛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多层面的、持续的影响,也与中国“新时期”之初特定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
王蒙“意识流小说”集中发表的时间是1979年底到1980年初。把这些“意识流文学”的出场与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与紧接着的邓小平访美、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辞中强调“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等看似散碎的“政治事件”串连起来,寻找其中的逻辑的话,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政治的转向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到官方文学指导方针的调整,再到作家有意识的呼应进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过程。中国的“意识流文学”,正是因为不论其作品内容还是它所代表的文学发展走向,都与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人道主义等官方倡导的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之间可以找到某些契合点,才得以被认可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当时,确实有人看到了“意识流文学”的出场与时代氛围之间的关联,并以此为根据对“意识流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比如,有学者把“意识流文学”的产生与“文革”结束后人们内心深处被长期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联系起来,认为“这个社会现象”“必然成为作家们研究的课题”,“描写这种被压抑了的思想意识也成为作家们义不容辞的任务”。“意识流文学”在这些批评家的心目中,被赋予了“极左”政治批判、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的复归等历史使命,其在中国的出场也因此被认为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甚至被表述为:“没有西方‘意识流’派的侵入,中国也会有自己的‘意识流’。”①彭建德:《“意识流”与国情》,《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 期。顺着这种思路为“意识流文学”辩护的学者还认为,快节奏、情绪化的“意识流小说”的出现,反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时,人们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内心体验方式。因为在巨大的时代变革面前,“人们突然觉得生活的节奏加快了,带紧迫性的问题那么多,而它们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质又使人无法掉过脸去”。“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普遍现象,不能不吸引作家的注意,激起在艺术创作中给以表现的欲望。”②吴野:《文艺的革新和意识流》,《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 期。因此,“意识流文学”便被赋予了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价值,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方式、“现代”艺术手法等发生关联,从内容到形式都传递出正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萌动着的“春天里的希望”。
看到“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出场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政治氛围与社会氛围之间的联系,无疑是深刻的。但在当时保守势力仍然十分强势的政治环境中,将“意识流文学”的出场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作直线式因果对接,以此为其合法性进行论证,则很容易让论争对手抓住其逻辑环节中致命的漏洞。因为在当时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常识”里,“意识流文学”在它的“原产地”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颓废没落思想”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实际上,1980年代初为”意识流文学”辩护的作家与批评家们,只有少数人采用上述有明显“庸俗社会学”倾向的思路,大多数人则另辟蹊径,最终使这次论争演变成了以“意识流文学”这一概念为核心的一次知识建构活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话语开始被学术话语所取代,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思路开始被有意识地加以回避,文学自身的规律与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
二
围绕“意识流文学”展开的批评活动能够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学术话语替代政治话语的标志性事件,与“意识流文学”的特殊身份有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与“意识流文学”几乎同时登场的,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等等。关于这几种同时并存的文学思潮的命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以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或题材为依据的,其名称本身与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之间就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评论界对这些文学思潮的关注,话题很容易就落在了文学的政治含义、与时代的关系及社会功能等问题上面。相关评论文章所使用的话语因此政治色彩十分浓厚,有时候干脆变成了脱离文学作品进行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批评。对“朦胧诗”的命名虽然着眼于文学形式,这种诗歌也具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还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青年一代冷峻的政治思考,以及他们那带有迷信色彩的政治理想失落后心灵深处的迷茫。而且,从根源上讲,“朦胧诗”仍然是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因此,当时的研究者面对“朦胧诗”时,基本上也都是沿习旧的思路,越过它的陌生化形式,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它出现的原因及包含的政治含义。这种形态的文学批评,与“新时期”之前的文学批评,虽然政治态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思维方式与批评路径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庸俗社会学”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其中真正有效的是政治话语。从学理层面看的话,许多观点很难经得起推敲。
与同时期其他文学思潮的本土化“出身”不同,“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则有着十分明确的渊源关系。一方面,当人们把王蒙等人的作品命名为“意识流小说”时,着眼的是它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形式,强调的是“意识流小说”的引入对传统小说创作方法是一次突破;另一方面,“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间无法切断的瓜葛,又使得用社会学的思路否定“意识流文学”十分容易,而要用此种思路为它进行辩护,却要面对一些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因此,在为“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出场进行辩护时,多数人都没有采用传统的社会学思路,去寻找它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而是从文学史发展、审美价值、文学形式的突破等角度立论。
在新时期文坛上,“意识流文学”是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流派,通过外国文学研究界把它介绍进国内的,这一时间要略早于王蒙被称作“意识流”的一组小说发表的时间。在有关介绍中,袁可嘉的几篇文章影响最大。1979年5月,《文艺研究》创刊号发表了他的《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一文;接下来,1979年8月《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他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一文,1979年11月《译林》发表了他的《谈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一文。这些介绍文章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了解西方意识流文学的最权威的文献,文章中介绍的文学史知识与作者的观点曾经被大量引述。而袁可嘉对意识流小说的介绍,除了指出“意识流”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首先使用的,“意识流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出现受到詹姆斯、柏格森、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代表作家是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福克纳等“客观的”知识外,还包含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包括意识流小说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反映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的局面,表现了那个社会制度下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界、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的脱节关系。它在题材上侧重描写失望悲观的情绪、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扭曲反常的心理;在方法上强调运用以暗示和联想为主但直接诉之官能的象征手段和某些自然主义手法”①袁可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文艺研究》1979年5月(创刊号)。。
后面的这段带有明显价值色彩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学术研究“政治正确”,沿袭着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出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判断”。正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判断”,不但使西方的“意识流”文学在进入中国的时候,要首先受到质疑,同时也使得当有人以“意识流”去命名中国的作家与作品时,这些作家与作品同样要接受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从质疑者所采用的社会学视角,用政治话语去论证“意识流文学”在中国出现的合法性不但有一定的难度,而且稍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置于一个在论争中十分被动的位置。而在要求文学“去政治化”的声音与官方“解放思想”的号召已经取得某种一致的时候,以学术化的语言,去消解加在“意识流文学”上的“意识形态判断”,实际上是试图为“意识流文学”进入中国进行辩护的人采取的一个十分聪明有效的策略。在这种策略的引导下,当时主要出现了如下一些观点:(一)强调“意识流文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可以分离的,而当代中国“意识流文学”从西方借鉴的仅仅是方法;(二)强调“意识流”这一方法早就进入了中国,并被包括鲁迅、郭沫若在内的现代进步作家所采用,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三)“意识流”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专属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四)强调“意识流文学”在西方也并不必然与资产阶级颓废思想相联系,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积极意义。
三
上述四种从学术的角度为中国的“意识流文学”进行辩护的观点之中,前三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被称为开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先河,且在“中国式意识流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作家王蒙。
由于王蒙最初发表的“意识流小说”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关注与争议,因此他不断地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解释与说明。其中最集中地谈论意识流问题的文章,是发表于《鸭绿江》1980年第2期的《关于意识流的通信》。尽管在当时,对评论界赋予他的“意识流作家”这一身份,王蒙还有些担心,但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是承认自己“读了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并受到它们的启发。由于其自身并非专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王蒙关于西方“意识流文学”的知识主要来自国内其他学者的介绍。在这篇以通信形式出现的文章中,他并没有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加给西方“意识流文学”的“意识形态判断”表示怀疑,甚至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认同。他说,外国“意识流文学”有许多作品读后“叫人头脑发昏”。因此,他自己尽管借鉴了一些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手法,但在文学观念上与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他说,“我绝不同意那种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感觉、印象、联想与思考、概念、判断截然对立起来……我们也不专门去研究变态、病态、歇斯底里的心理。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①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鸭绿江》1980年第2 期。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王蒙把鲁迅也引为意识流作家的同道,认为“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野草》中,就有许多写感觉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干脆说是意识流的篇什”。接下来,他又将古人也拉上,认为“李商隐的诗,也该做如是解”。
身为作家,而且用的是“通信”文体,因此王蒙并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论证。把他的观点变成学术话题,并沿着他提供的思路进行学术发挥的,是当时的一些批评家与文学史研究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少人开始把中国的“意识流文学”与西方的区别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无可以称为“意识流”的小说,意识流作为一种西方理论对哪些中国作家产生了影响,这种手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否存在等问题,作为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提了出来,发表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学术文章。比如,当时不少学者顺着王蒙的思路,认定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方法的文学家,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意识流小说;②代表性的文章有:杨江柱:《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 期;王许林、徐林英:《论〈狂人日记〉的“格式”》,《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3 期。一些学者认定,郭沫若也是一个写过意识流文学的作家,他的《残春》就是一部写人的性意识的“意识流小说”。③代表性的文章有:石子:《鲁迅、郭沫若与“意识流”手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 期;龚济民:《郭沫若·〈残春〉·意识流》,《齐鲁学刊》1983 第6 期。不仅如此,一些学者还论证了鲁迅、郭沫若等现代作家不仅创作了可以称为“意识流”的小说,而且还是在西方意识流理论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并提供了他们接触到或可能接触到与西方意识流相关的知识的证据。④代表性的文章有:黄全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意识流”纵横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 期;李春林、宁殿弼:《论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意识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 期。有学者通过对文学史的考察及文本艺术手法的分析比较,试图证明中国古典文学与意识流手法的关系,认为“至少在战国时代,屈原创作《离骚》等著名楚辞时,所穿插运用的打破时空界限的自由联想,奇幻多姿的神话传说,不按时序的主观想象的表现手法,即已是最初的意识流基因。后来的唐诗宋词、传奇志怪、南戏杂剧对意识流技巧的运用,就更不用说了,有的还因此成为不朽之作”⑤黄全愈:《得而复失 失而复得——“意识流”纵横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 期。。至于王蒙等当代作家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差异问题,中国现代作家与古典作家的“意识流”方法与西方的差异问题,更是一些十分热闹的话题。正是在这一氛围中,出现了影响很大的“中国式意识流”的说法。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对之前中国学者加给国外“意识流文学”的“意识形态判断”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质疑。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陈焜。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试图用社会学研究的思路,以政治判断击垮包括意识流小说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进攻”的时候,陈焜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名义,呼吁检讨对现代主义文学认识上的误区。他指出:“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解释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一定要把某种文学的性质同某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等同起来,仿佛垂死和灭亡的时代就只能有垂死和灭亡的文学,并且用这样的逻辑把现代派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这种看法在文艺理论上包含的观点是很不恰当的。”⑥陈焜:《讨论现代派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 期。正是在这一立场的支配下,陈焜在自己的著述中,凭着丰富的西方文学史知识,对“意识流文学”的理论资源、作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与评价。在对西方思想史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他指出无论詹姆斯、柏格森、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有科学合理的成分,正是在他们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开始形成了一种不同于18世纪理性主义的观念,最终把现代哲学与心理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⑦陈焜:《意识流问题》,《国外文学》1981年第1 期。在对西方意识流作家的作品进行详细的介绍之后,他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对“意识流文学”的成就作出了肯定,指出,“意识流方法的确是随着一种不同的人的观念发展起来的,它确实从一种现代经验的角度表现了现代人的形象,它一旦出现,就在审美意识和文学形式的观念上引起了变化”,它“打破了单线条的平面结构,表现了立体交织的结构,这种差别和音乐中的单项独奏和交响合奏的差别是相似的,与美术中的平面单线条与立体透视的区别也是相似的”。否定意识流文学的人,在艺术上采取的是因循守旧的立场,这种立场“从辉煌的过去出发,以写实主义的传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不是一种健全的态度,是值得考虑的”①陈焜:《意识流问题(续)》,《国外文学》1981年第2 期。。在当时,陈焜的这些观点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破除了加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头上的政治魔咒,为意识流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作出了更为有力的论证。
四
从现在的眼光看,1980年代初为意识流文学辩护的批评家与理论家们,表现出许多矛盾。一方面,他们热切地关心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希望它能够在不被现实政治所左右的情况下,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按照作家个人的审美兴趣,自由地选择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热切地关注着现实政治,关注着人的解放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他们强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态度与学术身份,希望自己的批评与理论建构能够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接近文学与艺术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受到了把文学裹挟进去的社会政治潮流的涌动,以能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当中而兴奋与自豪。这使得围绕“意识流文学”合法性进行的论争,实际上被两种逻辑力量所渗透:一种是学术自身的逻辑,一种是现实政治的逻辑。只是这两种看似相反的逻辑力量,在许多时候却并不直接对立,而是相互纠结地体现在同一个人的同一种观点、同一篇文章之中。
实际上,对1980年代初的一些为“意识流文学”进行辩护的学者而言,学术话语的运用,既是一种职业身份的回归,也是一种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时的策略性选择,象征的意义要大于其实际具有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当时的学界刚刚从学术话语被政治话语所压制与取代的氛围中走出,对学术话语的使用还不太习惯,许多年轻学者也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耐心,这使得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展开;另一方面,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学术态度的选择也便是政治态度的选择,在为“意识流文学”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对现实政治关注的程度可能远远大于对学术自身关注的程度,他们实际上是试图以学术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论争当中。不同的是,这种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是以要求文学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尊重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打破现实主义神话,突出文学的审美功能等“文学去政治化”的诉求体现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如果纯粹从学术成就看的话,1980年代初由为“意识流文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而延伸出的一些学术话题,比如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没有“意识流文学”或意识流手法存在的问题,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小说能不能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式意识流文学”这种提法本身,都是比较浮浅的,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学术话语背后的政治意图太过明显。随着对西方“意识流文学”了解的深入,许多当时学者所热烈讨论的话题,已经被证明多是一些不具有学术价值的假命题。就是对西方“意识流文学”基本知识的了解,也充满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误读。直到1987年,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还在提醒国内的文学研究者,中国学界流行的一些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看法,未必是符合实际的。比如,国内研究者一开始是把“意识流文学”当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介绍进来并加以讨论的,所以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西方的意识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所传达的“颓废”思想与创作方法能不能分离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柳鸣九则指出,“意识流在西方文学史上既无统一的理论纲领,又无具体的组织形式,甚至连运用了意识流的作家们之间起码的横向联系也不存在,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基本条件,把它作为流派,无疑与对文学史缺乏必要的考察有关。”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意识流文学”在20世纪的出现与发展有何历史的必然,它是否就一定表现潜意识,是否与泛性论有必然的关系,是否一定反理性或非理性,柳鸣九认为国内学术界的认识同样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对一些与“意识流文学”有关的更深入的问题,如如何对意识流、内心独白、潜对话这些相近或相似的心理描述方法作出界说与区分,西方运用了意识流方法的作家之间是否还有一些细致的区别等等,学术界更是缺乏认真的讨论。②柳鸣九:《关于意识流问题的思考》,《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4 期。这种批评,是切中肯綮的。而连这样一些基本的学术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的学术讨论,其学术含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新时期”之初文学界放弃政治话语,尝试着以学术话语为“意识流文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一选择本身仍然是有意义的。
实际上,当1980年代初的学者们为自己的包含明显政治意图的观点进行辩护时,选择学术话语而不是政治话语,这已经表明学术话语的有效性在明显地增强。而当围绕“意识流文学”的论争变成文学作品的介绍与中西方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基本文学概念的清理等学术活动时,必将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所使用的话语最终完成由学术向政治的转换起到十分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们发现,为“意识流文学”辩护的学者提出的一些学术论点,在当时就遭到另外一些学者的批驳。这些对具体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学者,未必是反对“意识流文学”的人,他们针对的是一些学者学术观点及其论证过程存在的学术漏洞。对他们而言,这一话题已经很少“政治含义”了,促使他们介入这一话题的主要动机是学术兴趣。因此,在批驳者的文章中,我们反倒能看到一些更具学理性、更加遵循学术规范的文字。这使得围绕意识流文学而展开的“学术讨论”成为一个学术话语的使用从尝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说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发展过程中,学术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取代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的话,这一事件正是在关于“意识流文学”的论争中悄然发生的。它与199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呼唤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声音遥相呼应,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走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