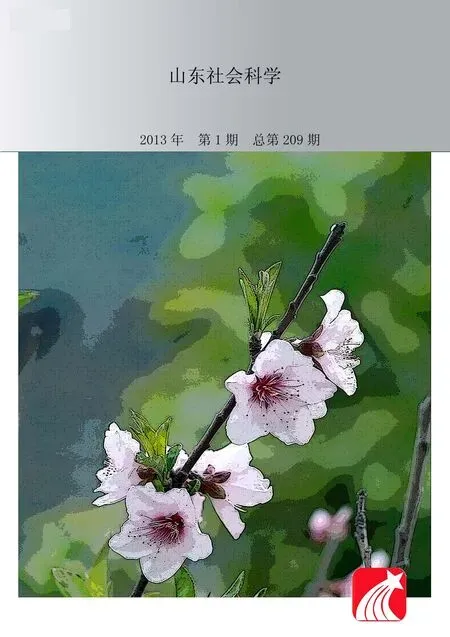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社会和学理基础
何中华
(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当代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汉儒董仲舒的德治思想越发显示出它的深刻启示价值。大致说来,道德的肯定依赖于两个层面的辩护:一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预设;二是道德的世俗基础的捍卫(这又包括道德的发生学前提和道德的社会土壤两个方面)。董仲舒正是着眼于这些方面来为其德治思想寻找理由和根据的。考察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社会和学理基础,对于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其德治思想的丰富意蕴无疑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
一
以德治国是董仲舒的基本立场。他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密,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他甚至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春秋繁露·保权位》)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有针对特殊历史语境的一面,因为汉兴之时,人们的普遍焦虑是如何避免秦亡的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鉴于秦王朝严刑酷法,汉代统治者和文人儒士便格外地突出强调德治的积极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矫枉过正的需要。但是也应看到,德治思想也有更一般的意义,有其普遍的一面,即在建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宗法制社会里它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汉代强调德治,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在于反思秦亡的教训。其实早于董仲舒的陆贾就已经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陆贾:《新语·本行》)的观点,并且有“怀德”与“恃刑”的比较和褒贬(参见陆贾:《新语·至德》)。他明确指出:“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陆贾:《新语·道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陆贾:《新语·辅政》)陆贾从中引出的教训是:“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陆贾:《新语·道基》)所以,他主张为政须以仁义为本。贾谊也总结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所谓“失理”,也就是“违礼义,弃伦理”(贾谊:《新书·时变》)。他还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汉书·贾谊传》)贾谊比较了“德教”与“法令”的高下,指出:“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书·贾谊传》)贾谊还评估了商汤和周武王同秦始皇在治理方式上的得失,指出:“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行一世,下憎恶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汉书·贾谊传》)路温舒同样对秦亡的教训加以总结,认为秦朝过于倚重法制而有失礼乐教化,曰:“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汉书·贾邹枚路传》)他称赞汉文帝,称其“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汉书·贾谊传》)。路氏从正反两方面得出推崇德治、反对法制的立场。
为了避免秦亡的悲剧,汉王朝采取了重农抑商、重德轻法的政策。“重农政策贯彻于两汉王朝的始终,而尤以西汉武帝时期推行最力。重农政策原是作为抑商政策的一个侧面而提出来的,抑末,正是为了重本。”重农抑商意味着崇本息末,无疑是从经济基础这一根本层面上强化德治的做法。陆贾谓“后世淫邪,……民弃本趋末”(陆贾:《新语·道基》)。此所谓“本”、“末”,分别是指农业和工商业。陆贾认为正是这种本末倒置,才导致了道德的沦丧。在战国以前的时代,中国社会大致是鼓励商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酒诰’与‘皋陶谟’来看,战国以前的当政者毋宁是相当鼓励商业的。”“战国时代以前,人君对商业并不排斥,而且相当鼓励。甚至于连囤积——这是商人的经营方式之一,而为后代社会诟病的对象——也不被苛责。”“以物易物”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还不是商业,只有当货币出现后,人们才能在商品交换活动中把货币本身当做追求的目的。此时的交换行为才具有商业的性质。正如傅立叶在《论商业》中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打猎碰到了好运气,他就拿一块兽肉去换另外一个人制造的箭,后者不打猎,但需要食物。这种办法还不是商业,而是交换。”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对于商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马克思把货币及其代表的商业所固有的自我扩张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商业本身有自组织性质,只要不加限制,即可自行扩张,成为一种独立存在和自主的力量。在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正如晁错在上疏中所言:“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前汉书·食货志》)这种情况,恰好构成汉武帝重农抑商政策的特殊历史语境。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商业扩张反过来极大地刺激并强化了历代王朝的抑商政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商业发达的同时,‘轻商’的思想也逐渐抬头”这一历史现象了。
此外,汉代的抑商,还有其时代的特殊原因。“经过短促的秦朝,到刘邦统一天下,社会经过长期的战乱,财政困难,民生凋敝,商人却趁机发财,深深引起统治者的恶感,于是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加以限制。”司马迁写道:“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巨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疋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说,水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农业文明对于水利工程有着尤其突出的依赖性。恩格斯说:“在这里(指亚洲——引者注),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马克思也认为:“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属于治水的文明,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而水利的重要性对于汉代又有其特殊的含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汉代的主要经济区,是位于华北的黄土平原和黄土高原地带,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干旱是对这个区域农业的主要威胁,因而水利的兴废,便成为社会经济荣枯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水利工程,尤其是涉及黄河流域的治理这一特殊因素,属于公共资源的开发。而作为公共资源的开发,公共工程只能由政府来承担,而不能交由市场来调节。“至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目的地大规模兴修水利,则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他的兴修水利计划,是他的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简单说,是富国强兵计划中的一环,因为水利是‘足食’的条件,而‘足食’则是‘足兵’的基础。”这显然也是汉代抑制商业的一个经济和社会原因。
但除上述因素之外,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否还有一般的原因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总体上属于农业文明的范畴。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崇本息末,是传统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一统帝国时代,中国文化中的经济生活而言,直到近代通商口岸外部经济兴起以前,中国经济始终以农业为主体,农村为中国人经济活动的重心,乡村市场为其主要交易地点。”当然,中国在很早就有了城市,而且城市的功能也是多元的,包括行政、军事、文化和商业(生产和消费)等等。所以,“向来认为中国传统城市只具备一种行政或军事机能的说法,并不确实;而认为传统城市仅是一个消费中心,不具备生产性因素,更是一偏之论”。然而,城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并不扮演主导的角色。“城市并不是主要据点,也不扮演重要角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城市居民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市民”。“如果与西方比较,中国城市居民不构成中产阶级(Bourgeois),不构成法人团体,也没有产生西方公民权的观念,‘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信念没有在传统中国体现出来。”这归根到底是由城市的从属性决定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城市说到底不过是农村和农业的延伸而非像西方的城市那种意义上的断裂。“我们似乎可将这种由各级市场所发展起来的市镇或城市,基本上视之为农村交换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城市之根仍在农村。农村依然是人及其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城乡一致性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且这种一致性是城市决定于乡村而非相反。由此就不难理解这样的现象,即“中国一直没有都市优越性(Urban Superiority)的观念,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可以说几乎没有明显的都市文化或都市特性。城、乡之间几乎没有界线”。“因此,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据点应是乡村,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乡村文化(农业文化)为特质。至少在中国传统中,城市没有扮演重要角色,没有明显的城市文化(参见F.W.Mote,The City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代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致力于发展农业,除了直接的现实经济原因的考量(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伦理本位主义文化)外,更重要的还是伦理上的考虑。就像《吕氏春秋》所言:“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农业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它对于人的德性的涵养。在古人看来,农业的劳作讲究有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它鼓励的是诚实、勤劳、纯朴,拒绝投机和讨巧。孟子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中庸》亦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天”无偏私,是无欺而诚实的,而农业是最接近自然(天)的一种劳作方式,所以最有利于敦化人的德性。大地的敦厚品性总是内化为农业劳作者的品格。商业则不然,它鼓励的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恩格斯曾经说过,“商业就是合法的欺诈”,这正是“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商业和商人均持贬低态度,所谓“无商不奸”的观念影响至深至远。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重视农业的根本目的不是功利的,而是为了巩固道德的根基,亦即重视农业不仅仅是“为地利”,更是为了“贵其志”,即通过农业这一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来涵养人的德行,敦厚人的品性。
董仲舒的“五行说”隐藏着道德本位的意涵,它从理论上提示了德治思想的发生学基础。董仲舒指出:“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土”居“五行之中”的地位,这是从时间顺序意义上说的。就空间位置而言,则是“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土居中央,谓之天润”(《春秋繁露·五行之义》)。所以,“中央者,土,君官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董仲舒还说:“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因此,“五行莫贵于土”(《春秋繁露·五行对》)。“土”代表或象征着大地和农业,“土”的独特地位表明以农业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所谓“土爰稼穑”(《尚书·洪范》),而“孝者,地之义也”(《春秋繁露·五行对》)。“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元帝纪》),这正是农业文明的突出特点。不重迁徙造成了血缘关系的稳固,稳定的血缘关系反过来又强化了农业文明的自足发展。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来说,伦理道德乃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和方式。所以,农业文明必然孕育出伦理本位文化的传统。董仲舒说:“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无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责于中,土德之谓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之所以突出“土”的核心地位,其根本用意和深刻用心就在于道德哲学上的考量和蕴含,即从原初根基上守望道德的传统之本。“土”作为五行之一的尊贵地位,具有伦理道德的含义,它植根于道德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发生学联系。正如董仲舒所言:“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五色莫盛于黄”(《春秋繁露·五行对》),何耶?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黄色,这与农业文明有关,因为黄色象征着土地,它构成农业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核心符码。对于“黄色”与“土地”的意象关联,历史上有不少类似的说法,例如:“黄,地之色也”(许慎:《说文解字》)。“黄色,土德之色”(《淮南子·天文训》)。“地谓之黄”(《考工记·画绘之事》)。按照五行的观念,“黄为土色,位在中央”(王充:《论衡·符验》)。“黄,中之色也。”(《汉书·律历志》)“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白虎通·号篇》)关于“土”的本源性,亦有种种类似的说法,诸如:“土,中央,生万物者也”(《汉书·五行志》)。“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周传》)。“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管子·水地》)。
从发生学角度说,道德必有其相应的伦理基础,它归根到底源自人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典型。因为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宗法制社会,由此决定了“家”、“国”之间的同构性。它的治理自然是以伦理道德为其基本方式。《礼记·礼运》曰:“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汉书·五行志》亦曰:“国君,民之父母。”在这样的传统社会里,血缘关系具有始源性和本然性的意义。所以,“夫妇,生化之本。本伤则末夭”(《汉书·五行志》)。从血缘关系的纵向传递看,“孝”在道德上具有根源性。这不仅表现在道德的历史发生依赖于血缘关系基础,而且表现为“百善孝为先”(王永彬:《围炉夜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汉书·艺文志》)这些说法都蕴含着“孝”的本原意味。《论语》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道德与血缘关系之间的发生学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文化传统特别重视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传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因为“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汉代把“孝弟”和“力田”并举,且作为基本国策予以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它的最直观意义似乎是指伦理道德与农业生产的统一,其实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力田”(农业)构成“孝弟”(伦理)的深层次土壤,而“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感应》)。“力田”即所谓“农”的本原性本身,从发生学根源和社会基础意义上表明了德治的前提。《史记·孝文本纪》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是为本末者无以异。’”集解曰:“本,农也;末,贾也。”《汉书·孝成本纪》记载:“阳朔四年诏:‘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汉书·食货志上》亦云:“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颜师古注曰:“本,农业也;末,工商也。言人已弃农而务工商矣。”这大概才是汉代“君国者”的真正用心所在。
作为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秉承儒家传统,在文化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化倾向。在一切事物当中,儒家主张人须“仁乎其类”。《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吕氏春秋》亦曰:“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爱类》)董仲舒说:“爱在人谓之仁。”(《春秋繁露·仁义法》)他说:“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在民族问题上,“夷夏之辨”以有无道德作为甄别不同民族的标准,以道德作为一个民族是否开化的尺度。这反映出华夏民族的自圣的情结,它进而又以道德型的自我意识为其内在根据和基础。它也契合了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观念。其实,“华夏”这一称谓本身就固有其自圣的意识。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诠释:“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邢昺则另解之为:“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论语正义》)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当然是对个人的要求。但在儒家看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同样也应该“据于德”。“德”乃是一个民族之成立的根据。《礼记》即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称谓(《礼记·曲礼下》),皆指周边道德不开化的民族。董仲舒认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春秋繁露·竹林》)这意味着“夷狄”并非是不可移易的,而是可以随着其文明水准的提高而改变的,是否夷狄不取决于种族,而是取决于道德觉解的程度。在人类当中,儒家则主张“仁者爱人”,而“爱有差等”。所谓“爱有差等”同样是上述自我中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从作为伦理关系原初基础的高度去领会儒家的“爱有差等”,才能理解这一主张背后的道德发生学含义。这里所说的“差等”,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坐标的。在社会学意义上,它表现为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经》则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贯穿于人物之间、民族之间、血缘之间关系中的这种自我中心化观念,确立了道德的核心地位,从而构成德治思想的深层意识形态背景。
二
董仲舒明确主张:“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在道义和功利的权衡中,董仲舒的选择非常鲜明而决绝,那就是道义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可以说,这一选择奠定了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应该说,董仲舒有其自觉的本体论预设,因为他说过,“元者为万物之本”,而“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春秋繁露·重政》)。他还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在董仲舒看来,所谓“元者”即为“天”。“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春秋繁露·顺命》)“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复包函,而无所殊。”(《汉书·董仲舒传》)从形而上学层面上说,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无疑植根于他的本体论预设。董仲舒把德治归结为“天”之“道”的内在要求,从而为其德治思想提供合法性辩护。显然,“天”成为最原初的根据。具有超越性的“天”及其秩序构成董仲舒整个德治思想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在董仲舒那里,德治的最后根据源自天道,所谓“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同上)。
作为本体范畴,“天”内在地固有其绝对性特征。所以,董仲舒特别强调“天道无二”。“无”乃“绝”,“二”乃“对”,“无二”亦即“绝对”。绝对之物的特征就是唯一性,它必然在时间上表现为恒定性,在空间上表现为齐一性。董仲舒在这里揭示了“道”的绝对性,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其理。”(《春秋繁露·天道无二》)“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董仲舒在德治思想上的独断性,归根到底来自本体范畴的绝对性。绝对的本体只能是唯一性的。因此,董仲舒坚持道德至上性立场就不能不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坚决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的局面,以至于演化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从哲学上说,这是由董仲舒强调“天”和“道”的绝对性所致,因为唯一性乃是绝对性的根本特征,它内在地要求“天”或“道”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变和在空间维度上的排他。不在古今,唯有合道而已。天或道所固有的绝对性,使其能够超越古今内外之局限。正因此,才如陆贾所言:“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陆贾:《新语·术事》)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就确立起两种对应关系:“体”——“利”(对应于“法”);“心”——“义”(对应于“德”)。对于人而言,义利都是必要的,因为“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然而,义利两相比较,还是存在着轻重和高下的。在董仲舒看来,“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个关系也是极其鲜明的,不容颠倒,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董仲舒说:“身以心为本。”(《春秋繁露·通国身》)此所谓“身”,亦即“体”,均指人的肉体存在。他还讲过,“信重于地,礼尊于身。”(《春秋繁露·楚庄王》)在他看来,信义比功利更重要,而伦理比身体更重要。“天”生“人”,而“人受命乎天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这里存在着这样一条内在的逻辑脉络:“天”→“人”→“利”(“体”[身])和“义”(“心”)。“利”与“义”的分野,说到底源自“体”与“心”的分别;而“利”与“义”的分野,又决定着“或上仁义,或务权利”(《盐铁论·杂论》)。“上仁义”构成德治的基础,而“务权利”则构成法治的基础。“义”(德治)与“利”(法治)孰轻孰重,由此可以得到论证。“义”优先于“利”,以“义”制“利”,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心”为“身”之主宰,此所谓“身以心为本”(《春秋繁露·通国身》)。它同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内在契合。孟子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人格之成立的理由,不在于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生物学规定,而仅仅在于人性之觉悟,亦即人的道德意识的觉解。“是非”既不同于“真假”,亦无关乎“得失”。因为“是非”是道德谓词,而“真假”是认知谓词,“得失”是功利谓词。孟子的这个说法不过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另一种表达而已。在这里,对于人格意义上的“人”亦即大写的“人”而言,道德的优先性地位已经显露无遗。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和心身(体)之辨,同孟子的有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董仲舒之所以特别地强调“常”和“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捍卫道德的合法性基础的需要。常者,即永恒之物;古者,即原始依据。前者乃道德赖以成立的逻辑理由,后者乃道德得以形成的历史根源。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其实,“奉天”和“法古”虽然探寻的都是道德的根据,但是可以分开来说。“奉天”是在逻辑意义上成立的,而“法古”则是发生学意义上成立的。从道德之成立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确立而言,逻辑上之绝对必致时间上之永恒。所以,董仲舒尝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天”何尝能“变”?“道”何尝能“变”?这种“不变”,即永恒性。唯有绝对之物方能不变,即无法被超越、超时空之局限者。正因此,董仲舒强调:“《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桓谭:《新论·本造》)了。当然,在道德问题上,也并不是一切都一成不变,所谓“新王必改制”,不然就无法解释一个直观的事实。然而,董仲舒又说:“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可变者无非是道德的历史形式方面,而变中之不变的则是那个使道德得以成立的永恒之物本身。所以,董仲舒的这个说法,与那种同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关。正是基于上述理由,董仲舒提出了“以古准今”的观点,他说:“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汉书·董仲舒传》)
与董仲舒标举“不变”和“法古”以捍卫道德教化的合法性基础不同,《淮南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则强调与时俱进,试图解构掉道德的合法性根基。它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子·氾论训》)“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同上)。如此一来,道德就被定位于手段和工具的角色,从而势必从属于一个外在的目的,因此丧失其独立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道德沦为“与化推移者”,所谓“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事而举事”(《淮南子·齐俗训》)。如此一来,“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既然这样,“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淮南子·氾论训》)显然,《淮南子》作者仅仅看到了道德的具体形式的历史变迁,而无视道德赖以成立的理由之不变。可以说,《淮南子》从否定的方面凸显了永恒之物对于道德之成立的前提性意义。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废德教而任刑罚”的历史后果乃是灾异的出现,所谓“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这一方面是解释“灾异”何以发生,另一方面又以灾异警告人们必须以德教为本。这里面有一个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神正论的难题:既然一切都是出于“天”,一切都由“天”来决定,那又何以解释灾异和恶的存在呢?董仲舒说:“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同上)陆贾亦曰:“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陆贾:《新语·明诫》)妖孽生、世道衰,其责任不在“天”而在“人”,在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君国者”。对于人来说,责任在己,非天降命。这样的解释,既解决了一切负面后果的责任问题,又保全了“天”的至上性和崇高性。
此外,董仲舒还援天道之阴阳关系来解释刑德关系,由阴阳关系引申出德治优先的合法性。他说:“为人主者……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春秋繁露·如天之为》)这里明确提出了“任德远刑”的问题。董仲舒认为:“阴,刑气也;阳,德气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他还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在某种意义上,德治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即为“王道”,它同霸道相对立,而“王道任阳不任阴”(《春秋繁露·基义》),所以“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是故,董仲舒盛赞孔子能够“反王道之本”(《春秋繁露·王道》)。
董仲舒以阴阳关系为基轴梳理“德教”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将其解析为不同的维度:(1)比重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与刑罚犹此也。”(《春秋繁露·基义》)换言之,“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德教与刑罚轻重分量悬殊,前者远远重于后者。(2)先后关系。“先爱而后严,乐生而哀终,天之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也就是所谓的“前德而后刑”(《春秋繁露·王道通三》)。“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春秋繁露·基义》)。请注意这里的顺序,它鲜明地凸显了道德的优先性地位。(3)经权关系。“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董仲舒在一定意义上承认“权变”的正当性,但毕竟以不害“经”为绝对前提。他说:“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春秋繁露·玉英》)他区分了“经礼”和“变礼”,曰:“《春秋》有经礼,有变礼。”虽然承认“变礼”的存在,但它也是“于道无以易之”(同上)。(4)主辅关系。“阴者阳之助,阳者岁之主。”(《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所以,“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能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秋繁露·基义》)。“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由此之道理决定了“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因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在董仲舒那里,德治优先论还同其性善论的人性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董仲舒通过“比类”的方法,阐释了他的人性论假设,由此给出了教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优先性。他以米禾、卵雏、茧丝比喻人的“性”与“善”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董仲舒未能仔细区分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不同,这是其性善论的弱点。关于人性的可变与不可变,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春秋繁露·玉杯》)他比喻道:“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于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又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天所为之内也。”(《春秋繁露·实性》)其中最可注意者,乃所谓“性比于禾,善比于米”。另外,董仲舒还指出:“性如茧如卵,卵待复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这里,董仲舒认为“教”只是为善的条件,而不是为善的根据。总体看来,董仲舒在人性论问题上存在着某种理解上的紊乱。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或者说,“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疑焉?”(同上)这意味着,善是性的结果,但善本身并不就是性。由性转化为善依赖于外部条件,那就是教化。在董仲舒那里,人性善的内在可能性规定着善对于成就人格意义上的人的优先地位。同时,性善论预设同人的责任之吊诡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因为恰恰由此引申出来了教化的必要性。这无疑给出了德治思想的人性论根据。
为了进一步论证道德的至上性和优先性,以便为德治思想提供辩护,董仲舒还特别注重人的行为动机,尤其强调防患于未然。例如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道德说到底不是治身,亦非治事,而是治心。这正是德治的深刻之处。恰如陆贾所言:道德能够使人“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陆贾:《新语·道基》)。所以,董仲舒坚持认为:“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春秋繁露·玉杯》)。诚如贾谊所言:“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因此,德治能够防患于未然。所以,如果说德治是“绝薪止火”的话,那么法治则像是“抱薪而救火”(《汉书·贾邹枚路传》)。德禁前、法禁后,这也是德治优先的一个理由。相对于道德,法律不仅不能从人的动机上避免恶念的萌发,相反,倒是强化了人的不良动机。因为使法律成立和有效的预设,就已经先行地规定了人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体。董仲舒说得好:“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单纯地依靠法律,就不可能“绝恶于未萌,起教于微眇”(《汉书·贾谊传》)。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此所谓“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陆贾:《新语·无为》)。这恰恰是法律本身的吊诡之处。制定并履行法律,其实只是利用了人们的功利心罢了。因为人们之所以选择遵守法律,乃是基于功利上的权衡,即守法成本小于违法的成本,这本身就是算计的结果。倘若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那么法律就会失效。人们守法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即“畏法教而为之”(陆贾:《新语·无为》)。在此意义上,法律正是对人们逐利动机的肯定和鼓励。所以,法律越发达,就越能激发人的功利心,它在客观上反而被强化了。这正是法治何以往往是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的缘故,它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德治则不然,它的彻底性在于不是利用功利心,而是试图通过人的意志的自律来克服这种功利心本身。从法治的实际后果看,诚如《汉书》作者在批评法家时所说的:“法家者流……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在董仲舒看来,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达到所谓“大治”,它意味着法律变得多余。“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所以,董仲舒推崇德治而不信任法治,因为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只有前者才能“豫禁未然之前”(《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从而能够使国家真正达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