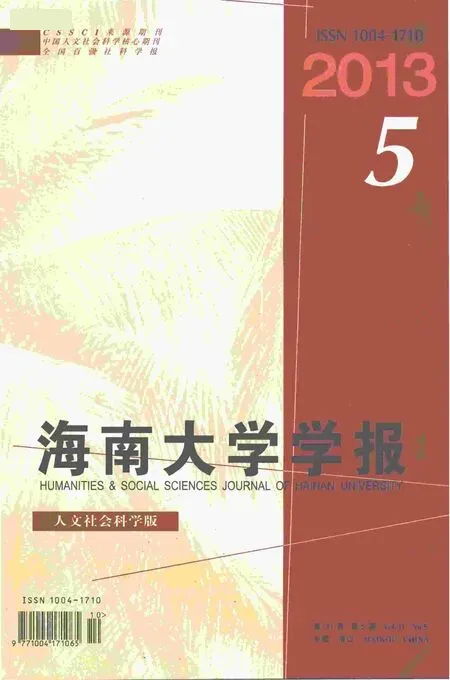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正本清源
姚万勤,张方彪
(1.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2.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浙江莲都323000)
一、问题的缘起:层出不穷的疑难案件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频频出现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例,尤其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中,更为明显。以盗窃罪为例,在认定某个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入户盗窃、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情形除外),不仅要认定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之下实施了转移财产占有的盗窃行为,而且要求被窃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在刑法中究竟处于何种体系性地位?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被窃财物的特殊价值时又该如何处罚?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刑法理论界,由此产生了诸多争议。尤其在我国近几年来,各类疑难案件频繁见诸报端:
例如,在实践中曾经发生过“天价葡萄案”(以下简称为“天价案”)和“卖淫女偷嫖客手表案”(以下简称为“偷表案”)。在前案中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该葡萄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在后则案例中,卖淫女只是随手拿走了嫖客放在桌子上的一块金手表,主观上只是认识到该表“数额较大”,但并没有认识到这块金手表是价值高达十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
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该类问题,我国学者对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进行了诸多的解释与改造,试图在维持刑法理论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处理类似案件。但是,这些剑走偏锋的解释方法和结论非但没有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发生各类案件的处理带来转机,反而使案件的处理结论更加扑朔迷离。同样,行为人在“数额较大”与“数额(特别)巨大”之间产生认识错误该如何处理?也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笔者认为,对于类似案件的解决,至关重要的便是要明确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体系性地位,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的性质。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拟提出自己不成熟的论断,希望能引起刑法同仁的共鸣。
二、理论的嬗变:“数额较大”的体系性地位
(一)“数额较大”的体系性地位之争
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由于对普通盗窃采取的是抽象式的立法例,即法条中只规定了“数额较大”,那么盗窃罪中规定的“数额较大”这一要素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目前在我国刑法中还存在激烈的争辩,纵观目前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1.独立构成要件说 独立构成要件说是由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所提倡,陈兴良教授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方法,因此根据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1]由于在我国刑法典中存在大量的定量要素,例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从而主张将犯罪的数量因素看作是判断犯罪是否成立的一个独立要件。即一个行为成立犯罪除了具备客观违法、主观有责之外,还必须符合“罪量”要件(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如果按照该说之主张,将盗窃罪的“数额较大”视为罪量要件,那么就不要求行为人对盗窃罪中财物的数额有所认识,即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盗窃的是具体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即可。
2.构成要件要素说 主张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数额较大”是盗窃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之一,即“数额较大”是和责任年龄、责任能力、主观罪过等要素同等重要,如果行为人所窃取数额较小的财产,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以盗窃罪论罪处刑,例如,行为人在超市盗窃几个鸡蛋的行为,就不能以盗窃罪评价。因此,以盗窃罪的数额是否达到较大来区分是否构成盗窃罪,是正确可行的[2]。如果将“数额较大”视为构成要件要素来看待的话,根据故意的认识内容,只有行为人对“数额较大“有认识时才能成立盗窃罪。
3.整体的评价要素说 该种观点由我国著名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所主张,其认为,一个行为成立犯罪所具有的必然是客观上具有法益侵害、主观上具有非难可能性的行为。但是纵观我国刑法分则不难发现,并不是对任何盗窃行为都作为犯罪论处,于是刑法增加了“数额较大”、“多次盗窃”等要素。这种使整体的法益达到可处罚程度的要素被称之为“整体的评价要素”。但是根据该种学说,作为数额较大的事实前提,只能是表明法益侵害性的事实,根据责任主义,要将客观的法益侵害事实归责于行为人,就要求行为人对客观事实具有故意或者过失[3]。质言之,作为整体的评价要素的“数额较大”也是行为人主观的认识内容。
4.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说 在刑法理论中,在构成要件要素存在与否的认定上,根据是否加入价值判断而将构成要件要素分为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支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认为,如果一个犯罪没有犯罪数额,危害行为以及危害结果等事实方面的要素,否则在规范上将失去意义。所以主张,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中的社会评价要素,而依据“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只要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认识到财物的价值有可能到达数额较大即可[4]。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除客观上实施了盗窃的行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之外,对财物的价值还必须是外行人领域的认识,如果一般人能够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而行为人没有认识到,也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二)对各种观点的评析
独立构成要件说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属于罪量要件,而非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并不要求行为人对此具有认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因为我国刑法第264条明确规定了普通盗窃罪的要件,即要求“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由此而将数额较大放逐于构成要件之外,还存在规范意义上的解释障碍,是其一。其二,到底在构成要件要素中何种要素属于罪量的要素,何种属于罪责的要素(需要行为人对此具有认识),其判断基准并不明确。其三,运用该种理论处理司法实践中的案件未必妥实。例如,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只是窃取了少量价值极其微薄的财物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少将其予以犯罪化处理。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通过罪量的要件排除犯罪性,而是该种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盗窃罪的违法性要件,即犯罪数额并没有达到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
构成要件要素说、整体的评价要素说以及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说,均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对此应当具有认识,在这点上应当说是妥当的。进一步而言之,构成要件要素说、整体的评价要素说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只是具体的名称有别①笔者认为,在贝林格发明了构成要件理论以来,财产犯罪中所要求的“数额较大”在我国刑法中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在我国刑法中是否有必要创造这一概念,可以另作进一步探讨。。但是,如果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认定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笔者认为不妥:
首先,众所周知,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提出是由于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使用了较多的抽象性术语,为了避免法律适用的不明确性,需要法官的评价要素,或者说需要法官的规范的评价活动,需要法官补充的价值的判断要素[5]123。换言之,规范的评价要素的适用对象是指向法官,而非行为人,即法官仅仅根据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还不能确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那么就需要就特定的事实进行价值的判断。例如,对“他人的文书”、“猥亵物品”的判断并不是通过感官的认识就可以获知的,还必须进行价值的评价才能获得其内容的要素才是规范的评价要素。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说”认为,如果行为人进行一般的价值判断就可以确知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话,就不应该排除其盗窃罪的成立。据此,该见解偏离了该理论的适用主体,对此不无疑问。
其次,能否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理解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值得商榷。刑法理论中对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该如何区分?德国学者Roxin认为:“记述的要素是一种感性的认识,相反,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精神上的理解。”[6]从以上的论断中,不难发现,所谓记述的要素,就是根据通常意义的理解也不会产生较大偏差的事实;而所谓规范的要素,是难以从通常的意义上予以理解,法官必须通过精神层面的价值判断才能得出合理结论的事实。由此可见,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并不符合规范要素的本质属性,因而不能将其归入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范畴。即使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财物的本身价值,也不能据此根据一般人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而认定为盗窃既遂,否则有违责任主义之嫌。尤其在我国刑法之中,一般对于财物价值的判断,并不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而是法官根据价格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即使法官难以直观判断财物的价值,据此就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归入规范的要素行列,毋宁说,违反了规范要素的定义本质。
最后,如果认为财物的价值不需要认识以及只需要平行人评价的标准加以把握的话,这样并不能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且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因为如果行为人只是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较小,而实际价值较大,那么与行为人明显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较大时而盗窃相比的话,其人身危险性较小,理应在量刑时有所差别,但是按照上述的观点,其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的处理结论并不妥实。从责任主义的立场来看,对行为人责任的判断应该是具体的、个别的、非定型性的判断,且构成要件对故意具有规制机能,那么,行为人对财物数额较大的认识应该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对所有的客观构成要素具有认识时才能成立故意。如果仅从一般人的角度出发,那么必然忽视了行为人自身的责任而从属于他人认识的角度给予行为人归责,这样的处理结论必然违反责任主义原则。
(三)解释视域下“构成要件要素说”之坚持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之中,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理解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妥当性。因为:
第一,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了“数额较大”。如上所述,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了普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那么,对于这一要素如何解读,笔者认为不应该偏离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既然我国刑法在法条之中以明言的方式列出了犯罪的要素,那么就不能无视法条的存在性,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我国通说基本也认为,行为人盗窃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盗窃罪,如果盗窃轻微财物的话,并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刑法一直以来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理解为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第二,将盗窃罪中数额较大归入构成要件要素,符合犯罪论体系的要求。在德日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成立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那么对于是否成立犯罪的判断也须进行阶层性的判断。如果把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的类型,则构成要件的要素可以分为作为违法要素的类型与作为责任类型的要素[7]。一般而言,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以客观的构成要件为中心的②当然,这种结论只是从一般的角度而言的,因为在德日刑法中还存在主观的违法要素以及客观的责任要素,其与我们传统的格言——“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并不相一致。。换言之,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一般是作为违法的要素而存在,或者说违法的构成要件要素一般上具有客观的属性。具体在盗窃中,犯罪数额是否较大是影响盗窃罪是否成立的客观要素,即盗窃数额是否较大并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通说认为对其判断也应坚持客观的标准。所以将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符合犯罪论的体系。
第三,盗窃罪中犯罪数额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能够反映法益侵害性。当代法律以保护法益为其本质属性,任何形式侵害法益的行为均是法所不允许的。但是,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而存在,并不是对任何侵害法益的行为均处以刑罚,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同样,在盗窃罪中,也并不是只要发生了盗窃的事实就要追究行为人的罪责。在我国刑法之中,只有盗窃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时才能动用最严厉的刑法予以惩治。那么,以犯罪财物的数额为标准,必然是保护法益的必然要求,只有盗窃的数额较大时,才能反映法益遭受侵害的严重性,才能对行为人处以刑罚。换言之,盗窃罪数额能够恰当的反映法益侵害性,数额越大,法益侵害性就越严重。据此,笔者认为,将这影响法益的要素理解为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并无不当。
三、财物“数额较大”认定模式的抉择:“天价案”出罪理由新探
在我国刑法之中,对犯罪数额的计算尤为重要,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犯罪数额的认定往往成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能否正确认定盗窃数额则是能否正确定罪量刑的关键。例如,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各类“天价案”,在我国刑法理论中,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将这种错误作为事实认识错误中的对象认识错误加以处理。由此,各学者在理论的高度对司法实践部门的做法③其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天价案”司法机关之所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是认为行为人所窃取的财物的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批判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对于发生的各种类型的“天价案”究竟该如何处理,首先应对刑法理论中财物的价值计算模式进行必要的梳理。
(一)日本刑法中认定财物价值的学说概述
纵观各国刑法的规定,不难发现,各国刑法之中并没有规定盗窃罪的数额,即盗窃罪原则上不必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由于盗窃罪是侵害财产的犯罪,所以,各国刑法理论认为,所窃取的财物应当是有价值的财物,对于没有任何价值的财物理应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那么,该如何认定财物的价值?在日本刑法中存在较大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物的价值可分为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即使没有客观交换价值,只要能认定为具有主观使用价值亦可。因为,只要对所有者、持有者具有效用,即便对他人并无效用而不能成为交换的对象,仍值得保护[8]。所谓客观价值,是指财物所具有的客观的金钱交换价值。所谓主观的价值,是指所有者的主观价值或感情价值[9]。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物的价值包括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其中客观价值以及主观价值均需要能够用金钱予以评价[10]。例如,如果窃取了他人的照片的话,还难以评价为盗窃罪。但是如果窃取了一张具有历史价值的并能够用金钱进行评价的老照片,就没有理由否认盗窃罪的成立。
一般而言,在日本刑法中,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是指客观的经济价值,也就是可以用金钱交换的价值,但另外的,诸如情书之类的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对于其所有者而言,具有主观感情价值,因此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有必要用刑法对这种价值加以保护的时候,其也能成为财物[11]。换言之,在日本刑法之中,只是将价值极为低廉的财物排除在财产罪之外,其余均予以宽泛的承认。
(二)我国财物价值的认定模式
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财物价值的判断同样存在主观价值说和客观价值说的对立。
例如我国张明楷教授对财物的价值判断支持主观价值说,其认为:“某些纪念品、身份证、出入境证件、信用卡、存折等,本身不一定具有经济价值,但对所有人、占有人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社会观念也认为对这种财物的占有值得刑法保护,因而属于财物。”[5]843而我国赵秉志教授则明确支持客观的价值说,指出:“判断某种物品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其标准应该是客观的,不能以主观上的标准来评判。经济价值是指能够用客观的价值尺度衡量的经济效用。”[12]
笔者认为客观的价值说更具合理性,因为:第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在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上采取的是本权说,即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才能追究其责任。如果某种财物本身不具有客观价值,而所有人或者占有人认为其具有金钱价值,例如情人的书信,即使对方将其视为珍贵财物,由于它体现的不是财产所有权的关系,因而不能成为财产罪的侵害对象[13]。第二,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的要求,对于单纯侵犯他人具有主观感情价值的财物,未必需要一律按照财产犯论罪处刑,如果在民法上能够得到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发动严厉的刑法追究行为人的责任[14]。第三,主观的价值说实际上是基于法律财产说的考量,而客观的价值说是基于法律经济财产说的立场。详言之,主观的价值说认为,如果行为人对他人的民事权利有所侵害,不问被害人是否实质上遭受了金钱的损失,均应认定为刑法中的犯罪,有所欠妥[15]。而我国通说认为刑法保护的是财物的所有权,只有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客观价值造成损害才能追究行为人的罪责。
从客观的角度理解财物的价值,在我国得到司法解释的支持,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明确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的有效证明确定。……”;“农副产品,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计算”;“盗窃行为给失主造成的损失大于盗窃数额的,损失数额可作为量刑情节”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从以上的规定之中,不难发现,我国在盗窃数额计算上采取的是客观的经济价值学说,即盗窃的天价葡萄,一般只是按照作案当时的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计算,且,对失主造成的损失大于盗窃数额的,一般诸如此类的间接损失不能纳入盗窃的数额之中。在我国刑法之中并不承认被害者主观价值的财物,除非该种主观价值的财物能够利用金钱予以评价且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否则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据此可见,我国刑法中对于盗窃财物价值的判断是坚持客观价值说的立场。
(三)“天价案”出罪理由之我见
如果认定“数额较大”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的认识错误,对于类似于天价葡萄案等案件,应当根据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来加以解决[4]。即使支持其他学说的学者一般也认为对于盗窃罪中财物的价值产生了错误,应当属于对象认识错误,因而对于天价葡萄案是利用对象认识错误处理原则将其出罪。对于这些学者的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所谓对象错误,或称客体错误,是指行为人意图侵害某一对象,因在认识上对某一对象发生错误,视另一对象为该对象而实际侵害的情形。具体到天价葡萄案中,行为人并没有发生认识错误,其认为自己所盗窃的是葡萄,只是不明知所盗窃的葡萄是由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能否将该类的错误归入事实认识错误的对象认识错误,不无疑问。因为,在刑法理论中,对象的认识错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行为人主观上有犯罪的意思,并且有明确具体的侵害目标;(2)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另一对象,但行为人并不是因为改变自己的犯罪意图;(3)未能对预定的对象造成侵害,是由于行为人主观对于对象认识错误所致。”[16]换言之,一般意义上的对象认识错误必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客体(预定侵害的客体与实际侵害的客体),只是没有认识到某一对象潜藏的科研价值,而将其归入到对象认识错误,这并不符合对象认识错误的理论构造。
笔者认为,“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公私财物的数额”,而我国在盗窃罪数额计算上采取的是客观的价值学说,所以,“不能将投入科研的成本计算为盗窃数额;不能将科研的整体价值和可期待价值计算为盗窃数额;也不能将盗窃所造成的损失数额计算为盗窃数额。”[17]那么根据故意规制机能,行为人只有认识到了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才能对行为人的主观进行非难,其他的要素并不是故意的认识的内容。在“天价案”中,葡萄所蕴含的科研的价值(财物的主观价值)并不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换言之,在盗窃罪中,只有行为人认识到了财物的客观价值达到了“数额较大”时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之所以对天价葡萄案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财物价值的计算方法,由此而计算的数额并没有达到盗窃罪所规定的数额标准,所以该类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四、“数额(特别)巨大”的性质之辨:“偷表案”结论的再思考
在前述“偷表案”中,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该手表数额特别巨大而予以盗窃,对行为人该如何处理?换言之,如果行为人认识到了财物的数额较大而予以窃取,但实际窃取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或者行为人认识到了财物的数额可能(特别)巨大,而行为人最终只窃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对于该类的情形该如何处理,便是本案的焦点所在。
(一)“数额(特别)巨大”性质之争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属于普通盗窃罪的结果加重犯还是单纯的量刑规则,在我国目前阶段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例如我国王志祥教授认为,刑法所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属于基本盗窃罪的结果加重犯,亦称为数额加重犯[18]。具体在盗窃罪中,基本犯中的“数额较大”便属于基本数额,而“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就属于加重的数额。在这种观点看来,既然盗窃罪中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普通盗窃罪的结果加重犯,那么应当按照结果加重犯的原则,在法定刑升格适用时,应当要求行为人对加重数额具有认识或预见的可能性。如果将其视为结果加重犯,行为人主观上以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目标,但实际上只是盗窃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应当先在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幅度内选择法定刑,并同时适用刑法总则中有关未遂犯的规定。
而我国张明楷教授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只是单纯的量刑规则,而非普通盗窃罪的结果加重犯。因为刑法分则条文因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使行为类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违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时,才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19]。如果将其视为量刑规则的话,那么,只有行为人客观盗窃数额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才能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
笔者认为将“数额(特别)巨大”视为量刑规则具有合理性:首先,将“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加重结果,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20]612。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一个行为不仅在定性上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在量刑上也同样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如果将盗窃罪中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加重结果,那么必然要对其具有过失,即具有认识可能性。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要求,并不处罚过失盗窃罪的行为,如果将其作为结果加重犯的原理而进行处罚,必须说,确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其次,将“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加重结果,形成了间接处罚。即结果原本不是刑罚处罚的对象,但由于该行为及其结果存在于某一犯罪中,导致对该行为及结果实施刑罚处罚[20]612。换言之,我国刑法对过失的盗窃行为原本是不予处罚的,但是如果将其视为结果加重犯的话,那么,只要行为人对其“数额(特别)巨大”有认识的可能性,就要承担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罪责。如此处理,必然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做出的错误裁决,这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间接处罚应当予以禁止。
最后,将“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加重结果,会造成处罚的不均衡。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行为人的罪行相适应,这是罪行相适用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加重结果,必然会造成处罚的不均衡。例如行为人故意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却过失的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从而在“数额(特别)巨大”中选择较重的法定刑,这将意味着行为人将会受到更重的刑罚处罚。再如行为人潜入银行盗窃,但是行为人在打开保险柜之后,只盗窃了数额较大的金钱,其客观上的确有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却要承担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罪责,然后再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的规定,这在无形之中造成了处罚的不均衡。
(二)对“数额较大”、“数额(特别)巨大”认识错误的处理
既然认为“数额(特别)巨大”属于量刑规则,那么表明行为人对“数额(特别)巨大”应该要有认识,即当刑法将严重的财产损失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时,如果基本犯是故意,那么,行为人对该犯罪的加重结果也应该限于故意[20]613。针对于前文中例举的“偷表案”,即使行为人在客观上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但也不能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因为行为人由于认识错误导致没有认识到所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即使行为人应当预见到数额特别巨大,也不能认定为故意盗窃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充其量也只是对加重结果有过失。而刑法并不处罚过失盗窃行为,不能令行为人对其数额承担责任[20]613。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以“数额(特别)巨大”等财物为盗窃目标,但是,由于认识错误而结果只是盗窃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对其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行为人对“数额(特别)巨大”不承担未遂的罪责,只需要承担“数额较大”的刑事责任。例如,行为人为了窃取银行保险柜的财物而深夜潜入银行,但保险柜中只有数额较大的现金,对行为人只能按照盗窃数额较大的法定刑论处,即使其主观上认识到了保险柜中有数额特别巨大财物的可能性,并且以数额特别巨大财物为盗窃目标,也不能据此认定为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如果不如此处断,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归罪”的泥潭,势必造成处罚的不均衡。
[1]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2003:275-280.
[2]王礼仁.盗窃罪定罪与量刑案例评析[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185.
[3]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8.
[4]郭晓红.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视野下的“数额较大”——以盗窃罪的数额认识错误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1(9):43-50.
[5]张明楷.刑法学[M].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Roxin.Strafrecht Allgenmeiner Teil Aufl.[M].Band I,3.München:C.H.Beck,1997:252.
[7]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83.
[8]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3-204.
[9]佐久间修.刑法各论[M].东京:成文堂,2006:162.
[10]江家义男.刑法各论[M].东京:青林书院,1963:264.
[11]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04.
[12]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59.
[13]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9.
[14]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758.
[15]童伟华.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87.
[16]马克昌,等.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642.
[17]朱孝清.盗窃科研葡萄、豆角案定性探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45-50.
[18]王志祥.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J].法律科学,2007(4):132-140.
[19]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J].清华法学,2011(1):7-15.
[20]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