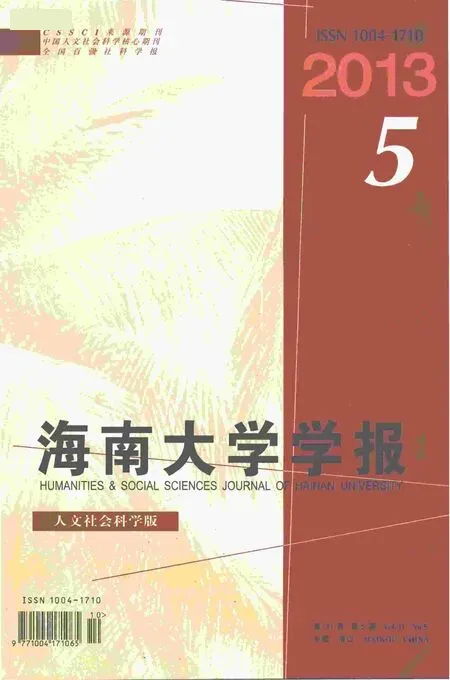“中国”人的德性——有感于“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①
朱 赢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中国”二字不离汉语语境。譬如英文China,无法表达“中”的本意。然而“中国”作为“中心之国”的直解已屡遭诟病。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们,对于古代“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多嗤之以鼻。由近代史观照,“中国”的优越感的确难堪。昔日傲视四夷的天朝上国不仅生生被打入“蛮夷”之属,更蒙受了古来四夷子民从不曾经验的绝境。莫非此乃天命之浩劫,欲使自视高贵者幡然觉醒?这是史无前例的一页,此后“中国”人只能背负扭曲:高贵的历史有多久远,衰败的讽刺就有多沉重——命运自身的晦暗似乎比列强击打更为惨烈,以至于烽火中幸存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之后,却仍面临“自立”与“认同”的困惑。不是有那么多人渴望褪去“中国人”的身份?所以真正的史无前例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何曾是羞愧的?
上述问题虽攸关大体,其犹疑颠覆,亦不过近百年之间:一百年,颠覆三千年。“中国”之“中心”意义的瓦解,实际在“东西之争”的背景下发生;对于“中国”之“天下中心”观念的自嘲,根植于所谓东西文明的悬殊对比。历史不能改写:无法假设,如果西方不是以坚船、利炮、鸦片、资本的方式直白强暴,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是否将顽固不化。历史惟独证明:即便劫后余生,中国只能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寻找出路——哪有什么“天下中心”?仅仅百年的历程已然揭示了三千年来的自大与自欺。
一
天下中心的优越感早已灭亡。那是祖先在“狭隘”中自取的灭亡。古人的目光太短,来不及一睹世界的真相;而中国的地位,只能由后代从劫难中检讨。或许耻于做中国人的群体都对此怀有深刻的检讨能力:祖先何其“蒙昧”,竟意图教导世代子孙自以为天下中心!所幸,终有那么一代人声称难辞其咎,进化的眼光几乎使他们无地自容于先辈可笑的自我中心论断。然而“中心”的观念由何而来?以“中”自居对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若不直面这些原初,似乎检讨总不够彻底。
“中”字在甲骨文中形同一面旗帜,其本义就是在中央之地立起旗帜:“立中即立旂,立中可以聚众”[1]39。据唐兰先生解:
本为氏族社会之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1]39
要严格从地理上确定一个中心似乎并无可能。幸而,先民蒙昧的思维不会以“科学”测量地域中心。从甲骨文释义可见:氏族群众构成共同体,而“中”的地域方位则通过共同生活的聚众行为得到确立。先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中”不为证明地界,而是出于群体共同生活的需要。起初的“中”如同姓氏,氏族部落血脉相连,旗帜就是他们的身份。族人见旗帜飘扬便向“中”聚拢,说明“中”可发号施令,但能否就此将原初的“中”等同于人为的权力?或许在产生政治“立法”之前,生存的本能已让先民主动“聚集”。他们一起觅食狩猎、抵御外敌、躲避天灾,一起守卫氏族血脉;在“立法”之前,死亡的阴影已为他们建立默契;自然法则牵引类生活秩序的形成。与此同时,他们也学会在聚集中“立德”。自然宗法的血缘纽带,让他们在繁衍生息中逐步形成风俗伦常。所以与其说是“旗帜”要人们前往,不如说是人们自觉向“旗帜”归往。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走向人为的政治法则,后者本自更原始的天道德性——其中或许就有政治的限度所在。
当然,在旗帜的号令之下终将建立起权威:人们从四方聚集,是由于有人立起了旗帜。就是那个站在正中的人。只有他可以站在那里,甚至是他界定了“四方”;因为掌管旗帜,所以围绕着旗帜的人们也都围绕着他。问题在于,人们是向着旗帜而来的;那面象征群体身份和生存的旗帜,何以由他举起?
二
举旗立中,乃王者所为。甲骨文中有“卜夬贞王立中”;又有“己亥卜夬贞王勿立中”[1]40。“立中”之举在王,但立或不立,仍求问于天。问天,意味着举旗者的有限权力:须心存“敬畏”,而不擅用“私意”。人是在限度中实现权威的。王者立中,是旗帜高高在上以招四方,举旗者甚至可以隐去。
中:旗帜——招人;
王:举旗者——人。
“中”因“王”而立,却并不因“王”而生。若不辨“人”之于其中的限度,谈王权几乎轻易就陷入政治的狡智。“王”在甲骨文中形似一把刀刃向下的斧头:“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徵王者之权威。”[1]32先民造字将王的斧钺立地:是放下?还是准备提起?耐人寻味的临界。至少,“王”不是高举着斧钺耀武扬威;他所高举的只是旗帜。
王权——生杀。行刑的正当性来自旗帜;但旗帜只发出归往的信号,它并不昭示刑法。斧钺是握在人的手中,就是那个站在旗帜之下的人;当他开口指令,斧钺也同时示威。王是可以杀人的,但一个德性有破绽的人可以凭德性杀人吗?天道与政治间的裂痕如此致命!所以一个不知限度的人是没有资格拿起斧钺的,就好比一个孩子不可任用利器。
人的鲜血试炼德性的利器。鲜血,令德性两难。德性不完整,不可掌生杀;但即便德性完整,就可以杀人吗?天道在这等两难中俯视人道。生死本为天命,然而在共同体中,正由于德性无法完满,才必须使人的天命受限于立法。如果杀戮也是人的天然能力,那么斧钺的威慑本身就是禁止:限制杀戮是对共同体安全的基本保护。只有王能执掌斧钺;四方之众不得私刑。在生杀大权未被滥用之前,王者无疑担负共同体的至高护佑。所谓生杀大权,除非替天行道,否则无以为正义。而真正的王者,在执掌斧钺时又势必抽象为旗帜——惟其将自身隐去,否则人的面目终有破绽。
甲骨文为殷商时代之记录。钱穆先生认为:“盖古代此黄河东、西两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时见舜、禹故事之流传。”[2]现有甲骨文资料中亦存有“尧”字。尧舜之德虽为儒家所主述,但想必在儒学诞生以前,先民对“圣王”德行已有知晓。司马迁曰:“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闲,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伯夷列传》)[3]2121天下权位在让而不在争,岳牧首领出自民众举荐,且被举荐者需通过“试用期”考验方为授政。这说明大至天下、小到部落,领袖权皆本自德性——王可以立中,是由于他有守“中”的德性,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洪范》)[4]311正直之“中”,使人们走向“王”如同走向旗帜。
旗帜—中—王,在德性上本为同一。《毂梁传》曰:“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庄公三年》)[5]《白虎通》释“帝王”为“号”,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帝王之号,汉儒认为“帝者,谛也,像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并引《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6]。在进入政治领域之前,是德性先于权力而自立。一旦四方归往,“王”自然成为“中”,即“王”的原初状态是感召凝聚,而非号令一统。“中”可以表现为统领四方的权力:它尊贵,因而四方卑微;它威严,因而四方禁止——但必须为此加上前提,“中”是由德性确立的,尊卑在德性意义得其正当;若德性损失,王道随即陷落,王权亦失之正当。
三
尧知其子丹朱不肖,无以担当天下,遂将王权授于舜。舜起初让位丹朱。然而“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知天命难违,“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史记》的这一说法在《孟子》中亦有相似陈述。此处“中国”指帝王居住的地方。《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五帝本纪》)[3]30
严格说来,上述表达可能存在漏洞。因为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并无“国”、“或”二字,周初金文中才有“中国”出现[7]212。故尧舜时代的先民或许尚无“国”之概念。且将作为政体概念的“国”悬置,则“中国”二字可显出多层次的意义空间。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7]216-226一书中对“中国名称的起源”有详细梳理,认为西周早期的“中国”有三种含义:一,指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与四方相对;二,包括丰镐、雒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区域,即“中原”地区;三,指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并以夏为族称。及至春秋战国,“中国”概念有所发展,出现统一趋势。春秋时中原诸侯称为“中国”,而秦、楚等为“夷狄”;到战国时七雄已同列“中国”。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中国”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概念。在上述含义中,“中国”一词在夏、商、周三族活动区域间的转换及融合尤需关注。“夏”的称谓极为特殊,它不仅指代夏朝,也发展为“中国”的代称。从《国语·周语》中可知周人自认为夏人的一支。在灭商之前,周人将自己的区域称为“区夏”;克殷后将夏代中心区域洛阳称为天下之中,即中国,又将商代中心称为“东夏”。何尊铭文记载了武王克殷后向天告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尚书·梓材》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可与铭文互证。此“中国”即是指雒邑。费孝通同时指出,在区域上周人在西,商人在东,而夏在二者之间,又因发达最早,宜称“中国”。《说文》称“夏,中国之人也”,从中亦可知“华夏”由来。此外,费孝通也注意到作为文化概念的“中国”:《春秋》明“华夷之辨”时,将“文化礼仪”置于“族类”概念之上,“礼”于是成为“中国”的准绳:所行“有礼”可称“中国”,所行“非礼”则视为夷狄。
上述“中国”至少可分5种层次:
(1)原初意义:与四方相对的中国——天子所居;
(2)溯源意义:尊夏为中心的中国——天子所立;
(3)民族意义:夏商周合流的中国——华夏形成;
(4)文化意义:合乎礼法的中国——礼仪教化;
(5)政体意义:天下一统的中国——中央集权。
“中国”在不断扩大。无论是地域上还是族群上,它日渐浮现出后人习以为常的形象:黄河长江,帝国王权;四书五经,人伦礼法。然而一种惟独属于原初的力量从高处俯视,它无争于世,却可能是历史真正的主宰。当周人将“中国”写为文字,实际就宣告了周取代殷而治理天下的正当性——因德立中。就是原初的那一种正当,在若隐若现中悄无声息地参与“中国”的一切演变。众所归往,因而有王;王者在中,于是有“中国”。“中国”曾是一个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结构。谈“中国”,难道可以省略作为定语的“中”——“德性”?这几乎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缘起。“德性—王权”结构,必须确保“中”首先作为一种德性概念,“中国”必须因德而立:一旦失德,中之不“中”,势必人心涣散乃至“国”之不存。“中国”也曾是一个抽象名词,象征由尧舜之治所抽象出的圣贤理想。尧舜必须余音不绝,以便令后代慕名归往。中国的意义或许已过于丰裕,甚至丰裕中竟含有国人的自我怜悯与憎意。但假如血脉犹可追忆,似汉字于古今之间尚可往来,那么反身而诚:“中国”二字天命至高,惟有圣贤德治可为匹配。
四
是什么德性在成就“中国”?
崇侯虎助纣为虐,使西伯被囚,然而他的“谗言”真实不虚:“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周本纪》)[3]116。司马迁此处的表述暗藏反讽。连崇侯虎这样的人都知道善与德,并能从积善累德中感到不凡的力量。恶人即便丧尽羞愧,却未必会颠倒善恶尺度。对善人施以恶行,亦是以恐惧反证德性。西伯德高却“不利于帝”,说明“帝”失其正当。诸侯皆向西伯,即昭示“王者”易帜。所以“西周”被描述为注定要成为“中国”的政权: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周本纪》)[3]117
虞国人和芮国人争执不下,到了周界,还未见到西伯就自知羞愧而回。他们入周是为找西伯裁决,说明西伯在他们心中有王者权威。但这个故事中的“王者”并没有出现,“权威”也一同被隐去。仅仅是民俗之美,便让两个国君臣服②《正义》引毛苌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君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所争地以为闲原。参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7页注释。。诸侯因此说西伯是“受命之君”。在他们的“说”中,西伯已拥有了事实上的王权——尽管由始至终他都立于“不争”。
据司马迁所述,武王是在商纣杀比干、囚箕子后才下定决心征伐,因为“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此前武王曾有过一次出征,途中遭遇异象。当时八百诸侯不期而会,都认为“纣可伐矣”,但武王认为“未知天命”,所以率队折回(《周本纪》)[3]120。即便有众心归往,武王对称王天下谨慎再三。在司马迁笔下,他并不意欲争立,除非天命使然。
《尚书·泰誓》可视为天命之佐证。尽管此篇被认定伪作,但自其“德性”观之,则可见“改旗易帜”的限度所在。朝代更替中必有征伐,“暴力”在何种情况下才符合正义?《泰誓》宣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4]272王者奉天而行,其正义取自天德而非凭人愿。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8];君王若违逆天德,也就失去了为王的正当性——所谓“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然而“替天行道”的一个前提是不可忽略的:当政权显出败相,施暴讨伐或许顺理成章,但以暴制暴者是否足以匹配“天德”?王道与霸道不可同论。时而,争霸者强立旗帜,亦自诩其暴力有德。
五
回到甲骨文中观“中国”的王道之治:中,旗帜所立;王,斧钺立地——二者皆有关政治权力,但亦有政治之界限所在。
不妨将旗帜与斧钺视作王权的两种象征:一种是抬头仰视,一种是紧握示威。以此观“为政”的两种立场:德治与刑法。一把时刻高举着的斧钺是令人难以靠近的,所以“王”必须保有旗帜与斧钺间的真实奥妙。
传说舜帝治民不施肉刑,仅以“警告”令民自律:“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戳,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9]
武王在平定天下之后,“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周本纪》)[3]129。成康盛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周本纪》)[3]134。
暴力若有德性,则其德应在“禁止”——禁止“暴力”以至于禁其自身。所以在一个有德的共同体中,暴力也应被隐去。武王克殷的正义在于制止暴力;《诗经·周颂·武》歌颂:“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10]1306,此处以克制杀戮作为武王的功绩。又“偃干戈,振兵释旅”是对德性的确立;《诗经·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10]134,此处王者收拾武力,所求乃是有美德之士。
“德”对“中国”这一共同体具有特殊意义。由于“中国”之根本是立于德性的,这使得“政治”对共同体秩序亦有限度——若简单将“中国”视为政治共同体,那么在德性的认识上恐不能周全。据《说文》:“政,正也”[11]123;“正,是也。从一……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11]69。至于对“一”的理解,就回到了“道生一”的大德之上:“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11]1因此必须重视“道德”先于且高于“政治”的前提。政治根本上不是确立权力主宰,而是为实现道德的追慕。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为政》)的叙述,就显示了“德”在“无为”中的力量③包注: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参见刘宝楠《论与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7页注释。朱熹: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1页注释。。
政——正——从一而止。止的两种方式:以外力禁止,或以自觉而止。共同体的立法属于前者。所以“政”在《论语》等经典中还解释为“法教”、“法制禁令”④孔曰:政谓法教。参见刘宝楠《论与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1页注释。朱熹注“政,谓法制禁令也”。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1页注释。。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12]41此处“政治”的局限性极为明显:“政”与“德”相对,“刑”与“礼”相对,说明以立法为根基的共同体秩序并非“上等”。某种程度而言,“以法治国”针对“中国”已属下策。刑法作用于恐惧,礼教作用于廉耻。德性无法因恐惧而立,正如一把举起的斧钺不是使人羞愧的根源。
孔子在论述政、刑与德、礼的优劣时,一个重要的衡量乃是“耻”——民是否有耻成为判断共同体德性的重要标准。这就涉及到“自觉而止”的层面。虞、芮二君向西伯决平:西伯既是德性,也表现为法度。但二君羞愧而回,法度被隐去了,所以在这一故事中,虞、芮二君不仅成全了西伯的德性,也由此实现了自身的德性。“中国”的礼教向德而立,落实到共同体秩序中,则人的羞愧自省意义重大。德性的地位甚至将人的自然属性消解——“人”随之也晋升为一种德性概念:有“礼”方可为“人”;非礼则可能被打入“非人”的境地。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曲礼》)[13]10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13]1411
以“礼”为“人”定义,使人的位格在“礼”中上升:人不再凭借自然属性而优越。一个人即便未经礼教,恐怕也能知觉到人与禽兽间的差别。但礼教恰恰否定了基于自然属性的差别——“礼”不给自然人以地位;人不能以自然属性为高,高贵必须从德性中求得。譬如弱肉强食、纵欲无度等,都是属禽兽的,而非属人的。
然而“人之为人”的限定,大概为“中国”人所特有:仅限“中国”,绝不“普世”。如果“人之为人”同时伴有“人之非人”的问题,那也仅限于“中国”人的自我反省。简而言之,“中国”的“人之为人”不是定夺“中国”以外“人之非人”的尺度。未经教化者如何能知守“中国”的德性?而知礼守德者是不应仗势凌人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曲礼》)[13]12——以“德性”自命高贵者本身就非礼失德。所以一个没有德性的自然人必定不是“中国”人,但“中国”人绝不能指责自然人非人。
“谦卑”不止于个人修养;更重大的意义在其作为共同体的德性。礼法所构建的德性即便“至善”,是否就应强制推行?如虞、芮二君是由于羞愧而领略德性的,这种羞愧可能强加?“中国”人的德性不可失其限度。哪怕礼法教化,也在德性的感召归往中实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曲礼》)[13]7在德性意义上,并没有强制成为“中国”人的问题;华夏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绝不应忽略基于德性的感召凝聚。孔子答叶公问政曰:“近者说,远者来。”(《子路》)[12]535不取人、不往教,持守德性使人“自来”,视为“中国”在德性光辉中的分寸限度,它避免了政治倚仗德性的势力而弱肉强食。
六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吗?恐怕也只有“中国”人会如此提问。那么不如将问题暂且收缩:中国人可能死于羞愧吗?哪一种“中国”?
孟子认为“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朱子注“羞恶”:“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14]229又孟子论“耻”:“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尽心上》)。朱子注:“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14]333。所以“人可能羞愧”的基本前提是:能将羞恶之心作为人之大义。即惟有当德性之于人是首要的,惟有当“人”必不可与“禽兽”同日而语时,舍生取义才是可能的。
伯夷、叔齐应是“死于羞愧”的典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列传》)[3]123
伯夷、叔齐是慕名归往于周的,然而他们却耻于宗周。为此,甚至连吃周人的粮食都成为罪过。他们莫非不知是商纣暴虐无度才自取灭亡,亦深知天下宗周乃人心所向。问题的症结在“正义”二字。“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即便武王伐纣依王道为据,暴力的本相却终究面目狰狞;《索隐》就直言司马迁此处是“谓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纣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惟有德性在反观中自省:“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暴力的正义与反讽同在。伯夷、叔齐以性命将正义的阴影画地为牢。西周代商本是德性的结果,但有德的政治却仍然让守德之人感到蒙羞。伯夷、叔齐拒食周粟,不过是以一己之德性持守而叩问“正义”的限度;他们既非不知好歹,也无心违逆潮流。“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叹息自己的死亡,乃是由于大道之不遇⑤《索隐》释“于嗟”为“言己今日饿死,亦是命运衰薄,不遇大道之时,至幽忧而饿死”。参见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23页注释。。
政治的德性、人的德性以及天道德性:三者关系如此微妙,以至于“正义”往往在人为的声张中断裂。但舍身取义者是清醒的,他们知道德性的尊严远在现实的言说之外。太公视伯夷、叔齐为“义人”,这一“义”字,莫不含有政治家未曾吐露的羞愧?
死于羞愧——死于羞耻。未免偷换概念之嫌,有必要稍作辨别。
“愧”字从心,段玉裁曰:“媿或从恥省。按即谓从心可也。”[11]626因而“愧”就有“耻”之含义。“耻”在《说文》中解释为“辱”[11]515。羞愧和羞辱在本意上可互通,二者都建立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上。但前者偏向内在的反省、持守,而后者转向外在的遭遇、评判。“羞愧”常与“惭愧”相连,“羞耻”常与“耻辱”相连:一惭愧、一耻辱,在意义转换间暗藏锋芒。
《礼记·檀弓》中也记录了一个在“羞愧”中饿死的人。
齐大饿,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13]298
嗟来之食的故事,直观看来是显现饿者的节操。相比伯夷、叔齐,《檀弓》中的饿死者更直白地表露了“自尊”二字。但曾子说,那是个不必饿死的人。他的死,可警醒人即便在行善之时亦不可失礼,却不应误导人轻易为自尊放弃生命。所谓“儒可杀而不可辱”在前提中必有区分。黔敖虽言语不敬,却非为大过,所以曾子认为“其谢也可食”。
“嗟来”的死者与伯夷、叔齐不可同日而语。那个人甚至没能留下姓名,而惟独抽象为一种教训。这种教训鲜血淋漓,仿佛从德性中伸出刀光剑影。倘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是出于德性的内在持守,那么“嗟来”之死却有着更强的外在受迫性。黔敖一呼“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这样的反应已非在“惭愧”之中;恐怕是“耻辱”感令一声“嗟”呼发挥出杀人以无形的威力。
七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为何是死于羞愧,而不是从善而生?所以这一命题必须倚靠“可能”二字。就是潜在的“可能”,以死之沉重焕发德之高贵;但也是“可能”二字,使德性徘徊于明暗光影。
(一)
明: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
暗:人是可能不死于羞愧的。
虞、芮二君相争,一入周界见周人互让便自觉羞愧,这当然是德性所焕发的力量。然而同样是感受德性的力量,崇侯虎却对有德之人施以恶行。一个知羞愧能反省的人大概是不需要暴力惩戒的,刑法示威反而会成为羞辱。假设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持守道德,那么刑法是否显得多余呢?或许可以假设,“法治”就是为不能羞愧者存有的——未能自律,必行他律。问题在于,对那些绝不可能“死于羞愧”的人,以暴制暴纵使“正义”,但德性是否能在“暴力”阴影中持守自身?如何使德性既不死于暴力(示弱),又不死于德性的丧失(示强)?
“中国”人的德性,其高明与困顿共存于“限度”之中。反省是惟一的出路,知其不可而为。
(二)
明: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
暗:羞愧可以致人于死
伯夷、叔齐之死乃为个案。但齐人的嗟来之死却可能走向群体。
死于羞愧或死于刑法,二者看似互为对立。然而道德一旦具有刑法般的威慑力,羞愧似已在恐惧中变异了。这可以解释,为何礼教立人最终走向礼教吃人。所以嗟来之死即便可作为“气节”之典范,曾子对此却并不赞扬。这一场“枉死”,警示贤者反思教化的分寸。吴氏澄曰:“曾子之言,得中之道。饿者之操,贤者之过也。”[13]298
不是所有道德都事关政治。“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此一命题当存照政治以外——它惟有立足德性自身,却不应成为统治手段,否则“耻辱”可能变异为凶刀。政治不是德性的规定,而是施展于德性的未及。伯夷、叔齐之死,决然有别于一种政治教人死于羞愧。这恰恰证明了,道德原本不是一种治术。
“中国”人有“中国”的“政治”取向。朱子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句:“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14]52纵观古今,未必所有的共同体都依德而治,“为政以德”也从来不是某种“普世”真理——然而“中国”一词,必须是与德性相匹配的。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12]42可见“政治”面向德性缺憾而用。谈及“政治”与“中国”,即便不能如圣贤般在缺憾中怀有羞愧,难道不应对德性阴影有所警觉?政治的定义倘若无度,那么“为政以德”几乎只流于修辞技巧,而“中国”之根本恐将面目全非。
八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史记·周本纪》)[3]131
箕子因进谏而被纣王囚禁,是武王进入商都后才将其以礼释放。纵然饱受故君之难又承蒙新君恩惠的人,箕子非但没有对“殷”控诉责骂,甚至不忍把既成事实的丑恶说出来。他了解“中国”的意义,也深知自己是“中国”的后人;即便生于失道亡国的时代,仍选择在“不忍”中持守其姓氏与血脉的尊严。连武王也因此羞愧。
武王的羞愧并不由于犯错。若论及对错,则武王更无需为伯夷、叔齐之死承担。“中国”人的德性,仿佛“对”有“不是”,“错”未必“非”——中道如此难求,但有羞愧令德性昭彰于“不得”。
[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
[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1.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杨士勋.春秋毂梁传注疏·庄公三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7.
[6]陈立.白虎通疏证: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4:43 -45.
[7]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8]王先谦.荀子集解·大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8:504.
[9]班固.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98.
[10]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4]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