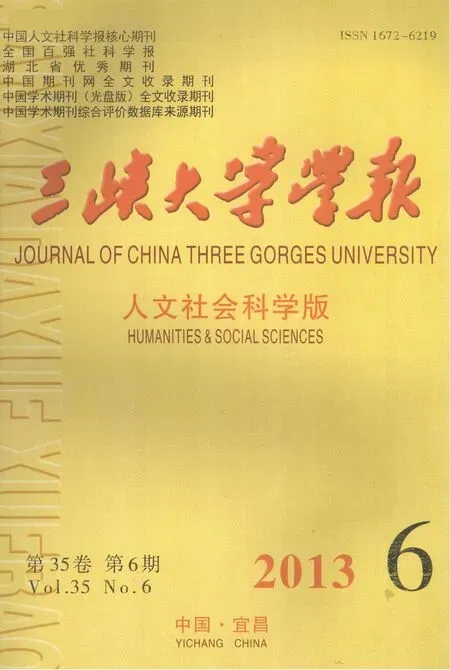异域抑或本土——从王国维的三种文艺论著看其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
邓新华,汪 鹏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以《红楼梦评论》为中心,中期以《人间词话》为代表,后期以《宋元戏曲考》为主干。分开来讲,早期的《红楼梦评论》从康德、叔本华美学入手,把《红楼梦》看作是“自律的解脱”;中期的《人间词话》虽然表面回归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模式,但围绕着“境界”而展开的理论体系则又极具康德、叔本华美学的思想内蕴;后期的《宋元戏曲史考》则从“史”的线索入手整理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直处于弱势的戏曲文学,似乎又彻底回归于本民族固有的学术轨道,然而这仍然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一次学术尝试。统观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三个阶段,我们发现: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思想一直激荡在异域和本土之间,从以西方文论为立场逐渐过渡到以本土文论为主体,西方哲学美学一直或显或隐地影响着王氏的文艺思想。
一、《红楼梦评论》——以西方哲学为本位的文学批评
王国维利用西方美学进行的第一次文学批评尝试当属《红楼梦评论》,该文发表于1904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过《汗德像赞》、《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绍介康、叔美学哲学的文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文章是他研究康、叔思想的产物。就文学批评而论,王氏对《红楼梦》的评论,康、叔概念的图解多于文学形象的分析。叶嘉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从哲学观点批评一部文学作品,其眼光乃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当批评时,乃是从作品本身寻找出它的哲学含义来,此一哲学含义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虽大可以有相合之处,然而却不可先认定了一家的哲学,而后把这一套哲学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学作品上去,而静安先生不幸就正犯了此一缺点。”[1]151但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王氏的尝试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意欲在形式上建立现代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另一方面他努力建立一种中西融合的诗学思想,即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不应该有国别和民族的界限,异域的文化及思想应该能够交流沟通。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表达,那就是王国维坚定地迈出了西方哲学美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成功。
《红楼梦评论》全文共分五章,这五章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印象式的点评,而是具有了西方式的谨严结构。第一章由叔本华哲学入手阐述“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王氏借助老庄哲学引出自己浸淫已久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2]1然而“欲”并不因为具体欲求对象的满足就可以让其主体得到解脱,“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2]1王氏指出人生本就摇摆在欲和厌倦之间。但人生的解脱之道又在于摆脱“我”和“物”的对立关系,进入纯粹知识,这就不得不求助于美术。王氏不但在认识论上继踵叔氏,而其所谓的解脱之道也步叔氏旧辙,即借助于美术让人摆脱意志的纠缠。美术中的优美、壮美和眩惑的区分使王氏很自然地排斥了《牡丹亭》、《七发》等作品,而将目光聚焦到了“一绝大著作”《红楼梦》上来。
由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起点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这种形而上的思辩体系而不是《红楼梦》作品本身,因此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牺牲了文学文本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开放性。《红楼梦评论》第二章里,王氏径直把《红楼梦》中“通灵宝玉”理解为叔本华所谓生活之“欲”。在叔本华那里,人存在的“欲”以男女之欲为最甚,它是形而上的存在,亦可以理解为意志本身的体现。在王国维看来,虽然从广义上讲人摆脱意志有“观他人之苦痛”和“觉自己之苦痛”两种,但普通人解脱是通过自己在历经各种生活苦痛之后的出世,宝玉的生活经历及出世正好契合了这种对意志的拒绝之路。在这里,王国维并没有紧紧围绕作品本身来解释宝玉悲剧命运的性格依据和社会成因,而是把小说主人公的归属按照叔本华提供的悲剧哲学的线性逻辑演绎出来,这无疑是对文学批评对象的一种背离,显然算不上对《红楼梦》的美学评价。此诚如叶嘉莹先生批评的:“《红楼梦》所写的出世解脱之情,其实并非哲理的彻悟,而不过只是一种感情的抒发而已。”[2]162不仅如此,王氏对《红楼梦》伦理学价值的评判,同样也是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立场出发,他不是将小说开始的“绛珠还泪”理解为一个浪漫的神话,而是将其比拟为基督教的原罪,进而得出结论:“则夫绝弃人伦如宝玉其人者,自道德言之,固无所辞其不忠不孝之罪;若开天眼而观之,则彼固可谓干父之惑者也。”[2]10在王氏看来,人一出生就附带着意志,也可以理解为“鼻祖之谬误”,出世在族类的意义上是还赎“鼻祖之罪”,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至孝”。宝玉能够“绝父子、弃人伦”,诉诸出世而非自杀,这非但不违背伦理,而且还具有极大之勇气。这种“无生主义”实则是人人渴慕的救济。王氏把宝玉所经历的苦痛看作直达最后解脱目的的产物,这固然符合叔氏的理论原旨,然而却放逐了导致宝玉苦痛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即便在《红楼梦评论》第五章里,王国维对红学界考证索隐的批判也不是完全出于对文学自律的维护,即文学形象总是源于生活中的某一具体的原型,即“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2]13,而是根据叔本华对于意志客观化的结果自然引申而来,即“美之理想存于经验之前”。
纵观整个《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都是依据某种先在的哲学概念来规整和图解小说文本,而不是从小说文本提供的文学形象和批评者的审美阅读体验出发。我们虽然可以从中看出王国维在中西化合方面的努力,但他这一时期钟情于西方哲学美学的基本立场使他的论述常常显得削足适履,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形象本身难以契合。这一时期除了《红楼梦评论》之外,王国维还有《屈子文学精神》、《文学小言》、《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等论著,内容虽然各异,但理论总体上却未超出从康、叔美学出发这一思维定式。比如《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虽然探究了“优美”、“宏壮”之后的“古雅”这第三种美学的可能性,但“古雅”的特征是以明显区别于康德美学中“天才论”而存在的,“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3]19“古雅”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后天学习而获得,是相对于前两种美学不可以通过人力修养取得而言的,这里明显有康、叔理论的影子。王氏的《屈子文学之精神》虽没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烙印,但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二元区分又陷入了对王氏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西方二元论的文学史观。总起来看,王氏第一阶段文艺思想是以决绝的姿态靠近西方哲学美学的,他的很多论点是概念和形而上的,他对文学的分析和评述也往往是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的简单照搬和图解。
二、《人间词话》——异域抑或本土的深度纠结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近代文论史上的重要论著,“境界”说是由该论著提出的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理论范畴,因此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从“境界”说入手来解说和阐发王国维的文论思想。如叶嘉莹先生就这样解说王氏的“境界”:“一个作者必须首先对其所写之对象能具有真切的体认和感受,又须具有将此种感受鲜明真切地予以表达之能力,然后才算是具备了可以成为一篇好作品的基本条件。”[1]182如果说叶氏对“境界”的解说仅仅着眼于王国维的论著本身,而佛雏先生则将王国维的“境界”和叔本华的美学联系起来:“审美静观以及再现于艺术中的境界的美,存在于‘特殊(个别)之物’中被认出的代表其‘全体’的‘理念’。”[4]177在佛雏看来,王国维的“境界”是受叔本华“理念——艺术的对象”说影响的产物,即当抒情主体克服了自身的褊狭而走向客观知识时,他的“自我”必定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全体族类的某种理念,这种在主体这里映射出来的以知识的抽象形式为本位的理念就是“境界”。佛雏用王国维所钟情的叔本华的理论来阐发《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这一核心诗学主张,无疑是深刻的,但这种解释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论对其“境界”说的影响又未免失之偏颇。我们认为,“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纠结在异域和本土之间的重要表征,它既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又包含有中国诗性文论传统的遗传基因。
我们先来看一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如何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继承中国传统批评的特点的。这首先表现在《人间词话》的言说方式是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而非完全西方概念推理式的。例如在批评词汇的选择上,王氏对词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基本沿用传统印象批评常用的“骨”、“神”、“气象”、“神理”、“深致”、“风气”、“生气”、“格调”、“高致”等概念和术语,如“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太白纯以气象胜”,“飞卿之词,深美闳约”,“少游词境,最为凄婉”等等。由于这些批评用语本身所具有的具象性、模糊性和多义性的特点,非常适合批评家用以表达自己对批评对象之独特的印象、感受和理解,所以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而王氏企图用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概念和用语来阐释他的“境界”说,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叔本华所说的单凭理智就能抵达“境界”的本旨并不可靠,对词之“境界”的把握还是只能像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所做的那样要依仗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感受和体验,这也许正是王氏在异域和本土之间颇感纠结的地方。其次,王氏的理论主张也是地地道道契合中国传统文论精神的。例如《人间词话》把创作上的“不隔”作为“境界”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他主张的“不隔”就是要求词人把目之所见自然而然不经人工锤炼地书写出来,比如“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两句,作者只要如实地加以表达,“语语都在目前”就可以了,这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崇尚自然真实的美学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特别是他的“境界”说,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人间词话》通行本是六十四则,各则虽然彼此言说不同的内容,但整部论著始终围绕“境界”这一核心范畴展开,如王氏提出的相辅相成的几对概念和术语:“造境和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洒落与悲壮”、“诗人之忧生和诗人之忧世”、“隔与不隔”等等,我们很容易从这一系列理论概念的背后看到一种相对稳定的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实,王氏对“境界”的这种二元论的解释有很多并不可靠,如第十七则关于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的论述:“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5]4王氏此处所言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南唐后主李煜,他本人尽管没有太多的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但也未必就算得上“阅世过浅”。在我们看来,李煜的词所以能够传达出他的真性情,不正是由于他亲历了国破家亡这样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故吗?这怎么能够说是“阅世过浅”呢?王氏对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的这种厘定无疑是他常年浸润于西方二元论哲学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驱使他即使在返回到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立场上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陷入到西方非此即彼的理论圈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有条件地接受佛雏先生的上述看法,即王国维的“境界”说的确受到叔本华“理念—艺术对象”说的影响。这样一来,王氏最核心的诗学主张“境界”说就不仅在思维方式上诉求西方哲学,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进一步说明,王国维貌似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人间词话》,从其深层表达来看,其实仍然在本土和异域之间徘徊。
三、《宋元戏曲考》——立足本土的文论尝试
1912年以后王国维逐渐从文学哲学研究转入了古史、古文字研究,这一转变固然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但与时代(辛亥革命及其失败)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大约是因为“可爱而不可信”的哲学和文学促使他去追求“可信”的史学,以期在乱世中找到些许的清净。王国维此期除了有大部头的《宋元戏曲考》问世外,还出版了《曲录》、《唐宋大曲考》、《优语录》、《戏曲考源》等戏曲方面的论著。至于王氏何以偏偏要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系统的考证式的研究,我们认为大约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考证作品的源流本就是古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甚至是史学家最引以为自豪的看家功夫。王氏坚信“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3]200王氏强调“凡诸材料”都是自己收集,这难以掩饰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古史研究者的自信;二是因为王国维的文学史观使然,即“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筊者。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沈晦且数百年,愚甚惑焉。”[3]200王国维认为文学史是渐进发展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没有必要重视唐诗宋词而忽视元曲,因为元曲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三是因为和西方蔚为壮观的戏剧文学相比,中国的戏曲发展显得相形见绌,因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民族戏曲学:“中国之文学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著,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3]30王氏面对中国戏曲文学尴尬地位的这种民族自卑心理反而从反面激发了他献身于中国戏曲考证和研究的雄心壮志。四是因为以元曲为代表的戏曲“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3]52中国传统戏曲真正引起王氏兴趣的恐怕还是他这里提到的“词采俊拔,出乎自然”,这是从《人间词话》“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继续而来的美学诉求。因为在王国维的心目中,中国文学境界之“真”和“自然”完全契合叔本华通过美术让欲求主体进入纯粹知识主体的思想蕴涵。
从以上分析可以见出,尽管王国维要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系统的考证式的研究与西方文学与哲学的介入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的介入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学术需要:与早期的《红楼梦评论》相比,其基本的学术立场已经有了彻底的改观;与中期的《人间词话》相比,其基本的学术态度也坚定了许多。
《宋元戏曲考》从上古五代之戏剧到宋代的滑稽戏,再到宋的乐曲和金的院本名目,最后到元杂剧,王氏完全按照“史”的线索展开。在重点突出的元杂剧部分,又从“渊源”、“时地”、“存亡”、“结构”、“文章”等几个方面逐层推进,结尾的南戏部分也注重考察时代和文章的关系。从王氏叙述的层次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他严格遵从历史的事实和传统考据学的章法。如“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夫人作享,家为巫史。”[3]200“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4]201对于宋代的滑稽戏则征诸丰富的材料,如大段引用刘攽《中山诗话》、范镇《东斋纪事》、张师正《倦游杂录》、朱彧《萍洲可谈》、陈师道《谈丛》等。而“宋之滑稽戏”一节,十分之九的部分都是材料征引。这样的考证文字还有“宋之小说杂戏”一节里对“舞队”目录的列举,“宋之乐曲”中对《乐府雅词》的征录,“宋官本杂剧段数”中对一百有三本大曲的征录等。在这里,王氏没有就某一作品本身进行哲理的思辨和诗学的归纳,而是让材料自己说话。即便有评价,也只是简略地分析所举戏目的本质特征,如“其中装作种种人物,或有故事。其所以异于戏剧者,则演剧有定所,此则巡回演之。”[3]217这种功夫基本上延续了清代考据学的余绪,已全然回归到本民族传统的学术轨道上来。
然而即便是考据文字,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见出静安先生的美学追求。“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3]253王氏在这里依旧坚守着自己的“意境”理论,并从写情、写景、述事三个维度入手,这和《人间词话》中的“意境”理论遥相呼应,如出一辙。对马致远的《任风子》,王评价道:“话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对《窦娥冤》第二折评道:“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对郑光祖《倩女离魂》评道:“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其实“言外无穷之意”是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论精髓,刘勰《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6]633就讲到了在场的情景和不在场的韵味问题。“令人忘其为曲”则是讲接受者进入了戏曲意境体验之中。从这个角度看,王氏这里所阐发的意境理论,一方面继承了本土文论的传统,但同时也没有完全摒弃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如他曾经指出:“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3]254为何王氏要独辟蹊径强迫式地要求来自俗语的“真”与“自然”呢,原因大约是因为俗语打开了一片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个领域的生动性、趣味性和鲜活性让审美主体进入某种“静观”,进而把自己的意志诉求驱逐出去,说到底其中还是有叔本华的影子在,由此可见王氏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哲学和美学影响。
纵观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三个阶段,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这样的一条线索:王氏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态度从以西方哲学为本位的概念图解到中西化合的深度纠结,最终还是选择了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这既是王氏个人所经历的治学道路,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范式,那就是异域抑或本土的激荡。这是西方哲学美学介入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论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王国维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和范式,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姚淦铭,王燕,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4]佛 雏.王国维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王国维.人间词话[M].黄 霖,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刘 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